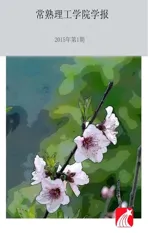翁同龢与洋务运动述论
——以同文馆风波为中心
2015-03-20沈潜
沈潜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翁同龢与洋务运动述论
——以同文馆风波为中心
沈潜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进入仕途之际,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在1867年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中,翁同龢并没有卷入论战的核心,但他站在守旧派一方,极尽密谋策划之心力,表现出了固守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翁同龢在同文馆风波中的言论举止,不仅有对西方列强持暴而来给中国造成的丧权辱国所宣泄的民族义愤,也隐含了在“华夷之辨”的传统等级秩序下表露出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
翁同龢;同文馆;洋务运动;守旧立场
翁同龢(1830-1904)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从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后步入政坛,先后身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历任国子祭酒及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并多次出任学政、考官、阅卷大臣,授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又先后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两授军机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举凡同光年间的内政外交重大朝政活动,无不参与其事。帝师之尊、宰相之位、枢臣之重,为有清一代所罕见。翁同龢进入仕途之际,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本文通过对翁氏日记的梳理解读,结合洋务派与守旧派围绕同文馆之天文算学馆的思想交锋,追寻翁同龢身处洋务思潮中的思想脉络及其根源。
一
1861年,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译署),成为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中枢机构,架起了沟通中西的一座桥梁。随后,朝中以奕、文祥等亲贵大臣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封疆大吏为代表,联手将事,共同推进了先后以“自强”、“求富”为目标、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也跨出了中国近代化艰难的第一步。
为适应外交和翻译人才的现实需要,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1866年12月,经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商议,奕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延聘西人教习,招取科甲正途出身的京外官员,包括进士、翰林院成员和有名望的编修投考入学,教授西方推算、格致、制器等科学技术。但这一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和文官体制的主张,很快触动了保守派势力的神经。
翁同龢自1865年起受命在弘德殿授读同治帝,当时日记记有流传于京城的各类嘲讽联语。1867年3月18日:“同文馆之役,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1]5483月29日:“京(语)[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551
守旧派意识到,华夏文化礼仪之邦正受夷狄威胁,西学正在侵染天朝臣子,必须申明“内夏外夷”的界限,随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清帝国权力最高层内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奏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2]28换言之,让科甲正途士人去学习此等“机巧”之事,且以仕途、银两赏赐来诱惑,这样重名利而轻气节的做法,必将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引向歧途。此论颇得弘德殿行走首席、大学士倭仁的倾心称赏。
倭仁(1804-1871),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侍讲、大理寺卿等职。同治初年起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调工部尚书,擢协办大学士,与李鸿藻、翁心存一起充同治帝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对宋代的程朱理学素有精深研究,倾倒了包括翁同龢、董文涣、游百川等当时一批新进的学士和门生,堪称咸同两朝著名的理学家,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3月20日,倭仁亲自出马,上奏竭力驳斥。在他看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①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以下所引有关奏折,未注出处者,均据此书。接着断言:“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就此引起的舆论争执,翁同龢保持了密切的关注,3月5日的日记记录:“是日御史张盛藻递封奏,言同文馆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员,奉旨毋庸议。”[1]547
在倭仁上奏当天的日记里,翁同龢写道:“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馆不宜设。巳初与倭、徐两公同召见于东暖阁,始询同文馆事,倭相对未能悉畅。”[1]548-549
鉴于倭仁在士林中的影响力,两宫召对谈话又未能达成共识,慈禧以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将奏折交由总理衙门评议。4月6日,奕随即上奏批驳,又附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奏稿信函。奏中痛心疾首地说:
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於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堕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臣等反覆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2]31-33
翁同龢在第二天的日记中笔录:
军机文、汪两公至懋勤殿传旨,将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事折交倭相阅看,并各督抚折奏及信函均交阅。复奏折语多姗笑,大略侈陈咸丰十年保全大局之切,并详陈不得已苦衷,而力诋学士大夫之好为空言,视国事漠然,并以忠信礼义为迂谈,而以正途人员为必能,习其算法而不为所用云云。督抚折信中惟李鸿章四次信函推许西士竟同圣贤,可叹可叹。[1]553
4月12日,倭仁复奏,不但坚持己见,又反唇相讥,认为“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心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4月23日,奕又复奏,针对倭仁前折所谓“不患无才”、“何必夷人”的空言论调,请旨饬令倭仁“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他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此招可谓击中要害。当天上谕允准发抄,倭仁无言以对。
翁氏4月24日记曰:
荫轩三日未入直,与艮峰相国至报房,并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称中国之人必有讲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某督饬办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等因,总理衙门所请也。朝堂水火,专以口舌相争,非细故也。访兰生,点定数语。[1]557
由此可见,翁同龢在此后数日里与李鸿藻等相互串联“商略文字”,斟酌奏折。25日,倭仁奏称自己“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撤回前奏。但奕并未就此罢休,还奏请太后准许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一个对洋务一窍不通的理学家去当总署大臣,无非要出其洋相。此举急得倭仁极显窘态,赶忙找来徐桐(荫轩)、翁同龢商议辞折。
随后几天的翁氏日记有如下记录:
4月25日:“甫出东华门,倭相邀余同至荫轩处,知今日递折,有旨一道,令随时采访精于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商辞折。出城,访兰生长谈。”4月26日:“还坐兵部朝房,与倭相议论,辞折未允也。”[1]557
4月27日:“出偕倭、徐坐报房商前事,酉初还家。”[1]558
4月28日:“汪泉生、史勖斋、王芷汀约同人法源寺素饭,良久始坐,即辞归。遇艮翁于途,因邀至家,谈许久,知今日仍不准,与邸语几至拂衣而起。有顷兰荪来邀,艮翁在座,商酌无善策。噫!去则去矣,何疑焉。”[1]558
4月29日:“是日倭相请面对,即日召见,恭邸带起,以语挤之,倭相无辞,遂受命而出。倭相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访兰生。”[1]558
4月30日:“艮老云占之得讼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决矣,相对黯然。”[1]558
尽管倭仁屡疏恳辞,力辞不准之下,4月29日只得含泪上任。三天后因“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为由请假,决意辞职。此间,翁同龢日记既记述了倭仁的无奈窘境,也记录了他随后频频趋候探望倭仁的行迹:
5月3日:“卯正三刻入内,饭后巳初二到。上到书斋,艮峰先生未到,读尚勤,惟精神不足耳,未初三刻退。闻艮峰先生是日站班后上马眩晕,遂归,未识何如也。……访阎梦岩、张少民两同年。两君真学人哉,张尤邃于程朱之学,于平湖尤有得,可敬可敬!”[1]559
5月4日:“问艮峰先生疾,先生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它人椅轿舁至家,疾势甚重也。访兰荪长谈。”
5月5日:“遣人问艮峰先生疾,稍愈矣。”[1]559
5月13日:“谒倭艮翁,未见,疾稍愈矣。”
5月15日:“倭中堂续假十日。”[1]561
5月21日:“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
6月6日:“入城至恭邸处,谒倭相国,贺各同乡。”[1]565
6月9日:“晚谒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1]566
6月13日:“倭相请开缺,旨赏假一月,安心调理。”[1]567
7月13日,倭仁再请开缺,慈禧“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翁同龢闻讯,不由得“为之额手”。[1]573
至此,持续半年之久的清廷高层正面冲突得以平息,但同文馆风波却并没有因此结束。守旧派士大夫内呼外应,共证同心,终使招考者惶惶不安,报考者寥寥无几,或一省中并无一人愿考,或一省中仅有一、二愿考。偶有其人,则为同乡同列所不齿。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洋务派旨在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人才计划因此严重受挫,几同夭折。
二
毋庸讳言,在这场同文馆增设算学馆的争论中,翁同龢尽管并没有卷入论战的核心,但与徐桐等同僚积极帮助倭仁修改奏稿,极尽密谋策划之心力,可见他站在守旧派一方,表现出了固守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
从翁氏日记之一二,看似并无明确的态度表白,也能窥其思想倾向。5月1日记曰:“章采南来长谈,言轮船、算法亦不可不学,而持论总以人心、廉耻、纪纲、法度为本,又言宁波人往往买轮船破家。盖无此资本,终为所绐耳。”[1]5585月12日的一则日记值得留意:
还汪慕杜《不得已》两卷。《不得已》两卷,国初歙人杨光先撰。光先世家子,让世职弗居,曾劾温体仁被廷杖,入本朝以布衣伏阙,争西洋算法,痛诋汤若望,著书斥天主教之妖妄。康熙初授钦天监监副,五疏辞,旋擢监正,后以置闰错误落职,中途为西人毒死。此书先有刊本,西人购而焚之,流传者鲜,此抄本后竹汀先生、黄荛圃有跋。[1]561
这里所说的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安徽歙县人,明末清初学者。清顺治年间,任用德国汤若望、比利时南怀仁等来华传教士改订历法,废明《大统历》,采用“西洋新法”制定《时宪历》。杨光先以《辟邪论》等文章加以驳斥,并屡次上书指控汤若望等以修历法为名图谋不轨,1665年(康熙四年),上疏在鳌拜的支持下得到审议,最终导致汤若望下狱,南怀仁等流放,史称“康熙历狱”。不懂历法的杨光先却因此升任钦天监监正之职,后来编纂《不得已》一书以自明心志,留下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传世之言。
事实表明,自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第一批传教士来华,拉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中西文化之争自此未曾停止过。无论是康熙朝的杨光先风波,还是同治朝的同文馆风波,均为实质性的中西会通早期发生的冲撞与交锋。此间日记表明,身为局内人的翁同龢借阅杨光先的《不得已》,体现了他疑惧、排拒外人与外来文化的心理。
曾有学者认为,翁同龢当时之所以支持附和倭仁,也有出于自身地位不高,资望还浅,因此在政治上还有依附于他人的思虑。[4]96实际上,翁同龢自入值弘德殿,第二年任翰林院侍讲,赏加四品衔,相当一段时期与倭仁相处共事,过从甚密,有如师生交谊。翁氏日记言必称倭仁为“先生”、“艮翁”、“艮老”。1866年7月17日记:“艮峰先生赠《孝弟图说》一本,《弟子规》两本。”[1]49910月19日记:“艮峰相国以日记二册见示。”[1]5171867年1月6日记:“看艮峰先生日记毕,竟有着落。”[1]5311月7日记:“读艮翁日录,先生刻苦自厉,字字从肝鬲中流出,异于空谈无实之学。”[1]5312月4日除夕:“回环一年事如醉如梦,大率理欲交乘,明昧杂出,如此为学,何时得成耶,书以自儆。”[1]5371869 年4月24日记:“艮老欲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又弹中官之无状者,风节可钦,余等不及。”[1]714
缘于咸丰、同治年间全国性的社会动荡,面临灭顶之灾的清政府迫切需要一大批读诗书、明义理、效忠于王朝的人才来挽救封建治统和道统的危机,因此迎来了程朱理学复兴的时期。[5]72-104翁同龢崇信理学,仁、义、礼、智的儒家道德伦理陶冶了他的思想情操,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本、道德修养之源、待人处事之基。翁同龢在这一时期敬重和取法理学名臣倭仁,每日反省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内涵着“内圣外王”的宗旨。日记里不乏“读《理学正宗》”[1]502、“读《续理学正宗》,稍有得”[1]502、“看《理学宗传》,顿觉身心有归宿”[1]1102的心得笔录,倭仁躬行践履儒家文化的道德操守,让翁同龢极表倾心向慕之情。1871年5月22日:“闻艮翁疾加甚,舌强痰涌,患处流水,奈何奈何!终日郁郁,人事之可忧者多矣。”[1]8796月8日倭仁病逝,翁同龢禁不住哀叹:“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1]884
由此,当倭仁在风波中披挂登场,翁同龢应声附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只可惜,纵然倭仁及其麾下追随者人品高洁,但其保守的思想投影表明,面对晚清社会所处内忧外患的现实挑战,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从自己所接受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出发,出于对儒家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无知,依旧固执地坚守着“夷夏之辨”的心理防线,沉醉在“天朝上国”的传统精神世界里。
追踪翁同龢身处同(治)光(绪)之际的立身行事,类似这样的墨守成规的守旧心态,还有不少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表证。
比如说对中国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使臣斌椿的看法。1866年(同治五年),在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建议下,总理衙门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人,前往欧洲各国游历考察。斌椿此行记事抒情,逐日记述了亲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十多国的见闻,后题作《乘槎笔记》刊行。翁氏1869年4月22日记:“斌椿者,总理衙门当差也,前数年尝乘海舶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主,称其官曰某公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耳。”[1]713可见,翁同龢对斌椿津津乐道于西方的言行颇为反感。后来参与总理衙门会见各国使节,也不难看他当时处理对外事务中的心迹。1876年(光绪二年)2月4日的翁氏日记里,记述了与外国使节见面的情景:“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沉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余等两旁坐,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一一通姓名,崇、成君主之。拱手而已。”[1]12171886年2月11日,翁同龢仍把前来参加总理衙门新年团拜的各国公使称为“一群鹅鸭杂遝而已”。[1]2033以上笔录字里行间流露了翁同龢不屑与洋人打交道、勉而为之的矜持心理。
三
结合翁同龢在上述同文馆风波中的言论举止的梳理,不仅有对持暴而来的西方列强给中国造成的丧权辱国所宣泄的民族义愤,也隐含着他在“华夷之辨”的传统等级秩序下表露出的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
滥觞于远古的夷夏观念一直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易》曰:“族类辩物”,《书·尧典》称:“蛮夷猾夏”,《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后经《春秋公羊传》加以引申和发挥,衍化成“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侯而外夷狄”的原则。这一基于文化内蕴而不仅限于种族地域来划分夷夏观念,意味着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强化了中国人对周边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优越感,助长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夷夏大防”观念。“用夏变夷”、“尊夏攘夷”,严格夷夏之别,经过千百年的脉绪流程,被纳入儒家“礼一仁”思想体系,成为全社会必须接受、信奉的准则,凝化为代代相沿的士大夫传统思维定势,支配着他们的价值评判尺度及其行为选择。正是这份民族文化的自尊与优越感,使翁同龢在面对近代西力东侵日显紧逼的情况下,在与洋人交往和对外事务交涉中,坚守“夷夏之防”,一时难以真正改变对西方的传统看法。
在翁同龢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日记笔下,经常以“夷人”、“夷兵”、“夷酋”等字样描述西方列强的军队与将领,凡英、法、美、俄等国的称谓前均加有“口”旁,一些洋人也多加“口”旁或“犭”旁。[1]104《北京条约》签定时,目睹“盘旋不绝”于京城的法军骑兵,翁同龢发出了“何物腥羶,污我城郭”的喟叹;[1]107至于西方宗教的渗入,更让他深感“仁义衰息,礼教寝微,而豺狼横于毂下矣,可胜叹耶!”[1]122“蛮夷”作为传统中国人对“匪我族类”的通称,包含了野蛮、不开化的意思。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文人士绅著作中,在道光、咸丰朝各封疆大吏的奏折里,“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的言论几乎随处皆是,所涉此等名称几乎大多加有虫、犬类的兽字部首标记。由此不难看出,支撑当时翁同龢的内在精神养料,无疑有着将西方人鄙视为禽兽的观念,流露着他对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的蔑视心态。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翁同龢,内心深处更有根深蒂固的圣学本位思想。尧舜周孔孟之道是亘古不变的大经大法,圣人之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真理。判断、评价事物的规范和尺度,无不从圣学本位的法则中衍生而出。面临外患频仍、内忧纷起的危局以及洋务“师夷”思潮的兴起,包括翁同龢在内身为恪守圣道的正统士大夫,在随之一系列的议事论战中显然有了充分的理由,强化传统道德秩序,挽救人心以固邦本,成为他们自觉的道义担当。
就此而言,纵然急剧变化的时势引起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震动,旧有价值观念、心理秩序、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随之产生不同程度的因时转变。但问题又远非如此简单。同、光之际守旧氛围的弥漫,依旧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语境。其实,守旧原本也是一种社会常态,未必一定就是贬义。但守旧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维系世道人心的必然选择,又必须与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革新相携并行。就近代中国的社会大环境而论,在遭遇中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冲突面前,因循守旧意味着落后和愚昧,与时更新是势所必然的时代要求。对于当时倡议与反对增设算学馆、筹办铁路建设的论战各方,如何化危机为契机、为转机,如何思考趋利避害、取长补短,才是他们应有的明智之举。可惜,在利弊兼存的新生事物面前,守旧派动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未免把不利因素绝对化并扩大化了,因此未免因噎废食,与时违逆。这也正是翁同龢在此期间呈现的真实思想状态。
不过,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体生命,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心理结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持续性的调整变动过程,并且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又难免表现出新旧交替的错杂与艰难。翁同龢生活的时代,正当鸦片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传统社会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型期。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扬州黄钧宰最先提出“变局”观念,指出当时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6]623-624稍后,郭嵩焘、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也随之提出“古今之变局”的观点,类似的看法在时人诗文中屡见不鲜。李鸿章在递呈朝廷的《筹议海防折》中,更明确表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著名命题,前所未有的变局观,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感应和舆论导向,成为越来越多的知觉在先者共同的认识。外患迫临的变局面前,如何应付?如何处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满怀忧患、迫切思考的时代新课题。翁同龢自不例外。在此揭示他本真的守旧心迹之同时,又决不意味着把他归属于深闭固拒、一成不变的顽固派行列。
迹象表明,本着儒家经世传统的使命感,更有伴随近代社会思潮的递相流转,以及与众多倡导和通晓洋务的官僚大吏如文祥、左宗棠、丁日昌等交相过从,翁同龢的思想并不始终恪守于传统士大夫守旧的立场上,而是交织了一个从固守传统向倾向革新转变的心路演化。本文限于篇幅,就此话题容另文加以论述。
[1]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M].翁以钧,校订.上海:中西书局,2012.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谢俊美.翁同龢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J].近代史研究,2003(6):72-104
[6]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On Weng Tonghe an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 Focus on Tongwenguan Crisis
SHEN Qian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China)
Whe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rose,the famous politici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eng Tonghe,started his political career.During the debating on setting up the Astronomy-Mathematics School in the Tongwenguan in the year of 1867,Weng Tonghe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core debating,but he was on the side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making his best efforts,displaying a tenacious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standpoint.Weng’s words and behavior not only harbored national indignation towards the western powers who brought violence and national betrayal and humiliation,but also implicitly showed the China-centrism complex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ranks differentiating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Weng Tonghe;Tongwenguan;Westernization Movement;conservative stance
G127
A
1008-2794(2015)01-0056-06
2014-11-20
沈潜(1965— ),男,江苏昆山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江南区域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