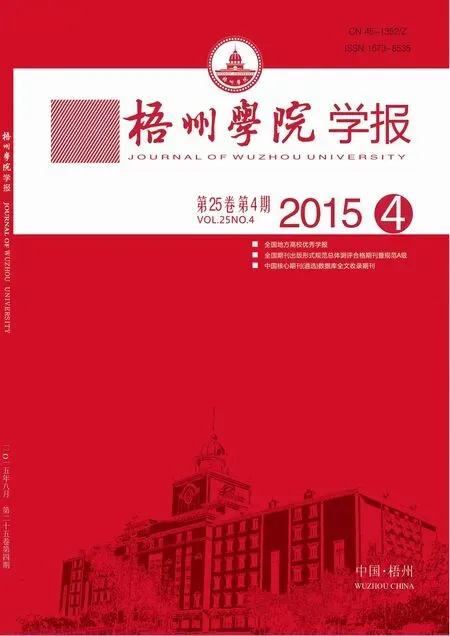张承志早期小说的男性叙事文本
——以《刻在心上的名字》为例
2015-03-20张芳
张芳
(辽东学院,辽宁丹东118000)
张承志早期小说的男性叙事文本
——以《刻在心上的名字》为例
张芳
(辽东学院,辽宁丹东118000)
《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张承志的创作中关注度不高的作品。小说的主要人物围绕父子、“养父子”两代三位男性展开,作品以“成长”与“自省”为叙事主题,以“苦难”与“救赎”为叙事视角,以“矛盾”与“抗争”为叙事内容,以冷峻与温情共存、叙事与思考共生的男性视角构建了一篇典型的男性叙事文本,具有思想与文化意蕴,丰厚了作家“为人民”的创作内涵。
张承志;早期小说,男性叙事
张承志早期小说的叙事空间有“一块大陆”被他称为“母亲的草原”,叙事时间横跨并延续着他的知青岁月,叙事母题直指异乡的成长与感恩,叙事视角常常是以“我”为代言,将生活中那个年代的“我”和小说中的“我”相照应,在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中时空交织,生发文学与文化意蕴。《刻在心上的名字》是张承志在1979年7月创作并于同年发表在《青海湖》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张承志所有的创作中,这个作品的关注度并不高,也鲜见文学评论。小说的主要人物围绕父子、“养父子”两代三位男性展开,以“成长”与“自省”为叙事主题,以“苦难”与“救赎”为叙事视角,以“矛盾”与“抗争”为叙事内容,构建了一篇典型的男性叙事文本。
一、“成长”与“自省”的叙事文本
关于“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在中国是舶来
品,西方文学的“成长”母题由来已久,古希腊、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界定。但是关于“成长”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义是研究者对这类作品的共识。芮渝萍认为,“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因此,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公从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进入知之状态的叙事。”[1]新时期以来,知青文学以特有的精神面貌呈现在文坛,这些以知青生活为素材的作品,有描写那段生活的苦难和艰辛,有对非常时期社会环境的描述,有缅怀青春岁月,有表达理想情怀。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成长”。有身体的成长,心理的成熟,还有精神的丰富。
作为其中的一员,知青生活是张承志早期小说记录的主要内容,在这段艰苦浪漫的生活中,作家作为一个都市青年逃离到乌珠穆沁草原,从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地道的牧民、一个真正的骑手和一个信念坚定的男人。在这里,有自然条件的艰苦,生存环境的恶劣,草原生活的不适,还有那个特定年代的政治风波。“我”在“成长”是张承志这段时间创作的主题。《刻在心上的名字》讲的就是主人公小刚流着红卫兵的热血投入到蒙古草原的广阔天地中,本想大有作为却在“错误”的斗争中看到自己入住蒙古家庭的哥哥丧命,在追求理想的路上用哥哥的血使自己的名字有了“为人民”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刻在心上的名字》就是小刚的“成长”叙事,这个心路历程在经历重大事件后得以认识自我和人生,在一系列的情感动态变化中让他的“成长”血肉丰满又蕴含深远。所以,作品中给我们展示的走向成熟不是表象的骨骼的强壮、生理的发育,而是心理的健全、道德的成长和精神的完善。
小说中小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个动态是伴随着他在草原“政治风波”的发生、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化而变化的,对红卫兵内涵的理解是他“成长”的线索,对这个内涵理解的深化成为他心理健全、道德成长和精神完善的内在因素。带着红卫兵的使命感和伟大的抱负到草原锻炼自己,感情炽热、爱憎分明是他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哥哥被怀疑为内人党,在监视、关押、审问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系列情感的变化,当哥哥用死祭奠了他的成长仪式,最终他也由于养父的引领完成了心理的自省、精神的成长与道德的救赎,也最终明白了红卫兵使命的真正内涵,那就是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成为真正的“阿拉丁夫”。
小刚的“自省”明确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对乌力记哥哥,小刚最初的情感是崇拜,因为他是草原上威风凛凛的摔跤冠军,小刚便央求要住到他的蒙古包里,一年多的共同生活让他品尝到草原异乡人的温暖和淳朴。乌力记刚被审查时,小刚坚信他的无辜,抱着很快过关的幻想,看到他的沉默使小刚与从前往事交织情感复杂,后来看见他牵挂马群主动提醒时的怀疑,想到自己生病时乌力记哥哥冒着逃跑罪名舍命相救的无地自容,他想到最后心里充满绝望自杀的悲愤。整个情感变化中小刚有着深深的愧疚与自省,后来他用在查干敖包山下打井来“偿还”和“救赎”。小刚的“自省”还体现在永红身上。当惨烈的斗争结束时,小刚看到永红轻松地与人谈笑风生时,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和对红卫兵精神的错误理解。“他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他比别人更不能宽恕自己”[2]35,就是在这种罕言寡语中审判自己的行为和灵魂。当桑吉阿爸用最简单的道理“为迷惘的骑手指点了前进的路径的时候”,小刚拥有了圣洁的名字,完成了“自省”和“救赎”。
二、“苦难”与“救赎”的叙事文本
苦难,是苦痛和灾难,同时还指遭受苦痛和灾难。这种对“苦难”内涵的界定不仅仅包括生理上的疾病、物质上的困境,还包括精神上的煎熬。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经历和过程。佛家的“八
苦之说”可谓集人生苦痛之大成,以此观照和感悟人生,人生就是一个苦痛的过程,人人都有苦难的历程。在西方,“苦难”是基督教一个重要主题,身处“苦难”经由信仰宗教而获得灵魂的“救赎”,由此信仰宗教便成为消解“苦难”的途径和方法。西方文学,乃至雕刻、建筑、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都对“苦难”与消解“苦难”这个无极限的命题,进行过多视角的阐释。同时,如何面对“苦难”,并在“苦难”中得以消解和超越也是中国文学经常探讨的主题。
关于张承志小说苦难意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对有关穆斯林作品的研究上。黄土高原的“西海固”成为作者抒写“苦难”的发生地,这个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人类不能生存之地”在张承志的笔下却成为一个文化象征。作家对这些贫瘠土地上存在哲合忍耶信仰的力量加以叙述,研究者也在作家的叙述中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意志力。实际上,“苦难”是张承志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也是张承志热爱抒写并涵盖了他成长经历的主题。在张承志的草原小说中,也有关于苦难意识的描写,与宗教信仰不同的是,成长中的苦难“我”时时在经历。
《刻在心上的名字》中具有苦难意识和豁达情怀的人的表象是桑吉阿爸,这个蒙古医生在老年失子的苦难中原谅了小刚,并在小刚的错误斗争中赋予红卫兵新的内涵。桑吉阿爸是个见过世面的蒙古老人,虽然沉默寡言但对小刚的心思了如指掌,在小刚高烧时没有绝情地离开放弃治愈一个生命,证明儿子被冤枉时老泪纵横而没有怨恨,当小刚痛苦地赎罪时,朴实老人的宽容和安慰充满真情,“风雪的春天总会有死去的羊羔子,可是羊群里的羊羔子还是越来越多……”[2]38这种朴实的豁达让小刚无地自容,也让他明白了简单的道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首先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做人民的儿子。
小说中真正在苦难中得以救赎的是小刚。小刚的背后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亲如兄弟的草原哥哥,一个是亲如父亲的草原阿爸。作家以男性视角描述了三个男人的情感与苦难,有关于人生成长的冷峻思考,有关于异乡亲情的温情描述,有面对问题的矛盾对抗,有人生苦痛的悲悯情怀……小刚的救赎就是通过这两个男人,以自我救赎和他者救赎两个途径完成的。自我救赎在小说里表象上是通过在查干敖包山下打井的具体事件去体现,实际上在整个事件的变化中的情感经历和内心煎熬都是自我救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我救赎的内在有机体。他者救赎是通过乌力记哥哥的自杀和桑吉阿爸的宽恕共同完成的。应该说,小说里“苦难”是成长的母体,是它的“温床”与“良药”,更是它清醒的催化剂。他者救赎是外在事件的推动与催促,自我救赎是内在的驱动力与基础。
一个知青带着激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这斗争让都市青年激情澎湃,也让热血青年失去了纯真和友情,甚至失去了朝夕共处的亲情,更悲凉的是,斗争中有亲如家人的兄弟的流血和牺牲。由于一场错误的斗争,让桑吉阿爸的儿子在屈辱中自杀,阿爸的豁达却让小刚理解到了灵魂的价值,他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这种世俗苦难的叙事让作家歌颂沉静、坚忍和勇敢的受难精神,也让他在经受苦难中看到了反讽和荒诞。如果乌力记哥哥果真是内人党,如果桑吉阿爸对他始终不原谅,小说的内涵就远没有现在的沉重与苍凉,这种讽刺和荒诞就失去了内在的张力。所以,张承志笔下的“苦难”表面上具有文本叙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实际上更具有文化叙事中悲剧里的讽刺喜剧的浓重色彩。这种在“苦难”中的超越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文本,也超越了文本,具有文化内蕴。
三、“矛盾”与“抗争”的叙事文本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叙事主题,不管是男性作家,如先锋小说作家余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莫言,还是女作家,如迟子建、毕淑敏等,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关于“死亡”的叙述,也有众多研究者分析他们笔下“死亡”的内
涵。“死亡意境”作为某一人物的戏剧化人生的最后一笔或某一生命形式的末端,一般是情绪高峰,常常是具有伦理力量的性格的最后表现,更能流露出死亡符号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艺术家的道德尺度也借助人物的死亡得以显现[3]。张承志的这篇小说也叙述“死亡”,这种生命仪式蕴含了作家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并且作家的道德与人性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小说中作为苦难的载体是白音塔拉大队民兵排长乌力记。他是桑吉阿爸的儿子,乌日娜嫂子的丈夫,小刚的哥哥。他因为在1965年保卫边防的民兵演习中表现积极而被误认为是内人党,在审查中因牧人的信念被践踏后绝望自尽。这是个悲剧性人物,在健硕的身体、沉默的性格、坚韧的信念和命运的抗争方面都表现出一系列的矛盾性,将草原的个人悲剧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这种死亡叙事对于塑造人物的决绝、窥探人性的苦难、加深灵魂的伤痛具有超现实的意义。其矛盾性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名字寓意与生命相违的人生矛盾。蒙古族很重视给孩子取名,《蒙古黄金史》中有成吉思汗对次子察合台最好饮宴的记载:“如果未出生,也为给你命名,如果没有出母腹,也未看见光明。在父母创造,母亲生产的日子恭敬地一起饮宴,这才是最好的宴会。”[4]所以按照传统蒙古孩子的名字是长辈取的,“乌力记”是长寿的意思,因为家境贫穷长辈盼他长命。而这个名字的家族企盼寓意与28岁生命戛然而止的命运实在是不相称,“人们并不一定能记住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的悲剧。”这似乎成了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这个矛盾本身就具有命运的讽刺意味。
二是沉默反抗与舍命相助的性格矛盾。小说中,乌力记的性格始终是矛盾的。沉默与开口的矛盾,逃跑与救命的矛盾是两个重要矛盾的生成点和爆发点。乌力记被审查后,在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辩解”遭来十几记耳光鲜血直流后便拒不讲话,但又自觉维护草原呼吸而主动叮嘱知青放马的注意事项。这种身份的转变没有停止他牧民的职业本能。另一方面,小刚高烧时,乌力记冒着“叛逃边境”的生命代价找来桑吉阿爸挽救小刚,这种身处逆境的冒死相救恰恰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和人性的善良,这是人性与命运的抗争,这个矛盾使人性站在了道德的高度。
三是身体勇武与精神无力抗争的命运矛盾。在小刚的眼里,乌力记是个宽肩膀的骑手,“像天神一样驰骋在马群中”,“在牧民的欢呼声里跳上摔跤场”,是个威风凛凛的冠军。这样一个勇武有力的年轻人面对误解在憨声憨气地分辨后满含泪水,拒不讲话。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关押,用腰带在屋里自尽。小刚压抑愤怒,乌日娜带着仇恨的目光粗暴地推开他,只有饱经沧桑的桑吉阿爸声音嘶哑,宽慰小刚。作家由衷地感叹:“这个时代的草原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能反抗命运,如果命运上盖着一个公章。”[2]30与其说乌力记精神上懦弱,倒不如说他为自己牧人坚守的信念勇武地殉葬,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矛盾,而是具有崇高意义的悲剧英雄。
诗人蒙田说过:“谁教会人死亡,谁教会人生活。”是的,草原在季节中轮回,羊羔在风雪的春天里越来越多,小刚在热血青春里寻找到了圣洁的名字。只是,在张承志的创作道路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坚持“为人民”的创作原则,用人民的生活丰满创作内涵。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和坚持的路上……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2]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
[3]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40.
[4]马哥孛罗.马哥孛罗游记[M].张星烺,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72.
On the Narrating Version by M ale Persons in Zhang Chengzhi’s Early Novels——Based on A Name Engraved in the Heart
Zhang Fang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Dandong 118000,China)
A Name Engraved in the Heart is one of Liao Chengzhi’s novels which draws less attention from people.The plot of the novel develops among threemale persons:the father,the son and the step-father.In this novel,the writer takes“growing-up”and“self-examining”as the narrative theme,sufferings and redemption a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conflict and struggle as the narrative content.Besides,hemixes coldness with tenderness and combines narration with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ale person.Thus,he creates a typical narrating version bymale persons,which contains the expression of both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enriches the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connotation of“writing for the people”.
Zhang Chengzhi;Early novels;Narration bymale persons
I206.7
A
1673-8535(2015)04-0056-04
张芳(1971-),女,满族,辽宁省丹东市人,辽东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孔文静)
2015-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