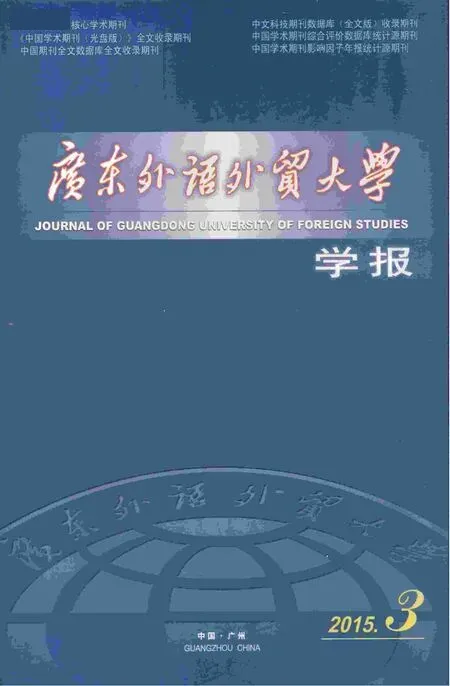弱者的自我救赎——庄子幸福学说及其现代阐释
2015-03-20王焱
王 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
人之需要幸福,犹如饥饿者之需要面包。越是不幸的人,对幸福的渴求就越为强烈。在庄子所处的时代,统治者的暴虐、社会的动荡以及欲望的泛滥,更使得幸福成为社会的稀缺品。其实,庄子并非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只关注自我逍遥,了无挂碍,否则他大可不必将这《庄子》一书留于后人。庄子之所以要立下文字,就是为了以其深邃的智慧教导世人,尤其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该如何在苦难中自我救赎、谋求幸福。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几乎是唯一不对帝王将相说话,而对那些芸芸弱者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着那些“治人”的诸侯喋喋不休地说着该如何拿到一副好牌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冷眼心热地告诉那些“治于人”的弱者该如何打好一副烂牌。时至今日,庄子仍被视为大众消解苦难、自我疗救的重要精神武器。刘笑敢 (2008:12-22)曾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美国的华人常说,中国人不需要找心理医生,因为中国人有老庄。”本文将立足现代语境,以庄子获得幸福的三种方法为例,对其幸福学说的启示与局限加以评说,希望能有助于人们提高判断幸福、感知幸福与创造幸福的能力。
一、唯道集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幸福是欲望的满足程度。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幸福可被视为所获之物与所求之物间的比例关系。从这个方程式来看,提高幸福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生命加法,即提高分子,增加所获之物;另一种是生命减法,即降低分母,减少欲望。世人多以生命加法作为获得幸福的武器,而庄子则选择了生命减法作为得道的法门,所谓“唯道集虚”(郭庆藩,2004:147)。
生命加法虽是人们实现幸福的主流方法,但仍有其局限。首先,一个人要获得所求之物,并非由己掌控,而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外在因素。其次,即使一个人幸运地实现了既定欲求,但由于欲望是无限膨胀的,而且总是先行于现实 (人常言“梦想成真”、“万事如意”,可见欲望总是走在现实之前),因此生命加法并不必然提高幸福感。布里克曼和坎贝尔曾揭示了一种名为“幸福水车”(treadmill effect)的普遍现象,即人们的经济水平虽然提高了 (这意味着人们实现欲望的能力增强了),但随之人们的欲望很快就会适应这个新水平,因而主观幸福感并无改善(Kahneman,2006:1908-1910)。这就如同在跑步机上折腾了半天,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幸福水车”现象的存在,表明幸福无法仅仅依靠生命加法而获得。
当今君临天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典型的生命加法。消费主义首先不断刺激世人的欲望;然后鼓吹世人通过不断体面的消费,以满足欲望;进而把消费更多、更昂贵商品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消费主义中,人们消费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显示身份、品位的符号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了凡勃伦效应: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非常典型地揭示了人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2010年,北京部分超市陆续收到五粮液厂家的新一轮提价通知,15种规格的产品每瓶提价高达50到70元,而涨价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为满足消费者身份需求。
不难发现,消费主义所要满足的,不是实际“需要”,而是“欲望”。“需要”对于每个生命体而言,是客观的、自然的、有限度的。而“欲望”则是一种被诱导、被塑造出来的主观感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称为虚假的需求,而且,欲望是无限度的。消费主义给世人以虚妄廉价的承诺,消费就能带来更多的幸福,因为消费即意味着有能力满足欲望,然而,即便是那些多金的富人,也并未得到消费主义所承诺的幸福,因为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欲望会无限膨胀,正如一句广告语所宣示的那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由于攀比心理的存在,消费往往演变成为一场“军备竞赛”。消费主义通过种种社会制度及媒介舆论,使人成为欲望的俘虏,使人在对金钱的无尽追逐中,忽略倾听生命的内在需求。心力交瘁而又难以自拔,这一切都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最大悲剧。
异于生命加法,庄子认为,幸福真正的奥秘在于减法。《人间世》篇中言:“唯道集虚”,意谓唯“虚”方能悟道。“虚”是一种通向道的内心功法,它通过排除世俗的名利关注、感官关注、道德关注、知性关注等,获得道的关注(王焱,2009:13-17)。这样看来,“虚”可被视为一种通过减少欲望以提升幸福感的修炼工夫。庄书《人间世》篇的“心斋”、《齐物论》篇的“吾丧我”、《大宗师》篇的“坐忘”与“外天下”、《知北游》篇的“日损”、《让王》篇的“忘心”等,其实都是这样一种“虚”的生命减法。
《大宗师》篇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郭庆藩,2004:228),《天地》篇亦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郭庆藩,2004:453)依庄子所见,欲望的膨胀会对生命造成戕害,离道渐行渐远。故而庄子劝说世人应忘却对欲望的关切,做到少私寡欲、无功无名。而当欲望对本真心灵的蒙蔽被驱散之后,我们便会步入道境之中,与天地精神同在,感受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间世》)的至乐体验。
庄子“唯道集虚”的生命减法,对于现代人超越欲望之困具有深远意义。烦忙焦虑的现代生活中,“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庄子“不物于物”、复初归真的思想,就越能显现其价值。沉溺于欲望之劫的西方社会近年极重视道家学说,原因正在于此。现代人面临着名利情欲等各方面的诱惑与重压,普遍感到身心疲累,的确应该向庄子“唯道集虚”的生命减法汲取心灵营养,懂得淡然、知止与退让,为更高境界的生命追求预留心灵空间。
然而,与生命加法一样,庄子“唯道集虚”的生命减法亦有其阿喀琉斯之踵。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揭示了幸福的秘密,幸福乃是一种欲望与现实相结合的价值判断,是客观与主观、生命加法与生命减法双重维度的统一。如要获得幸福,双重维度不可或缺。缺少客观努力与生命加法,幸福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如镜花水月般空幻飘渺;而缺少主观修炼与生命减法,再多的享受,都难以被阴暗贪婪的内心体验为幸福。由于庄子说话的对象,主要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人。弱者在外在行为上的无力感,使得自己更容易向内转,寄希望于一种生命减法的内心工夫,以获取幸福。故而庄子“唯道集虚”幸福学说的局限就在于,一味强调从主观维度用减法遏止欲望,却没有着力于从客观维度用加法去实现欲望。人不可能总是沉浸在道的体认中,因此,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庄子式的幸福难免会显出鸵鸟式的无奈,甚至是精神胜利式的自欺。不仅如此,庄子对欲望的片面压抑,还会严重稀释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进而导致物质文明的严重倒退。总之,缺乏坚实现实土壤的幸福楼台,就如同狂风中的枯叶一样飘摇。
二、自适其适
庄子主张应“自适其适”,而不应“适人之适”,即应听从生命深处对幸福的本真呼唤,不要以自我的痛苦为代价,通过迎合他人对幸福的理解,去实现自我幸福。用时下的流行话语来说,就是要活在自己的心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自适其适”出自《大宗师》篇:“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郭庆藩,2004:232)狐不偕等都是古代传说中的贤人,他们有的因为坚守节操而饿死,有的因为忠谏而被杀害。庄子认为这些人都是矫情伪行以邀名,乃“适人之适”,而只有那些善于发现并勇于追求真我需要的“自适其适”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
“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的差别,在《马蹄》篇伯乐治马的寓言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郭庆藩,2004:330)
在伯乐调教之下成为千里马,是许多人的梦想;而庄子认为,成为千里马并不符合马的真性,并非“自适”,而是“适人”。我们可以把伯乐,视作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把未经伯乐调教过的马,视作依从自我真实意愿生活的人;把经伯乐调教过的千里马,视作按照世俗标准塑造自我的人。从马前后生存状态的比较中不难发现:依从本性的马,能获得本真的快乐;而经过伯乐调教过的马,以自由甚至是生命的丧失为代价,幸福感远不足以弥补失落感。在庄子看来,与“适人之适”相比,“自适其适”才是一种真正的适意。
“适人之适”在当今表现为一种成功学的意识形态。依照成功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没有成为拥有豪宅名车、年收入上百万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他不行,犯了“不成功罪”。成功学意识形态以统一的功利标准来定义成功,以成功与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幸福,并通过种种社会舆论,剥夺那些非成功人士的幸福感。无论是铺天盖地的类似于某品牌汽车的广告“一个幸福的家庭,至少有两辆车,一辆用来改善生活,一辆用来改变生活”,还是泛滥于职场的成功速成培训班,都在宣示这样一种庸俗的幸福观:有钱就是成功,就是幸福;没钱就是不成功,不幸福。形形色色的媒体总在不遗余力地营造一种幻象:富人、名人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与幸福如影随形,而芸芸大众平庸细琐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成功学话语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资本之手在操纵。借用庄子的说法,成功是“适人之适”,而幸福则“自适其适”。成功与幸福并没有必然关联:强行将成功与幸福划上等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压迫。
《齐物论》篇中的一段话,能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为幸福强行制定标准何其荒诞:
正如不存在统一的居住、美食、美色的标准,世界上亦不存在一个人为规定的幸福标准。幸福有不同的模式,每个人都有其对幸福的独特体认,这种体认不应以他人为尺度。罗素曾言:“如果你自己觉得幸福,你才幸福。”禅宗亦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个人是否幸福,只有自己才是判断的最后因。如果自己觉得痛苦,即使拥有再多他人艳羡的目光,也无法把自己送入幸福的殿堂。
庄子对“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的区分,蕴含着深邃的生命智慧。尤其当“适人之适”成为这个时代压迫个体的强大意识形态,当世俗的成功成为定义幸福的“魔鬼之床”时,我们确实应该回归自我,叩问内心: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生活。
但庄子的不足在于,夸大了“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之间的鸿沟,夸大了世俗与自我之间的分裂与对立。我们知道,庄子救赎的对象,主要是弱者,而世俗的价值标准主要是由强者制定的,这一套标准本身也是有利于强者自我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弱者对世俗的价值标准的迎合,往往非常被动与艰难。这使得弱者往往容易放弃对“适人”的追求、对世俗的取悦,转而追求一己内心的满足。而积极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能够在他人与自我之间取得平衡的人,普遍比那些执于一端的人幸福,换言之,偏执于“自适”或者“适人”的人,很难获得持久而稳定的幸福。过分“适人”的人,常因生命的真实意志无法得以肯定与彰显,感到压抑与疲惫;而过分“自适”的人,则常因无法与他人达成共识,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自我的疏离。只有在“自适”与“适人”之间取得平衡的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到游刃有余,实现身心的全方位安顿。庄子后来在《外物》篇中提出了“顺人而不失己”(郭庆藩,2004:93),即一种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的处世态度,可视为对“自适其适”的扬弃与完善。
三、安之若命
生活当中总是存在种种无可奈何的困苦,成为实现幸福的障碍,该如何超越这些困境?庄子“安之若命”(郭庆藩,2004:155)的达观值得借鉴。“安之若命”出自庄子《人间世》篇,“命”即一种无力改变的必然性,安命意味着对已然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接纳,对无可奈何的一种安顺。
人生中最大的无可奈何,莫过于死亡或不治之症。在超越死亡之困方面,庄子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庄书中的死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终其天年”,即无可避免的自然死亡,如庄妻之死(《至乐》);另一类是“中道夭”,即可避免的非正常死亡,如北人无择之“自投清泠之渊”(《让王》)(王焱,2011:137-140)。对于后者,庄子是断然反对的,因为他们主动选择生命的提前终止。而对于前者,庄子则是安顺的。
庄子劝导世人豁达面对生命的自然终结,做到“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在庄子看来,死亡是气运造化的一个必然环节,《大宗师》篇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郭庆藩,2004:241)有生就有死,这是一种必然,就好比有白天就有黑夜。而且,生命的自然限度,属于命运掌控的范围,所谓“死生……命之行也”(《德充符》),因此,个人无法对生命的大限加以延长。庄子认为,既然生命的限度与亡逝,是一种人所无力改变的必然,那么,为注定的死亡而痛苦也就毫无意义。更何况,死亡并不意味着彻底的消失,而是新生命的启程。《知北游》篇言:“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 (郭庆藩,2004:744)。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死亡是一种未知的虚无,因而非常恐惧。但对于庄子这样一个具有宇宙情怀的大哲学家而言,个体的死亡,就好比宇宙这个大生命体在进行新陈代谢,意味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正如龚自珍诗中所写:“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至乐》篇中,庄子参透生死,对于妻子的去世,他非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庄子认为,面对生命的衰亡,悲痛恐慌无济于事,不如顺应大道的生命节奏,安然面对生死流转,在生命的舞台上优雅谢幕。苹果公司前执行官乔布斯对死亡的理解,与庄子存在本质上的契合:“死亡很可能是唯一的、最好的生命创造。它是生命的促变者。它送走老一代,给新一代开出道路。”这种安顺应对死亡的生命智慧,能够给予那些在生命终点线上挣扎的人以临终关怀,同时亦能为死者的亲友提供精神抚慰。
庄子不仅能安顺达观地面对生死,亦能安顺达观地面对时代的困境。《秋水》篇中有一则寓言: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 “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郭庆藩,2004:595)在匡地面临围困之际,孔子一改往日“累累若丧家之狗”之窘态,欣然弹唱,就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遇到昏庸的统治者,遇上这样的乱世,这是他的命运,无力改变,还不如坦然接受。庄子意欲通过这则寓言说明,一个人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时代,正如他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家庭,如果不幸遇上了一个坏时代,这是他的命,与其螳臂当车,做无谓的抗争,还不如安顺,做到“保身”,“尽年”,“养亲”,“事君”(《养生主》),保护好自己,颐养天年,对亲人、对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虽然我们今天的生活无法与庄子所处的乱世同日而语,但困境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庄子“安之若命”的启示在于:如果尚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不妨先去适应这个社会。这样能够避免无谓的抱怨,并为进一步的积极改变奠定平和的心态。斯宾诺莎曾言: “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们受苦。”(斯宾诺莎,2005:192)诚如其言,安命背后的安顺达观,是一种坚忍沉毅的生存理念,能够帮助人们释放痛苦。
当然,庄子的安命亦有其负面性。首先,庄子把困境的根源全部推诿于命运,简化了对困境根源的思考。以时代的困境为例,庄子过于浓重的命运感,无助于发现并消除那些严重破坏社会公平的恶的力量与社会制度,而这才是苦难的祸首,正如王中江所指出的:庄子对命运的妥协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了中国传统向现代政治自由之路的迈进,是不容易作出具体测算的,但很难否认它对此会有所影响。”(崔大华,等,2003:629)况且,对于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持一种顺应的态度非常明智,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如果我们不去积极治疗,怎会知道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如果不是孔子当时积极地奔走于各国之间,庄子怎会知道仁政在当时彻底行不通,统治者无可救药?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地改变一个困境,怎么知道这个困境改变不了。庄子说“安之若命”,就是把遇到的困境,当作一种不可改变的必然。至于这个困境是否真的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庄子并不去理会和追究。
庄子的安命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弱者的思维。弱者由于自身力量的微渺,往往无力对现实生活进行改变,因此只好无奈地让命运承担其所有不幸的缘由,而不去追问困境的现实根源,同时说服自己臣服于强大困境,不要试图反抗与挣扎,在弱者看来,反抗与挣扎往往只是一种“以卵击石”、“螳臂当车”的徒劳。这样的做法意味着主动权的拱手相让,弱者只能在困境的折磨中日趋弱小,从而成为“命运”宰杀的羔羊。从这个意义上说,“尽人事,安天命”比“安之若命”更胜一筹。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有胸怀接受不可改变的事物,方为一种更为明智的人生态度。
四、结语
南怀瑾曾把庄子比作“药店”(南怀瑾,2002:6)。诚如其言,庄子的以上幸福学说中的确蕴含着疗救人生苦难的药剂,从古至今安顿了大量破碎的心灵,对救治时代病症亦有深刻启示。然而,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庄子幸福学说亦有先天不足,更倾向于弱者的自我补偿和情感层面的审美救赎,仅停留于个体生命苦难的抚慰,无法根除社会现实的灾难,既无法提供政治救赎的制度保障,也无法建立道德救赎的公共理性。所谓“是药三分毒”,智者不可不察也。
崔大华,等.2003.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郭庆藩.2004.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刘笑敢.2008.庄子之苦乐观及其现代启示[J].社会科学(7):12-22.
南怀瑾.2002.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斯宾诺莎.2005.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焱.2009.论庄子“虚”的工夫[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17.
王焱.2011.论庄子的贵生[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37-140.
Kahneman D,Krueger A B,Schkade D.2006.Would You Be Happier If You Were Richer?A Focusing Illusion[J].Science,312(30):1908-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