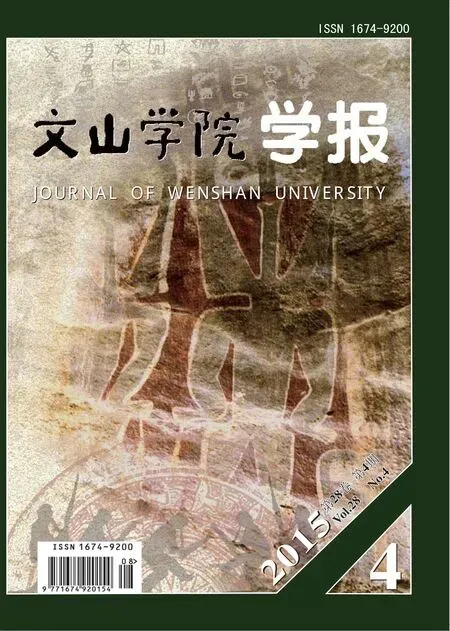南明与缅甸关系中的几个问题(1649~1662年)
2015-03-20李金苹娄自昌
李金苹,娄自昌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南明与缅甸关系中的几个问题(1649~1662年)
李金苹,娄自昌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摘要:通过对缅甸《琉璃宫史》与中国相关史料的比较分析,可看出1649到1662年南明与缅甸东吁王朝的关系充满了困扰。1649~1650年,因南明在中缅边境的土司地区征税,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各有胜败。1659~1662年初,因抗清失败,永历君臣入缅避难,双方互视对方为臣属,虽近在咫尺,永历与两任缅王却从未见面。永历政权在缅近三年,由于缅方长期软禁永历君臣,而李定国、白文选残兵多次寻驾救驾给缅甸造成严重破坏,双方怨恨日积月累,成为导致咒水之难的深刻原因。咒水之难使永历政权一蹶不振,1662年初,随着永历帝被引渡给清朝云南当局、白文选降清、李定国病逝,充满困扰的南明与缅甸关系终于结束。
关键词:南明;缅甸东吁王朝;琉璃宫史;宗藩关系;咒水之难
1644年,明朝灭亡,明朝宗室在南方军政官员和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张献忠大西军余部的支持下,在南方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史称“南明”。在南明各政权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为永历政权,与缅甸关系最特殊的也是永历政权。在永历政权与缅甸的关系中,有几个问题缅方记载与中方记载差异较大,争议也较大。如永历政权是否于1649~1650年间在缅甸东部城镇征税?永历政权流亡缅甸后双方是何关系,宗主与藩属还是其他?咒水之难是有预谋的屠杀还是突发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与澄清的问题。
一、1649~1650年南明是否在缅甸东部征税
据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载,缅历1011年(公元1649年),“有人奏报:中国永历帝在缅甸境内孟苏、西昆、登尼、盖马、景栋、景永等地征税”。听闻此奏报, 缅王便派大批人马向那些城镇进发以驱逐南明官兵,“缅历1011年10月10日(公元1649年12月2日)日曜日,摩诃乌巴亚扎之子明耶底哈律、亚扎丁卡各领一支人马,两支大军向登尼进发。11月15日(公元1650年1月6日)日曜日午后1时,御弟阿敏亲王明耶觉康、彬尼亚江道各领一支人马向孟卯进军,当日在界扎营,……11月24日(公元1650年1月15日)日曜日,二鼓过后1时,又派遂亚丁延军向孟卯进发。到达后中国人不敢抵抗而后撤。将此情况上奏后,缅王令孟卯、西昆收复后班师,新年到来之际回至京都。”[1]985- 986
半年之后,缅历1012年“ 7月17日(公元1650年9月20日)土曜日,御弟西博达亚侯德钦内谬耶觉、御弟德钦内谬搭达、劫抵丁因侯之子明耶亚那各领兵一支,三支象马大军向景永进军迎战中国人。8月17日(公元1650年10月19日)日曜日,岱达王、明南达梅各领兵一支,也向景永进发。进军途中在孟林与中国军队遭遇,发生战斗,因地形不利,缅军后撤。缅王见情况不妙,遂召回进军景永的御弟们。回师途中御弟西博达亚侯德钦内谬耶觉去世,缅军因疾疫损失三分之一人马”[1]988- 989。
英国学者哈威在其《缅甸史》中曾提到:“中国当明代衰微,其宗室后裔永历以众寡悬殊,被迫入滇,作殊死战,得以勉居数载,惟以贫乏无依,向兴威与其他边地诸土司曼莫等征敛。曼莫以负荷过重,突向缅甸投诚。缅王乃遣兵获质,阻其南渐。” [2]344- 345
关于永历政权是否在缅境征税,笔者未查到国内相关史料,学术界的研究也不多。余定邦先生认为,“这样的记载与事实不符。试想,永历在1659年初才入缅,在此10年之前,永历怎么可能在缅境内征税?”[3]290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须从缅方记载的可靠性、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首先,缅方是事件当事人,其记载中涉及具体的征税地点(孟苏、西昆、登尼、盖马、景栋、景永)、时间,缅方派出处置此事的多路兵马及每路兵马领兵将领的名字、处置结果(登尼、孟卯一线缅军获胜,孟林、景永一线缅军失败撤退),记载非常具体,可信度很高。
其次,《琉璃宫史》中提到的征税地点,在缅甸东吁王朝崛起之前,大多属于明朝云南当局管辖下的“三宣六慰”傣族土司地区。登尼,又称兴威,事实上就是以前明朝设置的木邦宣慰司所在地。孟卯就是现在的云南瑞丽,就是此前明朝的麓川宣慰司所在地。“西昆”,笔者暂不知现在何地,但离孟卯(瑞丽)一定不远,因为缅军出兵孟卯和西昆迫使南明征税官兵撤退、缅军班师回阿瓦,前后仅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反映出西昆就在孟卯附近。景栋,就是现在缅甸南掸邦的中心,也曾经在明朝的管辖下。景永,笔者暂未查到在何处,从记载推断可能是今天的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琉璃宫史》提到向景永进军的缅军在孟林被南明军队击退,孟林就是现在的云南孟连。盖马,就是现在云南的耿马。哈威《缅甸史》中提到的曼莫,就是八莫。总之,缅甸《琉璃宫史》中所提到的南明征税地点,大多集中在现在的缅甸掸邦和邻近的云南边境地区,而这些地区在16世纪中叶缅甸东吁王朝崛起之前,都是明朝云南当局管辖下的土司地区,直到缅甸东吁王朝崛起,这些地区的部分傣族土司才转而臣属于缅甸东吁王朝,但仍与中国明朝云南当局保持着特殊关系。由于明朝与缅甸东吁王朝并未正式划分边界,虽然上述地区的土司有的已经臣属于缅甸,但从明朝的角度来看,仍然属于云南的土司地区,因此,南明政权派官兵到这些地区征税是很正常的。
第三,从云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派人到上述地区征税的可能性非常大。在1649年之前的几年中,云南政局曾经非常动荡。先是1645年底1646年初,滇东南土司沙定洲在昆明造反,云南最高军政官员沐天波逃奔永昌,沙定洲控制了滇中和滇东南地区,与仍然效忠于南明的滇中、滇南土司争战。然后是1647、1648年,已控制贵州的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兵攻入云南,打垮了沙定洲,控制了云南。孙可望、李定国决定以云南、贵州归属南明永历政权,共同抗清,并派人到永昌请回沐天波,恢复了云南的稳定。随后,孙可望、李定国、沐天波与云南各土司团结起来,练兵征饷,为北伐抗清做准备。南明云南当局是否派人到前述中缅边境的傣族土司地区征税?从当时情况看可能性是较大的,因为1649~1650年正是云南恢复稳定、南明云南当局开始大力练兵征饷的时候,派人到以前管辖过的土司地区征税甚至征兵,以此积蓄力量与清朝一决雌雄,是非常合理而又正常的事情。不过,由于这些地区的土司有的已经臣属于缅甸,如《琉璃宫史》所言,南明云南当局的征税遇到了缅甸东吁王朝的抵制。
总之,1649~1650年南明云南当局在“缅甸东部城镇”征税的事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从南明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属于南明的土司地区而非“缅甸东部城镇”。
二、南明与缅甸东吁王朝是否存在宗藩关系
(一)南明自视为缅甸的宗主
从中国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南明政权一直将缅甸当作藩属国来看待,即使永历政权流亡到缅甸的时候,仍自视为天朝上邦而将缅甸当作藩属国。如根据永历从臣邓凯讲述而记载下来的《狩缅纪事》中谈到,1649年初永历帝及其随从入缅之前,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囊本河,“距缅关十里,黔国公先入晓谕,缅人见天波皆下马罗拜”。“二十九日到达蛮莫,其土官思线来迎。至五里,上入木城,慰劳思线,厚赐以金牌缎帛。”“(二月)二十四日,缅王请二大臣过舟讲话,上乃命中府都督马雄飞,御史邬昌琦入缅宣谕南幸之意。”[4]382- 3831661年七月的咒水之难发生后,“缅仍修旧地,请上安住,贡米、铜等物。二十五日,又贡铺盖、银、布等物,遣人奏上云:‘缅王实无此意,盖以晋、巩两藩王杀害地方,缅民恨入骨髓,因而报仇尔’。”[4]391另一史料《求野录》也记载到,永历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缅酋使使迎之,……进表天朝,则称缅甸宣慰使臣某。……帝至蛮莫,缅人执礼甚恭,并进衣衾、食物。……五月初八日,缅人来贡,礼仪甚腆。……九月,缅人进谷。”[5]357- 358根据邓凯讲述而留下的另一部史料《也是录》记载说,“永历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抵蛮莫,缅人迎贡亦颇循礼。……五月初九日,缅酋遣贡甚厚,上亦优答之”。[6]364- 366
从中方史料的这些记载来看,永历君臣虽然避难入缅,但一直自视为缅甸的宗主国,将缅甸当作藩属看待。如沐天波、马雄飞等本是请求缅甸允许永历君臣入缅避难,却使用居高临下的“晓谕”、“宣谕”这样的词来记载;缅甸历次援助永历君臣的各种生活物资,南明流亡政权使用的却是“进”“贡”这样的字样;缅甸方面向永历君臣传达缅甸国王的意思时,永历君臣将其称为“奏”。从这些用词可推断出永历君臣自视为天朝上邦,而将缅甸视为藩属国。
但从缅甸的史料来看,缅甸从未承认是中国的藩属,更没有承认是南明的藩属。因此,永历政权将缅甸当作藩属国来看待,不过是自我想象而已。
(二)缅甸认为永历帝在缅甸称臣
从缅甸《琉璃宫史》中的记载来看,缅甸朝廷将永历政权入缅避难当作是向缅甸称臣。《琉璃宫史》说,“住于孟赛(云南)的永历帝遭到清军强力进攻溃败后,派使节前来交涉:如允进驻八莫,将向金殿之主献黄金一百缅斤。八莫土司回话说不敢将此事奏报吾王金殿之主,使者返回。后又派使者来八莫说愿在金殿之主阶下称臣。八莫土司将永历帝派来使者的情况奏报,国王吩咐:如不带武器来投,可用舟船将永历等安全护送前来”[1]990。永历帝答应缅甸条件后,缅甸准许其入境。《琉璃宫史》记载说:“在永历称臣之后,据报永历部下恭新文(巩昌王白文选)还以大军侵扰缅甸边境地区。缅王遂(派人)问永历:‘现在有人奏报你的部下骚扰朕边境地区,这是为何?’永历上奏缅王:‘安迪文(李定国)、恭新文(白文选)等不知我等在此称臣,故骚扰边境一带,如果安迪文、恭新文见到我加盖印章的手谕,都会放下武器归顺的。’”[1]991在咒水之难发生后,缅王派人对永历进行慰问,并解释杀害永历从臣的原因,《琉璃宫史》记载说:“永历奏到:他们做得不对,教训他们我心中并无责怪之意,我们本为活命而来称臣,请放我们一条生路吧。”[1]1002
从以上记载中,可明显看出缅甸将永历政权入缅避难当作向自己称臣对待。除《琉璃宫史》外,永历从臣的某些回忆也隐约透露出这一点。如根据邓凯讲述成书的《也是录》记载,“(1659年)八月十三日,缅酋来招黔国公沐天波渡河,并索礼物。盖缅酋以中秋日各蛮皆贡献,故责币帛以彰声势。天波至,胁令椎髻跣足以缅礼见,天波不得已而从之。”[6]366《求野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十五日,缅酋胁黔国公沐天波执臣礼以见……缅俗,八月十五日,群蛮贽见,酋张嘉会以享之。至是,绐天波至,胁令从缅制,白衣,椎髻,跣足,领诸海郡及僰夷酋长而拜,以夸示远近”。[5]386
不过,由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夷夏观念和天朝上国心理,南明政权是不会向被自己视为“蛮夷”的缅甸称臣的,南明从臣的相关回忆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沐天波被胁迫以臣属之礼拜见缅王后就遭到永历从臣的弹劾;[6]366再如1660年阴历七月,缅甸再度邀请沐天波见缅王,并表示可着中国服装(意为不必着缅装行臣服礼),但沐天波“终不允”[7]373。综合两方面的记载来看,永历帝虽然在缅甸流亡很长时间,但并没有与前后两任缅王见过面,很显然就是因为不愿俯首称臣。因此,缅甸将永历政权在缅避难当作阶下称臣,与永历政权自视为缅甸的宗主一样,事实上都是双方的自我解读而已。
(三)双方互视对方为臣属的原因
之所以会出现双方互视对方为臣属的现象,原因有三:一是“夸示远近”,服务于各自君主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即用对方的“臣属”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既满足自己的荣耀心理,又让本国臣民服从统治。对于这一点,古代中国和缅甸都很盛行。特别是古代中国,常常将与本国打交道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当作“藩属”来对待。从缅甸的相关记载来看,缅甸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由于信息闭塞、视野不宽,古代中国和缅甸都自以为是天下最文明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应该向本国表达敬意或学习本国,遵从本国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三是“惟汉人通事者往来传说”,即双方依靠翻译人员进行沟通,而翻译人员利用两国语言不通、文字不同、风俗习惯和礼义各异、对同样的事情理解各不相同的实际,在其中斡旋转述,谁向谁“称臣”于是成为一种自我想象的“各自表述”。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例如,1729年老挝南掌王国是否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史书记载说,当时南掌王国曾经派使团带着两头驯象到北京朝贡,雍正很高兴,给南掌王国很多赏赐,并规定以后五年一贡。但了解内情的倪蜕(时为云南巡抚幕宾)在其《滇云历年传》中记载说,南掌王国赠送驯象只是礼尚往来,其国书中并无朝贡、臣服、请求册封或仰慕中国之意。云南当局者(总督鄂尔泰)嫌南掌国书欠恭敬,“令维玺确定款式而行,……乃与素来行走阿瓦、通晓缅文之人商议,编蒲为表,而以金叶书之。……当事亦以外国使臣待之。将奏送入京,而其二象道死,乃以部购已至之象抵解焉。”[8]604因此,这次所谓“朝贡”不过是鄂尔泰为讨好雍正而编织的骗局而已。再如 1790年缅甸国王孟云与乾隆谁向谁称臣的问题?据中国史书记载,缅甸国王孟云派使团到北京“朝贡”,表达对乾隆皇帝的“恭顺”“仰慕”和“臣服”之意,并请求册封。乾隆很高兴,因为中缅战争结束二十年后,缅甸终于臣服了,于是派使团前去册封。孟云举行盛大仪式,行三跪九叩大礼接受册封。而缅甸史书的记载则相反,称中国为了向缅甸示好,派出庞大使团前来表达敬意。使团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奇珍异宝,而且还将中国皇帝的三个年轻公主敬献给缅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据法国学者白诗微的研究,这次所谓的“朝贡”与“册封”,不过是双方地方官为了解除中缅战争以来边境封锁、恢复双方边境贸易,利用双方语言文字不通、信息不畅而大胆编织的外交骗局而已。[9]311- 335三年后即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前来促使中国开放通商,而清朝将其当作英国前来臣服朝贡处理也是同样的情况。[10]在此之前的明朝也是如此,如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马六甲国王由中国明朝册封任命,其国王曾亲自远涉重洋,率庞大使团不远万里来中国朝觐,极为“忠诚恭顺”。但是,从许云樵所译《马来纪年》的记载来看,马六甲王并不承认是中国的藩属或附庸,而认为自己与中国王平起平坐。《马来纪年》中记载:因为中国王试图将马六甲王当作附庸,结果遭到了神的处罚,浑身发痒难治,只好派人取来马六甲王的洗脚水饮用和洗浴,才治好了痒病,从此中国王再也不敢小看马六甲王。[11]170- 177
总之,古代中国与缅甸史书中的外国称臣纳贡大多是一种自我想象,并非真实的事实,永历政权与缅甸互视对方为臣属,也是这种自我想象的产物。
三、咒水之难是突发事件还是有预谋的屠杀
永历十五年(1661年)阴历七月十九日发生的“咒水之难”,致使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众多文武大臣(包括沐天波在内)被缅军屠杀殆尽,永历政权最终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复兴的希望。对于咒水之难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中方史料与缅方史料的记载各不相同,值得斟酌。
中方史料《求野录》认为缅甸是有预谋的屠杀,目的是为了翦除永历身边从臣,以便顺利将永历帝移交吴三桂,“缅人于是谋杀从官,以孤帝势”。至于发生的场地和过程,记载含糊,似乎就发生在驻地(行在),又似乎发生在“赴咒水之会”的场所。[5]362显然,此史料是后来听别人传说而记录,并非亲见。
根据邓凯(因脚受伤,陪在永历帝身边而未参加“咒水之会”,得以幸免于难)讲述成书的《也是录》、《行在阳秋》和《狩缅纪事》中,记述了事件的大致过程,各有详略,互相参照,可知邓凯所讲述的大概内容如下:事件发生前三天,即七月十六日,缅官来请当事大臣过河议事,但没有任何官员前往,“皆辞不行”。事发前一天,即七月十八日,缅官再次促请众臣前往饮咒水,并解释说:“此行无他,我王子虑众心不善,请饮咒水,后令诸君皆得自便贸易生计耳。否则,我国安能久奉刍粟耶?”事发当天,即七月十九日上午,缅军三千人包围了永历君臣驻地,“大呼曰:‘尔大臣可俱出饮咒水,有不出者,乱枪攒刺之”,包括沐天波在内的诸大臣于是在犹豫中离开驻地,前往饮咒水盟誓,最终全部被杀。
至于在何地如何被杀?邓凯的讲述认为,诸臣走出驻地后,即被缅兵二十人(或三十人)捆住一人,当场杀害。而沐天波见事危急,从袖中取出流星锤反抗,击死缅兵九人,然后为缅兵所杀。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各持柴棒横行,杀缅兵十余人而死。但由于邓凯并没有走出驻地,不可能亲自看见当时的场面,而参加饮咒水的文武诸臣已全部被杀,不可能向邓凯讲述当时的场景。因此,邓凯只是在事发两、三天后听缅官向永历帝解释(通过翻译)事件情况时才了解到大致情况。由于缅官向永历解释时的特殊场合,再加上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失真,邓凯与永历帝一样,不可能知道具体的细节,因而其讲述中有很多自己的猜测、想象之处,不完全可信。
前往饮咒水诸臣被杀当天,永历君臣驻地随即被缅军洗劫。根据邓凯的讲述,事发当天中午到下午时分,大批缅军官兵蜂拥冲入永历君臣驻地洗劫,永历帝和皇后预感到前往饮咒水者可能已经遇难,最后时刻可能已经到来,准备自缢,因邓凯等人极力劝阻而作罢。而随侍在永历帝身边未前往饮咒水的部分官员和内侍人员(宫女、太监等)以及诸臣妻女不愿被缅军侮辱,纷纷自杀,“尸横满地”。在一片混乱中,永历帝与太后、皇后、太子等“二十五人同聚一小屋中,惊惶无措”。直到下午近傍晚时分,通事(翻译)才带着缅甸大臣前来,“乃喝兵曰:‘王有令在此,不可伤皇帝及沐国公’”,混乱局势才平息下来。由于永历帝驻地死人太多,缅官将幸存者二百余人(或三百余人,大多为妇女)迁到附近的房屋中安置,缅甸僧人送来饭食。根据邓凯的讲述,两天后,永历帝才得知饮咒水者的确切消息:过江饮咒水者已全部被杀。又过了四天,即七月二十五日,缅官前来慰问并送来生活物资,通过翻译向因惊吓过度而病倒的永历帝解释说:“我小邦王子,实无伤犯诸臣之心。因各营兵杀戮村民,民恐实甚,乃甘心于诸臣,以快其忿也。幸无介介于小邦。”永历帝仅能点头表示同意而
已。[6]368- 369 [7]374- 376 [4]390- 391
与中方史料相比,缅甸《琉璃宫史》的记载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可相互补充,相互验证。首先是原因,《琉璃宫史》记载缅王之所以让永历从臣饮咒水,是因为不想让这么多人在缅甸白吃白喝,而是要让这些人为缅王效力。让他们去饮咒水,事实上就是要让他们宣誓效忠缅王,然后分散安置。但永历从臣坚持要带上孟赛侯(沐天波)才肯去(可能觉得沐天波在场比较安全),缅王同意。其次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根据《琉璃宫史》的记载,在图巴永佛塔,即准备举行饮咒水仪式的地方,就在永历君臣驻地的对岸。三是具体过程:《琉璃宫史》记载说,永历诸从臣到达图巴永佛塔后,缅兵将孟赛侯沐天波与众人分开(因沐天波在缅人心目中地位高,让其饮咒水宣誓效忠不合适),沐天波误以为要杀他,从一名缅兵手中夺过刀来砍杀,导致多名缅兵死伤。其他大臣见状,也纷纷抢夺武器砍杀。经短暂混乱后,缅兵封锁了佛塔四边大门,从佛塔围墙上用火枪射击,将包括沐天波在内的在场众臣杀死。事后,缅王(派人)对永历说:“你的随从被召去佛塔宣誓,他们从朕的士卒手中夺刀砍杀,朕军伤亡很大。朕的士卒想,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将他们尽数杀死。你不要担忧,安心住下去吧。”而永历则表示并无责怪之意,希望缅王能给一条生路。[1]1002
从双方记载对比来看,咒水之难事实上是一场突发事件,而非缅甸有预谋的屠杀。但事件的发生也有着深刻的原因,即双方的长期怨恨已经达到临界点,随时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果。对永历君臣来说,长达两年半且完全没有希望的囚禁生活早已忍无可忍。对缅军官兵来说,两年多来,由李定国、白文选率领的南明残军不断给缅甸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早已使他们充满仇怨。而沐天波的误会最终引爆了这场悲剧,正是这一误会,让沐天波等人最终选择了快意砍杀和死亡来结束长期屈辱的生活。也正是这一误会,让充满仇怨的缅军官兵找到了快意复仇的对象。总之,这是一场已经难以避免的悲剧。
咒水之难使永历流亡政权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任何复兴的希望。1661年底1662年初,清军兵临缅甸首都阿瓦城下,缅甸将永历帝引渡给吴三桂。不久之后,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白文选降清;李定国病逝于边境,其子降清。明朝复兴的希望就此破灭了,而南明与缅甸这场难解的恩怨和困扰也就此宣告结束。
参考文献:
[1][缅]琉璃宫史(下卷)[M].李谋,等.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英]戈·埃·哈威.缅甸史[M]. 姚梓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3]余定邦.《琉璃宫史》有关中国的记述评析[C]//李谋,李晨阳,钟智祥.缅甸历史论集:兼评《琉璃宫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清)无名氏.狩缅纪事[Z]//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清)无名氏.求野录[Z]//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6](清)无名氏.也是录[Z]//于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清)无名氏.行在阳秋[Z]//于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8](清)倪蜕.滇云历年传[M].李埏.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9][法]白诗薇.著.陈燕萍.译.阿摩罗补罗宫廷的三位中国公主——1790年一段外交骗局的稗史[C]//李谋,李晨阳,钟智翔.缅甸历史论集:兼评《琉璃宫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新加坡]许云樵.译.马来纪年[M].新加坡南洋书局,1965.
(责任编辑杨永福)
A Few Problem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Ming Dynasty and Myanmar (1649-1662)
LI Jin-ping, LOU Zi-c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Ming dynasty and Myanmar Taungoo dynasty from 1649 to 1662 is fi lled with troubles which can be foun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Myanmar and related records of China. Military conflicts happened between South Ming dynasty and Myanmar Taungoo dynasty from 1649 to 1650 because South Ming dynasty taxed in Tusi region over the border and both sides has victory or defeat. Yongli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took refuge in Myanmar for the failure in fi ghting against the Qing troops from 1659 to early 1662, both sides treated each other as the subject and Yongli emperor had never met with two Myanmar kings. Yongli government was in Myanmar for 3 years,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were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and the remaining soldiers led by Li Ding-guo and Bai Wen-xuan brought a lot of destructions to Myanmar for looking for the emperor, so mutual hatred accumulated which directly caused the disaster of loyal ceremony. Since the disaster of loyal ceremony Yongli government never rose again. The troub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Ming dynasty and Myanmar Taungoo dynasty ended at the beginning of 1662 when Yongli emperor was extradited to Yunnan authority of the Qing dynasty, Bai Wen-xuan gave in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Li Ding-guo died of illness.
Key words:South Ming dynasty; Myanmar Taungoo dynasty; Glass Palace Chronicle;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 disaster of loyal ceremony
作者简介:李金苹,文山学院人文学院2011级历史学专业学生;娄自昌,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收稿日期:2014 - 11 - 07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5)04 - 0050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