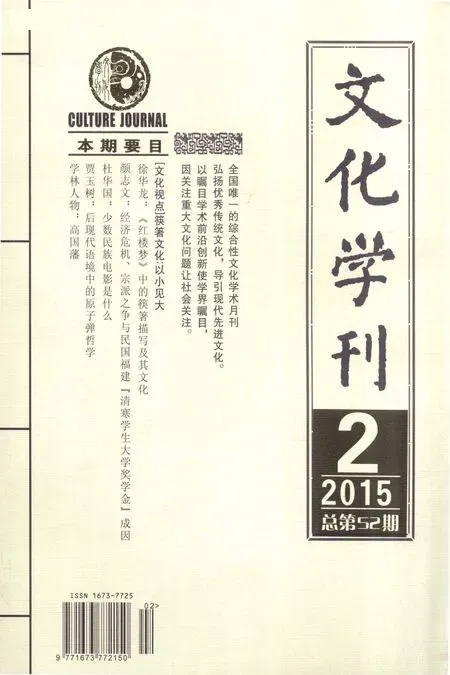微观权力说视角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权力来源
2015-03-20王梦
王 梦
(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天津 300000)
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其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领域的注意。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大多只有模糊的感觉,无法给出明确的界定。确实,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活动范围广等原因,难以进行简练明了的定义。但如果从“组织”到“非政府组织”再到“国际非政府组织”,一层一层地深入,还是可以对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1]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是个体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使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联系起来,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组织一方面带有集体活动的力量,另一方面构成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这为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基础。什么是非政府组织?1950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得出决议:只要不是通过政府之间的协议而创立的国际组织,都可以被视为非政府组织。1968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又将这一定义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认为即使组织的成员受当局政府指定,只要该组织成员能够不受政府干预,自由地表达自身观点,那么这一组织也可以划归到非政府组织的范畴之内。这两个定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美无缺地诠释非政府组织当下的发展状况,但却指出非政府组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非政府性质和独立自治性。[2]随后,学者们又进一步明确“非营利性”为界定非政府组织的一个重要指标,即社会公共问题甚至是全球性公共问题是其关注点,公共利益是其关切点。这三点基本构成现今广义的非政府组织,即非政府组织是那些不根据政府之间协议而建立,同时也不属于企业之列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3]而所谓的“国际”,即要求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目的与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或机构设置与成员构成具有国际性,或资金、其他主要资源来源、用途等具有国际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就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真正进入迅猛发展时期要到20 世纪70 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至今,其自主性问题可以说是备受争议。[4]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在政府之外独立发挥作用,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讨论的焦点,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希望借助福柯的微观权力说,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权力来源进行解释,从而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
一、福柯的微观权力说
福柯的微观权力说是在回应20 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福柯试图向我们展现微观权力的各种形式,并对“权力”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重构。对于福柯的微观权力说,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
(一)关注点
福柯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不围绕王权,也无涉法律与禁令的政治哲学。“砍下国王的头颅”是我们急需达成的目标,也是政治理论还未完成的事情。之所以要“砍下国王的头颅”,就是要摆脱以往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眼光更多地投向现代的、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权力形式及其政治效应。[5]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国家、政府机构不再重要,而是强调除此之外,诸如学校、工厂、家庭等微观权力的强大控制力。
(二)实现方式
在福柯看来,研究权力不应只局限于《利维坦》的模式。传统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多地借助于禁止和惩罚,而现代社会的政府管理则是通过科学与规范等一系列知识手段来实施的。权力不再高高在上,不再仅仅意味着限制和压迫。福柯开始认识到,权力与知识是相互关联的,权力关系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关的知识领域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知识的产生同样需要建立和设定相应的权力关系。
(三)实施主体
福柯认为,传统权力观将其实施主体定位于政党或阶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政治的重要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以往政党政治的范畴而深入大众。大众虽然缺乏宏大的政治纲领,看似凌乱,但正是大众的多元化诉求引导着当今政治的走向,并当仁不让地成为微观权力说中的实施主体。
(四)权力关系
在福柯的微观权力说中,权力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重要特点是对权力泛化的强调。权力需要通过各种关系、各种行动,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动,而是弥散性的,分散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时而有形,更多时却又发力于无形。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权力来源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之外的必要补充力量,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支撑,为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进行佐证,福柯的微观权力说正好满足了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一需求。
(一)二者的旨趣相同
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使传统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家的局限性日渐显露。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全球治理工作,更灵活、更高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一种可以突破地域限制的行为体,于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而福柯的微观权力说的“现代性态度”,充分彰显了其对传统权力观的不满。“现代性态度”在福柯看来是人在当下所进行的反思性存在,这种存在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不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出现,还是福柯微观权力说的产生,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现实的反思。
(二)二者都强调对他者权力的关注
国家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作为最高权力权威,控制着社会的日常运转。由于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因此其他权力主体被长期边缘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对自身的权力功能进行一定的调整和转变。例如,通过参与全球性立法为本国创造相对公平的有利发展的法律环境;借助各国间达成的相互约定,对国际犯罪、恐怖主义进行打击。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单一行为主体不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对他者权力的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的。对他者权力的关注,使国际非政府组织区别于国家,并在全球治理中大放异彩。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行体制也特别强调权力的多元化,不再将眼光只集中在国家这一层面,注重多行为体的共同协作。福柯微观权力说同样是关注他者权力的典范。福柯以精神病学权力及反抗研究作为自身研究的重点,将非理性受传统理性秩序压抑和遮蔽的事实公之于众并予以批判,从而对理性秩序的现实困境和自身界限进行回应,其目的就是要恢复非理性的地位,使人们意识到关注他者权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二者都认为知识是重要的权力来源
福柯尖锐地指出,一些知识分子总是认为知识领域是无上光荣的,象征着真理和自由,因此,知识领域和权力运作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所有人文知识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权力的背景下进行的。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知识喻为权力的眼睛,认为知识所指涉的地方往往与权力所指涉的地方相重合,二者互相依赖,知识化身真理为权力提供理论支撑,而权力又为知识化身真理保驾护航。这种现象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相关关系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来源。首先,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保持其独立自主性,不仅需要在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控制优势,还需要确立自身在该领域的权威性。权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主性,也就是其权力的重要来源。一般情况,国际非政府组织所追求的使命是国际社会所珍视的目标,如保护人权、提供发展、促成和平协议。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推动这些目标赢得尊重,从而获得道义性权威。另外,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基本通过理性的、技术性的、非暴力的方式,这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大众中拥有更多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体成员很多由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拥有者构成,因此,专家权威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权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以上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显性权威的话,那么以下这点便是其隐性权威,这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效果经常会超出人们预期的原因。国际非政府组织追求的目标由于往往是国家所淡化的,所以,这一领域在最初往往缺乏规则。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旦创立起来,工作人员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们严肃对待使命,在工作实践当中发展观点,组织文化。[6]久而久之,这种观点、组织文化成为行业习惯被固化,渗透于大众的日常思维当中。也就是说,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仅控制信息,还分析和解释信息,并赋予信息确定的含义,由此把信息转化为知识,这与福柯对知识的强调可谓异曲同工,即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按照福柯的思路,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可以借助自身拥有的强大信息储备,通过改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决策的动机来改变它们的行为,以达到控制与管制其它行为体的行为的目标,从而充分发挥自主性。另一方面,福柯强调对知识的应有之义,即知识对世界的建构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对世界的建构,创造出崭新的社会现实,使其自主性发挥到极致。
三、小结
保持自身独立性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要确保这一前提,国际非政府组织需要清楚了解自身的权力来源。需要借助一定的策略,运用得到的外在资源,同时把握好源于内在的观念、道义、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性微观权力优势。只有这样,国际非政府组织才不至于丧失立足之本,才能够不断促进国际行为体多元化以及世界秩序民主化,有效缓解国际性冲突,帮助解决全球性问题,为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1]Michel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M]. 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ed.New York:The New Press,2003.309.
[2]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27-1977[M]. Colin Gordon ed.Brighton:Harvester,1980. 102.
[3]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1979.27.
[4]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ther.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38.
[5][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8.
[6]张国清. 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权力理论的哲学批判[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