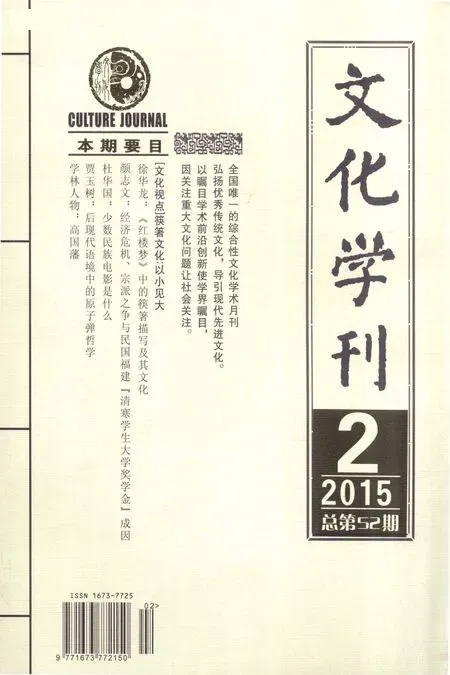少数民族电影是什么
2015-03-20杜华国
杜华国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电影是什么?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安德烈·巴赞从艺术类型本体论出发探讨了“电影”与“戏剧”“绘画”类型特征上的交叉与分离,论述了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摄影影像本体”“我性”,论证了“戏剧”“绘画”相对“电影”的“他性”。“摄影影像具有独特的形似范畴,这也就决定了它有别于绘画,而遵循自己的美学原则。摄影的美学潜在特性在于揭示真实。在外部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湿漉漉人行道上的倒影或一个孩子的手势,这无须我的指点;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激起我的眷恋。”[1]一如电影的“我性”要从艺术类型本体论出发一样,笔者认为也应从电影类型本体论出发,阐释“少数民族电影”的“我性”,厘别与其他电影类型的“他性”。
一、“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混乱现状
学界、业界一直没有对“少数民族电影”作出明确界定,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王志敏在《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界定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三原则”:文化原则、作者原则、题材原则。民族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相互指代是学界、业界的惯常做法。“民族电影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总体和宏观的建构,但如果缺少具体的研究,宏观的建构便会显得空泛。”[2]这里的“民族电影”泛指中国电影。“《盗马贼》沿袭《猎场札撒》风范,全部启用藏族非职业演员,角色与演员合二为一,演员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角色的表演内容。……通过这部同样极少对白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田壮壮继续着自己对‘他者’世界的探讨。”[3]“田壮壮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呈示了两种特征:一是追寻宗教,二是平视角度。”[4]“正是出于对少数族群和非主流文化的尊重,田壮壮的民族电影悠远而单纯,不居高临下,不妄加评论,沉静的影像充满冥想的张力,它们逆转了1949年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的汉化倾向,以没有‘外在’偏见的表述留下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地缘纪录。”[5]上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民族电影”所指相同。在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第一章标题“曲折中发展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60—1966)”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第七章标题“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2000—2010)”的“少数民族电影”内涵一致,综上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电影”适用的混乱现状。
二、类型电影与电影类型
不像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的“生日”无法考证,电影从1895年诞生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艺术界是最年轻的类别,类型在文学领域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开始了,电影的类型研究借鉴了文学类型研究的成熟体系。类型电影是高度模式化的影片,是依随美国好莱坞制片厂制度建立的产物,类型电影的产生是为了方便制片商在某种“规范”(类型片)指导下流水线生产影片,以期获得最大利润,可以说类型电影就是商业片的代名词。“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便是好莱坞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它为好莱坞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学基础和稳定性,更使好莱坞可以生产出在摄影机运动、剪辑、叙述方式和影片类型等方面可以迅速得以辨识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影片。类型电影实质上是一种拍片方法,是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6]类型电影是制片商与观众的缝合握手体系,当看到《音乐之声》(罗伯特·怀斯,1964)类型介绍为歌舞片时,观众就会想到“音乐,歌舞在影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成为影片叙事、表意、抒情的重要艺术元素,也是观众观赏的兴趣中心。”[7]类型电影的概念传达,需要制片商和观众的“前呼后应”,“类型电影作为一种通俗叙事艺术,与其说它是为了公众而制造的,不如说它就是由公众所制造出来的。”[8]电影之类型经历了从类型电影到电影类型的所指嬗变,时下类型电影已摆脱了经典好莱坞时期大制片厂生产管理模式,衍变成了电影类型,笔者认为,时下类型电影指的就是电影类型。电影类型的划分一般从“观念”与“范式”两个维度来界定,“观念”指的是主题方面,是该类型片共同体现着的价值趋向;“范式”指的是形式结构方面,比如歌舞片中的“歌舞”、西部片中的“西部牛仔”等。
类型电影和电影类型的区别是,类型电影的制作主体是制片商,而电影类型的制作主体则是理论学者。影片制作前类型电影就存在于制片商的意念里,影片按某套“观念”“范式”制作完成后类型电影宣告造就。电影类型是影片制作完成后,理论学者按类型片划分标准将其归属,可以看出,类型电影是“含义先于存在”,电影类型是“存在先于含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影类型的不断演绎变化,相对稳定的判断标尺——“观念”与“范式”的界限也愈来愈模糊。《阿甘正传》(罗伯特·泽米吉斯,1994)有着政治片和爱情片的双重“观念”与“范式”。“政治片(Political Film)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将某一社会或国家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故事主线,艺术地传达导演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的电影类型。”[9]《阿甘正传》展映的种族歧视、垮掉派、水门事件、总统被刺、越南战争等事件贯穿了整部影片,可以说该片是一部承载了美国沉重社会政治问题的政治片。“爱情片(Romantic Film)是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的统称。”[10]阿甘和珍妮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度过了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在美国社会急剧转型期,两人几度悲欢离合。待铅华洗尽,蓦然回首,珍妮发现最值得爱的男人——阿甘还在原地等着她,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得不说该片也是一部凄美感人的爱情片。当一部影片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观念”与“范式”(主题的多义性)该如何“定型”呢?笔者认为,类型归属要看影片最显著的“主控主题”、最明显的“类型症候”。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罗伯托·贝尼尼,1997),犹太青年圭多突破身份勇敢追求多拉的壮举令人钦佩,为儿子的“美丽人生”免受泯灭人性法西斯暴行影响,这个外表弱小的父亲做出了一系列铮铮硬汉行为,直至付出生命,浓浓父爱呼之欲出。该电影出现了三种“观念”“范式”,该片是“战争片”“儿童片”还是“爱情片”呢?笔者看来,男女主人公美好爱情、婚姻的破灭,圭多为塑造儿子的“美丽心灵”不得不“欣然赴死”,一切悲剧的根源都指向了战争,创作者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对战争荒诞、残酷的反思和救赎,因此,该片应归入“战争片”。
三、少数民族电影的“我性”
笔者对王志敏的“少数民族电影”界定持不同意见,按其原则蜚声海内外的经典影片《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就不属于“少数民族电影”,因为导演不是少数民族,不符合“作者原则”。章家瑞的“红河三部曲”——《婼玛的十七岁》(2003)、《花腰新娘》(2005)、《红河》(2009)也不属于“少数民族电影”,因为导演也不是少数民族。不难发现,“作者原则”有着逻辑悖论和粗糙修辞:少数民族导演乌兰塔娜(蒙古族)可以创作非少数民族电影(如《暖春》,2003),汉族导演为什么不能创作“少数民族电影”呢?
类型作为电影学科的研究视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臻成熟,国内外都有丰硕的理论成果,比如沈国芳的《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卡明斯基的《美国电影的类型》等。类型片的概念界定不能缺少理论学者的声音,其概念界定应由制作者、理论学者及有一定电影知识素养的观众共同完成。“‘少数民族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电影准类型。”[11]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电影”是类型视域下的称谓,因此其概念定义应在类型范畴内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其生存经验独特、人文环境复杂、生产力关系赢弱,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势必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在潜滋暗长地变迁着。放眼当代中国文化进程,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更多是文化的进化。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进化。纪录少数民族文化进程— —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最重要的适格功能。”[12]“少数民族电影”应该纪录急遽变迁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也唯以纪录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为宗旨的影片才是“少数民族电影”。“文化”的概念广受争议,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culture)的定义影响深远,“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道:‘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13]笔者试着给少数民族电影下个定义:少数民族电影是以纪录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为主旨(观念);在形式结构(范式)上,少数民族电影中往往有着一贯的类型人物(角色是少数民族)、类型环境(故事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类型对白(少数民族语言)等;理论学者及有一定电影知识素养的观众也认为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影片。
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民族电影、影视人类学片的“他性”
题材是指“电影剧本所反映的生活现象的对象、性质和范围。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等’”[14],笔者看来,题材和类型毫无关联,少数民族电影可以是农村题材(如《五朵金花》),可以是历史题材(如《暴风中的雄鹰》,王逸,1957),可以是宗教题材(如《静静的嘛呢石》,万玛才旦,2006)乃至神话传说(如《阿诗玛》,刘琼,1964);反之,《李时珍》(沈浮,1956)是“历史题材”,在类型视角下则属于“传记片”,《边寨烽火》(林农,1957)是“少数民族题材”,在类型视角下则属于“反特片”。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涉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因子的影片,狭义指涉猎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份量不足以构成少数民族电影的影片。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在少数民族电影中是主旨诉求,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只是被涉猎,广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包含少数民族电影的。
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对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自诞生到新世纪初一直是“普通话”对白,政策的松绑对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诞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广电总局2003年出台的四大改革政策和2004年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放松了电影行业的“国有事业”属性,不仅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电影产业,电影制作也不再“上纲上线”。此背景下,或出于展示“原生态”“原汁原味”抑或制作成本考虑,2005年始一批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应运而生。电影作为“现实的渐近线”,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少数民族语言对白不仅是纪实美学的契合需要,更是少数民族文化自觉的意识体现。时下学界、业界把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统统归入少数民族电影,笔者以为不然,少数民族母语影片是否能归纳入少数民族电影,要看其是否以展示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为宗旨。《黑骏马》(谢飞,1995)是蒙古语对白,影片中不乏广袤的草原、蒙古包、马头琴等蒙古族社会文化因子,该片“貌似”少数民族电影,但该片的主题是赞美坚韧、豁达的生命力,讴歌穿越世俗的人性大爱、大美。因此该片不属于少数民族电影,而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斯大林对“民族”是这样定义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5]民族在我国的探讨始于民族学领域,文艺领域的民族承袭了其民族学涵义,因此,我们探讨民族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的语义区别,不能绕开民族学民族的含义。时下民族学使用的“民族”大致有两类内涵:“第一是在特定的场合与条件下,专指现存少数民族,相当于英文的 minority。如“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民族人口”“民族聚居区”“民族散居区”等等,都是专指少数民族的概念表达。第二是在特定的文脉中,“民族”一词也能用于指称像“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样的对象范畴。……“民族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等就是指的这一层面的概念。”[16]“民族教育”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而“民族解放战争”却指的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笔者认为,所谓“在特定的场合与条件下”“在特定的文脉中”其实是民族概念滥用后的“墨守成规”,民族的民族学语义模糊顺延到了电影领域,从而导致了民族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的双向歧义。全球语境下民族电影(National Cinema)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在西方,‘民族电影’是指与好莱坞电影相对立的电影事业。”[17]我国电影理论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当面向全球语境的北京国际电影季民族电影周的“民族电影”指称着少数民族电影时,必然会引起涵义歧义。笔者认为,民族电影与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区分开来:民族电影泛指一个国家的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指的是某少数民族电影。
顾名思义,影视人类学是以照片、影片等影像媒介为主要手段研究人类学的一门学科。“和文字资料不同,影像虽然也是二手资料,但是相对而言,比田野调查笔记更具有客观性和直观性。避免了由于文字叙述的不准确和含糊性导致的理解障碍。”[18]少数民族电影的纪录媒介只能是动态影像,而影视人类学不仅以动态影像为媒介,照片等也是重要的纪录手段。笔者认为,在动态影像上,影视人类学片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影视人类学片就是民族志记录片,比如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县德昂族水鼓制作过程的记录,而广义影视人类学片不是“原汁原味”地纪录,它是经过人类学者依自己诉求选择纪录而结构出的艺术样式。“在概念上,‘纪录’涵盖了整理择取、讲道叙纲,也就是有主题、有阐释、有选择、非虚构地讲述生活中的真实。”[19]也就是说,广义影视人类学片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少数民族电影和狭义影视人类学片的区别显而易见,其与广义影视人类学片的区别在于后者要求画面绝对真实,不能有“虚构性”和“文学性”等艺术修饰痕迹。“怎么区别对于我们以外的真实世界的记录和对于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世界的建构?后者被我们称之为虚构”[20],而少数民族电影是“艺术作品”,是“虚构”的。
五、结语
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民族电影的一朵奇葩,如清水下明石般熠熠耀闪的明珠镶嵌在民族电影历史长河中,如画旖旎的自然风貌、多彩斑斓的服饰、纯洁烂漫的爱情、肃穆神秘的民俗……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总是让异族人回味再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已然走过六十年光阴,无论是“将纷繁的类型电影分成比较稳定的类型群组:西部片、歌舞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传记片、强盗片、政治片等”[21],还是陈林侠在《中国类型电影的知识结构及其跨文化比较》一书中把国产类型电影分为伦理片、战争片、爱情片、恐怖片、武侠片、喜剧片、枪战片、灾难片,少数民族电影芳迹难觅。从电影类型本体论出发,以类型片维度审视,是对少数民族电影内涵的追本溯源。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的确定不仅给电影类型研究增添了新家丁、开拓了新视域,这对其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2]沈小风.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3][4][5]杨远婴.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寻[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6]黄文达.外国电影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11.
[7][9][10][21]沈国芳.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8]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11][17]胡谱忠.命名与修辞: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元问题”[J].影视艺术,2014,(02):10-20.
[12]杜华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适格功能探析[J].电影评介,2013,(15):42—44.
[13]王四代,王子华.云南民族文化概要[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14]许南明,富澜等.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15][苏]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二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6]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8]邓卫荣,刘静.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9]焦小惠.纪录片的再现与表现[J].电视研究,2001,(10):36—38.
[20][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