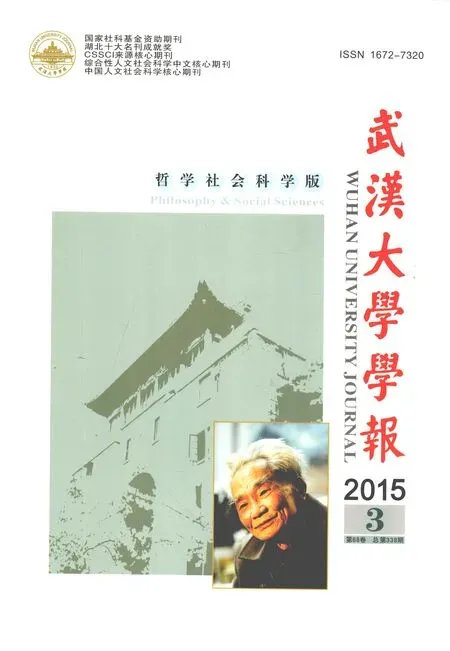商鞅之“法”的政治哲学反思——兼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2015-03-20吴保平林存光
吴保平 林存光

商鞅之“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兼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吴保平林存光
摘要:以商鞅之“法”的含义和目标为切入点,有助于理解商鞅以“以法治国”为中心,围绕“农战”而形成并展开的法治思想。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以及“至德复立”、“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学视域,商鞅之“法”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关键词:商鞅; 以法治国; 法治; 政治哲学
商鞅是先秦时期前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绕“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刑赏”则是“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法”不仅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是“农战”和“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重新审视并反思商鞅之“法”*“世传《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所著”的观点在学界已成定论。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后学者”为“秦法家”,并在论著中将商鞅及其“秦法家”简称为“商”或“商鞅”,如林存光在《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中即以此称之;有学者则将此“后学者”称为“以商鞅思想为中心的商学派”,如郑良树在《商鞅评传》中即以此称之。鉴于此,本文所言“商鞅之‘法’”中的“商鞅”,既指商鞅本人,也指“商学派”;“商鞅之‘法’”中的“法”,既包含商鞅本人的法治思想,又包含“商学派”的法治思想。的含义和目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 “法”的含义
在《商君书·修权》篇,商鞅提出了“法”的概念,即“法者国之权衡也”(蒋礼鸿,1986:83)。这一概念道出了商鞅之“法”的三层含义:在基本语义层面,“法”就是法律、禁令;在政治思想层面,“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在具体制度层面,“法”又具有“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即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一) 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
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等同于法律、禁令,《商君书》中的“法令”、“法制”以及有时所言的“法”都有此种含义。如,“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蒋礼鸿,1986:131)中的“法”,即指规范、约束人们言行及社会活动的法律、禁令;“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蒋礼鸿,1986:130),“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蒋礼鸿,1986:144)中的“法制”、“法令”都含有法律、禁令之义。此外,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则是“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如《垦令》中颁布的20条垦荒法令。正因为商鞅之“法”具有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商鞅所主张法律之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吴保平、张晓芒,2012:42-4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才具有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二) 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
政治思想层面的“法”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更能突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缘法而治”、“任法而治”、“以法相治”(蒋礼鸿,1986:130、137)等,意指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鞅之“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管子·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这段话道出了“法治”的深层含义,即“依法治国”。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6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法”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程燎原,2011:7)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层面的“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以法为治”,“生法者君也”,“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程燎原,2011:8)。其中,“法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那么,商鞅如何使“法之必行”呢?
其一,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商鞅认为,“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吴保平、张晓芒,2012:43)。《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统治者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蒋礼鸿,1986:82);“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蒋礼鸿,1986:65)。
其二,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在《定分》(蒋礼鸿,1986:146)篇再三强调其“法”要“明白易知”;同时,又主张“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何建章,1990:71)可以看出,普法教育成效显著。
其三,要使“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壹刑”,也就是司马谈所称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1959:3291)。他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蒋礼鸿,1986:100)在商鞅看来,“法之必行”的关键在于“上”和“贵”,只有自“上”、自“贵”行法,“刑无等级”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商鞅将“法之不行”归于“自于贵戚”(司马迁,1959:205)和“自上犯之”,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司马迁,1959:2231)以惩太子犯禁之过。
其四,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权制断于君”。商鞅认为,权势只有集中在国君一人之手,所颁布的法律、禁令才具有威慑力,才能保证“法之必行”,才能顺利推行“法治”。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蒋礼鸿,1986:82)对于国君而言,不仅要独揽大权、树立威势,还要“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即作尊法、守法、依法行使的表率,才能称得上“明主”,才能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具有威慑力,进而推动“法之必行”;对于民众而言,“从令”是“尊君”的最好表达方式,因为“君尊则令行,……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蒋礼鸿,1986:130)。
(三) 具体制度层面的含义
商鞅在《画策》篇指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蒋礼鸿,1986:109)他认为,要使“法之必行”,除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应具有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等特征外,还应有“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作保障。那么,“必行之法”和“必得之法”中的“法”指的是什么呢?
商鞅认为,实施“为法置官吏”制度,就是“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在《定分》篇,商鞅详细论述了“为法置官吏”制度的方法、目的和意义。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设置法官、法吏,既可达到“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的普法目的,又可形成“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之人人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还可杜绝类似于“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等违法、贪腐案件的发生(蒋礼鸿,1986:144)。同时,该制度又以“重刑”作保障,即对知法犯法的法官、法吏施以严酷的刑罚,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蒋礼鸿,1986:101)。首先,商鞅要在臣、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机制,从而营造一个人人知法、人皆守法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其次,这种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之时,也就是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之时。所以,商鞅所指“必行之法”的“法”既是一种制度的支撑,也是在这一制度支撑之下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的体现。虽然这一制度是在“重刑”的保障下实施的,但是仍对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商鞅之“法”在制度层面的深层意涵也正表现在于此。
二、 “法”的目标
商鞅之“法”的目标分两个层级逐步推进,第一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强”,即实现富国强兵;第二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治”,即实现天下大治。为此,商鞅以“法”为工具,以“刑赏”为手段,建构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政治治理体系。
(一) 目标的实现原则
商鞅“法”之目标的确定乃至政治治理体系的建构都是从“定分”开始的。“定分”即确定名分,而与当时社会历史密切相联的焦点问题就是“名分”。战国初期,“土地私有的国民富族正催促着以血族纽带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发生变化”(侯外庐等,2004:20-21),从而使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七国纷战犹如“众人逐兔”一般,看似在争夺霸主之位,实质则是要确定土地的权属(名分)问题。那些“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蒋礼鸿,1986:145)的祸乱现象,均源于“名分”之不确定。基于此,商鞅认为:“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蒋礼鸿,1986:52)这样,在“土地私有与公权制度以及法律相为联带的关系”(侯外庐等,2004:21)之下,“分定→立禁→立官→立君”逆向承接,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政治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国君管理群臣,群臣执行法令,法令保障之下的土地、货财、男女等“名分”问题得以确定,纷乱和争斗随之止息。同时,为使“公私之分明”,商鞅还将“名分”法律化,即“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蒋礼鸿,1986:84)。正如蒋礼鸿所言:“商鞅之道,农战而已矣。致民农战,刑赏而已矣。使刑赏必行,行而必得所求,定分明法而已矣。”(蒋礼鸿,1986:19)可见,“定分明法”之后,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和臣民行为的规范都更加明确,“致民农战”的手段更加集中,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为实现这一层级的目标,商鞅提出“教民作壹”的主张,并通过“壹赏”、“壹刑”、“壹教”三项原则,以统一思想认识,驱使人民于农战之中。在这三项原则的合力下,商鞅之“法”第一层级的目标得以实现。
对于商鞅之“法”第二层级的目标——天下大治,商鞅认为,要通过人民的“自治”才能实现。那么,人民何以“自治”呢?这仍需要“定分”、“明法”以及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实现。在商鞅看来,只有将“名分”问题以法律的形式将确定下来,同时让人人都了解法律的利、害之处,纷乱和争斗才会随之止息,人民才会安于“自治”。正所谓“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蒋礼鸿,1986:146)。但是,无论是从“定分”到“自治”,还是从“避祸就福”到“自治”,都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使外在的“硬约束”变为人民内在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人们行为习惯在法律这种稳定性及明确性的制度约束下,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将由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渐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律,并且最终内化于心成为无意识的行为习惯,法作为对权利的保护和对过错的防范将让人们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仰”(何山、张磊,2012:95)。由此,社会开始进入“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和“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蒋礼鸿,1986:40、41)的自治而有序的“天下大治”(蒋礼鸿,1986:146)状态,并经此迈入“至德复立”(蒋礼鸿,1986:57)和“能述仁义于天下”(蒋礼鸿,1986:82)的“至德”阶段。令人扼腕的是,这种“至德”的理想社会形态的设计还未及成型,即随着商鞅身遭“车裂”之刑而陨灭于萌芽状态,从而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由非人格化的法律机制、‘技术’和神秘的权势支配”(史华兹,2003:359)的“乌托邦”梦想。然而,就是这个“梦想”让人体悟到,“社会完全法治化之日,恰恰又是社会高度道德化之时,至大至刚的法之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水乳交融”,所形成的“仁义的真正底蕴”(曾振宇、崔明德,1997:32),正是当今社会孜孜以求和亟须实现的目标。
(二) 目标原则的特质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出和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价值,而“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基本内容,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吕嘉,2006:76)。依此观照商鞅之“法”,其“法”之目标——富国强兵和天下大治,正是其价值目标;其“法”之目标的实现原则——“壹赏”、“壹刑”、“壹教”,也正是围绕价值目标而形成的价值标准。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二者共同成为秦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首先,从价值标准的制定来看,“壹赏”、“壹刑”、“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有理论支撑,而且还具有“特定性”。商鞅“壹赏”、“壹刑”、“壹教”的制定,完全以“历史进化观”、“好利恶害人性论”和“力治说”为依据。其一,在“历史进化观”的支撑下,新法的制定才有了理论基础;以新法为工具,“壹赏”、“壹刑”、“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自战国初期各国展开以“求富求强”为目标的变法活动,是一股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政治潮流。在这股洪流的推动下,商鞅根据秦国国情以“壹赏”、“壹刑”、“壹教”为原则形成的“农战思想”,呈现出显著的“特定性”——既与当时各国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又以秦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可以说,“历史进化观”是实施“壹赏”、“壹刑”、“壹教”的前提。其二,提出“壹赏”和“壹刑”的出发点在于人民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战国中期前的秦国,是一个地处偏远边境的“半野蛮国家”;在这个国家,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条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史华兹,2003:344)。在商鞅看来,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秦人都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因此,将“利禄官爵”之“实”和“名”的获取限定在“军功”的范围内,即“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蒋礼鸿,1986:139),则有利于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其三,人民在“刑”与“赏”且是“刑”大于“赏”的利、害权衡之下,“壹赏”最终将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实现,即“利出壹孔→作壹→民不偷营→多力→国强”。这样,蕴藏在“壹赏”之中的“力治说”随之清晰地呈现出来。总之,“教”、“刑”、“赏”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规定和实施,使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即“壹赏”、“壹刑”、“壹教”和“富国强兵”很快成为秦国臣民的共识。
其次,从“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效来看,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能被秦人很快认同和实现。对于“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能,商鞅总结道,“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蒋礼鸿,1986:96)。可见,“壹赏”、“壹刑”、“壹教”三者逆向依次递进而又相互补充,即由“下听上”实现“令行”,由“令行”致“兵无敌”,从而成为实现商鞅之“法”第一层级目标——富国强兵的有力推手。也就是说,“壹教”不仅强化了人民的法制意识,同时又使商鞅所制定和树立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壹刑”的法律保障之下,这个“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壹赏”则最终将该价值目标变成现实。
三、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在国家治理中,“法”是“以法治国”、“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而“以法治国”则是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主要手段。“以法治国”是“运用和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且“在字面上等同于近现代法治的意味”(卓泽渊,2002:16)。因此,在“以法治国”过程中,法治应兼具法律的基本特征。这样,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自然也就体现出法律的强制性特征。这种强制性作用将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的行为逐渐由他律转化为自律后,法治的发展开始进入到“法治国家”阶段,其间也需要道德的内化作用。在“法治国家”阶段,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主要体现出自律性特征。当国家与社会完全依靠法治及道德的自律性作用运转时,即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时,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得到充分发展和体现,法治的发展开始进入“法治社会”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法治国家”还是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或者是在二者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法治的强制性作用都没有被弱化,而是内隐于其自律性特征或根本精神价值之内。依此观照商鞅之“法”,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和“至德复立”及“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商鞅之“法”中同时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既然在“以法治国”过程中法治具有法律的基本特征,那么商鞅所言的“法治”也兼具时代性、必要性、公开性、公平性、强制性等法律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其一,商鞅以历史进化观为依据,认为治国不应墨守陈规、照搬旧法,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反观商鞅“度俗而为之法”(蒋礼鸿,1986:63)的“法”,虽没有“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但却是根据秦国的社会现实“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郝铁川,2000:7)。列宁(1986)指出,“千万年来人们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最可怕的势力”一旦上升为法律,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商鞅之“法”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才使“以法治国”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其二,要“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法”的必要性。在商鞅看来,法律是“民之命”和“治之本”(蒋礼鸿,1986:144),只有慎重立法并做到“立法明分”,才能使“民不争”(蒋礼鸿,1986:84),才能实现“治”的目标。商鞅对法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其“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以法治国”也就具有了实施的可能性,而不终落为一种理论的设想。其三,法的公开性既有助于加快法治发展的步伐,又有利于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为此设置“法官”,以使臣民明确知晓法的内容并按其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令臣民主动守法的目的。同时,也能在臣、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由人人知法、人皆守法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秩序以及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不仅是“使法必行之法”运行的最优环境和最佳制度支撑,也是“法治国家”阶段的基本特征。其四,法的公平性、强制性是“以法治国”的要旨所在。商鞅认为,法代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必须兼具公平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赏与罚应一律平等,不能因人而异。这样,坚持法的公平性和强制性才能将人性好利这种“可资因循利用的人性弱点”(林存光,2014:330)发挥到极致,才能将人民驱使到农战之中,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总之,商鞅对法之时代性、必要性、公开性、公平性的认识和阐述,突出的是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同时,在法的公平性、强制性作用下,刑、赏共同实施于农战之中,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及进入“法治国家”阶段夯实基础。
商鞅之“法”中还含有通过法治实现“万民自治”和“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尤其是表现于其上的强制性作用,不仅可以实现富国强兵,还可以使秦国进入“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阶段。商鞅理想中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的标志是“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和“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天下大治”状态,特征是“至德复立”和“能述仁义于天下”。同时,这一特征恰恰又是以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为标志,进而充分体现出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
从法治的主体来看,“法治的主体是社会不是个人,故而得到满足的是整个社会不是某个人”(鲁鹏,2013:6)。因此,法治的价值也不应是个体价值的体现,而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的体现。作为君主专制的倡导者,商鞅把君主定位为全国唯一的、最高的立法者,依此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样,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以法治国”,自然也就成了君主的“以法治国”。如果法治的主体——君主不变,那么商鞅之“法”终将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所以,商鞅的“以法治国”注重的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控制、驱使和镇压,体现的也仅是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的强制性特征;而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也只能停留在理想状态,无实施也更无实现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而言,商鞅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随着秦朝的速亡而融于“外儒内法”的绥靖政策之内,也在情理之中。若要使“以法治国”真正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及精神,则必须将法治的主体归于社会、归于人民。
参考文献:
[1][美]本杰明·史华兹(2003).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陈烈(1929).法家政治哲学.上海:华通书局.
[3]程燎原(2011).先秦“法治”概念再释.政法论坛,2.
[4]郝铁川(2000).法治功能的二重性.检察日报,2000-10-18.
[5]何建章(1990).战国策注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6]何山、张磊(2012).马克思与商鞅对法治认识的契合.前沿,23.
[7]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2004).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8]蒋礼鸿(1986).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
[9]江必新(2013).法治思维——社会转型时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法学评论,5.
[10] 黎翔凤(2004).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
[11] 列宁(1986).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 林存光(2014).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鲁鹏(2013).法治的价值.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4] 吕嘉(2006).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学习与探索,1.
[15] [汉]司马迁(1959).史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
[16] 吴保平、张晓芒(2012).商鞅之“法”及其刑名逻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7] 曾振宇、崔明德(1997).由法返德:商鞅社会理想之分析.中国史研究,1.
[18] 卓泽渊(2002).论法治国家.现代法学,5.
■作者地址:吴保平,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2249。Email:wuping1010@126.com。
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媛
◆
Political Philosophy Reflection of Shang Yang’s Law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Function,Value and Spirits of Law-ruling
WuBaop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inCungua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meaning and objective of Shang Yang’s Law as its starting point,which can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hang Yang’s law-ruling thoughts.Shang Yang’s thoughts centered in “ruled the country by law”,formed and expanded around “agriculture strategy”.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statesmanship is emperor in his law-ruling thoughts,but making the whole country rich and its military force strong is not the only purpose in his ideology,“all-people self-governance”,“the whole world’s stable”,“re-establish the highest moral” and “inherit the virtue in society” are the other political ideas to be achieved.Fro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s perspective,Shang Yang’s Law reflects the function,value and spirits of law-ruling.
Key words:Shang Yang; rule the country by law; rule of law; political philosophy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8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ZX077)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