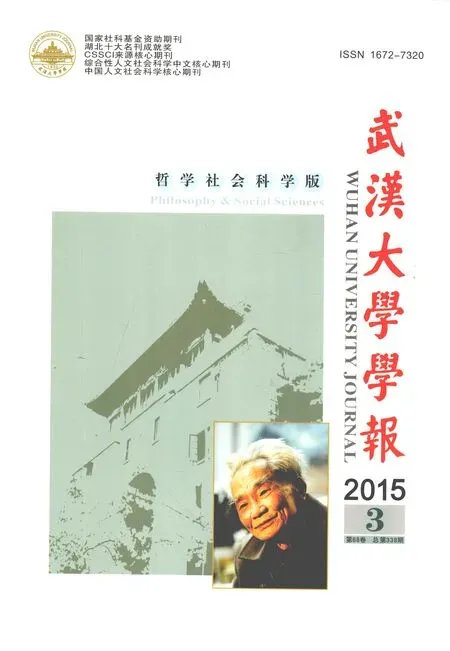微观权力:后现代语境中权力的生物学解读
2015-03-20胡国栋
胡国栋

微观权力:后现代语境中权力的生物学解读
胡国栋
摘要:权力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现代主义哲学赋予权力以工具性、经济性和技术性色彩,使之成为具有统治性和专有性的稀缺资源。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则发展出一种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微观权力,这种权力形态具有关系性、流动性、分散性及生产性特征,它与具体的、体验性的“地方性知识”相关并以“规训”的形式来运行。微观权力能够通过“规训”机制生产出自愿服从的温顺身体,以对个体进行更为精巧而委婉的统治;同时也可以通过伦理发展出一种自我技术,增加个体在组织中的自主和自控能力。通过对现代权力观的解构,福柯试图将权力纳入“自由-自治”这一后现代主题之中。组织秩序事实上由两种权力共同塑造,权力的不同观察视角及运用机制往往带来不同的组织结果。
关键词:微观权力; 后现代主义; 地方性知识; 生物学
权力作为政治学、管理学与社会学中的核心术语是建构一切人类秩序的基础,正如罗素所指出,“权力作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如同能量之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伯恩斯,2006:2)。权力是影响人类组织行为的一种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哲学及相关学科建构的基础性概念,后现代主义者解构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其权力基础进行批判和重建。对于这种学术旨趣,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米歇尔·福柯最为彻底。福柯等人以考古和解剖的方法对权力的来源及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和提炼了现代性权力的压迫性、统治性特征,进而针对这种以强制性控制为中心的宏观权力,福柯等人发展出一种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微观权力,开启了权力研究与观察的一种独特视角并揭示了权力在组织的政治生活与管理活动中可能具有的积极解放功能。
一、 压迫系统:现代管理中的统治性权力及其运行机理
一般认为,管理是一种以自己意愿去规范别人行为或利用他人达成自己目标的强制性活动,管理似乎与“强迫”、“被动”、“约束”、“控制”等词汇之间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克洛克等考察了管理与奴隶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是奴隶制兴起的直接结果,奴隶被认为是一件要去操纵的东西、一件要去使用的工具、一头要被束缚的牛和一位要被惩罚的孩子。这种态度或观念虽然有所收敛,但依然还存在于现代许多组织之中,目前的管理系统仍旧被视为强迫性工作与局部奴役的场所(Cloke & Goldsmith,2002:46)。管理产生之初与奴隶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管理至今具有诸多负面形象的历史根源,那么管理在现代社会依然同强迫、奴役相关联的逻辑基础又是什么呢?管理作为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活动必然要通过某种媒介来实现,这种媒介便是权力。克罗齐耶指出,权力在现代社会往往被视为一种禁忌,在世人看来,权力禁忌等同于暧昧可疑的交易,权力关系浸润着漫无止境的盘剥(Crozier,1973:37)。很明显,管理的负面形象源于权力禁忌,而权力被视为禁忌则源于人们将现代性权力的运用等同于“权力的滥用”。那么,权力作为一种支配他人行为的中性力量为何易于被滥用而成为一种禁忌呢?对此,需要考察现代性权力的基本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具有两种基本模式,分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式(economic model)和韦伯的法权模式(juridical model)。前者认为权力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服务;后者将权力视为某种可以通过契约占有和转让的商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规制之下,通过天赋人权契约可以产生国家权力的代理和使用,通过维护效率、秩序的契约可以产生官僚制组织的权力。福柯进而认为这两者都没有说明权力的真正本质,都属于“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福柯,1997:223),即无论哪种模式,都最终将权力归结到经济,其本质是权力的经济还原论。这种权力模式中的经济本质在布劳那里被更精准地称为不公平的交换关系。布劳认为,当某人为得到实现目标所必须的服务而越来越多地开始依赖他者时,不平等交换就会发生,如果他缺乏资源来报答别人的服务而又不愿意放弃这种服务并且无法从其它关系中获得类似服务时,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屈从于别人的意愿,从而以接受别人的控制的方式来报答别人提供的服务,同样,取得这种控制权则是提供他特需服务之人的动机之一。正是在这种不对称因素的交换过程中产生了权力关系(Blau,1964:124)。在福柯与布劳的分析中,现代权力的两种模式都可以归结为由工具理性塑造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ico-ecnomic paradigm),这种权力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成为现代主义者理解权力现象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
“技术-经济范式”的权力模式从根本上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观的制度设计,它在社会运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经由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运动而确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理性精神率先成为一种激烈的政治诉求并率先改造了欧洲的政治制度。人们依照自身的理性而非中世纪的神性来重建政治生活,欧美各国先后通过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天赋人权、法制观念、契约精神、三权分立等启蒙理性设想的现代政治文明成为国家制度的核心部分。政治生活的理性化为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提供制度支撑和体制保证,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巩固为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运动铺平了道路。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从英格兰中部兴起并迅速向欧美大陆蔓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理性化权力运作的逻辑从思想领域,经由政治领域逐步向经济生活推衍,最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776年,处于工业化高潮中的英国出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这是当时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并且为其后工业革命的进展与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富论》提出了理性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并依据无数个体利益活动的最大化自动导致社会利益实现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法则,确立劳动分工、经济自由、有限政府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基本原则。工业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升华以及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同时为“技术-经济范式”权力的发展及其向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以及最终取得权力分析与运作的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与逻辑基础。
“技术-经济范式”中的权力是不平等交换和非对称控制关系基础之上的统治性权力,它将现代管理构造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强制性控制或约束的压迫系统。统治性权力的运行是通过结构化来实现的,即嵌入在某种宏观的结构或体系之中并固定化为一种合法秩序。其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式嵌入在阶级关系结构之中,韦伯的法权模式嵌入在官僚制等级体系之中。这种结构化的权力在组织管理中的逻辑结果就是,管理的一切出发点是站在掌握资本或知识的具有优势地位的资方或管理者立场,而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立场,更没有顾及人在组织生活中的如何实现其本质这一问题。因而,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组织产生的大部分权力没有被用来服务于大众支持的目标,而是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名义事实上被用来保存阶级特权、延续剥削系统以及获取狭隘利益(Scott,1998:76)。如妇女、少数民族人员及缺乏技艺的员工被阻止进入权力高层或被有意排除在平等权益和保护之外,而不得不接受底薪和安全程度较低的职位。
在奴隶制时代,古人由于缺乏资本概念,个体在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主要被视为一种占有物而非一种独立的资源,彼时对人之行为的控制主要基于赤裸裸的暴力和具有普遍主义的绝对性伦理,由此构筑的宏观权力对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控制与支配过程残酷而野蛮。近现代以来,由于资本文明的发展,人在组织中逐渐被视为一种资源,并且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是为获得利润或绩效而做出的最重要投入之一,人的尊严和地位不断提升,对人力资源的控制也不像古代那样明显、直接和残暴,而是以一种更为文明和科学的形式在管理制度与规则中嵌入了一种合法性知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曾经使强有力的劳动工会对资方的控制与压迫可以形成一股制约力量,但标志现代管理开端的泰罗制对管理的精巧设计则事实上削弱了熟练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追求“设计和控制工作过程以保证效率最大化”的过程中,“科学管理使集体谈判和工联主义成为不必要的事情”(Cloke & Goldsmith,2002:51),通过计划与执行分离,科学管理取代了外部的管理权威和雇员自我管理的训练,将控制权完全转让给管理者,这样经验管理时期基层操作人员(工匠)的技术能力及自我控制空间被清除,工人只需要机械执行被分解为精确定时并具一定次序的任务元素。可见,以科学标榜的现代管理事实上仍然是以统治性权力构造一种压迫与剥削体系,只不过使控制和压迫变得更加文明、精细和含蓄了。
二、 后现代语境中的微观权力及其生物学特征
权力分析是米歇尔·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传统的权力理论都从宏观角度对社会中的权力现象进行总体性的描述,试图找出普遍性的解释原则,其目的是通过宏观权力建构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通过强制途径迫使权力客体做出权力主体的期望性行为,否则便会遭到报复性打击或被社会边缘化为异端与他者。福柯认为,这种对权力进行经济主义分析的经典模式构筑的是一种统治性的宏观权力,并没有真正揭示权力的本质。为此,福柯主张对权力进行非经济解读。福柯对权力的非经济研究并没有给出一种规范的定义或一贯而明确的界定,而是从各种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阐释其发展的新权力观的相关意蕴。福柯的这种权力研究方式,与他所持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排斥关于现代主义关于社会普遍性与一致性的观念,主张透视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及片段性。为反对启蒙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构筑的宏观叙事模式,福柯从发生学*发生学方法最初主要用于探讨生物是发生发育及演化问题,如哈维1651年发表的《论动物的发生》中“万物皆来自卵”观点即由此方法得出,后被应用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经由瑞士哲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被译介入中国。福柯对权力的研究之所以是发生学的,在于他考察权力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如何发生和演化。详见楼培敏:《发生学方法》,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的视角发展出一种微观视域中的新权力观。为与现代经典权力模式相区分,我们将福柯的非经济权力模式称为微观权力。
与具有普遍性、结构性与压迫性的经典权力模式不同,微观权力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一,权力微观而无形,广泛分布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权力的普遍存在并不是因为它包罗万象,而是因为它来自于所有的地方”(福柯,1988:75)。福柯认为权力无需授权和合法化,它无处不在,存在于任何具有不同势能之间的两个点之间,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与类似于人体骨架的现代结构化权力相比,这种渗透于毛细血管中的微观权力类似于一种肉眼观察不到的细胞。其二,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有机体。福柯指出,微观权力“每时每刻地产生,或者说在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上产生”(福柯,1988:102)。此外,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可以生产现实,塑造或建构它的对象(福柯,2003:76)。也就是说权力不是某一集团对另一集团实施控制的消极存在物,而是一种在行动中能够主动生产和塑造个体的有机体。其三,权力具有关系性与流动性,不能够被占有或转让。福柯认为微观权力是关系性与策略性的,而非一种类似商品的可占有物,如他所指出,“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福柯,2003:28)。微观权力之所有不能被占有或转让,是因为它具有流动性和无中心性,“各种力量是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的场(field)”,“除了不断地向别处扩散,快感和权力绝不可能在某个权力中心点、某个循环节点或联接点、某个场址中……凝结或驻留”(福柯,1988:49)。其四,权力没有主体,因而是分散的、多元的。与其“主体离心化”的主张相对应,福柯反复强调权力分析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如何发生和运用,从而淡化权力的行使主体问题。福柯认为,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是权力发生和运行中的一个点,而并非能够对权力进行绝对操纵的权力主体,因为他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载体,同时也是权力生产或塑造的对象。权力主体的解构事实上使每一个相关个体都成为权力的主体,从而将聚结或固定到某一主体的宏观权力化为由许多个体行使的分散化与多元化的微观权力。
微观权力的关系性、流动性、分散性及生产性等特征凸显了权力的生物学意蕴。与现代权力模式构造的类似于没有血肉的“骨骼”或“机器”这种庞然大物不同,福柯的微观权力是一种运动着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细胞”,是一种微型有机体。福柯本人将这种权力分析称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或“权力的解剖学”(福柯,2003:28),而在自然科学中,微观物理现象可以划归生物学领域,因为微观物理学事件,不是由物理学的统计规律决定,而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福柯的微观权力事实上开辟了权力研究的生物学空间或视角,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非经济的权力分析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权力研究的思路。此外,对权力的生物学解读意味着权力具有不同于压迫与控制系统这种纯粹物理学范式中的运行机制,它将权力还原到了人的生物本能,契合了马尔库塞等后现代主义者通过恢复人的生物本能或欲望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目标(马尔库塞,2001:9)。需要明确的是,微观权力尽管更能揭示权力的本质,但它并不是与宏观权力相对应的另一种存在物,而是观察权力的一种新视角或者权力存在的另一种形态。也就是说,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考察的是同一种社会现象,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及目的不同。
三、 “规训”:地方性知识与微观权力的运行机理
为反对现代权力的占有性与中心性主体对他者的压迫,福柯在消解权力的主体时强调权力的运作远比“权力由谁实施”这一问题重要,为此福柯权力理论中的重点部分放在了权力的运作即其运行机制方面。微观权力的发生及其运行与知识密切相关,这便构成福柯理论中极富后现代主义特色的“权力-知识”观。在审视人口管理技术中,福柯提出了“管制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即“管辖、政治”(government)与“合理性”(rationality)两词的组合(Gordon & Miller,1991:73)。福柯用这一术语来表达广泛存在于家庭、医院、学校、教堂和国家等群体性组织管理之中的权力训练(power exercised)现象。其中,“管制”是一种塑造、指导与影响人的行为的活动,“合理性”是事物被管制之前必须被知晓的观念,“管制”天然地依赖于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可认知的才是可管制的。也就是说,权力与知识相互纠缠,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权力的实践生产知识,知识持续地产生权力效果,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实践,没有权力也没有知识”(Foucault,1980:52)。权力的产生及运行与知识的形成及积累具有共时性,两者紧密结合并拥有共同的作用范围。在微观领域,任何不对称的信息与关系都能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因为这种信息与关系本身是一种知识。在现实中,具体的不确定性因素事实上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如果不确定性存在,那么能够控制不确定性的行动者,即使仅能对不确定性部分地加以控制,即可利用不确定性,将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那些依存于不确定性的人们。就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从行动者的观点看,不确定性意味着权力”(费埃德伯格,2005:265)。不确定性能够产生权力就在于它本身是一种不对称性知识,也就是说,A相对于B如果拥有更多的不确定知识,就意味着A对B在适当的行动中能够产生权力以控制B的行为。
与微观权力的运行相关联的知识不再以宏大叙事模式来陈述,而更多的是具体的、体验性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反对知识的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任何知识都是在特定情境中由特定的主体来感受和据以行动的(Clifford,1983:17-18)。组织的现实往往是由这种地方性知识建构,员工具体行为也更多产生于由地方性知识生发的微观权力及其交互作用。福柯在论述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时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进行必要的封闭,即微观权力通过一种可以对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进行控制的纪律来运作。在组织中建立“单人密室”、“场所”或“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的,又具有使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封闭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标志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福柯,2003:167)。微观权力就是地方性知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互动的过程,而纪律则控制了这些微观权力的流向和产出。这种在纪律约束下的微观权力运行轨道便被福柯称为“规训”(discipline)。
“规训”即“规范化训练”,具有纪律、训练、校正、教育、训诫等多重内涵。规训是对人的姿势、身体和行为进行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其目的是制造出按照某特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而温顺的肉体。微观权力的规训与宏观权力的强迫式统治不同,它不是通过对财力、暴力、意识形态等强迫性的控制来运作,而是通过规范化的监视、裁决和检查来运行。福柯以边沁设计的全景敝视的“圆形监狱”来形象地说明微观权力的规训模式。圆形监狱是圆环一样的全景敝视建筑,中央有座开启很大窗子的塔楼,塔楼四周、圆环内侧的外围建筑被划分成许多间囚室,每间囚室都有面向塔楼的窗户,塔楼通过窗户可以监视囚室内部的活动,而囚室内的犯人却看不到监视者,但却知道自己时刻处于监视之中,从而依照监狱的规范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圆形监狱中的注视性控制,被福柯形象地称为“权力的眼睛”,它使外在的强迫通过成为一种自我看管,其高雅性在于,它无需通过昂贵而粗暴的人身占有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规训使“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习惯性的动作”(福柯,2003:153)。
具体来说,规训有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三种途径,它们均通过对知识的分类、编码和矫正来发挥作用。监视是一种对个体持续进行的、分层的、切实的监督技术,圆形监狱就是监视的一种理想形式。在圆形监狱中,不同的角色被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中,按照一定的规范或标准被监视和训练并以此进行自我看管。如果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大的圆形监狱,那么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监视之中按照自己的角色被规训为一个个温顺的身体。规范化裁决就是用具体的纪律、规则或条例以对被规训的对象进行约束和裁决,它通过分类、编码等程序标识出每个个体的规范化角色,并通过裁决来比较并标示其差别,通过惩罚来矫正和训练出现偏差的行为,以此使个体按照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检查是一种综合性的规训技术,它将标准的确立和强化、惩戒力量的部署及权力运作的仪式等结合起来。检查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以此人们可以区分、判断和矫正个人的行为,这便是检查在权力运作的各种机制中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福柯,2003:153)。学校里的考试、医院里的巡诊、军队里的检阅,企业里的绩效考核都是检查的常见形式。
四、 控制与解放:微观权力的两种政治功能
从对微观权力运作的规训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相似的统治功能,只不过它提供了实现权力之控制功能的一种委婉而精细化的途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权力不可能彻底与控制摆脱关联。微观权力对人的身体的规范化训练,通过塑造人的灵魂和意识来支配其行为,其结果是增强了权力的控制效应。但微观权力对控制对象的规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看管,它将结构化的宏观权力的压迫功能尽量隐性化,使控制对象产生理性的顺从,在减少控制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控制的效应,这就提供了一种控制的非对抗形式。控制的非对抗实现形式的出现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它毕竟消除了古代社会对人的身体进行直接的暴力惩戒的恶果,使赤裸裸的剥削与压迫关系转化为一种控制对象可以自觉接受的合理行为。除了转变权力之控制功能的实现形式之外,微观权力的另一层积极意义是它本身蕴含的解放功能,这在晚年福柯对伦理及自我技术的关注中得到了明显体现。福柯晚年将微观权力及其规训机制导入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分析,从而将其理论重心转移到对伦理问题的探讨。
福柯认为个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Foucault,1983:57)。也就是说,微观权力的规训机制既可能使个人在话语实践中受他人统治,也可以使个人通过伦理或自我建构创造自我的认同。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知识,在Peter Dews看来,“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结果”(Dews,1987:65-66)。基于对个体自由与非压抑性文明的向往,福柯晚年将微观权力的非对抗性压迫功能转向与后现代伦理息息相关的自我技术,从而使微观权力具有了自由与解放的政治功能。福柯将自我技术定义为,“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Foucault,1988:16-69)的实践。福柯赞成个体通过这种自我技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自主的、自我控制的、乐意享有别具一格的新经验、快感和欲望的存在(Kellner & Best,1991:173)。自我技术可以减少组织用以制度、规则的建设与维护成本,更关键的是它可以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一种自由的体验和某种自我实现的愉悦。
自我技术在实践中表现为不受外在权威主义和基础主义约束并具有审美化倾向的伦理。在福柯看来,伦理学就是个体反抗各种统治与压迫性力量的斗争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伦理成为“自由所采取的审慎的形式”(Foucault,1988:4)。如果组织中的员工通过自我设定的伦理规范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可能使其所从事的工作成为一件自我创造的工艺品,而不再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在雇主的监控下被迫地做不情愿的事情,那么组织中的管理系统就会变成一种令人振奋和富有意义的艺术实践而不再是冷漠的科学、技术体系。但是,从微观权力视角出发的伦理不应是具有普遍主义、永恒性与绝对性的道德律条,而是每个个体使自己的生活过得优雅、美好与体面的责任,是一种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伦理。这种导向自我技术的后现代伦理将个体导向如何塑造自身所需要的生活方式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因而,后现代主义伦理蕴含着一种自组织机制,它有可能将宏观权力统治之下的压迫系统转化为一种自我约束的自治系统。
总之,微观权力能够通过规训机制生产出自愿服从的温顺身体,以对个体进行更为精巧而委婉的统治,以一种非对抗性的形式增强控制的效应;同时,微观权力也可以通过伦理发展出一种自我技术,增长个体在组织中的自主能力,从而蕴含着积极的解放功能。也就是说,微观权力能够将控制与自由、压迫与解放两种现代主义中的对立性价值融合在一起。这种双重政治功能,正是微观权力在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巨大潜力所在。微观权力在增强管理控制的幅度和深度的同时,也在消解管理本身的外力强制色彩,使之以一种更为柔和与文明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在权力之于人类组织的意义方面,微观权力使权力真正回归到一种中性力量本质上来,其作用的发挥不再依赖于人们对权力位置的占有和贪恋,而更多地在于人们如何拥有运作权力的知识和机会以及如何使用它。
五、 结语:两种权力共同塑造的组织现实
微观权力服务于后现代主义者反抗现代压迫、重建人之自由生活的基本主张,它对于管理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拓展了权力在组织中的解放功能,弥补了权力在控制这单一维度发展的不足,改观了权力作为一种禁忌的消极面貌。微观权力对传统的经典权力模式有很强的补充作用,拓宽了权力研究的视野,为组织与管理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分析模式。它颠覆了权力一经拥有便可解决一切难题的传统权力观,将权力的发生与运作深入到组织的微观领域,拨开了权力运行的迷雾。福柯认为权力和理性嵌刻于各种话语和制度性场址中,因而支持一种多元的、片段性的和不确定的,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权力分析模式。这对于我们认知和观察组织与管理中的权力实践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运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关注组织中员工行动的具体领域,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整体性、一致性的行动场所。
需要明确的是,微观权力毕竟对权力做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在高度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现代社会,马克思与韦伯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依然在现实的权力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少数人运用技术的或经济的力量来统治其他弱势群体的现象是组织生活中无法彻底改变的现实。此外,权力的主体不可能彻底消解,组织中权力的运作实践必然要解决其由谁来掌握权力这一问题。在反抗现有权力模式构筑的普遍主义与权威主义对他者的压迫时,福柯消解权力主体的主张无可非议,但悬置权力由谁控制这一根本问题则明显与现代权力运作的现实不符。尽管这样,福柯的微观权力毕竟开启了权力分析的一种新的模式,它代表着权力在构建未来的组织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事实上,现实的组织生活由两种权力共同塑造,员工的行为不仅基于组织的宏观命令与控制体系,同时也基于不确定性知识在微观领域中的协商性交换,因此组织行为是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交互作用的博弈行为。微观权力观启发我们在审视组织管理问题时,不能将员工视为一种仅仅对制度与规则被动反应的消极力量,必须正视各种利益群体在建构自己意愿时的积极作用,关注组织中存在的各种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而不应将组织与所有员工的行为假想为铁板一块式的可控整体。
参考文献:
[1]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2006).领导论.常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5).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米歇尔·福柯(1988).性史.黄勇民、俞宝发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4]米歇尔·福柯(199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马尔库塞(2001).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P.M.Blau(1964).ExchangeandPowerinSocialLife.New York:Wiley.
[8]Kenneth Cloke & Joan Goldsmith(2002).TheEndofManagementandtheRiseofOrganizationalDemocracy.New York:John Willy & Sons,Inc.
[9]Geertz Clifford(1983).LocalKnowledge-FurtherEssaysinInterpretive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s Books.
[10] Michel Crozier(1973).TheStalledSociety.New York:Viking Press.
[11] Peter Dews(1987).LogicsofDisintegration.London:Verso.
[12] Michel Foucault(1980).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byMichelFoucault,1972-77.Brighton,England:Harvester.
[13] Michel Foucault(1983).Afterword:the Subject and Power.in H.Dreyfus & P.Rabinow(eds.).MichelFoucault:BeyondStructuralismandHermeneutic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4] Michel Foucault(1988).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L.Martin,H.Gutman & P.H.Hutton(eds.).TechnologiesoftheSelf.London:Tavistock.
[15] Michel Foucault(1998).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in James Bernauer & David Rasmussen(eds.).TheFinalFoucault.Cambridge,Mass:MIT Press.
[16] Burchell C.Gordon & P.Miller(1991).TheFoucaultEffect:StudiesinGovernmentality.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
[17] D.Kellner & S.Best(1991).PostmodernTheory:CriticalInterrogations.New York:Macmillan.
[18] Richard Scott(1998).Organizations:Rational,NaturalandOpenSystems.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作者地址: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Email:hgdong2010@126.com。
■责任编辑:叶娟丽
◆
Micro-power:The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ower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HuGuodo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Power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moder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In the modernism philosophy,with instrumental,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power is dominant and exclusive in the scarce resources.Michel Foucault,who is one the leaders of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developed a kind of micro-power with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which closely linked local knowledge,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quidity and dispersion,and which operation mechanism is called “discipline” by Michel Foucault.Under this mechanism,micro-power can produce obedient and docile body,which is a more exquisite and hidden control to the individual.At the same time,it also developed a self technology through the ethics,which increases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of individual in the organization.Through deconstructing the modernism power,Foucault tried to take the power into postmodern theme of free and autonomy.
Key words:micro-power; postmodernism; local knowledge;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14FGL002)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