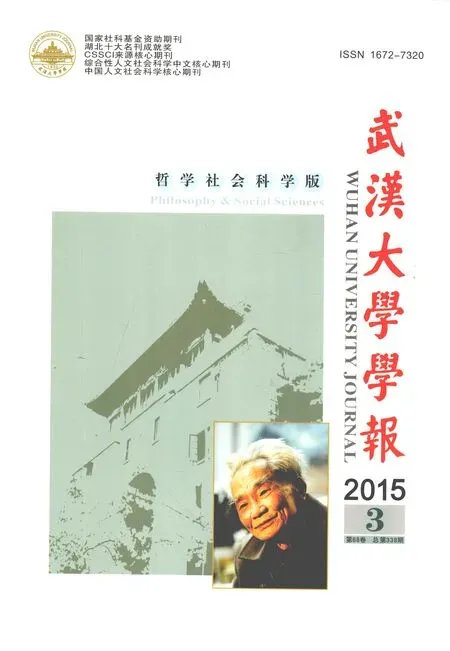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发展与论争
2015-03-20邢瑞磊
邢瑞磊

理解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发展与论争
邢瑞磊
摘要:理性选择理论以韦伯的“工具理性”和“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为起点,考察政治领域的各种政治行为,构成了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主流理论。然而,由于过于追求理论的简洁性,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诸如制度和文化等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从而陷入到理论驱动而非问题驱动的问题之中。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和争论的过程中,随着“理性”概念内涵的不断扩充,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可以把文化和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构成了一种以个体工具理性为基础,同时亦能考察个体“价值理性行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如今,在争论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还为学界推动人类行为与制度研究的整合性问题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 简单理性; 充分理性; 价值合理性
理性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基础,尝试对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解释。具体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实证观察不断修正其假设,扩展理论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在政治学领域得以广泛应用。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把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方法上升到了新的境界,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可以说,理性选择理论构成了政治科学研究的一种主流的范式,其理论建构逻辑和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改变了政治学的面貌,重构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尝试从理性选择的理论基石、理性概念的演化以及争论三个角度梳理其发展脉络,希望有助于加深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
一、 理性选择的理论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政治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逐渐走上了现代政治理论构建的阶段。由于此时政治理论趋向于严格地与政治哲学或道德评判分离,期望完全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故称为经验理论。对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与过去完全背离的趋势,伊斯顿称之为政治学的理论革命(Easton,1966:2)。当然,政治学理论革命和经验理论发展并非完全是政治学家的贡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此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一些经济学和数学家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早在两百多年前,法国数学家让-查理斯·波达和马奎斯·孔多塞就开创了投票规则问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理性选择研究的滥觞。此外,在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及托马斯·霍布斯的论著之中,都曾或多或少涉及到理性选择理论。1929年,哈罗德·霍特林提出了著名的霍特林模型,为安东尼·唐斯阐明空间竞争理论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伴随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布莱克、布坎南和阿罗的数篇重量级文章相继发表,理性选择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在研究者视野之内(Mueller,1997:3)。1951年,阿罗运用经济学的模型,指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限制,引发了学界对民主社会中投票规则与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兴趣。在随后的40多年的时间里,沿着阿罗论证的逻辑,社会选择理论中又相继证出了许多“不可能定理”或“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与其他悖论的数理论证与综述可参见:Prasantak K.Pattanaik,“Some Paradoxes of Preference Aggregation”,in Dennis C.Mueller(eds.),PerspectivesonPublicChoice:aHandbook.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1-225.。这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受到了1957年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和1965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路径”的确立,填补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空缺,也扩大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与内容。
(一) 立法者、选民与政党行为
1957年唐斯把霍特林的空间竞争模型运用在分析政党竞争问题,把地理距离转化为意识形态空间,解释并预测出了政党为获得最多的选票支持所采用的定位策略。唐斯把选举比拟为经济学里的交换市场。选民与政党都希望通过这个市场,交换各自所需。对唐斯而言,每个政党的竞选纲领相当于赢得大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政党的任务清单。同时,唐斯运用经济学逻辑和空间模型分析了两党制下的投票行为,认为当两党在赢得选民支持的努力中,沿着意识形态的空间抢占有利定位时,两党的纲领会向“中间选民”的意识形态位置趋近。唐斯的论证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政党政治研究,改变了政治科学家对待大众舆论与政治参与的方式。唐斯对政党竞争、大规模选举、理性的忽视和投票参与的解释,重塑了美国政治研究。所以缪勒赞誉《民主的经济理论》对从事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政治科学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格林、沙皮罗,2004;10)。
1962年,政治学家威廉·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付梓出版,推动了早期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政治联盟理论》一书可能是政治学者为理性选择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在这本著作中,赖克结合了经济学理论和以数理为基础的博弈论,并将之成功运用在政治决策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最小获胜联盟法则。更重要的是,赖克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的科学化,为之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赖克认为政治学最大的贡献应该在于可以把政治行为分析的结果普遍化,经由普遍化,研究者具备预测的能力,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是政治学实现科学化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 国家形成、政治动员与经济发展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把“搭便车”的概念引入到了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探究了集体行为及其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推翻了政治学中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共同假设,即,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奥尔森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却往往会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有害的结果。在奥尔森看来,个人是否决定搭便车的行为,取决于社会压力和个人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团体规模、重复互动、有选择的激励,迫使人们把策略性互动带进集体行动。这样以来,把博弈论引入政治分析就成为了必要之举,推动了博弈论方法与理性选择分析的融合,而这两个分析工具的结合,又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整体繁荣。
此类的理性选择研究旨在探索现代国家兴起的理论解释,探讨民主政体与民主制度的性质及内部的决策过程。显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制度的特征与局限,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明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决策产出,从而确保政策制定的效率与透明;评估乃至预测选民、政党和利益集团等行为体的行为,从而提高民主决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而这都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同时,理性选择学者也从最初对政党和立法的关注,转向探索与政治、经济发展与转型相关一般性问题,呈现出了一种经济学转向的发展趋势(Levi,2000:822-844)。
总之,从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的应用看,理性选择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或方法,旨在提供分析与解释问题的概念框架、体系或模型,也可成为政治理论发展的动力。其二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理论流派,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借用演绎模型、博弈论与定量研究等具体方法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以“理性”行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
二、 理性概念的演化与理性选择理论
长期以来,“理性”一直都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旨在澄清且充满争议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理性概念同样是构成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在不断阐释和解释“理性”,并依据不同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基础大致划分出了理性学派与反思学派两种相对的知识体系。“理性”是构成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基石,也是该理论赖以成名的最为显著的特点。目前,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理性”已经发展出了强调行为体人性的“简单”理性(thin rationality)和强调社会情境的“充分”理性(thick rationality)两种类型的理性观,分别对政治学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利希巴赫,2003:30-40)。
一般而论,“简单”理性通常与行为体的人性与目标相关,是一种界定相当宽泛的概念。威廉·赖克认为凡是有目标的行为都可称为理性行为,其主要假设是行为体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且可以对目标列出优先顺序。不过,赖克也承认,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也可以获得快乐,在特殊情况下,追求目标的过程本身也算是一种目标(Riker,1995:22-44)。显然,围绕“简单”理性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属于理性行为体理论的范畴,是一种一般性的分析路径(Monroe & Downs,1991;1-23)。这种分析路径强调理性的个体不断追求自身目标,并在具备充分信息、明确偏好排序和遵守自利与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前提下,在竞争性方案之间做出最终的决策。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会借助辅助性工具(逻辑演绎、数学和博弈论方法),在“理性经济人”行动假设基础上,推演具体的理性行为模型,解释或预测理性个体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进而演绎出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和整体图景。以“简单”理性或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与不足都非常突出: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把政治学理论建构逻辑提升至一个新境界,研究者从“人皆是理性”的基本命题出发,尝试为政治学建立解释政治行为的演绎理论,具有简明和预测性的特点。另一方面,鉴于政治学的复杂性,建立演绎理论是极为困难的。理性选择理论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作为演绎基础的“公理”,因为基本命题“人皆是理性的”不能称为一种“公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由其推理出的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除此之外,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尽管已经初具演绎理论的雏形,却大多只能解释静态的政治现象,而无法有效解释政治变迁现象,因为理性选择理论家会先假设行为体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推测行为体的行为,并预测结果,而政治变迁必然会导致行为体目标的变化。对于这一点,理论研究者通常会重新设定目标,直至设定的目标能够说明行为选择与结果为止。当然,由于目标不止一个,而且彼此之间可能对行为的要求不一,这就成为了理性选择分析的瓶颈,也是该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最多的一个方面。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一部分理性选择理论家开始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并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之内,从而在政治科学内部形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政治过程是理性经济人一系列交易和博弈过程。同时,他们也吸收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强调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对制度运作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承认制度对理性个体的约束和激励,从而把政治过程视为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设计某些制度规则(何俊志,2002:28)。也就是说,早期理性选择理论家主要研究在某些制度约束下理性行为体在政治领域的决策和行动;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开始关注政治制度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如此构建的问题。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传统的理性选择学者把个体选民、利益集团成员、政治家和官僚看成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影响和促进了政治学的发展。然而,这些早期研究却难以在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而且许多个人决策与行动都是与理性选择的假设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理性选择政治学家转向关注约束个人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因素,这一发展对重新发现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乔治·提斯比利斯(George Tsebilis)认为理性选择在解释行为体行为方面有着独特的能力,因为用于评估个体选择和效用最大化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内嵌”在政治与社会的制度语境之中,这意味着,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制度设置的限制,为理性选择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Tsebilis,1990:10)。理查德·菲奥克(Richard Feiock)也率先分析了形塑和鼓励个体理性行为的情境性因素,通过地方治理制度的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把有限理性与理性选择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构成了所谓的“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Feiock,2007:47-63)。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强调的那样,正确理解理性概念的进步对理解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奥斯特罗姆认为一些理性选择批评者对理性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把“简单”理性模型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理性行为理论混为了一谈(Ostrom,2006:3-12),忽视了理性概念的演化,误读了理性选择理论。
从逻辑上看,研究者选择从两个层次论证社会场景对理性行为体行为影响因素。一方面是从微观角度深入挖掘行为体的内在属性(如,文化、规范与偏好);另一方面则可从宏观角度探讨外部制约因素(制度、结构与限制条件),扩充了理性的内涵,建构了一种“充分”理性观。也就是说,“充分”理性强调行为体的行为是“内嵌”在社会场景之内的,对行为体行为的分析必须考虑相关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界定下,除有效率追求目标的理性行为外,“充分”理性不但增加了行为体的信仰、心理需求、文化价值,还把经济、政治与社会情境的制约因素考虑在内(Friedman,1996:1-4)。在“充分”理性或“社会场景”理性的条件下,研究者就可以首先分析界定行为体目标、信念与选择的具体历史机会结构,再对行为体理性行为的原因与结果进行解释,从而,把文化与结构带入到理性选择研究的范围之内,构成了以理性选择为基石的理性主义、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三大主流研究范式(利希巴赫、朱克曼,2008:6),确立了三大主流范式融合的基础。
三、 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与争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理性选择对政治科学的价值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格林与沙皮罗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一书中对理性选择理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在该书中,格林与沙皮罗对理性的个体能否作为政治现象的最终解释持怀疑态度,重点指出了理性选择在经验研究方面的不足和方法论上的缺失。他们挑选了投票决策、集体行为、立法政策与政党竞争等领域,依次展开批判,这些都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大量运用了理性选择的研究领域。
格林与沙皮罗认为,理性选择的理论“臆测”大多无法经过经验的检测。也就是说,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均衡结果,通常是无法测量与观察的。另一方面,理性选择者可以选择性寻找可以佐证其理论模型的证据,刻意忽略了那些与其推论结果不符的实证结果,或藉由逆向推演,修正之前的论述来规避这些实证结果,进而宣称理性选择可以解释这些现象。这使得理性选择宣称的经验性研究变成了“理论驱动”而非“问题驱动”,而且其研究设计大多是为了挽救或辩护理性选择的某些变异,而不是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格林、沙皮罗,2004:8)。
针对格林与沙皮罗的批评,理性选择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理性选择的误解,只选择了特定的议题与特定的学者,并未涵盖理性选择所有的范畴,因而他们的批评是片面的(Cox,1999:147-16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辩护者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理性选择理论的缺陷。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研究在经验研究方面的缺失,让理性选择理论的辩护者难以释怀。例如,公共选择的代表人物丹尼斯·缪勒就承认了格林和沙皮罗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实际上,缪勒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批评公共选择的。在他看来,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在规范理论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是失败的。公共选择理论家过于沉迷理性选择模型的精致与严谨,而牺牲了理论对于现实行为的解释能力。当然,缪勒也辩称这些问题都是建模者和研究者自身的问题,而非理性选择模型或所用方法论的缘故(Mueller,1997:15)。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也坚持认为格林与沙皮罗误解了许多以理性选择研究方法为出发点的美国政治经验研究,指责他们用狭隘的角度看待经验研究,对科学方法的要求有些过时和理想化。菲奥里纳抱怨称,如果都按照他们的标准看待政治学,那么就没人可以对政治学的经验研究做出实质性贡献,更遑论让政治学成为一项科学研究(Fiorina,1996:85-94)。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理性选择理论本身争论的密集度有所下降。然而,受到美国政治学界中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再次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改革运动”代表着美国政治学的改造要求,其所借用的俄文名称反映了此次运动的核心理想:致力于重建美国政治学,以及将新观念、新参与者引入政治过程(Monroe,2005:3-4)。在一些学者看来,要实现这两个理想,首先在于大力整顿“操弄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的美国政治研究现状,反对以理性选择理论、形式模型建构以及量化研究等在内的“硬科学”研究。改革主义者主要批评理性选择利用形式模型和定量分析导向的研究方式,湮没了有关政府、政治与政策等相关的真实知识,甚至“讥讽”威廉·赖克绑架了政治学:“威廉·赖克曾言政治学是一艘正在下沉的破船,理性选择是唯一能把政治学拖回港口的拖船。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赖克的门徒们如海盗一样绑架了政治科学,将之带向更为荒凉的孤岛,他们的海盗行为注定要走向失败。”(Kasza,2001:597-599)
当然,由于此次改革运动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政治学会的组织体系、学术期刊的编辑方针和研究生课程设置等议题的改造要求,对数理证法与实质内涵之间的关系并未展开深入探讨。然而,作为数理证法和形式模型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在这次运动中引发了广泛争论,尽管这次争论是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大辩论背景下完成的。
四、 小结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性概念为基石、解释与预测理性行为体行为及结果的一种理论路径或方法。客观而言,理性选择理论的广泛应用在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由于理性选择理论旨在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方法,旨在对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简明的解释,这个特点一方面改变了政治学建构理论的方法,从传统的规范思辨转至假设的逻辑演绎,并通过实证观察修正假设,扩大理论的解释范围,得以不断“外溢”至政治学的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大多秉承了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简单”理性观,多数的理性选择理论模型尽管具备了简明的特征,并初具演绎理论的雏形,却大多与现实差距较大且只能解释静态的政治现象而因此受到广泛批评。
为解决这个问题,理性选择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入手发展出更具弹性的“充分”理性,发展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充分”的理性选择理论。文化主义强调个人功利行为以理性人的政治文化与其他个体属性为前提,不同社会个体偏好排序由于政治文化差异而有所区别。政治文化的类型为研究者展开集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框架,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同时又足够具体,避免了概念延伸带来的问题(斯瓦德洛,2012:105)。结构主义则从宏观角度探讨了社会结构(规则、制度与限制条件)对理性行为的限制作用,认为理性行为体的选择是“内嵌”在制度语境内的,强调制度对理性个体的约束和激励,把政治过程视为一系列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困境的出路就在于设计某些制度规则。
当然,理性选择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过程中所凸显出的理论与方法,而政治学科学化本身亦争议不断,这使之成为政治学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种理论。然而,正如缪勒所言,有关人类行为与制度研究的专门知识,终将会整合为享有共同方法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跨学科的混合研究中,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理性选择毕竟为之提供了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贝茨(2009).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刘骥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格林、沙皮罗(2004).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徐湘林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2008).比较政治学:理性、文化与结构.储建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马骏(2003).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贡献、批评与前景.郭正林、肖滨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5]何俊志(2002).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5).
[6]布莱登·斯瓦德洛(2012).文化理论对政治学的贡献.贾彦艳译.国外理论动态,(5).
[7]Robert H.Bates(1989).BeyondtheMiracleoftheMarket:ThePoliticalEconomyofAgrarianDevelopmentinKeny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Gary Cox(1999).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a Reply to Green and Shapiro.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11).
[9]David Easton(1966).VarietiesofPoliticalThe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10] Richard Feiock(2007).Rational Choice and Regional Governance.JournalofUrbanAffairs,29.
[11] Morris Fiorina(1996).Rational Choice,Empirical Contributions,and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In Jeffrey Friedman(eds).TheRationalChoiceControversy:EconomicModelsofPoliticsReconsider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2] Jeffrey Friedman(1996).TheRationalChoiceControversy:EconomicModelsofPoliticsReconsider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3] Gregory Kasza(2001).Perestroika: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34.
[14] Margaret Levi(2000).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3.
[15] Mark Lichbach(2003).IsRationalChoiceTheoryAllofSocialScience?.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6] Kristen R.Monroe & Anthony Downs(1991).TheEconomicApproachtoPolitics:ACriticalReassessmentoftheTheoryofRationalAc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
[17] Kristen R.Monroe(2005).Perestroika!TheRaucousRebellioninPoliticalSci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8] Dennis Mueller(1997).PerspectivesonPublicChoice:aHandbook.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Elinor Ostrom(2006).Converting Threats into Opportunities.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39.
[20] William Riker(1962).TheTheoryofPolitical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1] William Riker(1995).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PoliticalPsychology,16(1).
[22] Kenneth Shepsle & Barry Weingast(1995).PositiveTheoriesofCongressionalInstitution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3] George Tsebilis(1990).NestedGames:RationalChoiceinComparative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地址:邢瑞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xingruilei@163.com。
■责任编辑:叶娟丽
◆
Understanding Rational Choice:History,Development and Debates
XingRuil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As one of crucial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rational choice,constituting a unique knowledge system,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man hypothesis”.It is the theory that accompanied fierce academic debates,contributes to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search.Nowadays,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 have been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thick rationality” in which the factor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can be included,not only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its earlier version,but some “value rational ac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rational choice theory.Nowadays,rational choice is a main paradigm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y,and more importantly,its evolution process has endowed the possibility to take up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with a unified methodological base.
Key words: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in rationality; thick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Z006)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