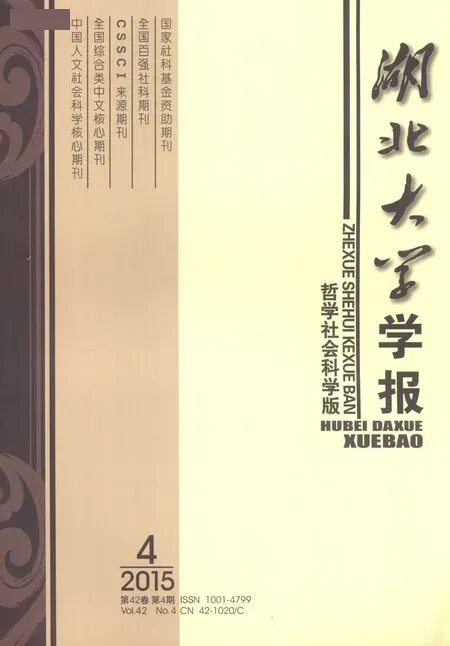民国湖北寺庙产权结构与庙产纠纷(1911—1931)
2015-03-20刘元
刘 元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庙产兴学是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进程中提出的,是清政府“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理念下的具体举措。具体来说,清政府鼓励地方利用庙产、庙地等民间公产,为各地自办乡村公立小学筹措资金。庙产兴学虽是教育改革的举措,但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层面。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政府顷刻瓦解,但清朝以来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得以延续,其中包括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民国以来,“庙产兴学”在清末的基础上,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推进,寺庙产权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围绕庙产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纠纷。本文拟以湖北地区为例,根据所收集的庙产资料,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寺庙产权变化:“化私为公”抑或“化公为公”
从清末开始,国家加强对庙产的控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逐渐将庙产变成政府所拥有的公产,否认原有产权结构中施主或寺僧的权利。
清朝时期,随着国家控制的逐步弱化,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寺庙的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通过对寺庙的管理,地方士绅也进一步宣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清末兴起及民国时期继续推进的“庙产兴学”却不断缩小甚至否认地方士绅对寺庙产权的控制和管理。
(一)否认寺庙组织对庙产的经营管理之权
传统社会中,寺庙财产如何处理和经营,在国家法律中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大清律例》中仅仅只是规定庙产不得转卖,在实际中,对庙产的控制就掌握在士绅或经士绅授权的僧人手中。对于寺庙田产、房屋,寺庙往往会用于经营,其中包括放租、开设旅店等等,以作寺庙收入。但是在庙产兴学过程中,士绅或僧人的自由经营之权被否认,这一过程从清末开始。
明清时期,汉口聚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商帮,很多商帮都会建有奉着各自神像的庵堂寺庙。这些庵堂寺庙既可以供往来商旅居住,又可以堆放货物,用处很多。汉口沙家巷后稷宫由窖业公所苏货帽帮所建,寺庙用于参拜外,其余寺庙房产用于租给同业会所或其他小贩所用,在清末庙产兴学过程中,寺庙产业被用于开办学堂。汉口绅商胡永兴等人一路上告,直至圣殿。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汉口胡永兴等联名禀称沙家巷后稷宫不便开办学堂,请查三月初八日之谕,将庙给还,得到的批示是:“近奉谕旨庙宇不得充公,亦只言庙宇产业不准提做兴学经费,庙宇房产不准充公改为学堂,并非谓庙宇不准借开学堂,何得以奉旨为藉口?然不愿租作学堂,亦不免强,惟学堂犹不肯租,则凡有租给住户以及各小贩等类,尤属不应。”[1]
寺庙产业既不能为办学所用,亦不允许士绅用于其他经营,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施主对寺庙的产权。
民国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民国初年,政府为了大量控制庙产,继续否认与庙产相关的各种习惯性权利。1912年,各省政府公报对寺庙财产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凡各庙主持僧道除由该教祖宗遗产或僧道自置私产准其自由处理外,对于官立或公立各庙产均只有管理权不得以个人名义擅自转移及影射抵押,暨已脱离宗教仍旧占据各情。其有曾经典当抵押者所立契约概作无效,仍勒令该僧道自行备价偿还,各僧道对于宗教一经脱离,其管理教产即由该管官厅为之处置,并饬嗣后如再有以上情事该管官厅即依法处理。庶财权不致混淆乱亦免各该僧道等有违法侵占之行为也。”[2]1~2
在这一份政府公报中,明确将僧道自置的产业之外的一切产业都视为公产,包括地方所捐献的产业均为公产,寺庙不仅从现在开始失去了对公产的管理权限,而且还采取追溯的方式,对以往寺庙的管理也进行了否认。
民国十一年(1922年),老河口南乡磨针井,有住持将寺庙产业私卖,知事贺作霖走马上任之后,称:“南乡磨针井前住持赵理章不守清规,败坏庙产,私拐本庙图章逃走,交与地痞,擅印红票,在庙滋饶……前任饶领颁图章,并出示保存古迹,不准觊觎私卖,及擅入庙内恣意骚扰在案。本知事下车伊始,访闻附近无赖之徒仍敢勾串土匪,不时至庙内扰害,寔属不法已极。除出示晓谕外,合行谕饬。为此谕抑该图縂,凡属庙内所有各财产,务宜认真保存以重古迹。所有以前盗出图章票据,一并作为无效,毋得任人妄生觊觎或藉端寻害。倘有对于此庙仍有不正当之行为者,抑即捆送来县以凭严办,切切特谕。”①2012年12月抄录于武当山。此晓喻以碑刻的形式刊刻于磨针井,不仅对现在寺庙财产进行了管理,而且之前的寺庙财产出售等行为,都被视为无效。
(二)庙产提成
将部分庙产提成用于建学校,在庙产兴学中是最常见的方法。全部没收庙产一般会受到多数士绅、民众和寺僧的激烈反对,而将部分庙产用于助学,承认寺庙对其他庙产的产权,相对来说,受到的反抗没有直接没收庙产激烈。
1911年,由抚部院批准实施的《修改庙产助学章程》中对庙产提成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一条,各厅州县或城镇乡已办之学堂经费如有不敷得酌提庙产补助之;第二条,酌提数目以该庙产十分之三为限如该庙僧道尼等逃绝被人占据或假托祠堂抵抗以及干犯法纪者不在此限,前项所指庙产凡不动产与动产能生息者悉包含之;第三条,凡庙产向已提拨者均照旧办理;第四条,凡应提之庙产须由自治职员确查呈请地方官核办,自治会未成立以前劝学所负查报之职任;第五条,依前条规定提出之庙产应由自治职员或劝学所勘明界址,现属某区者即定位某区办学之基本财产区域,有变更或连合时亦如之;第六条凡已提庙产所办之初等小学其产息年值五十元者该庙中得送一人入校不收学费,多者类推;第七条现有主持之庙产年收租息不满百金者免提;第八条凡由抽提庙产补助之学堂当由该区自治会稽查账目,各该学堂管理人并应造具预算决算详细分册请该区自治会核议[3]9~10。
在庙产提成中,显然是一个将私产部分转化为公产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有势力者会觊觎这部分财产,政府对此也进行了规定。同样也是巡抚部院批准施行的规定:“育才兴学,责在有司,若地方刁生劣监品学卑污,人格不备本足以败坏学风,安能以兴办学,务平时以法相绳,当不敢公然出头为害乡里。年来新政举行,若辈得所藉手,往往借公益之名,为私肥之计,不肖州县又从而放弃责任,不辨黑白,辄假之以事权而于酌提庙产兴办学堂一事名义,似较正当。群思染指以致酿成纠抢拆庙之谬举,似此刁风亟应严加整顿。”[4]9
庙产提成,早在清末即已开始,但在民国达到高潮。试以几地举例说明。如黄冈麻城:
麻城县城路口西大山的纯阳山灵感观,民国十二年为万道人崇山创建,房屋四重,水田四石五斗,内有一石八斗由垦荒所得,二石七斗系郭姓乐捐。现被汽车道压占五斗七升,捐入福田河县立第五小学八斗,又干田四斗亦拟捐归第五小学管业,其余捐产仅九斗三升速同垦荒之田一石八斗均留归住持僧耕种,永远作观中香火之费,已向县府备案。
再如英山县城:
定慧庵,位于县北五十里上水田。明弘治元年,桂若愚建捐八斗斛田课五十石,内捐三十石入县学堂,实存二十石。
慈云庵,位于县北五十五里擂鼓岩下。明弘治元年,且可得建捐八斗斛田课十二石,内捐三石入县学堂,实有田课九担。
护国庵,位于县北五十里碧岩山。僧梵文建,张家塘六斗斛田课五十五石,内捐田课八石入县学堂。
万峰寺,位于县北三十五里闻家冲。层峦叠嶂,寂静异常。元至正中闻方程三姓共建捐田课八十四石,后捐田十四石入县学堂,实存田课七十石。
庙产提成用于兴办学堂外,还会有其他用途。20世纪20年代,《僧界筹认川粤汉鄂境铁路股分启》,当时川粤汉铁路已入外人手,绅商军学各界无不踊跃认捐,仅僧界没有认捐,原因是僧界自“东土以来,以不经营外事为宗旨,兼之所入无几,衣食而外,无多蓄积”。但是政府认为“生今之时代,究不能以古礼拘守……虽皈依佛教,要皆子民,亦当尽一份之责,务必节衣省食,勉为筹认。多至千股少至十股或多或少不留余力”,“谨择三月初九日十二点钟凡我丛林方丈执事及各官庙社庙当家住持僧等届期一体至寺,公同筹认”[5]8。
(三)没收庙产
没收庙产比庙产提成所受到的阻碍更大,更不易于推行,而且受到的批评更多。各地没收庙产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借口僧道品行问题对僧道进行驱逐,侵占庙产,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中就明确提出:“寺庙僧道有破坏清规违反党治及妨害善良风俗者,得由该管县政府呈报直辖上级政府转报内政部核准后,以命令废止或解散之。”(湖北省档案馆藏:《随县拟提庙产花捐作教育经费》LS19-4-5470)虽然内务部在此前曾下发文件:“查中国习惯,各项祠庙莫不以慈善为性质,公益为目的,无论对于国家、对于宗教纯粹正当公产。而祠庙既非自然人,自不能不借居住人代行其职务。若该居住人不本其性质,不遵其目的,而以己意妄自行事,则对于该祠庙已犯有违反职务之罪,该祠庙不惟不应代其受祸,其职务名誉反因之而受大损失,往往因其居住人之不法而罪及主体,目为淫祠,概予没收者。现时不应追溯外,以后如遇居住人不法者,即不能罪及祠庙,以符世界各国保护慈善公益之意。”[4]
虽然内务部对此作出规定,但并不能禁止此种行为的发生。1914年,《佛学丛报》对此现象进行了报道,湖北等地“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令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该管官厅拘捕,各僧道累讼经年。迄未得直强半假托议会议决莫可迥护,于是抽提庙产者益肆行无忌,仍欲继续勒捐,否则,认为违犯罪。凡所有财产均一律充公”[7]1~2。
《广益丛报》对这一现象进行过报道:湖北枣阳县五泉寺产业颇多,前任官吏因事判令充公田六百亩作学堂,经费屡经学臬两宪札催限缴陈大令。闻奉札后当即传寺僧仁林等勒限将其产业充公以备兴办学堂[8]9。
湖北各地庙产充公的也有不少。如黄冈麻城:
玉皇阁,位于麻城皇阁区,庙产水田五石又当三石有余,现议拨办小学。
中寺,位于木樨河区。清初住持僧建,庙产田八斗。宣统三年,丁华宇重修,改办三育小学。
文昌宫,在中馆驿西门,内贡士喻学陶林锦凤同四乡着士募资修建。民国二十二年,地方奉令兴学改设为县立第四小学校。再如英山县:
观音庵,位于县北五十里碧岩山,清康熙五十七年闰时雨时取共建,捐八斗斛田稞二十石,皆转入县学堂。
这是在民国时期寺庙产权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化私为公”的过程。在本节的标题中,出现了“化私为公”抑或“化公为公”。对于庙产等财产来说,“公”、“私”是相对的概念。对于国家与政府来说,庙产属于私产,但是相对于宗族、村社甚至地方来说,庙产又成了其组织内部所共用的财产,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寺僧道长等住持仅仅只拥有对庙产的使用权,并没有产权,有时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
在民国时期的寺庙产权转换过程中,当国家介入之后,这部分财产就是私产,至多也只能被认为是村社或团体所共同拥有的私产。庙产兴学的过程,就是将部分“私产”转化为国家“公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冲突,有时甚至会转化成大的暴力运动。
地方社会的士绅、宗族及其各种类型的施主由于其捐赠,对寺庙拥有所有权,虽然不为国家所承认,却在民间形成了习惯法。将庙产改为学校,同样是地方公共事务,却是国家“化私为公”的举措,将地方上的财产转为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而是展开了地方社会各类捐赠团体和政府之间的竞争。
国家通过“庙产兴学”的过程,希望将原属于地方社会的权势人物纳入国家体制之内,将原属于地方社会的公产纳入到国家财政之内,表明国家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冲突和纠纷是难以避免的。在下文中将会对民国时期出现的寺庙产权纠纷进行分析,以此为角度,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二、民国寺庙产权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在寺庙提产的过程中,发生了各种纠纷,主要是否认了地方社会的团体和寺僧对于寺庙的习惯性权利。以往寺庙管理的产权结构以一种民间的、没有受到国家承认的状态存在,依靠的是一种民间约定、习惯法的束缚。清末及民国以后,这种民间习惯逐渐受到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不满往往通过纠纷和暴力行为发泄出来。为了解决寺庙产权的问题,政府、地方社会和寺庙通常采取以下方式解决纠纷。
(一)驱赶寺僧
在庙产“化私为公”的过程中,受到的最直接的反对就是来自寺僧的反对。寺僧往往代表的是地方社会背后的势力。地方社会的士绅和团体为了避免自己的寺庙财产拱手让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煽动行为,反对官方的提拨。有的甚至教唆租种寺田的佃户“抗缴租课”,反对政府的提拨庙产。地方官员为了保证提拨庙产的正常进行,不会轻易姑息这种行为,往往会对幕后肇事者进行惩罚[9]。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驱赶寺僧。
如襄阳老河口袁木沟村所属磨针井住持赵理章被认为不守清规,败坏庙产。被指“将观音堂大殿指与明安康,收租库房斋堂指与程宝童,菜园指与杨光辉,该庙前后柏树打皮挂号指与陈伯卿,作钱八十串文”。且赵理章“有嫖赌,洋烟负债被累拐走图章,畏罪潜逃等情……但理章在琼台观勾串土匪,扰害地面,又将该庙图章私存伯卿手,狼狈为奸,渔利分肥,私出红票,暗使地痞在庙滋扰”。该案由老河口均县知事贺作霖审理,并刊刻于碑以示警戒。地方官员同时另请新住持管理寺庙,“嗣后凡关该庙所有业产等物须加意保存,以重古跡,勿得觊觎私卖及擅入庙内恣意搔扰”①2012年12月抄录于武当山。。所卖产业悉数追回,由地方政府代为管理。
1929年,湖北随县拟提庙产花捐作为教育经费,其中提到县属庙稞总在二千石以上,但是这些庙稞都用做了僧侣的“酒肉之资”,“与社会风俗有害无补”,于是要求寺庙划拨三分之一充作教育经费,如果这样的话,能“取彼无益化作有用”(湖北省档案馆藏:《随县拟提庙产花捐作教育经费》LS19-4-5470)。
民国以后,似乎载记于文的僧道不守寺庙清规的事例逐渐增多。但僧道不守寺庙清规的事情一直都有,只是在清中期以后,此类案件更多由地方社会进行管理,主要由地方士绅审理。地方士绅凭借其对庙产的控制和在地方的声望,履行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但是,民国之后,地方官员又重新介入了地方庙产案件的审理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便利于推行庙产提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逐步加强。
章太炎对于僧道屡屡被驱逐、庙产被侵占的情况,进行了抗议:“僧徒作奸,自有刑宪。爰书论罪,事在一人。所住招提,本非彼僧私产,何当株连蔓引,罪及屋乌?必若全寺皆污,宜令有司驱遣。所存旷刹,犹当别请住持。今则缘彼罪愆,利其土地。夫处分赃吏,但有籍其家资,未闻毁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夺牛,依何典法?”[10]173
(二)对簿公堂
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庙产纠纷问题,是1920年代之后采取的比较多的方式。这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法律意识的滥觞,同时也反映了民众纳入国家管理之下的一种自觉。
民国时期的政府否认地方社会团体和僧道对庙产享有的习惯性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其他势力对寺庙产业的争夺。清末庙产兴学之后,出现了一批办学士绅。办学士绅、寺庙绅首、僧道住持、地方政府负责自治的人员,都企图借此机会对寺庙产业“分一杯羹”,因此而对簿于公堂的事情,屡屡出现。
如湖北随县在1929年调查中称“各地劣绅,私占田产,驱逐僧人”,“第九区清莲寺被李匪尧夫等侵占……九龙贯被杨木斋、夏彩之侵占……汉升寺被黄铜高侵占”,“第五区延寿寺被刘晓帆等侵占”,“第七区朝阳寺被佳仁轩、王鼎三侵占;宝峰寺被杜远凯侵占”(湖北省档案馆藏:《随县县政府关于清鉴核属县第九区清莲寺等庙产被占一案的呈文》LS1-3-0464-016)。
1931年,宜昌县土城寺庙产一案中,此案由该县士绅易家培、许长云连同土城寺僧月清控诉,控诉第二区区长李崇德“藉公敲诈、欺压平民”。案件经审理调查后,易家培、徐长云被称为豪劣,寺僧月清被控勾结豪劣,主要控诉为:“土城寺每年收稞谷二百二十石,向例由当地士绅管理,年提谷十五石,包谷三石,钱五十串作该寺住持僧月清一名生活费。又提谷十五石做围防补助费,余则名为津贴私塾,实则全归虚糜。”后根据《监督寺庙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地方政府裁决,“除住持生活费仍旧提拨外,其余围防补助费及私塾津贴一律停止”,所有余款一并用作第二区第一初级小学校的筹建工作。但僧月清、易家培、徐长云仍互相勾结,抗不换据完稞,“致学校无法维持,行将倒闭”。为以惩效尤,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亲自下令革除僧月清的职务,“易家培、许长云二名移送法院”。三人的罪名为“违抗政令、破坏公益、尤复任意妄控、实属恶不可长”(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政府关于民政厅查办宜昌县土城寺庙产案的指令、训令及宜昌县政府呈文》LS1-3-0657-006)。
此类案件在整个1930年代屡见不鲜,寺僧被推上公堂,传统的绅被称为“劣绅”或“土劣”,成为了被控诉的主要对象。和清朝庙产纠纷解决方式不同的是,政府成为了解决纠纷的主导力量。传统的官绅民模式中,绅斡旋于其中,如今竟两面受敌,以往的官绅合作模式开始瓦解,而绅民关系亦开始紊乱,社会秩序开始重建。
[1]庙宇不愿租作学堂批词[N].申报,1905-06-03.
[2]僧道不准押售官有庙产[J].佛学丛报,1912,(3).
[3]修改庙产助学章程[J].北洋官报,1911,(2751).
[4]庙产兴学之手续[J].北洋官报,1911,(2673).
[5]僧界筹认川粤汉鄂境铁路股分启[J].广益丛报,1910,(234).
[6]内务部咨浙江都督覆陈本部对于各项祠庙意见请酌量办理文[G].政府公报,第247号,1913-01-13.
[7]重申攘夺庙产之禁令[J].佛学丛报,1914,(10).
[8]寺产移充学费[N].广益丛报,1908,(161).
[9]禀控阻扰寺产兴学[N].申报,1907-05-06.
[10]章太炎.告章官白衣启[M]//马勇.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