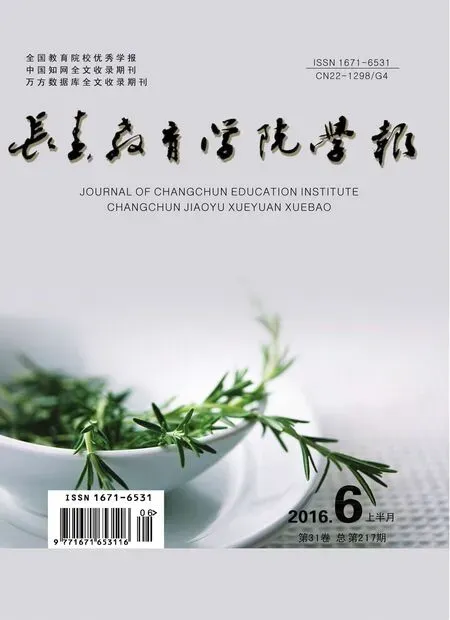三重创伤下的玛丽
——《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解读
2015-03-20刘玉婷
刘玉婷
三重创伤下的玛丽
——《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解读
刘玉婷
多丽丝·莱辛笔下的玛丽·特纳是一位边缘人物。在整部小说中经历着三重心理创伤。她虽为白人,但父母的不和谐关系和贫穷给玛丽的童年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迪克的匆匆结合又是另一件悲剧,迪克寡言且与玛丽的观念大相径庭,导致两人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黑人雇工摩西的介入在当时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无疑又加速了玛丽悲剧命运的进程。三大创伤集于一体,致使玛丽的主体化意识一步步弱化并走向丧失,直到最后也没有从创伤中得到复原。
女性主义;创伤理论;三重创伤;悲剧命运
一、引言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享誉盛名的作家,一生佳作无数,并于200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 “世界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1](Oates,40)。
《野草在歌唱》[2]是莱辛的处女作,此前有不少的研究者对该小说进行过细致的研究,有从种族问题出发,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玛丽的悲剧命运,也有从悲剧观出发研究摩西命运……近年来,创伤理论的风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野草在歌唱》的新视角。
《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玛丽出生于南非殖民地的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父母的争吵与彼此漠视让玛丽的童年时期蒙上了厚厚的阴影;成年后由于独立的生活和工作使其享受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随之而产生这样的幻想:自己的幸福生活将继续下去。在一次聚会中,无意听到朋友私下谈起自己竟然三十岁还独居,猛然发现自己与周边世界格格不入。于是,在匆匆忙忙之中与农场主迪克结合。迪克的出现并没有给玛丽带来所谓的 “光明的前程”,也没有使生活变得富裕。迪克是位懦弱、无能且贫穷的农场主,在玛丽一次次寄希望于迪克又失败时,玛丽的幻想最终破灭。此时摩西,一个具备男性魅力的黑人雇工的出现深深吸引住了玛丽。摩西身上具备的品质正是迪克所缺少的:体贴、勇敢、男人味十足。于是玛丽不可救药地与摩西发生了暧昧之事,而这是当时社会所不允许的,因而在事情暴露后,玛丽站在白人的立场想辞掉摩西,摩西难以受辱,持刀将玛丽杀害并静等警察的逮捕。玛丽正是这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步步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并以悲剧结尾。
本文将从创伤理论的视角来分析该作品,试图以分析玛丽悲剧命运为出发点,阐述在经历创伤之后,主体性意识的丧失将导致复原的不确定性甚至不可能性。
二、创伤理论
“创伤(trauma)”既是病理学术语,也是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该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于社会边缘性群体的创伤经历,如弱势群体中的女性、儿童、少数民族及战争中幸存的士兵等。“如何再现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的创伤经历,通过他们的记忆修正和颠覆正统历史的叙述,并帮他们走出创伤,成为当代欧美创伤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3]。“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4],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在其著作《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中如此说道。美国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露丝在其《不言的经历:创伤与历史的可能性》中指出,“创伤描绘了对突发或灾难性的事件难以承受的经历,而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滞后的,并出现难以控制的重复性的幻觉以及其他的困扰症状”[5]。当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不由自主地再现时,创伤承载者便会表现出与情绪相关的创伤症状。他 “可能会对与先前创伤有关的行为或情绪表现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6],同时也可能表现出“情绪状态的大起大落和/或难以应对的负面情绪”[6]。“日常生活中因人为原因或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难都会导致创伤的产生,比如,在事故或者自然灾害中失去亲人、遭遇性侵、目击恐怖事件等。除此之外,长期处于不利的家庭环境之中也会导致创伤,比如家庭暴力、贫穷和父母之爱的缺失”[7]。
三、悲剧命运解读
陶家俊认为,创伤可分为以下类别: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家庭创伤与政治恐怖创伤;工业事故创伤与战争创伤;儿童创伤与成人创伤;性暴力创伤、民族/种族创伤与代际间历史创伤;施暴者创伤与受害者创伤;直接创伤与间接创伤[8]。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将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野草在歌唱》中玛丽作为个体所遭受的创伤,并进而分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纵观全文不难发现,玛丽的悲剧命运并非是偶然的,其创伤经历也偏复杂,且伴随着其出生到死亡。年少时家庭带来的创伤,婚后的婚姻创伤,处处充满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的社会现状也是导致玛丽心理创伤的重要因素。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创伤事件后,玛丽的主体意识和身份意识也开始丧失,她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并一次次地陷入创伤的漩涡。
(一)家庭创伤
童年时期所产生的创伤会在受创伤者的潜意识中生根发芽,并会对日后的生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的潜意识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童年时期所克制的且极力想忘却的那部分记忆[9]。
玛丽的童年正是在父母的打斗和漠视中度过的。玛丽一家靠父亲来维持,但父亲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常常使这个家入不敷出。她的父亲“身材矮小,头发肮脏蓬乱,一张干瘪的面孔虽有几分爱诙谐的情趣,却又不自然。芝麻绿豆大的官来找他,他都叫他们‘大人';见到身份比他低的土人,他就吆喝;他的差使是在铁路上当抽水员。”由于玛丽的母亲经常哭诉和抱怨玛丽的父亲酗酒和无用,因而玛丽“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无力支付在商铺赊下的账,玛丽的父母每年都要有12次的打斗和永无休止的争吵。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玛丽对于自己哥哥和姐姐的死还抱有感激之情,因为父母固然悲伤但却不再争吵,“所以,这样得到的快乐实在是补足了悲伤还有余……她回想起这一时期,真是她童年最幸福的阶段”。在其后来过起寄宿生活时,玛丽也是非常高兴,“高兴得连假期也不愿意回家去看看醉醺醺的父亲和辛酸的母亲,以及那座风吹得倒的小屋子,那屋子就好像架在台阶上的小木箱似的。”这种关于童年的不快乐甚至不幸给玛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玛丽16岁工作以后,每次回忆起便心生不快甚至恐惧。
创伤承受者在童年时期经受的创伤会在后期表现为分裂症。该分裂的症状表现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情绪低落、恐惧、害怕和易怒。玛丽的不幸童年导致其在之后的生活长时间受到童年创伤的影响。她害怕家庭、婚姻、小孩和贫困。
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玛丽喜欢别人的孩子,但是一想到自己生孩子,就心惊胆战。看到人家结婚,她就觉得伤感,可是她又很讨厌男女关系。
创伤的另一个表现是回忆再现。即创伤承受者在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在其成长后还会以某种形式再现。例如,玛丽即便成年以后也经常记起自己醉酒的父亲、时常抱怨的母亲、摇摇欲坠的房子以及令人不堪回首的穷苦生活。在玛丽跟着迪克到了农场进了房间后,玛丽有这样一种幻想:
“她渐渐开始感觉到,现在并不是在这所屋子里跟丈夫坐在一起,而是回到了母亲身边,看着母亲在无休无止地筹划家务,缝衣补袜。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突然跌跌冲冲地站了起来,着了魔似的,好像觉得是自己的亡父从坟墓中送出了遗嘱,逼迫她去过她母亲生前非过不可的那种生活。”
玛丽的父母并未从子女的视角出发,而是一味地泄私愤、抱怨,使玛丽的幼小心灵蒙上层层乌云,并在玛丽的婚姻中埋下不幸的种子。她渐渐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自己走的路就是母亲的翻版。
(二)婚姻创伤
玛丽从16岁开始参加工作自食其力以来,一直都是单身状态,自由自在并引以为豪。直到一次无意中听到他人谈论自己三十岁还未结婚的事实以及自己的装束问题时,玛丽才开始感到恐慌,并开始给自己物色对象。在此,玛丽结婚的目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结婚,而是自己不结婚在外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要结婚,对婚姻的态度也是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正是源于其父母不幸婚姻的负面影响。迪克之所以想与玛丽结合,则是因为自己的农场需要一位持家的妇人,他也想要一个孩子,虽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们都不明白,爱和相互吸引才是幸福婚姻的开始。蒋海升对幸福的婚姻有这样一个定义:“幸福之家虽无固定的模式,但确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即: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和家人的健康、生活的充实和宽松的范围、家人的有秩序和和睦。”[10]因而玛丽的婚姻悲剧也是注定发生的。
结婚初期,玛丽和迪克对未来都是憧憬的。玛丽也渴望迪克能帮助自己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和迪克经常意见相左,比如用水、修房顶、对待佣人的态度等一些琐碎的事物上,迪克的重心都放在农场上。其实双方都曾为婚姻的不和谐和生活的困窘做出过努力,但最终都不得不向彼此向生活妥协。在经历过这种从憧憬到失落的落差时,玛丽感觉自己在走母亲的老路,对迪克的无能、固执和胆小感到失望,因而自己也时常精神恍惚,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
恰遇斯莱特夫妇第一次拜访,玛丽备受羞辱,玛丽想在佣人前出气,迪克不解,两人发生争吵后,玛丽心灰意冷:
“她不由得一阵心酸,勾起满腔自怜的情绪,接着便哭了起来。她接连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哭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后期由于生活的无望和梦幻破碎时的状态:
“她常常在那张破旧的沙发上接连坐上几个小时,褪了色的印花布窗帘在她头上啪啪地飘动着,她似乎失去了知觉。她的五脏六腑好像突然被什么损坏了,她整个的人正慢慢地枯萎,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她对一切都不闻不问。她整天闭着眼睛,麻木不仁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热气冲昏了她的头脑。她口渴,想倒杯水喝,可是去倒杯水或是叫佣人给她拿杯水来,她都嫌太吃力。她老是想睡觉,但是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爬上床去睡觉,又得费很大的力气。于是她就睡在原来的地方。她走起路来两条腿非常笨重,讲一句话也吃力得要命。接连几个星期,她除了跟迪克和佣人说话以外,没跟任何人说过话。”
奥斯汀有言,幸福的婚姻不仅需要思想交流,也要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心里,也就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玛丽和迪克不美满的婚姻正是由于缺乏沟通、没有精神上的慰藉、彼此不了解以及彼此心存偏见和芥蒂才将彼此的幸福葬送。玛丽儿时所经受的创伤又再一次重现在自己的生命里。
(三)社会创伤
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个人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关系非常密切。玛丽的悲剧命运与当时的种族问题、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同样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非洲正是殖民统治时期。一方面,白人作为统治者,占据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黑人则沦为雇佣工人、奴隶,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在白人的世界里,黑人又脏又黑,几乎与动物无异。另一方面,白人虽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白人与白人之间又有地位的差别,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财富的多少。
玛丽虽生为白人,但由于童年时期父亲的无能导致家庭的困窘和入不敷出,因而家庭地位不高。婚后迪克的无能又导致自己被周遭的居民看不起。在斯莱特太太第一次来访时,玛丽因自己的餐具、房子装饰和穿着的寒酸而害臊,斯莱特太太也为玛丽的经历而“感到惋惜”。玛丽在婚后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也因为自己的贫穷和不得体而不敢答应斯莱特太太的聚会邀请。但周遭的闲言碎语却不曾停歇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声势,声讨玛丽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这一方面源于玛丽和迪克的贫穷,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斯特莱先生想借迪克破产而趁机占有其农场。
作为白人的玛丽,从小就被灌输黑人是二等公民的思想,因而玛丽对黑人是厌恶的。玛丽认为黑人妇女“是些奇形怪状的原始人”,对待雇佣工也“要用鞭子来收拾他们”。但当雇工摩西出现时,玛丽却重拾快乐。摩西身上的果敢、男子汉气概、体贴与温柔都是迪克所缺少的。玛丽在精神上找到了慰藉,她可以在摩西面前大声哭泣,指使摩西做任何事情,玛丽在这样的氛围中找到了存在感。摩西的出现,虽然给玛丽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但在当时种族歧视盛行的南非,这种不能见光的关系无疑是危险的,会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因而在他俩的关系被人发现时,玛丽别无选择,只有驱使摩西离开。她的内心充满恐惧、纠葛,她甚至预见了自己的死亡,最终她惨死在摩西的刀下。
四、结语
在《野草在歌唱》中,玛丽作为个体经历了残酷的心理创伤,并深受记忆创伤的困扰。受创伤的心灵就像皮肤上的疤痕,虽然血已止住,但伤痕依旧触目惊心。创伤记忆的再现如果给予正确的引导,可以帮助创伤承载者正视过去,并在自己和他人的帮助下走出阴影,重新树立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但在19世纪的非洲,社会根本无法给玛丽提供这一机会。沉重的童年创伤、不如意的婚姻创伤、种族歧视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创伤,合力成为玛丽悲剧命运的助推器。
[1]Oates,Joyce Caro l.One Keeps Going[M].London:The South Review,1972.
[2]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33-133.
[4]Alexander,Jeffrey.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C]. Jeffrey 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 Identi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1-30.
[5]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History[J].Yale French Studies,1991(79):181-181.
[6]Judith A.Cohen,Anthony P.M annarino,Esther Deblinger.心理创伤与复原: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王俊生.创伤视角下的《追风筝的人》——国殇家恨与灵魂救赎[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1):56-56.
[8]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9]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0]蒋海升.家庭伦理与幸福之家的构成元素[J].政工研究动态,2009(2-3):11-13.
责任编辑:贺春健
I106
A
1671-6531(2015)11-0036-03
刘玉婷/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广东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