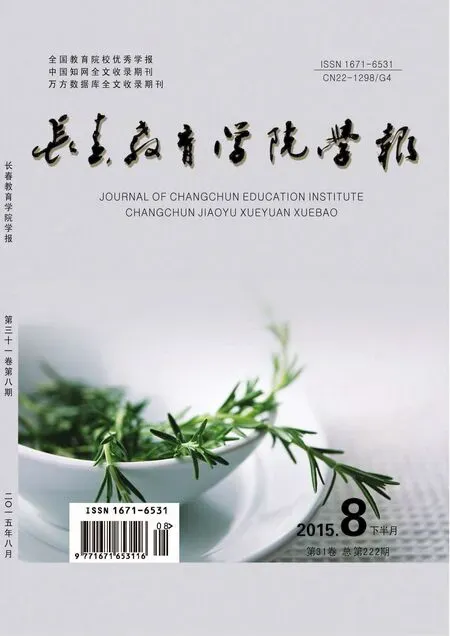“集体记忆”下的暴力文化——分析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2015-03-19张婵婵
“集体记忆”下的暴力文化——分析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张婵婵
摘要:《红雨》立足于中国湖北省麻城县这样一个小地方,从多方面分析麻城从元末到民国初年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给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纵横切点。一个中国历史的盲点被揭示出来。文章讨论被忽略的“集体记忆”下中国的暴力文化,分析我国潜在的暴力文化。
关键词:集体记忆;暴力文化;《红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学者罗威廉教授的关于中国暴力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底色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等等。都是以和为中心的。罗威廉另辟蹊径从暴力文化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底色,通过阅读《红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中国的文化,也把一直被中国人忽视的暴力文化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李里峰以“小地方、大历史、长时段”三个词来形容《红雨》一点也不夸张,从一个中国小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历史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暴力“隐”文化的发展历程。《红雨》探寻历史的足迹,罗威廉从社会形态、历史时间、宗教问题、经济发展、精英文化、奴仆战争等等方面探究了中国的暴力文化。
一、麻城——中国暴力文化最突出反映
《红雨》是从元朝末年开始记载了暴力的发展史,罗威廉从深层次挖掘出了暴力的集体记忆。可能看了这部著作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是麻城?它的暴力文化能代表中国的暴力文化吗?罗威廉在这本著作中也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之所以选择麻城主要是因为麻城的特殊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以及阶级基础。作者在开篇就给我们交代了麻城优越的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这道山脉将华北平原与长江中游区分割开来。纵贯大别山的无关,尤其是该县东北角的松子关和长岭关,在当地历史和帝国历史上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也就是说麻城是鄂豫皖交界处的小县城,一直以来处在战略要地的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这样朝代更替频繁,麻城必然受其影响。在《红雨》中,罗威廉搜集了很多流传在麻城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纂者也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时而把强人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为盗贼、土匪”。[2]罗威廉提到,在麻城精英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暴力文化,所以在某些方面,麻城的文化体系是以暴力为中心的。“历史属于少数的职业专家,而记忆是更广泛的集体的财产”。[3]所以说麻城的暴力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集体记忆,更是精英文化的体现。精英人士所发起的暴力战争在麻城是很普遍的,这是麻城独特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麻城的奴仆战争,官逼民反这一暴力模式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有多少的底层民众为了反抗达官贵族的压迫,揭竿而起。
麻城的暴力文化是中国暴力文化的缩影。罗威廉教授选取麻城这样一个小县城,研究了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研究的仅仅是地方的暴力文化吗?很显然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学者愿意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此,况且我们在阅读《红雨》时看到的不仅仅是麻城的暴力文化。作者在叙述麻城的战争时,也不时地叙述了周边地区的战争,况且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麻城也必然会发展战争。当然特殊的文化也使得麻城这个地方时不时地遭到战争的迫害,如宗族发展,掠夺权势的战争。麻城本身是一个尚武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不断延续的是大家对于山寨的热衷,绿林好汉都聚集在此。麻城一个明显的暴力文化模式就是英雄和武侠观念。至此,我们也会了解到不论是麻城还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暴力文化其实是很普遍存在,尚武的精神不是单单指的麻城,中国本身就是尚武的国家。“武”可以保证国家乃至自我的合法权益,这也就给暴力提供了存在的合理解释。唐代时,好多文人为了获取功名都会去边关参加战争。暴力本身就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因为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暴力文化总是被边缘化。我们在书中也可以看到农民起义、朝代更替、民族之间的冲突、家族衰微等等暴力的表现形式,很显然这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麻城不仅仅是一个小县城的暴力文化的体现,而是中国暴力文化的缩影。而且这种暴力文化长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中。
二、“集体记忆”下的中国暴力“隐”文化
之所以在标题中提到中国暴力“隐”文化,因为暴力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是属于亚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是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但它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在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实践经验中,中国和大多数人类社会一样暴力”。[4]
从先秦时期开始,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人们的思想被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束缚着。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和“礼”,在这种以“仁”为主流文化中心的儒学中,暴力理所应当是被排除在外的。对于中国来说,暴力是外文化,一种被压制、被忽略的文化形式。而儒家“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所以暴力也就不会被主流文化所接纳,甚至是处在被排斥的范围内。但是这种潜在的暴力文化一直是存在,而且是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就是追溯到人类起源,中国的神话时期,我们依然可以觉察到人们对于骁勇善战的英雄的崇拜,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杀蚩尤、共工颛顼争帝、刑天与帝争神等这些暴力的存在,他们都是用暴力来为自己赢得荣誉。暴力是我们的集体记忆,它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只不过传统的主流文化有所束缚。中国的朝代更替大多是以以暴制暴的形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于用暴力夺取王位的帝王,大家大多都是顺从,甚至是欢呼雀跃。人们也对于这种暴力的潜在形式是认可的。
“哈雷尔注意到,在童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的儿童总会因打斗而受到惩罚,即使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因为他们没能坚决地共同避免冲突。”[5]这就是我们对于暴力文化的态度。热爱和平是每一个人的美好的愿望,但中西方对待和平却不同,中国是以忍让换取和平,西方则更多的是争取和平。这也就是中西方对待暴力的态度,我们更多的是隐忍,是避免冲突,所以暴力自然也是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所以我们的历代中对于暴力是不谈论的,对于我国的历史来说暴力用正义与非正义所取代。这也就是李里峰在《红雨》序言中提到的“社会健忘症”,他们把不合乎中国主流文化的暴力选择性的集体遗忘了。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暴力文化的存在。这种暴力的文化形式在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他的足迹,我国的四大名著中两大著作《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暴力文化的体现;发展到近现代,金庸小说的推崇,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集体记忆下的暴力文化被唤起。
暴力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并存的,从远古时期到现在的社会,它都是并行存在的。就像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显性文化,而暴力文化是中国的隐性文化一样。但我们却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就像《红雨》中我们看到的,暴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不会因回避而丢失。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暴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暴力文化是人类历程中必经历的文化形态,重视暴力文化才能使得中国文化以一种完善的文化体系展现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且这种暴力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认为暴力文化已消逝,它是一种与主流文化共存的文化形态。现在的监狱也就是现代暴力文化的一种潜在的存在。因为暴力文化的集体记忆性,暴力文化永远都不会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我们理应重视暴力文化,不断完善中国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美)罗威廉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M].李里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6.
[2]刘军.麻城烟云七百年——读罗威廉《红雨》[J].阅读札记,来源于知网.
[3](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导言.李里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0.
[4](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导言.李里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3.
[5](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导言.李里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4.
责任编辑:魏明程

霍冬旭/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在读硕士(吉林长春1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