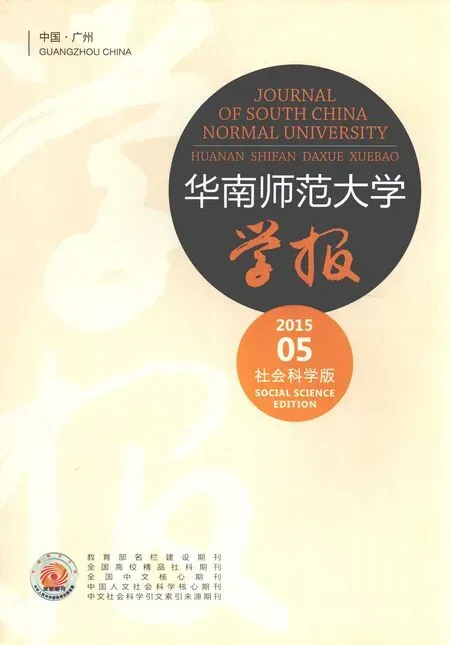虚静:文人画的审美心境
2015-03-19潘义奎
潘 义 奎
虚静:文人画的审美心境
潘 义 奎
【摘要】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精髓的虚静不但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根性,而且更在终极审美层面上影响着传统文人画意境的生成和作为其最高评价标准的界定。文人山水画以虚静为特色的审美心境自古以来对中国画家的创作理念及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虚静审美心境文人山水画意境
一
作为中国古代审美体验的发端,虚静既是一种审美心境,又是一种创作态度,它把中国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转换为艺术审美追求,使这一本来虚无飘渺的情感状态和一种近乎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自始至终制约着整个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人们在从事艺术活动的过程中,难免要把个体某一特殊的心理活动或情感体验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其中,形成特定的审美心境。但个人化的审美心境并非空穴来风,它必然要受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民族文化的制约,凡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的审美心境,往往容易在作品与欣赏主体之间达成共识形成共鸣,反之则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隔膜,甚至招致艺术受众的疏离和排斥,这缘于某种共同的或近似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审美心理结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感牢不可破地左右着我们对中国艺术几乎各个门类的审美观照方式和价值标准;同时,虚静作为中国艺术的文化根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观照本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审美心境。[1]
道,是发端于中国古代本土的哲学,几千年来它对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影响甚巨。同时,道是中国艺术意境中最深刻、最本质的文化根性,当然也是最终极的价值取向,支持着几乎所有中国艺术中源自于其的、意境和韵味的虚静美、清淡美和空灵美。中国艺术精神的本源决定了中国艺术的体验就是一种对道的体验。先秦时期,思想家老子提出了道家修养的主旨为“致虚极,守静笃”。 他认为世间万物原本都是空虚而宁静的,一切的生命都是由“无”到“有”,由“有”再到“无”,而根源则是“虚静的”,从而“虚静即是生命的本质”。庄子在继承老子“虚静”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与之相关的概念,认为“虚静”是自然的本质,亦是艺术的本质。作为构成道家思想主要审美范畴的“虚”即源自于庄子的“虚室生白”及“象罔”说,其中的“象”当然是具体有形的外在的物象现实世界的反映,而与之对应的“罔”则意味着超越具体有形的现实世界或隐藏于其中,虚幻莫测的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宗白华认为,“所谓顽空,是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这正是对庄子 “唯道集虚”的最佳注脚。“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有了天地间的“虚”,才有了万物的流动,而“道”是有限和无限、混沌和差别的统一,天地万物皆是“有”和“无”“虚”与“实”的统一体。以庄子看来,要达到“虚静”的境界就必须远离世俗利害关系,摆脱个人欲望杂念干扰,真切体悟世间的“道”,达到物我合一,才能真正地融入自然、体会自然,创作出真正与自然融会贯通的艺术作品。老庄“虚静”学说的提出和发展,确立了“虚静”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种必要的态度。这从理论源头上为后来的艺术创作者进入艺术体验的境界指明了方向,也对后人的艺术创造与评价标准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虚静”说被正式引入了审美的范畴,进而渗透到艺术创作实践中。西晋时文艺理论批评家陆机在其所著的《文赋》中提到“伫中区以玄览”,认为持有“虚静”的心态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前提,强调在创作之前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心境,在过程中不受外物和杂念的干扰束缚。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论述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这又对“虚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文艺理论范畴内进一步高度强化了“虚静”的概念。他明确指出“虚静”是在文艺创造过程中所达到的最佳创作状态,能使创作主体虚静凝神,最大限度地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心无旁骛,方能进入审美观照的境界。
虚静的心理层面一方面要求审美主体无我无物心无挂碍,另一方面要求以一种高度专注的精神来从容细微地体认永恒的生命状态,这两方面共同指向一个终极的审美目标及道所昭显的精神境界。这个过程就是用一种以静制动的审美观照方式和一种了无挂碍、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进入一个自由酣畅、挥洒自如的审美体验。中国艺术对生命的体验是以物为起点以心为主宰的心物感应之旅。用心来体悟外物需要的是直觉和静悟,这决定了中国哲学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就是徘徊于心物之间的生命体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核心问题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领悟问题,这种认识方式是中国艺术对人类艺术的特殊贡献。主体与客体结合就是用主体的虚静之心来应对客体的虚无之体,一旦落实到艺术活动中,则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作品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艺术只对个体心灵负责,道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心有助于我们去除功利、纯化心境,从而将中国文人画家塑造成一个摆脱尘世羁绊、心明如镜的单纯艺术创造者。道家“虚静”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影响至为深远。
二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唐五代兴起的文人画及评价标准从理论上强化了这一理想化的审美心境,并引导后世文人画家在创作实践中对虚静无为的身体力行。魏晋文士谈玄论道,追求清静无为,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定位在清新淡雅的韵味上。自然与心灵、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这个时期以来文人士大夫阶层艺术实践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尤其南朝文人画家宗炳所首倡的“澄怀味象”和“洗心”“卧游”的静观方式与老子的清静无为和庄子的“斋以静心”的出世心态更是一脉相承,在画面中自觉表现作者遁世离俗的主观情思并将绘画的功能锁定在“怡情悦性”和“自喻适志”等审美愉悦功能上,画家从此大多通过对世俗利害的超越来达到审美心境的空灵清静,从而实现道家所倡导的虚静艺术精神。而后,宋代画家郭熙发挥了宗炳的思想,发现了山水的“三远”,将老子思想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精髓深深地渗透在山水画中。通过历代文人画家王维、苏轼、直至赵孟等人的大力提倡,画外之意象之趣味成为文人画最基本的审美追求,一旦落实到画面上,常常表现为空灵之境、幽远之境、清逸之境、萧散之境、荒寒之境、苍茫之境等等。以北宋中后期中国画审美观念的转型为标志,玄远超逸的品格成了文人山水画的自觉追求,最终作为影响文人画创作的心理基础。
“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3]这种审美心境就意味着给外在的客观世界打上主观的印记,无形中赋予艺术家和欣赏者一种超然尘外的出世情怀,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涵盖着一切美的艺术和人生,直接关系到对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是一种所谓“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审美心境,它受特定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和个体审美心境的左右,被历代美术评论家确立为逸格的经典作品就是这种审美心境的产物。其意义对于艺术创作的行为和行为主体而言,就是要在画面视觉之外营造出一个心理意境,这是评价文人山水画艺术格调的基本标准,也是决定其艺术质量的根本所在,舍此则遑论文人画。可以说,文人画家艺术生命的整个历练过程就是对“技进乎道”毕生追求的生命体验过程,而“道”在引导人们穿过有限自我达到无限的过程中,必然引导画家于此获得一种超越对象和客体化的约束的体验,即虚无之境。这一体验的具体成果就是作品所具有的意境。虚静的审美心境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同时也作为一种创作观念对山水画的最大价值,首先表现在意境之上,通过意境的追求进而影响创作观念、表现手法乃至山水画的品评标准。没有意境就没有文人山水画,那么虚无意境便无从谈起。
意境源于中国语言观所强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者,意境也。宗白华认定它是中国艺术“中心的中心”。意境是在文人画审美心境创作中对自然物象的虚空转化和对艺术形象的超越。一方面,它在可视的形式层面上通过惨淡经营的空白分布和高度概括了的笔墨语言将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作用于客观事物之上,并把有限的画面和语言拓向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把艺术本体提升到“道”的层面;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层面上,它穿透客观事物的表象直接进入其内部以实现主体对客体在思维上、视觉上和形象上最大限度的超越,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美的体认和挖掘。意境作为中国山水画的生命之所在,其妙处主要取决于画面的各种虚实关系,往往通过虚处笔墨的控制与构思和空白区域的经营来营造足以使人展开想象的心理空间,因而决定意境产生的因素不在于有形的实体而在于无形的空白,虚体的空间运作得失决定着山水画乃至中国画的美学品格的雅俗和艺术质量的高低。
老庄道家的观念认为艺术中的空白既是一种“无”,更是一种“有”,这是将老子“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审美境界切实地落实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它常常营造出一种幽深莫测的空间和空灵玄远的思绪,也给人一种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想象空间,不经意间就能使观者从画面半遮半掩、欲言又止的有形空间中自然生发出无限的画外想象空间,从而下意识地进入到一种“可卧可游可居”的审美境界中。这种对表现客体形而上的独特把握方式最终把艺术活动的主体从纷繁复杂的自然中解救出来,使其得以摆脱客体的制约从而实现从观照方式到体验过程再到具体的艺术活动的全过程都能不受太多来自于外在的各种羁绊;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态一旦落实到创作中就自然而然得以呈现出一种流动自如的气息,而且无处不在并贯彻始终,因而成为把握和进入中国艺术审美心境的一道门槛。一旦跨过这道门槛,在进一步的艺术实践中就能够以意境为价值指归来实现审美的超越,这意味着向艺术的自由王国又接近了一步。
三
在道家看来,艺术的本源就是道,只有置身于道的境界,艺术才能够获得精神和生命,道是艺术的升华,艺术是道的直观呈现。因此,艺术是人生,更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于中国文人而言,绘画之道最终是天地之道所规定的,画之本根宗于天地之本根,只要把握了那根本的道,则可尽天地之造化,通古今之流变,无往而不胜。在率性自由不为物役的创作心态下,从静态的山川物象中彰显出天道的瞬息万变而进入合於天机的自由创作境界,这其实就是庄子所论的逍遥游境界。文人画要冲破造物的束缚达到自由挥洒的忘我状态,首先要解放个体的心态,放松对现实物态的拘泥,那就意味着把主体的心灵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并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以达到物我同化,而不是甘当自然造物的奴仆,被动地接受其摆布,也不像西方艺术实践观所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感性活动将主体的意志和人的本质力量凌驾于自然之上,并将自然对象化予以支配。在中国清代文人画家石涛看来,山水画属于人而不属于自然,因而它只对人的内心世界负责而不是对客观外在负责,艺术活动的终极价值就是表达自我而不是复制自然。[4]所谓山川为我而化,就是自然在我心中的驻足和我与山川的神遇,这一切都以主观内省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艺术活动主体的内在生活中,从而完全消融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对立或疏离,使主体的心灵实现了诗性的栖息,完成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终极目标。
创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着作者的技术发挥和作品的艺术质量,这就决定了文人画审美心境必须转换成创作过程中的现实发挥,后世文人所追求的魏晋风度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理想化境界。所谓的“解衣般礴”,强调的是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种超然心态和自由境界。诚然,当代的文化情景已不可能给人们提供古代的文化氛围或使人们实践古人的文化行为。如果只是出于视觉文化的需要而将生活常态下的欺世癫狂人为地拔高到文化学的意义上进行牵强附会,所谓的虚静无为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和装腔作势的标榜,所谓的审美心境也只能是一个虚设的文化概念而已,在艺术实践中并无实质性的审美价值。而传统文人画的审美心境所自然形成的审美感知方式无形中给不同的表现客体强行设定了共同的精神,客观上使艺术家疏离了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和千变万化的自然物象及其自身所蕴含的具体而独特的精神属性和形式元素。更不用说由此而产生的审美评价标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足体系,一旦遭遇到人文精神的流失和文化身份同化,它自身不可避免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就必然会给文人画的末流不经意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思维定势和表现程式。显然,当下仍然有一批坚守传统文人画探索的中国艺术家,遗憾的是,这样的探索只能在一个虚拟的文化氛围中通过全方位地考察和模拟古人的内心生活、知识结构和创作方式来试图唤醒某种远古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执着纠结、挣扎于时代大的文化变迁,同时也在艰难地挑战自身极限。但这样的艺术殉道精神并没有文人画在当下所遭遇的新的程式化、类型化和风格化倾向。
时过境迁,20世纪中国经历了3 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传统文化更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严格地说,文人士大夫阶层早已不复存在,传统文人画的创作主体亦已成为昨日黄花。那么,今时今日,昔日的文人画审美心境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审美标准必然要经历新一轮的诠释和转换。
参考文献:
[1]张强.中国画论体系.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121—122.
[2]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325—328.
[3]宗白华.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207—209.
[4]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89—92.
【责任编辑:于尚艳;实习编辑:杨孟葳】
作者简介:(潘义奎,甘肃平凉人,甘肃省画院副院长。)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5)05-0187-03
【收稿日期】201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