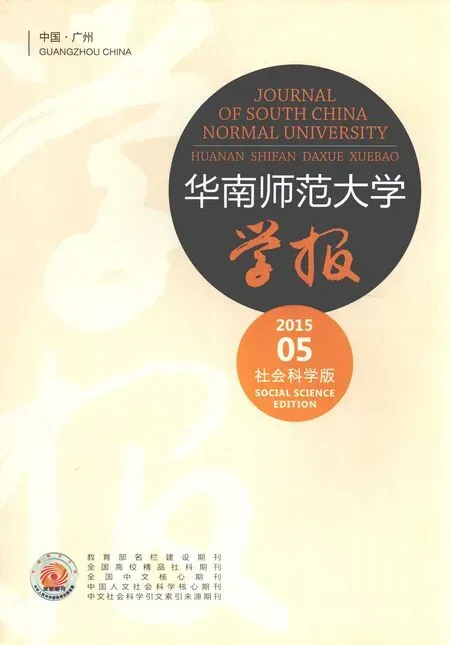新诗“情绪节奏”命题的由来及其可能性
2015-03-19张中宇朱寿桐
张中宇, 朱寿桐
新诗“情绪节奏”命题的由来及其可能性
张中宇, 朱寿桐
【摘要】郭沫若最早提出“内在的韵律”,由于概念存在逻辑矛盾,随后演变为“内在节奏”“情绪节奏”。但“情绪”波动性很大、变幻莫测,通常并不像潮起潮落一样规则有序。要考察是否形成节奏,需要确认节奏的最小构成单位。但迄今近百年,没有任何学者能划分出“情绪节奏”的基本单元;也无法确认这些构成单元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更无法确认这些节奏单位的强度、时长相当或接近,以构成“规律性再现”。因此,新诗诞生以来甚嚣尘上的“情绪节奏”,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其产生的背景是消解基于声韵的诗歌韵律,为废韵律、散文化提供依据。从实践层面看,所谓“内在律”“情绪节奏”等,近百年来也没有引导汉语新诗走向稳健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新诗“情绪节奏”伪命题
一、从“内在的韵律”到“情绪节奏”
郭沫若最早明确提出“内在的韵律”。他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甚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甚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长’。……大抵歌之成分外在律多而内在律少。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郭沫若:《论诗三札》,见《文艺论集》,第204—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郭沫若的“内在的韵律”,原本并不是立足于充分论证一个新的理论发现,而是要针对他所称的“外在的韵律”,也就是基于声韵的通常所称的“韵律”。郭沫若首先以不证自明的姿态断言“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然后,通常所称的韵律被极力贬损为“外在的韵律”。这样,以“内在的韵律”代替“外在的韵律”,理直气壮地为全面废韵确立依据。“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裸体的美人”等,成为郭沫若诗论的标志。其影响延及于今,甚至愈演愈烈。
但是,“韵律”一词本有明确的定义。《辞海》释“韵律”:“诗歌中的声韵和格律……主要包括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组合”,“节奏的形式和数目,押韵的方式和位置。”*《辞海》(缩印本),第23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要素对应于汉语诗歌,分别为平仄、节奏、押韵。英文Prosody,汉语译做“韵律”,《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释义为:the patterns of sounds and rhythms in poetry and speech;the study of this.指言语和诗歌的节奏及语音形式以及对其的研究。郭沫若把原本清晰而确定指语音或艺术形式的韵律,变成属于内容层面的“情绪的自然消长”,这其实是一种概念的转移。后来戴望舒说:“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戴望舒:《望舒诗论》,载《现代》1932年第2卷第1期。戴望舒连郭沫若“内在的韵律”这样一个为着转移概念所作的过渡,也懒得提起,直接就说“诗的韵律……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也是把一个原本指语音或艺术形式的概念,强行移植到属于内容层面的“诗的情绪”。
从语言运用来说,这样的“转移”并非不可。*汤琼:《语用学的“言外之意”理论和文学的“意境说”》,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但是,概念一旦形成并习用,其内涵和外延就具有稳定性。因此,概念的“转移”或“移植”,必须具有“一致性”,即逻辑上的“周延性”,方能适用。“韵律”概念有明确的构成要素。以汉语诗歌为例,包括节奏、韵、平仄三要素。如将“韵律”移用于“情绪的自然消长”,称之为“内在的韵律”;那么,这个“内在的韵律”概念也需要包括“内在的节奏”“内在的韵”“内在的平仄”三要素,才能确保概念外延的一致,即逻辑的“周延性”,否则就不合逻辑。显然,不管是郭沫若还是后来的追随者,都从未也根本不可能确认存在“内在的韵”“内在的平仄”,只能认为“情绪的自然消长”可以和“节奏”发生关联。这样,既然“内在的韵律”外延不能与“韵律”的外延相等,且差异很大(汉语诗歌韵律有三个要素,但“内在的韵律”只有一个要素),于是“内在的韵律”不得不渐渐变成“内在节奏”“情绪节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不管“内在节奏”“情绪节奏”是否可以成立,起码与“内在的韵律”或“情绪韵律”比较,不存在概念不周延的逻辑问题。为了标榜与“外在的韵律”不同,且强调“情绪节奏”的地位,仍把“情绪节奏”称为相对模糊的“内在律”。最初的“内在的韵律”之说,逐渐搁置。
尽管谁也无法对“情绪节奏”进行科学的把握或论证,但“情绪节奏”具有相当丰富的想象空间。由于有郭沫若、戴望舒等提出在先,自由诗派客观上需要为极度自由化、废韵寻找一个理论依据,“情绪节奏”就成为自由诗派必须维护因而不可动摇的根基。陈本益先生《汉语诗歌的节奏》1994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2013年改由中国大陆重庆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是新时期最早的节奏专论,他指出:“诗歌的情绪节奏却不易捉摸。情绪节奏对自由诗形式尤为重要,它构成自由诗的内在韵律,是自由诗分行的主要依据。”*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第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虽然学者们都坦率指出所谓情绪节奏“不易捉摸”,根本无法具体描述、论证,还是先入为主设定为理论前提再说。因为这样可与自由诗的要求吻合,而且毫无学术风险。张桃洲先生认为:“由于现代汉语的种种限制,新诗的格律大概只能趋于内敛即‘内在化’。”*张桃洲:《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第7、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里所谓“内敛”“内在化”,虽然较郭沫若等人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理由:“现代汉语的种种限制”,但并没有深入研究现代汉语的性质,没有系统考察古、今汉语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异,为汉语新诗提供了何种可能与不可能。这一类学者承袭“内在律”之说,似乎有些无奈。即新诗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废韵思潮和惯性,其发展方向看来难以扭转。同时,汉语的嬗变导致传统的韵律体系不能直接借用,现代汉语可提供的新资源又尚未充分论证。既然如此,“内敛”“内在化”之说,不失为一种学术策略。把传统的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韵律贬损为“外部音响”“低级音乐性”,以内、外之别显示立论的微妙,从郭沫若、戴望舒等以迄于今,从大陆到台湾,几无例外。
二、“情绪节奏”与音韵节奏的整合
“内在的韵律”以及此后提出的“内在节奏”“情绪节奏”等,其立论的实质是废韵、散文化,由此把汉语新诗引向自由化的极端。由于新诗文体形式逐渐消弭了诗与散文的界限,导致“诗性”魅力流失,由此引起了以新月派为核心的格律诗派的反拨。问题是,新诗格律诗派从理论到创作也走向了刻板一律的极端。这一缺陷导致以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格律诗派,无法完成匡正汉语新诗发展的失序。
当代诗学一个显著动向是,试图在互不否认的前提下,寻找对立两派各自的合理性,以把一开始尖锐矛盾、水火不容的两大诗派理论融合起来。例如骆寒超先生《新诗创作论》指出:“就诗歌而言,情绪不同的表现特点大多显示在心态表情和声音表情上。于是,在诗歌创作中作为心态表情反映的观念推移就导致情韵节奏,声音表情则产生了声韵节奏。”*骆寒超:《新诗创作论》,第3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骆寒超先生提出“情韵节奏”“声韵节奏”两个概念,解释二者关系,和郭沫若以“内在的韵律”代替“外在的韵律”,以此强烈否定“外在的韵律”已有根本的不同。他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似乎要完成一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可想象的超级折衷。
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有效论证“情绪节奏”确实存在。若“情绪节奏”子虚乌有,则“情绪节奏”与“声韵节奏”的统一也无从立论。和“韵律”本有明确定义一样,“节奏”的内涵也非常清晰。《辞海》释“节奏”:“语音学术语。指说话时声音变化的配列模式。由作为语音基本要素的音长、音高、音强等在语言运用中所形成的长短、高低、强弱、轻重的规律性再现所构成。”*《辞海》(缩印本),第9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毕歇尔指出:“我们总是把具有同一强度和在同样时间内运动的规则性重复看作节奏。”*[德]毕歇尔:《劳动与节奏》,见[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1卷,第208页,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不管是《辞海》还是毕歇尔,都指出“规律性再现”“规则性重复”是构成节奏的核心。例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均为两个音节构成一个基本节奏单位,基本节奏单位之间具有区别性特征,这些最小的基本单位强度和时长相当或接近,形成多频次“规律性再现”“规则性重复”。“情绪节奏”这样一个被自由诗派广泛使用的概念,迄今却并没有人能对它的最小构成单位为何、如何区分,以及这些最小单位如何构成“规则性重复”这样的核心问题进行过具体描述或论证。这正是本文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郭沫若说:“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郭沫若:《论节奏》,1926年,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这算是他对“情绪节奏”比较具体的说明,也是自由诗派认为可以构成“情绪节奏”的基础。问题是,这个“波状的形式”,它可分解出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又如何构成“规则性重复”?浙江大学骆寒超教授对此有一个评价:“这位(指郭沫若)一再提倡写诗只需讲究内在律的浪漫派诗人,虽然在理论上从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讲清楚内在律的表现,这一段创作体验倒颇能给人启发。”*骆寒超:《新诗创作论》,第383,37,372,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治新诗颇为深厚的骆寒超先生明确指出,郭沫若“在理论上从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讲清楚内在律的表现”。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来不及“讲清楚内在律的表现”,在他一生此后五六十年中,尤其是建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逾30年,有充分的学术条件和思考时间,郭沫若为何还是不把这个“内在律”讲清楚,或者作一番深入的思考?这其实颇值得深思:所谓的“内在律”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几十年来郭沫若为何不试图哪怕稍微“讲清楚”一些?除了狂飙突进的新诗创作,“内在的韵律”“情绪节奏”其实是郭沫若新诗理论的核心遗产。如果郭沫若坚定确认和维护他的理论核心,不可能几十年对之如此漠然。这里需要指出,艾青青年时代极力主张诗歌要有“散文美”*艾青:《诗的散文美》,见《广西日报》1939-04-20。,可是到了中后期,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所谓“散文美”,诗歌呈现出新的面貌。戴望舒若天假以年,是否会反思他的极度情绪化的诗论,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看一看他的如《雨巷》等创作,还是可以推测,他不大可能真正滑向完全废韵、散文化的极端。
骆寒超先生指出,“节奏是情绪流动的一种规律性表现”⑤骆寒超:《新诗创作论》,第383,37,372,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已经注意到“情绪”若要构成节奏必须具备的要素。较之于许多自由派诗论刻意回避“规律性表现”这样的核心要素,骆寒超先生无疑试图增加理性的分量。他似乎要进一步论证“情绪”确实可以形成“规律性表现”:“作为流动着的情绪,在心理感应的特定阶段上,情境的显隐、疏密、宽窄、强弱等理所当然地给人一种节奏感。”⑥骆寒超:《新诗创作论》,第383,37,372,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可是骆寒超先生还是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进一步说明那个“理所当然地给人一种节奏感”的“显隐、疏密、宽窄、强弱等”,或者“空间差异”“时间差异”“虚实差异”“宽窄、刚柔差异”,怎样构成“情绪节奏”:它的最小的构成单位是什么?这个最小构成单位如何“规律性表现”?骆寒超先生说:“至今为止,学术界研究的着眼点还是在声韵节奏上,对情韵节奏的系统考察却还鲜见。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客观的原因。就是说,前者具体易谈,后者却相当抽象,颇难把握。”⑦骆寒超:《新诗创作论》,第383,37,372,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相当抽象,颇难把握”不是一个研究者的感叹。可是,既然近百年时间,这么多学者都感到“不易捉摸”“颇难把握”,即根本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描述或进行有效论证,无法确定它的最小构成单位和如何构成“规律性表现”,为何却能“理所当然”地断定可以构成“情绪节奏”?
三、讨论与结论
这里进一步讨论节奏的构成要素。R.L.特拉斯克编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这样解释“节奏”:“在言语或诗歌中由突显的要素有规则地间断出现所产生的知觉模式。这些要素可能是重音(如英语)、音节(如西班牙语)、重型音节(如古希腊语)或莫拉(如日语)。”*[英]R.L.特拉斯克:《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第229页,《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R.L.特拉斯克指出,节奏基本单位(由“突显的要素”构成)之间需要有“间断”。朱光潜指出:“要产生节奏,时间的绵延直线必须分为断续线,造成段落起伏。这种段落起伏也要有若干规律,有几分固定的单位,前后相差不能过远……节奏是声音大致相等的时间段落里所生的起伏。这大致相等的时间段落就是声音的单位,如中文诗的句逗,英文诗的行与音步(foot)。”*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第14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朱光潜认为,要产生节奏,需要把一个时间流动过程“分为”多个“断续线”——即基本节奏单位,且分出来的这些关键单位“相差不能过远”,以构成“若干规律”。由此来看,形成节奏,必须考虑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能把一个连续的过程,“分为”若干基本节奏单位(最小构成单位)。
第二,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具有可识别的区别性特征。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是“间断”、“断续线”,例如汉语音步之间可感知的短暂停延或“间隙”(如“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是轻重、高低、长短等的显著区别,例如英语诗歌的重音、潮起潮落的高低起伏。
第三,可区别的基本节奏单位具有等强、等时或接近等强、等时的特征,通过多频次出现,构成“有规律的重复”。例如,正常状况下每一次潮起潮落的强度、时长是相当的,反复出现就构成“规则性重复”,这是自然界形成的天然节奏。汉语诗歌、英语诗歌,都需要利用语言的特性对普通的交际语言进行适当调整,以使它的最小构成单位的强度、时长接近,这样才能形成节奏。
“情绪”能否构成节奏,需要考察它是否具备这些关键因素。从郭沫若以迄于今,学者们之所以都无法描述或论证“情绪节奏”的真面目,其实就是无法回答上述三个问题。首先,没有学者能找到情绪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其次,假设存在“最小情绪单位”,那么,这些基本单位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来使这些最小单位之间形成“间断”。例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邶风·伯兮》)汉语依靠音步(通常为两个音节)之间存在的可感知的时间停延形成“间断”(朱光潜称之为“逗”)。可是,一段情绪可以像一个语段一样,划分成若干最小单位吗?这些最小单位之间存在可感知的“间断”或某种区别性特征吗?第三,既然无法划分出最小单位,无法找到最小单位之间的“间断”,也就无从调整每个最小单位的强度、时长,异常复杂的情绪,如何能形成反复多次的“规律性再现”?
其实,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诗歌里的情绪,本身几乎没有“规则性”可言。情绪具有突然性、爆发性,有时来无影、去无踪,情绪波动的强度或时间长度通常也毫无规则,可能相当剧烈,也可能因为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突然为之一转,并不像自然界中潮起潮落那样,强度和一个波动周期的时间长度相当,本身就有规律性。例如,《离骚》里面写屈原的情绪变化,还有像《胡笳十八拍》写情绪的变化,感情起伏十分剧烈、无序,决没有那么规则,或呈现出“有规律的重复”。所以除了罕见的个例,情绪本身不可能普遍呈现强弱、高低或长短的规则性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情绪的呈现状态甚至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混乱的,而不是有规律的。
正是由于抒情艺术的取“材”具有这样非理性的无序,所以它才更需要韵律的有序,如节奏、韵等来进行组织或平衡。“柯尔律治认为,诗是自内向外生长的,像植物一样;而格律是外来的,是人为强加给它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也说,诗要像树上的树叶一样,自然生长出来。但是柯尔律治主张要用格律去节制激情,因为激情的喷发是没有形式的,需要用外来的形式去把它平衡一下。”*傅浩:《自由诗》,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英国湖畔派三诗人之一的柯尔律治(译作柯勒律治),其理论主张明显倾向于自由诗,但他注意到诗歌文体的题材、内涵特点和“格律”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在英美自由诗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代表性。中国自由诗派深受英美自由诗的影响,但是,强调了“自然生长”,却忽视了英美自由诗的另一面。虽然英美自由诗内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分歧很大,也存在完全废弃“格律”的倾向,但英美自由诗主要还是主张需要进行“制衡”:“所不同的只是:柯尔律治所用的制衡手段是传统格律(艾略特与此类似,只不过更松弛些);威廉斯和奥尔森们则主张另铸新体而已。”西方自由诗的主流诗人如惠特曼、艾略特、威廉斯、庞德、劳伦斯等,均强调“平衡”“节制”,并且都有“向古典、向形式回归的倾向”。③傅浩:《自由诗》,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苏珊·朗格说:“赋予语言以节奏的强调性发音,发音中元音的长短,汉语或其他难得了解的语种的发音音高,都可以使某种叙述方式比起别的方式来显得更为欢愉,或显得倍加哀伤。这种语言的韵律节奏是一种神秘品格。”*[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299页,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指出,“人们一直在思考着和研究着诗的音韵和诗句表达的意义所起的不同作用……诗造成的效果完全超出了其中的字面陈述所造成的效果,因为诗的陈述总是要使被陈述的事实在一种特殊的光辉中呈现出来。”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140页,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即使英美自由派的主流诗人,对于由语言的音韵特性而形成的“特殊的光辉”或者“神秘品格”,仍然抱有高度敬意,并没有提出诸如“情绪节奏”之类的命题。这和郭沫若、戴望舒等试图以“内在律”“情绪节奏”完全消解汉语诗歌韵律的倾向,存在本质的不同。
刘富华指出:“郭沫若将无形律绝对化了,认为有情调的诗可以不用韵律,即使用,也不过是加强效果而已。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比较片面,因为即使情律不用韵律——行末、句尾的音节不讲究押韵音调,至少也还得与节律配合,而节律也必然涉及音调即行内、句中语词音节的扬抑和顿挫,否则情律就是彻底无形之物了。”②刘富华:《中国新诗韵律与语言存在形态现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刘富华注意到,所谓的“无形律”,或称“内在律”“情绪节奏”等,若不“涉及音调”,“就是彻底无形之物”。换言之,单独的无所依附的“情绪”,根本不能构成节奏。基于这样的思考,即“情绪”至少不可能单独构成所谓“情绪节奏”“内在律”,当代多数学者力求把郭沫若的“内在的韵律”论——实质是反韵律、废韵律论,与传统的音韵论这样一对尖锐的矛盾,进行“整合”。像这样“兼收并蓄”,即试图把当时就尖锐对立的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的主张捏合起来,目前具有相当代表性。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学术界认定郭沫若作为新诗发生时期的重要实践者,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问题是,这样的“整合”,恐怕郭沫若、戴望舒都未必接受,因为他们提出“内在的韵律”“情绪的抑扬顿挫”,根本的目的是反韵律、废韵律。如果“情绪节奏”非得与传统音韵结合,则他们提出“内在的韵律”实际上就失去了它的根本目标,也就失去了必要性甚至正当性,当然也违背了郭沫若、戴望舒的初衷。
但是要指出,像这样无可奈何的“整合”,闻一多、朱光潜、王力等从未考虑,也许他们不需要对郭沫若的废韵论有那么多的顾虑。朱光潜《诗论》1943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1948年中华书局出增订版,后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是中国迄今最为系统的诗歌理论著作。王力的《汉语诗律学》1958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初版,1979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新2版,70余万字,系统地揭示了汉语诗歌尤其是古代汉语诗歌韵律的特征、构成与运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当代最为理性,也最具代表性的诗学专著,根本就不专论无韵诗,更没有讨论所谓“情绪节奏”。
事实上,“情绪节奏”如果始终不能回答构成节奏必须解释的三个问题,它从逻辑上就很难成立,即可能形成一个无法证明的伪命题。如果从实证角度来考察,只要观察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史,打着“情绪节奏”“内在律”“无形律”旗号的极端自由诗派,不但没有留下真正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没有把汉语新诗引向稳健发展的道路。不但如此,只要稍微观察和做一些比较,就会发现,不理会所谓“内在律”的有韵诗,表现要优异得多。笔者曾指出,当代新诗集销售量最大的两位诗人席慕蓉和舒婷,极少写作无韵诗;当代有韵的“歌诗”——包括流行歌曲、民歌等,不亚于宋代“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盛景。③张中宇:《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在理论上始终无法具体描述和证明,与创作实践相对拙劣的表现,应该有助于重新反思所谓“内在律”“情绪节奏”潜藏的废韵、散文化主张及其本身成立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赵小华】
作者简介:(张中宇,重庆市人,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朱寿桐,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5)05-0163-05
【收稿日期】2015-03-16
【基金项目】澳门大学重点研究项目“汉语新文学学术可能性”(MYRG123(Y1-L2)FSH11-2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