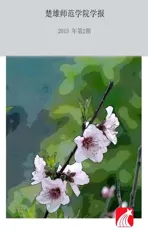从话语修辞看张爱玲的语言风格演变
2015-03-19布小继
布小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话语修辞是说话人或者文学家在说话或者创作过程中如何使用相关的修辞手段来获得最佳的话语文本表现力的问题。实际上,话语修辞绝不仅仅是对话语的技术性处理的问题,也涉及到思想表达和文化内涵的问题,话语修辞的手段与策略直接关乎文本的深度和厚度。
自《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伊始,张爱玲正式亮相于上海小说界。至1978年《色,戒》发表,历时35年之久,其间张爱玲的语言风格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这与她的整体创作风格有何关联?从话语修辞的角度切入,结合她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秧歌》、《半生缘》和《色,戒》,可以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论述和思考。
先看下例: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1](P247-248)
由红色的“杜鹃花”起首,从墙里到墙外,自山上到山下,从一棵杜鹃花到满山坡的杜鹃花,由一小片红到一大片红,整个场景对读者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角冲击力。杜鹃花与海、船作艳异的对照后,再聚焦于白房子,又是一番从外到里、从大物件到小摆设的不厌其烦的描写。视点转换频繁,层次感突出,体现出了张爱玲对立体空间描写的极好的驾驭能力,而色彩的组合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色彩映照出人物心态,作家不仅要给读者一种色彩交汇中的时空错乱感觉,更是对人物外在世界的精心建构。大把大把地泼洒着自己的诗歌化(诗性)、散文化 (散文性)的语言豪情,很有一种撕碎一切重新来过的意味。该段引文的话语修辞特点可以归纳为:浓艳交错的色彩、精致的意象、泼辣大胆的对照以及精雕细琢的词语感触。力图传达给读者的印象是:半殖民地的香港华人富家的生活环境是奢靡中带着迁就,豪华却失之淫乐,非但无法给人以安全感,反而有一种暴发户的家庭缺少高雅文化熏陶、没有自我或者说自我迷失的意味。“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既可以看作是语词的移用、又是感觉的扩张,带有戏谑化、嘲弄性的意味。同时,香港社会中所谓的高等华人在英国主子面前的地位亦可见一斑。展开来看,这和张爱玲在《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等散文中所涉及到的对洋人及西洋文化的理解是一致的——传达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在小说中则是消解西洋文化,对其进行“去势”处理。这在张爱玲前期小说中还有不少例证。
《金锁记》开头由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之心理感触与年轻人的感受做比对,刻意地营造出一种苍凉、艳异的氛围。几次“月亮”描绘,在配合故事进程之同时,彰显了张爱玲良好的色彩感和以景物烘托人物心理的积极修辞方面的本领。与《沉香屑——第一炉香》多用隐喻、象征以表现人物内心的空虚、焦虑和无名目的恐惧相类似,《金锁记》中无论是巨细无遗的华丽的人物服饰描写,还是对话的双关、戏仿,抑或是机警、令人回味无穷的语句,都是对前文中的话语修辞策略延续、发展和扬弃了的结果,即在包括“月亮”等景物描写上极尽阡浓艳丽之能事。目的之一在为故事的发生、发展而张目,之二在于这样的话语极易让读者获得迥异于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通俗言情小说的全新审美体验,而丰富的镜头语言、蒙太奇的使用,又使小说准电影化,闪出闪入。如“二奶奶来了”、 “金山绿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毫无疑问这些语言拓展了小说的文本内涵、扩大了想象空间,是语言张力的巨大释放。对女主人公命运的表现也不似前文可以任凭读者继续加以想象。换个角度看,《金锁记》的话语修辞一方面减少了前文中强烈的色彩对照,增加了不少烘托性的描写以及注重人物刻画的内容,强化了整个故事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金锁记》通过持续释放新话语扭转了读者的阅读习惯,颠覆了读者原来的审美认知。譬如对曹七巧的描写,由年轻时的“有过滚圆的胳膊”到进入老景后能够将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实际上就隐含了曹七巧的一生,她的青春岁月流逝了,她对美好感情的渴望被彻底压抑了,她本是受害者,但大家族的生活环境最终把她变成了一个害人者,她的恶毒并非天生的,而是被形成、被塑造的,她借助自己的家庭权势来无限度地发泄这种恶毒,从而使读者在面对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时不得不充满复杂的感情,无法以简单的善恶美丑来评判。也就是说,读者原来的审美习惯遇到了挑战,只能换个角度重新思考。挑战就是来自于张爱玲描写人物时话语修辞的多变性,即曹七巧在丫头小双和凤箫口中是嫁给残废二爷的粗鄙乡下妇人,贪荣图利,还有小偷的嫌疑。一出场就令满屋子的人难以招架,和季泽的关系暧昧,与娘家人的关系磕磕碰碰。分家时因为被欺负而大闹一场,是弱者。分家后却一步一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保住财产而挥剑斩断情丝,儿女、媳妇、婆家人、娘家人全都“恨毒了她”,因为她的强势使家里鸡犬不宁。可见,曹七巧形象就是被作家的话语修辞充分营建的结果。
1955年,胡适在给张爱玲的回信中认为《秧歌》 “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2](P14)《秧歌》在话语修辞上的特点,可以通过下例得到一些体现:
他用心盘弄着那炽热的大石头,时而劈下一小块来,掷给下首的月香。月香把那些小块一一搓成长条,纳入木制的模型里。她从容得很,放了进去再捺两捺,小心地把边上抹平了,还要对着它端详一会,然后翻过来,在桌面上一拍,把年糕倒了出来,糕上就印上了梅花兰花的凸纹。桌上有一只旧洋铁罐,装一罐胭脂水,她用一支五根鹅毛扎成的小刷子蘸了胭脂水,在每一块年糕上随意地点三点,就成为三朵红梅,模糊地叠印在原有的凸凹花纹上。[3](P157)
这是对金根月香夫妇一起完成上级摊派的劳军任务的叙述,勤苦、温馨而不失乐趣。和《金锁记》相比,显然多了不少平和自然的语言,去掉了许多的修饰,以最为接近人物生活原生状态的方式来刻画他们,细腻、生动、优雅、传神。在话语修辞上逐渐由夸饰性向平实性,由华词丽句向朴实恰切转变,这也是张爱玲前期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如果再结合胡适“最佩服”的段落,即顾冈每天因为吃不饱而要偷偷地吃自己从镇上买回的东西,再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一段及他“从来没注意到 (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2](P14-15),更容易看到此点。实际上,《秧歌》即使写到月亮,也是褪尽了早先的铅华而更有实在感。如妹妹金花结婚当晚,金根连夜回家。 “一路回去,有月亮,所以没点灯笼。走了这么一截子路,离周村远了,在月光中穿过沉寂的田野,金根这时候才开口向老头子说:‘那费同志不是个好人’”,[3](P23)以突出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和金根对生活的直接感受。相反,描绘太阳的话语多了起来,这既可以看作是小说行文的需要,也不妨看作是作家有意识地扭转自己的话语修辞方式之努力。除了必要的景物描写之因素外,如果把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包括《赤地之恋》中的“青黝黝的天空里大半个冷白的月亮。看着那没有时间性的月亮,刘荃心里想他也愿意生在另一个时代。”[4](P56)和“太阳”意象作一个简单比较的话,起码可以发现几点:第一、作为主人公心境的对应物而出现,比如《金锁记》中芝寿死前的月亮描绘,《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安白登死前所见到的“他走到那里,暗到那里”[1](P343)的月色;第二、作为故事进程发展的推动物,如《金锁记》开头。第三、作为故事发展的时间线索,如《秧歌》中的前引段落。“太阳”意象主要是第三种作用。但“太阳”意象的多次出现,也可以证明张爱玲相对前期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动,即不再把清冷、寒凉、皎洁的月亮作为主要描写物,艳异靓丽的话语修辞背后的冷峻、清奇和刻意在世易时移后被逐渐置换成了热诚、平实和稳重。尽管一样的有悲悯情怀,但它的意涵却悄然发生了位移。前期创作中的悲悯里还有不少的冷眼旁观,自《秧歌》起始的后期则有了新的质地。不仅是景与物谐,更多的是情随物移。如《秧歌》结尾“他们缓缓地前进,沿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越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呛呛啛呛呛!呛呛啛呛呛!’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3](P230-231)这样的劳军场面非但没有喜庆色彩,反而是悲凉无比了,却是对死去的金根月香一家的纪念。
1969年出版的《半生缘》(1951年发表并出版的《十八春》之改写版)中,其话语修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的动作虽然很从容,脸上却慢慢红了起来。自己觉得不对,脸上热烘烘的,热气非常大,好容易等这一阵子热退了下去,腮颊上顿时凉飕飕的,仿佛接触到一阵凉风似的,可见刚才是热得多么厉害了。自己是看不见,人家一定都看见了。这么想着,心里一急,脸上倒又红了起来。”[5]这是对有着初次恋爱体验的曼桢心理、神态和动作的描绘,纯粹、简单而直接。曹七巧也有过同样的体验,在季泽倾诉了一番衷肠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1](P148)富有诗意的、延展性、烘托性的语句、用词、语气都可以见出作家铺排、描叙曹七巧时是细致绵密的。由《金锁记》复杂性的话语修辞到《半生缘》简单性的话语修辞,不仅仅是作家的才情发生了变化,更是作家话语修辞上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也和她的创作心态、创作经历、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在《色,戒》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6](P405)尽管这里依然使用迂回描述的方式,借助王佳芝的眼睛看出去,经过了若干路标店铺到了珠宝店,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到无招牌的,叙述时不断回收、由大到小,由扫描、变焦到特写。这种不直接点出珠宝店地点的话语修辞固然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技法,但它也确实扩大了描写的空间,是对常规话语的偏离,又是对《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着重于外在物事色彩敷陈的偏离,这种双重偏离就形成了话语修辞上的新特点:剔除繁琐描写,不断向事物本真靠近;不再致力于寻常意象的翻新和超常规的使用,而是力图在直陈中获得对人物内心的深刻把握;不再对小说话语进行“散文化”和“诗化”的经营,而是回归到了小说语言的质朴上来。也就是说,在张爱玲这里,当语言越来越多地回归到趋向质朴时,她的话语修辞也就由前期的“色彩迷醉”和“苍凉风格”转为平实、妥帖和准确了。靠话语修辞挑战读者审美认知水准、扭转其阅读偏好的做法也一变为借助故事本身的魅力和人物刻画的深度来赢得读者。同样,简洁而有分寸的对话,拿捏到位的心理描写,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人物性格特征。以此而言,张爱玲的话语修辞绝非静态,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的。
众所周知,语言风格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文学创作语言的良好感觉既是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话语修辞策略和手段运用的结果。唯有在话语修辞上精益求精,才能促使自己不断获得新的感悟、有新的收获。同时,可以不断丰富汉语的文学宝库,形成层叠式的语言记忆和累加效果。话语修辞作为语言风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毫无疑问担负着风格建构的任务,话语修辞的使用及其效果,既可以是“立其诚”,也可以是立体系。在张爱玲这里,话语修辞从处女作时色彩缤纷、艳异纷呈到《色,戒》时回到事物本身,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或者说是返璞归真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可以说,张爱玲前期小说之所以会呈现出那样一种样态,与她的厚积薄发——幼年的文学积淀包括《金瓶梅》、 《红楼梦》、 《九尾龟》、《基督山伯爵》等的熟读和香港大学就读时对西洋文学的沉浸濡染是分不开的。少年时期的美术绘画训练和学钢琴的经历激活了她的艺术细胞,1942年5月回国后给英文的《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评论和散文的过程又锤炼了她良好的话语感。和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早期作品类似,对意象的刻意经营、对话语修辞的高度重视、翻陈出新、对篇章结构的把握,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由此,其作品就会呈现出年轻人特有的激情澎湃、感觉洋溢、诗性十足的特征。其后期的作品,之所以会洗尽铅华呈素姿,是对小说话语修辞本质充分认识的结果,抛弃了对诗意和散文意蕴的一味追求,越来越贴近事物本身,追求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对小说的理解超越了前期“参差的对照”。“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7](P12)“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确实有矛盾性的一面,但其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多面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他无疑会过于片面。同时,上述两对矛盾也并非无可调和,依然可以有许多的解决方式。即使是“参差的对照”,也并非一定要排斥前者,此时才高气盛的张爱玲之概括远非完整。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中,张爱玲不仅回应了“域外人”对她的指责,而且特别对文中的许多细节进行了解释说明,针对“域外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富有价值的问题:“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其读了“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一段的“毛骨悚然”之感觉正是作家“企图达到的效果,多谢指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P114-115)显然,张爱玲对人物尤其是反面角色如汉奸一类的理解要深刻了许多,她对“域外人”言论的批驳正是回归到事物本身的结果,即好人与坏人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和鸿沟,写出他们的复杂性和可理喻性才是小说的根本。这样的理解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尽管1978年后张爱玲已经不再创作小说了,但依然可以带给后辈作家许多启示,减少自我摸索所造成的损耗。
综上所述,从话语修辞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张爱玲语言风格的演变过程——由浓艳华丽到逐渐洗尽铅华回归事物本身,这不仅和她的创作心态、生活阅历、思想变迁相关,更和她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小说与生活关系的理解相关。也就是说,张爱玲的文学历练使她越来越回归到小说本体,在主动、自觉的探寻中获得了更深的感悟。语言风格是作家整体创作风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包括话语修辞在内的诸要素的理想配合使得作家在人物塑造、文本思想特点和文化内涵表达的效果上臻于完善。
[1]张爱玲.倾城之恋 [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张爱玲.重访边城 [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张爱玲.秧歌 [M].香港:皇冠出版社,2009.
[4]张爱玲.赤地之恋 [M].香港:皇冠出版社,2010.
[5]张爱玲.半生缘 [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6]张爱玲.郁金香 [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7]张爱玲.流言 [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