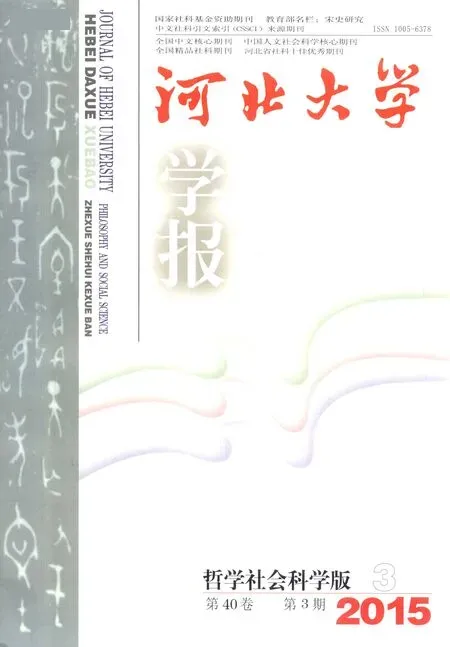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2015-03-19马学良
马学良
(国家图书馆 研究院,北京 100081)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
——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马学良
(国家图书馆 研究院,北京100081)
摘要: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关键词:内府刻书;司礼监;刻书机制
明代内府刻书是中国刻书史上重要的版刻类型之一,这是版本学界的共识。但是关于明代内府刻书的评价,一直以来并不甚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刻书事业在封建社会中一向被视为弘文布道的崇高事业,而明代内府刻书在永乐七年(1409)之后主要由内府机构司礼监负责,所以很多学者直接将司礼监经厂刻书等同于内府刻书。司礼监经厂是一个太监执掌的机构,太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识字,加之太监这一群体在封建社会中特殊的身份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人们“出于对宦官的鄙视,因其人而及其书,对明内府刻本多所指斥诋毁”[1]。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批评明内府刻本《广韵》道:“明内库镂版,缘古本笺注多寡不齐,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数,颇失作者之旨。”[2]潘承弼、顾廷龙认为:“明内府雕版,阉寺主其事,发司礼监梓之,纳经厂库储之,凡所刊者即称之为经厂本……集贤宏业,讬诸刑余,传本当不为世重”[3]。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一书中“古籍版本”一节写道:“经厂本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大黑口,鱼尾相向,大黑双边。字大如钱,多做赵体,醒目悦神。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多作包背装,装帧华美大方。但经厂由太监主持,学识不高,错讹较多。”[4]于是,“校刊不精”几成世人对明代内府刻书的不刊之论。然而,作为明代中央政府刻书和皇家意志的刊布途径,其质量真的如此不堪吗?明代内府刻书在明代刻书事业中的地位与价值如何?笔者认为,欲还明代内府刻书之公允,还须对明代内府刻书的运作机制做一番具体考察。
按照图书编纂时间,明代内府刻书主要可以分为本朝修纂图书和翻刻前朝已有图书两类。由于时隔清代民国,迭经兵燹水火,明代宫廷档案亡佚无徵,明代内府翻刻前朝已有图书的档案也无以稽考。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将修书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亦不例外,故明代统治者在《明实录》的纂修凡例中规定“凡奉敕纂修书籍必书”,这为我们窥见明代内府刻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敕纂修图书的具体运行机制和业务流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依据。
一、组织纂修队伍
明代统治者在政治上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推行与之相应的文化专制政策,力图把全国的思想意识统一到中央层面上来。因此,明代自太祖以降,历代皇帝都比较重视通过图书编纂来传布统治思想,维护皇权。这是中国刻书史发展到明代敕纂修图书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
明代皇帝敕纂修图书的第一个步骤是由皇帝指定纂修班子,即确定纂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一般而言,较大部头的图书修纂活动,会有正、副总裁官总其责,与修人员则可多达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甚至更多。明朝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敕命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徴,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等为总裁官。徵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壎、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上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稽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
可见,这次编纂领导班子的构成,是朱元璋以诏书的形式确定的。除了编纂队伍,朱元璋还对这次纂修活动具体参与编纂的人员构成(征山林遗逸)、修纂目的(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备一代之史)、取材来源(历朝实录、《经世大典》)、修纂原则(直述其事)等各项具体内容都做了详尽地安排。
对于图书编纂工作而言,编纂队伍无疑是直接关系到图书质量的关键因素。明代皇帝敕纂书都是由哪些人来充任编纂人员的呢?这一点,可以从存世的明代内府刻本以及《明实录》中找到答案。在明代内府刊刻的图书卷端,除了常见的目录、凡例等附件之外,一般还会附有皇帝的“御制序”、纂修官的“进书表”以及“纂修人员职名”等。如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朱棣敕纂的一部大书——《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卷端即有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以及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领衔所上的《进书表》,附于《进书表》之后的纂修人员则由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五经博士、庶吉士、奉议大夫、奉训大夫、奉直大夫、承直郎、承德郎、文林郎、承事郎、修职郎、迪功左郎以及泉州、常州、靳州、济阳、善化、镇江等地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数十人组成。
天顺五年(1461)内府刊刻的《大明一统志》则由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彭时以及翰林院学士、奉政大夫吕原联合任总裁官,翰林院学士奉政大夫林文、刘定之与翰林院侍读学士、奉直大夫钱溥任副总裁,纂修人员同样是以翰林院人员为主。
在笔者经眼的明代敕纂书中,无论是主持纂修图书的总裁,还是参与人员,基本上与上述两书结构类似,即纂修队伍为朝廷中的文学之士与朝廷征召的山林宿儒组成。
在明代,不但图书编纂活动伊始就由皇帝定好组织、人员以及编纂基调,而且整个纂修过程也往往受到皇帝直接关注,并不时对编纂活动作出明确指示。在传世的明代内府刻书中,《大明会典》就是这样一部由皇帝敕纂,并经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皇帝多次过问纂修而成的图书。在万历十五年(1587)内府刊刻的《大明会典》一书正文之前,“御制序”后附有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弘治十年三月初八日、正德六年四月初十日、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及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敕谕五篇。详细记录了皇帝对修纂此书所做出的谕示。弘治十年(1497)三月初六日,明孝宗任命少傅兼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迁为总裁官;任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兼左春坊左谕德王鏊、侍讲学士杨守址为副总裁官,开始修纂一部“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的图书。仅隔两日,孝宗再次颁发圣谕,亲自为这部书确定了名称——《大明会典》,敕谕内阁。在修纂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弘治皇帝多次调配人员,充实《会典》一书的编纂力量。弘治十年八月,将太常长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侍讲学士焦芳二人补充为修纂副总裁。除了动员在京翰林院、左右春坊、国子监等机构的力量之外,还征召起复外地官员及因病修养官员进京同修纂,启用专门的誊录译字官协助修纂,从人力方面保证了《会典》一书的正常进展。但是,此书尚未完成而孝宗崩,于是武宗即位后重加校正,于正德四年完成,李东阳等具表以进;正德六年正式刊布天下。嘉靖间,世宗以正德刻本“纪载失真,文辞抵牾者比比有之”*《重修大明会典》卷端“皇帝敕谕内阁”。。乃令各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如有差错,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然世宗命儒臣续修之《会典》,起自弘治十五年,止于嘉靖二十八年,虽经进呈,而并未刊布。万历间,神宗以嘉靖续修之本“讫未颁行……且自嘉靖己酉而来,又历二十余载。中间事体,亦复繁多。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尠谙国体。法令数易,条例纷纭”*《重修大明会典》卷端“皇帝敕谕内阁”。。故又命儒臣重加修辑,芟繁正讹,终成万历十五年二百二十八卷本《重修大明会典》。
通过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明代敕纂修书籍的编纂完全是在皇帝掌控之下开展的图书编纂活动,从纂修官到参与纂修队伍的组成均是经过皇帝指定的御用“编辑”,而且所编书籍从取材来源到大致内容,从去取标准到思想主旨均要按照皇帝旨意进行。
二、图书审定
根据《大明会典》规定,皇帝敕修的书籍编纂工作完成后,还不能直接交付工匠锓版,而是要首先进呈皇帝御览审定。
进呈敕纂修图书是明代朝廷中的要事。一般要由该书的正、副总裁官领衔先写一道《进书表》,与预修图书一同按照严格的礼仪规范进呈皇帝御览。对此,《大明会典》有专门的记载:
凡纂修书籍进呈,前一日内执事官设案于文华殿内稍东,至日早朝退,上御文华殿。鸿胪寺官设表案一,书案一,于左顺门内当中,纂修官捧表并书各置于案。鸿胪寺官四员举案,二员前导。锦衣卫设伞盖二,具随案行,由文华门中门入,纂修官后随,从二门入,至丹陛上。鸿胪寺官举表与书案由中门入,置于殿内正中,出。赞四拜,礼毕,鸿胪寺官二员,从左门入,举案进上前,出。赞进表,纂修官一员,从右门入,取表进上前,展表,俟上览毕,收表至于前案。赞进书,纂修官取书进上前,展书,俟上览毕,收书至于前案,出就班。鸿胪寺官六员,由左门入,二员撤御案,四员撤表与书案,各置于殿内东,出,赞四拜。礼毕退。内执事官收所进表并书。*〔明〕徐溥等:《大明会典》卷七十三,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六年(1511)内府刻本。
进书礼仪隆重庄严,其实质在于纂修官向皇帝汇报纂修结果,请皇帝御览裁定。
但是,有时纂修官所进书籍也有可能不完全合乎皇帝心意,不能通过审查,也就无法刊行。据《明实录》记载:
万历九年四月乙卯。户部进《万历会计录》。先是,尚书王国光辑部中前后条例,编纂成书,濒行奏上,请刊布中外。上贤之,嘉其留心国计,命户部再加订正。至是,书成。凡四十三卷,名《万历会计录》,部臣誊写进呈,仍乞刊布。上命留览,依拟刊行。仍送使馆采录。*《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一。
显然,王国光所编纂进呈的私纂书籍最初得到了神宗的鼓励,但是神宗对于内容并不满意,故又“命户部再加订正”。但是订正之后的《万历会计录》似乎仍未达到神宗要求,故只是“拟刊行”,并需继续送史馆采录。
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皇帝对于敕纂修书籍的审查是一项例行的环节,所有敕修书籍都要据表进呈。通过审查环节,如果皇帝满意,就会御制序文一篇,冠诸卷首,以示审查通过,准予刊行。
三、图书刊刻
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是由多道工序连个构成的。这一点从《大明会典》所记载的各地轮班工匠中有刊字匠、笺纸匠、印刷匠、摺配匠、裱褙匠等多个工种也可以看出*参见《大明会典》。。
(一)书写版样
首先,编辑定稿的书籍需要书写清样。清样是用来贴到木板上供刻工影照刊刻的,所以一部书籍的质量好坏,与负责书写上板的人员素质关系尤重。因为这涉及书写的质量,即是否会出现讹、脱、衍、倒;还涉及到书籍刻成后的艺术水准,如字体是否优美,行格是否疏朗等问题。
关于明代内府刻书书写上板这一环节的记载史料不多,目前笔者所见仅有两则:一是明太祖《御制文集》中有朱元璋为《相鉴》一书所作序文一篇,称该书“于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营缮成书,令工刊就,以利后人”*〔明〕朱元璋:《御制文集》,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根据这条信息,可以确定《相鉴》一书是由翰林院儒臣书写的,由此推论,其他内府刻书也有可能由翰林院的儒臣来完成。另外一则信息是嘉靖九年(1530)内府刻本《大明集礼》一书每页版心下方均有“儒士某某写”,此处称为“儒士”者,显然不是宫内太监或一般工匠,而应该是翰林院儒臣或者国子监儒生。据此推算,负责内府图书书写上板的人员素质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个群体。
从现存内府刻本来看,绝大多数内府本的字体工整秀丽,非普通书坊刻书所能望其项背,大概与此有关。
(二)刻板
刻板又称镂板,雕版印刷中指在木板上刻字(或图),从而形成印刷用的底版的过程。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明代内府刻书的具体负责机构这一问题存误最深,认为负责内府图书刊刻的仅有内侍机构司礼监下设之经厂,故往往将内府刻书直接等同于司礼监刻书或者经厂刻书。
事实上,司礼监经厂负责内府刻书始于明永乐七年(1409),之前则是由工部与早期内侍机构内官监负责。且即便在永乐七年(1409)之后,司礼监也并未独揽刻书事宜。纵观有明一代,参与过内府刻书的机构,除了工部、内官监与司礼监经厂之外,还有秘书监、钦天监、礼部等中央机构,甚至还吸纳了地方书坊、寺庙等力量的参与。关于明代内府刻书的具体机构,笔者已于《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5]一文予以探讨,兹不赘述。
四、印刷装帧
(一)印刷
既然内府刻书的负责机构并非仅有司礼监一家,而是由明代中央各府、部、监、院与内府各相关机构联合完成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按照其刻书单位来称谓他们刊刻的图书呢?这还要从内府刻书的书板管理机制说起。
现有文献可以证明:明代各个机构负责刊刻的书籍,在镂版完成以后,书板均需交由内府管理。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的记载。刘氏称司礼监经厂库所藏为“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而其后所列“有板”图书,实际上是司礼监经厂库所现有的图书板片,而并非印成的书籍,其计量单位以“叶”计可以证明,一叶即一块书板。这些板片中,不仅包括了历代司礼监所刻板片,也包括《明实录》中明确为礼部刊刻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史馆刊刻的《明伦大典》等中央各部所刻之书的书板。据《明实录》载:
成化十三年冬十月乙未……南京钦天监监副贝林等奉敕修《大统历》、《回回历》成,刊印进呈。上曰:“礼部移其文,令以刊板送京。”*《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另外,弘治年间,内阁大学士丘濬曾在奏疏中说:
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超出万古帝王之上。御极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裹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词臣之比也。今颁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虽已编类,刻板藏在内府,天下臣民得见者尚罕。*《明孝宗实录》卷六十三。
可见,各刻书机构在雕版工作完成后确实是要将书板交往内府管理的,而且这一制度在洪武时期已经形成。
司礼监经厂成立之后,专门设置了相关人员对内府书籍板片进行管理,《酌中志》云:“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6]这样一来,内府机构司礼监既是内府图书的刊刻机构之一,还同时成了所有图书板片的管理者。既然板在禁中,内府图书的印刷在宫内完成则是情理之中了。
但是,太监群体毕竟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群体,这注定他们不能从根本上重视文化。随着万历皇帝后期的昏庸,不理政事,司礼监经厂库的管理也日趋混乱,书板损毁严重。对此,《内板经书纪略》记述说:
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秩,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或占空地为圃,以致板无晒处,湿损模糊,甚或劈经板以御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板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十减六七矣。[6]
此中所云,“有宝图书”指已印制好且钤印的图书;而御寒所劈经板则为雕刻好的图书板片。
(二)装帧
书籍至明代,所流行的装帧形式已经是包背装。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内府刻本来看,除了宗教类图书仍有经折装之外,内府刻书大部分使用的是包背装。
包背装的制作过程是将印好的书叶子以版心为中轴线、以有字的一面向外对折,即版心朝左向外,文字对人,将一叠折好的书叶摞好对齐,这就是所谓的“摺配”;配好的单册书籍以纸捻订固,再用一张较厚的硬纸按照书脊厚度双痕对折,用浆糊粘包住书背(书脊),即所谓“包背”。司礼监工匠中有所谓“摺配匠”“包背匠”,说明内府刻书的装订已经完全专业化了。
永乐间所刻佛经单本,也多做包背装,如永乐十五年(1417)至十八年(1420)所刻的《神僧传》《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感应歌曲》等均为包背装,且厚度达到六、七厘米,内府使用包背装技术之纯熟可窥一斑。
五、发行
明内府修纂之书数量之多、涉猎之广,可谓空前。其修纂的主要目的在于颁示天下,广为流传,所以除起居注、历代实录、《永乐大典》等书仅有抄本外,大多都由内府予以刊布。
内府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其发行权在皇帝。据《明实录》记载,几乎所有皇帝敕命纂修的图书都是经过皇帝命令颁行的。如:
洪武三年九月乙卯,修礼书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所该之目:吉礼十四,曰祀天、曰祭地、曰宗庙、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农、曰太岁风云雷雨师、曰岳震海滨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马祖先牧马社马步、曰祭厉、曰祀典神祗、曰三皇孔子;嘉礼五,曰朝会、曰丹拜、曰冠礼、曰婚礼、曰乡饮酒;宾礼二,曰朝贡、曰遣使;军礼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凶礼二,曰吊赙、曰丧仪。又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各一,乐三,曰钟律、曰雅乐、曰俗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缄悉备具,通五十卷,诏颁行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六。
为了表示所颁书籍是皇帝诏准发行的官本,明代统治者还将广泛用于诏书的“广运之宝”钤于内府所刻图书之中。这一做法给版本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赵国璋、潘树广在描述经厂本特征时说:“经厂所刻书多为大本子……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册首或钤有‘广运之宝’朱文玺印。”[7]曹之在述及经厂本的版式特征时也说:“(经厂本)册首多钤‘广运之宝’印。”[8]
其实,除了“广运之宝”,明代皇帝从朱元璋起就专门在玺印中增制了“表章经史之宝”和“钦文之玺”两枚御玺用于经史图籍*《明史·职官志三》。,这两枚御玺在今天传世的内府刻本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另外,笔者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嘉靖六年(1527)内府本《大学衍义》中钤有“亲亲之宝”玺印,则应系皇帝颁赏宗藩图书所用。除了皇帝玉玺,对于必要的图书,还需要后宫表态支持,故我们还能在传世的内府刻本中见到明代后妃的宝玺。如存世的永乐五年(1407)内府刻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卷前附有永乐三年(1405)二月初九日徐皇后自制《劝善书序》,该序末尾落款处一般钤有“厚载之记”;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处所藏嘉靖九年(1530)内府本《女训》一书则同时钤有代表嘉靖皇帝生母蒋氏的“章圣慈仁皇太后宝”与代表皇后的“中宫之宝”。
帝后宝玺用于内府刻书代表的含义是皇帝诏准颁行,与藏书印用于书籍收藏代表图书所有权截然不同。
六、结论
通过对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考察,可以发现:明代内府刻书并非仅指雕版印刷一个环节,而是包括了从组织纂修队伍,到皇帝审定图书,再到写书上板、印刷装帧,最后由皇帝诏准发行的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流程。在这一过程中,皇家是刻书的主体,翰林院儒臣与地方宿儒是敕纂修图书的御用编辑,所刻图书的发行是借助国家权力颁行天下,从而保证明代统治者所倡导的文化与思想意识能够传布天下,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内府刻书的实质是皇家的刻书,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国家级出版活动。
在明代内府刻书的运作流程中,作为内侍的太监只参与了司礼监经厂刊刻书的管理工作以及其他部门所刻书板的管理工作,因此,明代内府刻书谈不上“阉寺主其事”,内府刊刻图书的质量好坏,也基本与太监无关。相反,明代内府刻书作为明代皇家刻书,于当时政令、制度、史事记载尤为详实,值得引起文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3.
[2]朱彝尊.曝书亭序跋[M]//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
[3]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157.
[4]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33.
[5]马学良.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42-46.
[6]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57.
[7]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581-582.
[8]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45.
【责任编辑王雅坤】
Examination of Woodcut Print Mechanism by Imperial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Compiling Books of Imperial Order
MA Xue-lia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Ming Shi-lu and Da Ming Huidia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mpiling books of imperial order in Ming dynasty, and clears about that woodcut Print in the court of Ming Dynasty is a kind of national publishing activity including a set of business process of compiling,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organizing, binding and distributing. Its essence is the imperial woodcut Print of Ming dynasty. The eunuch only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woodcut Print of Silijia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but has litt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quality of woodcut Print of court.
Key words:the Woodcut Print by Imperial; Silijian; woodcut Print mechanism
作者简介:马学良(1980-),男,河北枣强人,管理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版本学。
基金项目:国家图书馆2014年馆级课题《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内府本研究》(NLC-KY-2014-19)
收稿日期:2015-02-22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3.015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5)03-008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