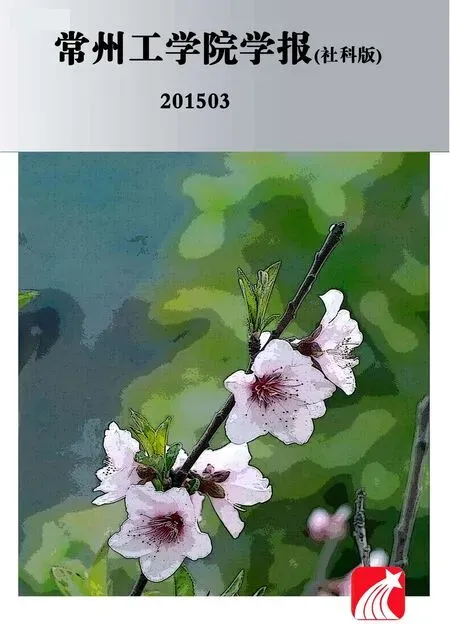《S.》与《红字》的互文性解读
2015-03-19臧晓虹
《S.》与《红字》的互文性解读
臧晓虹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摘要:作为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S.》以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为前文本,从海丝特的视角出发,叙述了莎拉——现代版海丝特在当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命运和困境。文章从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两性关系的角度对《S.》和《红字》进行互文性解读,探讨美国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转化性,揭示两位小说家在宗教观、价值观等方面的交会与相异之处。
关键词:厄普代克;霍桑;《S.》;《红字》;互文性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5.03.011
收稿日期:2015-03-18
作者简介:臧晓虹(1969—),女,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5)03-0050-04
当代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与19世纪浪漫主义大师纳撒尼尔·霍桑相隔百年,以“《红字》三部曲”续写了霍桑的经典名著《红字》,并以此表示他对前辈的敬爱之情。厄普代克的三部曲,即《全是星期天的一个月》(1975),《罗杰的版本》(1986)和《S.》(1988)分别从《红字》的三个主要人物——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和海丝特的视角出发,叙述了《红字》主要人物在当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命运和困境。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37厄普代克的当代作品《S.》作为《红字》的后文本,在深层次体现了对前文本《红字》的吸收、转化、扩展,乃至反叛。毋庸置疑,一方面,《S.》中蕴藏着霍桑时代的文化基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发展,《S.》又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差异性,表现为对前代文化的反叛和背离。
《红字》和《S.》有着共同关注的主题,如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矛盾,性别间的冲突等。对前后文本的互文性解读有助于挖掘两部作品所蕴含的相同的文化因子和因时代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发展及转化,探索两位小说家在价值观、宗教观等方面的契合、延续以及差异、改变。
一、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矛盾
霍桑和厄普代克都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作为清教徒的后裔,霍桑曾说:“他们刚强的秉性与我的性格水乳交融。”[2]251事实上,他的作品蕴含着浓厚的基督教思想。厄普代克曾多次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对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境遇和发展有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宗教情怀,厄普代克的小说《S.》和它的前文本——霍桑的代表作《红字》都涉及了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矛盾这个主题。
《红字》以17世纪的英国殖民地波士顿为背景,而实际上霍桑旨在影射他自己所处的时代——19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此时,清教思想逐渐走向衰落,盛行的超验主义进一步动摇了清教主义根基。爱默生的“超灵”论认为:人可以通过感受每个人心中存在的“超灵”而把握人性中的神性,因为除了个人完整的心智之外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超验主义不仅打击了上帝以往独有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肯定人的作用和价值,而且它还发展成为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哲学基础。霍桑一生坚信清教教义,接受上帝的绝对权威,相信人的“原罪”,拒绝超验主义思想。在他的多部作品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最终都结局惨淡。《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便是一例。她藐视教规及法则,因通奸罪而被迫佩戴红字,可她内心却从未屈服过。在她看来,“世俗的法律并不是她心灵的法律”[3]241,“我们做过的事,有它本身的神圣性”[3]265。海丝特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用自己的行为阐释爱默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当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产生冲突时,“相信自己”的海丝特选择了个人自由。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是一名长期传教、富有威望的牧师,熟稔清教教规,却在个人欲望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中顺从了自己的个人欲望。直至丁梅斯代尔死亡时海丝特才有所悔悟。小说这样的结局安排显然是霍桑对个人主义信条的反击,对当时超验主义者们的盲目乐观倾向的回应。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从1835年爱默生首次提出“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到厄普代克创作《S.》的1988年,150多年过去了,个人主义也已演变、发展成为美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厄普代克的《S.》也表达了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一主题,无疑它既是《红字》同一主题之延续,又因时代的变迁而带有明显的差异性。《S.》从《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的视角来叙述,其女主人公莎拉则是现代版的海丝特。42岁的莎拉是一名中产阶级家庭妇女,丈夫的背叛和生活的空虚使她离家出走。为了寻求个人自由和信仰,她抛弃富裕舒适的生活,来到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的印度教避居地,体验集体崇拜的群居生活。自以为找到精神家园的莎拉想开启新生活、重建新世界,却发现一切都是骗局,她所崇拜的宗师阿汉特不过是个骗子。
莎拉和海丝特都是追求个人自由的女性,海丝特为了个人自由不惜违背清教教规,而莎拉抛弃代表过去的舒适生活和传统宗教,决定到“在我父母把我养育成人的那个已经衰老的基督教僧侣统治之外的任何地方找到自由”[4]102。霍桑和厄普代克都在哀叹传统宗教信仰的日益衰落,然而霍桑始终坚信清教的力量,海丝特发自内心的从善的后半生不仅是有力的证明,也是霍桑给人类的美好希望。生活在20世纪的厄普代克在发出无奈的哀叹声之外更多地表达了他的绝望之情。莎拉的离家出走是对基督教信仰和家庭传统的挑战,“向这个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垃圾社会挑战”[4]112。避居地成为她心目中的精神圣地,在那儿她充分享受着个人自由和精神宁静,然而她早就跌入了那个“一心只追求金钱和物质的美国式的陷阱中了”[5]110,非但不能自拔,还丝毫没有察觉,也就根本不可能自救。莎拉利用管理财务之便私自挪用公款,将其全部转入自己的账户。可见,传统宗教早已被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挤出历史舞台,在人们的头脑中荡然无存。
虽然霍桑和厄普代克都对美国传统宗教在他们各自时代的衰落表现出关注和忧虑,但他们对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持有不同观点。霍桑接受了清教的基本教义,把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置于不可调和的状态。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都因为追求自我、抛弃宗教教义而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同厄普代克所说:“霍桑从基督教中接受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并且吸收得较为彻底……霍桑的内在信条是灵与肉始终处于不可避免的战争之中。”[6]76个人主义在美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基督教也从没停止其日益世俗化的脚步,厄普代克在解释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时融入了个人见解和时代气息,奢望能将两者调和起来。莎拉带着寻求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双重目的离家出走,在避居地她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虽然每天要艰苦劳动12个小时,她却慨叹“感到自由”[4]46。她的宗教信仰也没有阻碍自己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在避居地她先后与弗里兹、阿卡林和精神领袖阿汉特建立了亲密关系。她一度以为在阿汉特身上获得了灵与肉的双重满足,最后却发现只是一场骗局。在个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上,厄普代克没有采纳霍桑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他欲调和两者关系的奢望终被压倒一切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扼杀了。
二、两性关系的矛盾
《S.》是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更多地谈到女性问题和两性关系。霍桑和厄普代克创作的盛期正好分别处于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饱含同情地描写了女性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反驳了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过激的言论和行为。霍桑和厄普代克在女性问题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和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他们又表现出更多的差异。这些在《红字》和《S.》中有明确的体现。
由于继承了欧洲的父权文化传统,美国长期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美国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一直进行不懈的斗争。霍桑发表《红字》的1850年正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蓬勃发展的年代,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宗旨是妇女解放,使妇女获得政治权利。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超验论者玛格丽特·富勒。她在1845年发表了美国第一部反映女性问题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女性》,提倡女性的自立和自我修养,强调两性平等。富勒驳斥男人是女人监管人的思想,认为男女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她在书中写道:“不存在具有完全男子气概的男人,也没有纯粹女性气质的女人。”[7]255富勒还在书中提出了女性独身这一理念,她认为女人需要很多时间完善自己,而结婚则使女人受困于家庭和感情。霍桑对富勒的代表作《十九世纪的女性》的评价是否定性的:“它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总的说来显得太不高尚,我认为玛格丽特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东西。”[8]235霍桑用海丝特的故事讽喻了富勒的女权思想。《红字》中的海丝特具有女权主义者的特征。和其他传统女性不同,海丝特经济独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她开始了对女性权利的思考,而在霍桑的描述中,正是海丝特的这种思考让她失去了女性特有的美和精华。霍桑在《红字》中写道:“海丝特所给人的印象是如大理石一般地冰冷,这大都是源于环境的关系,她的生活大部分已由热情和情绪转向到思想上去了。”[3]240海丝特认为两性关系之间的变革必须是彻底性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社会整个的体系,重新来建树。其次,男人的本性,或者说男人已变成本性的长期遗传的习惯,必须要根本改造”[3]242。对于这种彻底变革的女权思想霍桑是极力反对的,他写道:“一个女人,无论怎样发挥思想,也从来克服不了这些难题。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或者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如果女性的感情能够占有绝对的优势,那时这些问题便消失了。”[3]242霍桑认为富勒所藐视的女性的感情和亲缘关系却正是女性的价值和精华所在。
在《红字》中,霍桑表达了他对海丝特的同情和偏爱,她的美丽、善良、坚韧和助人的品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海丝特的悲惨结局也反映了霍桑对女权运动的复杂态度,他同情女性在父权社会的不幸遭遇,却不能接受女权运动中在他看来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比如抹杀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女性独身等理念。厄普代克在女性问题和两性关系上和霍桑一样有着复杂的态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断断续续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这一时期正是厄普代克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他对女性问题和两性关系的思考。距离霍桑时代一百多年过去了,海丝特所期盼的建立起男人与女人双方幸福的新关系这样的理想在美国并没有实现。在厄普代克的《S.》中,莎拉——现代版海丝特仍然生活在父权社会的束缚之中。她受父亲逼迫嫁给医生查尔斯,为此她放弃了大学学习和攻读研究生的机会。22年的家庭主妇生活中,她“辛辛苦苦,尽心尽责做事,不领分文工资”[4]60,却遭到丈夫的背叛和漠视。为寻找个人价值和信仰,她离家出走来到沙漠地带的印度教避居地。莎拉希望在避居地建立新型的男女关系。在避居地她先后与弗里兹、阿卡林和阿汉特建立亲密关系。弗里兹是莎拉产生婚外情的第一个男人,他给予莎拉的不是冷落和疏离,而是对她肉体和灵魂的由衷赞美,从弗里兹身上她得到了自信。在与阿卡林发展的同性恋中,莎拉扮演了男性的角色,称自己为阿卡林“情意炽烈的王子”[4]169,完全摆脱了自己在父权社会中的被动地位。在与避居地宗师阿汉特的恋情中,她仿佛找到了想要的一切,阿汉特使她体验到肉体和灵魂的和谐统一,激发了她的女性力量。在避居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性爱中,女人都处于主导地位。莎拉以为在避居地建立了理想的新型男女关系,却发现一切都是骗局。最后,莎拉独自来到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上,像海丝特一样住在孤零零的小屋里,“呆呆地望着远方,仿佛追随着那虚无而去了”[4]267。厄普代克对莎拉在父权社会不幸境遇的详细描写反映了他对女性的同情,而莎拉的追求和反叛是一场虚空的结局又表明了他对女权运动激进派的不满。激进派所主张的以群居来代替婚姻家庭,女人要男性化以及对同性恋的提倡都在《S.》中有所反映,厄普代克以讽刺的口吻质疑了激进派的某些极端理念。
海丝特和莎拉在父权社会遭受的压迫、她们的反叛以及最后的结局都有相似之处,反映出两位作家既同情女性,又反对女权主义的过激言行的中间立场。厄普代克没有采用霍桑《红字》中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而是采用第一人称,赋予女主人公话语权的叙事视角,体现了莎拉直抒胸臆的现代女性特征,莎拉也由此呈现出比海丝特更复杂的现代性。
三、结语
《S.》是厄普代克与霍桑跨越时空的对话,霍桑和厄普代克都关注了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两性关系等话题。两位作家对这些话题的思考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美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如两部作品都描写了宗教信仰在个人自由追求中的衰落,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等;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两位作家价值观的不同,他们在探讨这些话题时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对《S.》及其前文本《红字》进行互文性解读,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两个文本的理解,有助于梳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探索在两位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转化。
[参考文献]
[1]Kristeva J.Word,Dialogue and Novel[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2]兰德尔·斯图尔特.霍桑传[M].赵庆庆,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侍桁,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4]约翰·厄普代克.S.[M].文楚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Schiff J A.John Updike Revisited[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8.
[6]Updike J.Hugging the Shore:Essays and Criticism[M].New York:Alfred A Knopf Inc,1983.
[7]Fuller M.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Inc,1998.
[8]Miller E H.Salem is My Dwelling Place:A Life of Nathaniel Hawthorne[M].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1.
责任编辑: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