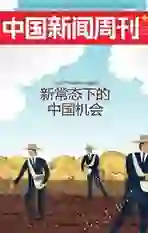“精准医学”的未来
2015-03-18
2015年1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一项名为精准医学的计划,打算通过分析100多万名美国志愿者的基因信息,更好地了解疾病形成的机理,进而为开发相应的药物、实现精准施药铺平道路。
精准医学在时间上是承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而在本质上是对现行的以药物治疗为主体的医疗进行根本改革,因而将影响和改变未来的医疗、药物研发和临床使用。
奥巴马在宣布精准医学计划时对其作了解释,即“基于患者的基因或生理来定制治疗方案”。唯一一位既参加起草1987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报告,也参与了“精准医学计划”报告撰写的科学家——华盛顿大学的欧森博士认为,精准医学就是强调个性化,这实际上应该是医学实践的正常形式,分子水平信息的正确使用会使医学更加精准。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科学部副主任乔·汉德尔斯曼则称,精准医学是“一种考虑人群基因、环境、生活方式和个体差异的促进健康和治疗疾病的新兴方法。”
种种解释都意味着,基于每个个体的基因差异而进行的个体化治疗才是有效的,也更有效率,因而称为精准医学。正如要根据一个人的身高和胖瘦来量体裁衣才能制作出合身的衣服一样。
显然,精准医学对医药的革命首先是观念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预期是,根据精准医学的概念,未来的药物将会针对每个个体或一小群人进行定制,目前这种一类药物的大批量生产,以及患同一种病后所有人都服用同一种药的局面,将逐渐式微或被淘汰。今天,精准医疗、个体基因组研究等科学进步为精准用药、少用药和有效用药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科学基础。
为此,有人提出“需要治疗的病例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NNT)”这一概念并进行实践。NN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针对临床药物的评价指标,指的是有多少人接受治疗或预防(服药)才能确保其中一人有效或受益。
经过大量的临床调查,NNT显示药物治疗效果的低下令人吃惊。例如,如果2000人每日服用阿司匹林,坚持2年以上,才能防止一起首次心脏病突发事件,即NNT为2000。同样,当哮喘病发作时,有8个人使用类固醇药物,才能避免一次入院,也即对一个人有效,NNT为8。如果鼻窦炎发作,15个人使用抗生素,只有其中1例会改善或治愈,所以NNT为15。原因在于,尽管所有患同一种病的人都在吃同一类或同一种药物,但是,每个人的基因是不同的,这也证明,世界上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绿叶。
人们会感到奇怪,阿司匹林、类固醇药物和抗生素不是公认的治疗(预防)心脏病、哮喘和鼻窦炎的有效药物吗?为何它们的实际效果对不同个体差别如此之大?实际上,人们虽然在患病后服了药,但却未必是药物治好了疾病,很多人的痊愈是机体的自我修复所致。这也证明了霍姆斯的判断,很多药物是人类不需要的,因为不是精准用药,所以对治疗疾病无效。从NNT的角度来看,在一般临床治疗中,NNT达到30就相当不错了,低于10的则比较少见。
早在奥巴马宣布精准医学计划之前,这一理念就在癌症的临床治疗中体现出来了。例如,癌症的个性化和靶向治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过度表达HER2蛋白的侵袭性乳腺癌亚型,随后,针对这种亚型乳腺癌的药物——曲妥珠单抗研发了出来,并于1998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使用,曲妥珠单抗治疗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就是首个癌症分子靶向治疗——虽然那时并没有明确的精准医学的概念。
在奥巴马宣布精准医学计划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病人——比尔·埃尔德。这名病人本身是一名27岁的医学生,他患有G551D突变囊性纤维化,在患囊性纤维化的患者中只占4%,正是由于服用了针对罕见的G551D基因突变的药物Kalydeco,埃尔德才获得救治,这种新型的靶向治疗是精准医学的具体体现。
显然,精准医学计划的实施意味着精准研发和使用药物时代的到来。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许还有很漫长的道路。以Kalydeco这种药物为例,其服用一年的费用高达30万美元,因而《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索性称之为——“30万美元药片”。
文/张田勘
学者,资深媒体人,著有《生命存在的理由》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