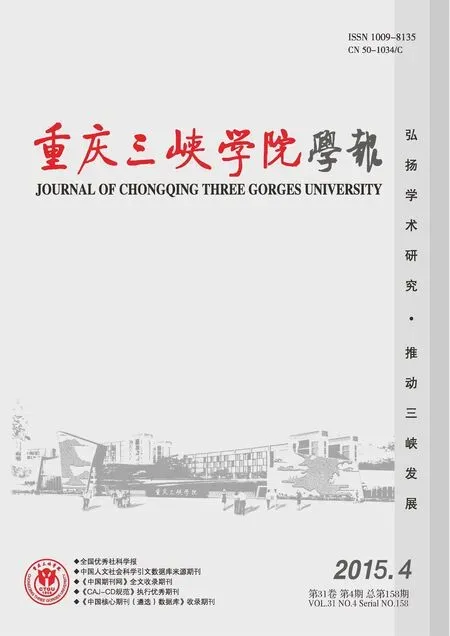浅谈“五四”之“反传统”
2015-03-18陈亚琼
陈亚琼
浅谈“五四”之“反传统”
陈亚琼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062)
五四文学产生的文学意义,不仅局限在对新文学新思想的倡导,更是打破了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间对话的隔膜,搭建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间的沟通桥梁,实现了文学自身现代意义的转型。
五四文学;传统;反传统;胡适;周作人
学界有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对旧文化且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的,即“全面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和“全盘西化”。显然,这一观点并没有用辩证的眼光正确看待“五四”之“反传统”。“五四”之“反传统”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反思,包含了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和情感在内。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在对传统重新认识并加以借鉴改造的基础上,现代文学的转型才得以实现。
一、何为“五四”之“反传统”
如果将传统文学单纯理解为与现代文学相对的文学形态,那么由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维新文学,就是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进化所必经的初始阶段。传统文学孕育了维新文学,而五四文学作为维新文学的延伸和拓展,以其更为明确的现代性要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五四”之“反传统”,不是,也不可能是彻底地与传统割裂,更多的是传统文学不断发展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特定表现。
“传统”是相对“现代”而言的,五四文学从思想内容到具体形式都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现代性,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受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思潮影响,故将人性解放作为第一诉求。五四初期由北大创办的《新潮》期刊,它的英文刊名是,即“文艺复兴”。发表其上的作品,从文学目的、创作原则到具体实践,都呈现了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样态。但由于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人性的解放,又自觉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能。
二、“五四”如何实现其“反传统”
五四新文学素以白话文的提倡,以及“人的文学”的发现这两方面的突出贡献成功挑战传统文学。但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五四文学反传统的最好说明。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从“八事”入手,认为“第一,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为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现在才步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第二,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1]胡适所说的第一点是针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学从诗经、楚辞发展到后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种文体臻于完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当时代环境发生改变,会促使在先前颇为兴盛的某种文学形态孕育下的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新出现的文学形态会被同样的方式取代,从而推动文学一直向前发展。因此,断言文学发展的趋势在于向着白话前进,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把这种断言作为发起白话文运动的原因,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是无法确定将来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文学形态具体是怎样的,最多是依据文学发展规律做出预测。当社会主流需要一定的文学形态时,这种适宜的文学便会应运而生,即便是要克服各种顽固障碍。正是时代的变化使传统文学选择白话文作为自己生命力的延续,白话的提倡志在必行。胡适所阐释的第二点,指出白话相对于古文而言的优势。白话当然是活的了,毕竟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提倡白话文的原因并不在此。周作人曾经对胡适这一观点进行辩驳,“古文和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而且一句死了的古文,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说是由于这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很多古句中的字还都时常被我们运用,那么,怎么能算死文字呢?”[2]这同样说明了提倡白话,不是古文本身出现了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需要。
1918年12月《新青年》5卷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他明确指出应该提倡新文学,简言之就是“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文学”。他所强调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而是指从“动物”进化的充满兽性的人和从动物“进化”的充满灵性的人这两方面的结合,即人是“灵肉一致”的。因此,封建纲常和传统礼教中那些对于人性压制和扼杀的内容是新文学所反对的,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于私欲情欲的正当表达是新文学所提倡的。在之后的《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主张。可以说,周作人是从思想内容的层面对于胡适从语言形式层面的变革给予支持和补充,从而丰富和完善了新文学理论的建设。但当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时会发现,早在诗经中就存在着揭露黑暗的作品。比如流传最广的农事诗《七月》,全篇详细记录了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情况和艰辛劳作,无疑是一种有力控诉。除了保存于书面的文字,还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像梁山伯祝英台双双化蝶,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虽然他们不被允许在现实中相守到老,但富于神话色彩的结局也正表现了人们的理解与肯定。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只不过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压迫下微弱地喘息着。直到周作人将其挖掘出来供人警醒的时候,“人的文学”才第一次以完整清晰的面貌被世人所知。
五四新文学的创建者们在倡导新文学的时候,这种反传统的态度似乎过于激烈。或许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又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毕竟,培育五四新文学主要建设者的土壤仍是传统文学。就以陈独秀为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之前,在第一个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之前,他竟然是1896光绪年间的秀才。当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的核心已深入血脉的时候,积极入世、追求仁义礼智信的坚定信念早已转化成救国救民的真挚愿望。他们“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只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掀起的尊孔复古的逆流,而不是对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的全面否定。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人如何来承担建设新文学的重任。换言之,五四新文学反的是传统文学中那些落后消极的因素,对于那些进步积极的因素还是在有意无意间承袭下来的。
三、如何看待“五四”之“反传统”
探索新文学发展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挣脱传统文学束缚的勇气,需要有在西方文化启发之下结合现实对传统文学进行借鉴和改造的魄力,而这一切,新文学的创建者都做到了。尽管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无懈可击,但在当时的年代却是振奋人心的积极呐喊。其实早在胡适之前,就有裘庭梁和陈荣衮等人提倡白话,当时社会上一直是文白并用的。继而,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后提出了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四条主张”,最后又总结出了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这和胡适的一系列论断互为补充,共同推动新文学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本身就是认识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新文学在逐渐展开扩大影响的过程,更是为了推行新文学而不断做出反思改进的过程。
五四新文学虽以新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整个运动中存在的缺陷还是必须重视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固然是进步的,但新文学所强调的文学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文学,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底层人民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现,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只是在有一定素养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展开,而没有和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林纾在与新文学辩论的时候,曾攻击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根本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当然新文学创建者利用这一机会,和保守势力进行了论战,指出白话不是“鄙俚浅陋”的,是“说的出且听得懂的话”、是“不加粉饰的话”、是“明白晓畅的话”。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不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文学,都在潜意识里将真正记录底层百姓的通俗文学排除在文学范围之外。从维新文学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起,新文学的创建者们共同致力于开创新的文体格局,把小说推到了备受瞩目的地位。但在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影响下出现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直到后来鲁迅创作小说,通过对阿Q、孔乙已、祥林嫂等人物性格的展现,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才在思想性内容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后来社会各界曾大力支持“国语运动”,白话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取得了“国语文学”的尊称,国语教育变得顺利,但教育岂能在一朝一夕间得到明显效果。因此,在新文学进行得吐火如荼时,主要的受众依旧是之前那些有一定基础的小知识分子,而在国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是活跃不起来的。但值得肯定的是,当国语的推行被重视起来,这本身就是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中文化资源分配不合理的一种补救措施,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也有机会识字读文。
此外,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应是清楚阐释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到“烂纸堆”中打妖捉鬼,把传统文学中的“国渣”清理出去,将余下的“国粹”继承下来。“整理国故”并不是一味地对于传统文学全盘吸收,也不是向传统文学投降而背弃五四新文学,是以一个成熟文人的身份更为宏观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以一个年轻学人的身份更为微观地分析中国文学的具体细节。他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全面细致梳理了新文学兴起推进的来龙去脉,为中国文学史的史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阐述“五四”之“反传统”这一问题时,最为激进的要数林毓生先生所坚持的五四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他尖锐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间历史发生的相似性,二者都是以彻底摒弃中国传统主流的思想文化的改革来掀起政治社会革命的。但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领导人错误发动,终极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才发生的,这场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却是历史必然,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促使时代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文化大革命中的全盘性反传统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不是文学出了问题,而是要人为地将文学纳入为政治发展服务的轨道。而五四文学的反传统,是建立在传统旧文学的诸多不合时宜暴露出来,急须倡导新的进步的文学来与时代配合。这种“反”是因为“反思”传统后,发现有“反”的必要,有“反”的意义,“全盘性”的“反”虽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却是当时五四文学建设者与传统割裂去倡导新文学的态度与决心。
五四文学顺着时代的潮流,始终在建设与破坏中斗争,在传统和现代里纠结,不断探索建设新文学的正确道路,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富于时代转型意义的关键点。
[1]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3]胡适.胡适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郑宗荣)
On the Anti-Traditional Literary Movement in May Fourth Movement
CHEN Yaqio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Movement is not only to advocate new literature and new ideas, but to break the conversational barrier and serve as the bridg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us the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the modern-sense transformation.
May Fourth Literature; tradition; anti-tradition; Hu Shi; Zhou Zuoren
I206.5
A
1009-8135(2015)04-0053-03
2015-03-15
陈亚琼(1991-),女,山西大同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重要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