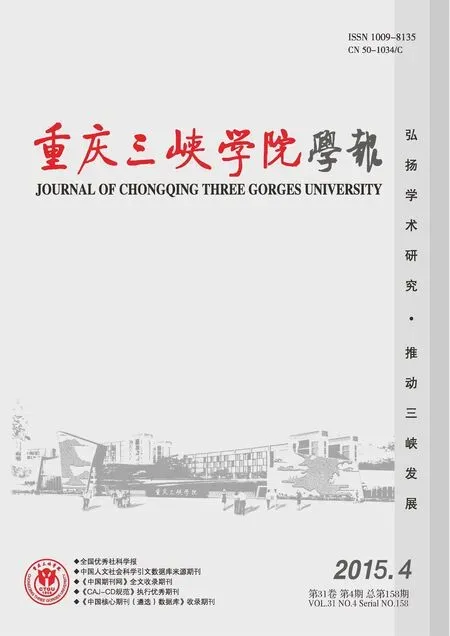般若“色空”观视阈下的谢灵运山水诗
2015-03-18李真真
李真真
般若“色空”观视阈下的谢灵运山水诗
李真真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晋宋时期大乘佛教般若学与文学相互渗透,在般若“色空”观的视阈下,依据“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谢灵运开南朝山水诗之先河,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主体,通过多重感官去“即色体物”,以虚静的心态观照山水,完整记录“即色”的动态过程,塑造清丽空灵的诗歌风格,并从中体悟到“真空妙有”的佛法,以求使自己因仕途不得志所产生的失意无奈得以排解、精神得以愉悦,最终达到极乐致空的境界。
般若;色空观;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之际,佛教与文学的相互渗透达到近乎水乳交融的境地,其中大乘般若学“色空”理论与山水诗创作的结合令人瞩目,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着重讨论万物性空理论的般若学自魏以来一直到东晋后期始终是中国佛学的主流,其“色”“空”范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虚无”范畴颇为相似,在精神追求方面也与玄学有着相通之处,容易被理解与接受,因此般若学大受中国佛学者的重视与提倡,“为了适应江东流行的玄风,僧众纷纷融玄入佛,来阐发自己对般若空义的理解”[1]32,形成“六家七宗”的讨论局面,讨论的中心便是对“空”义的阐发以及“色”“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僧人常于山水间探寻世界本质、体味人生真谛,观照山水是佛教徒重要的修行方式,佛家对自然山水的重视势必对文学界产生影响,因此“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67宋初的山水诗,玄理逐渐淡化,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成为文人观照的着重点,罗宗强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指出:“自南朝始,中国士人对于山水的接受,逐渐由理入情,以情之所需,情之所好,来体貌山川。”[3]186宋初文人将山水作为一方净土,从中寻求内心的虚静与淡泊,这与佛家体认山水的方式极为相似,般若学的“色空”观便为其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这股文学潮流之中,谢灵运的山水诗可谓开山之作。平生的经历使他渴望在山水间寻求慰籍,且谢灵运一生好佛,“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巨子……”[4]155“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5]260在出任永嘉太守年间,谢灵运常常与名僧结伴出游,徜徉在山水间,“刘宋时官至临川内史,曾与慧远交游,与慧琳、法流十分友善。”[6]8其创作的山水诗自然也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般若“色空”观与“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文学潮流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发生碰撞,完美结合,形成独特的审美境界,并为诗人宣泄失意无奈之感、表达恬静愉悦之追求提供渠道。
从“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到“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般若“色空”观使得谢灵运山水诗形成独特的观照山水的方式,也影响了其山水诗的风格以及所寄托的精神追求。
一、即色体物,观照山水之万相
色空不二是佛教坚持的本体论,也就是所谓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7]42这里的“色”是指五蕴中的色蕴,定义为“变碍”,即一切物质及现象。色与空相即不离,也就是说物质现象与其本质的空性是相即不离的,“要通过物质现象看到其本质的空”,同时“空是落实在物质现象上面的。”[8]323因此,般若“色空”观强调空的同时不摒弃色,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指出:“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9]146他认为物质现象都是不真,是假名相(假号),这种彻底的空观背后,是赋予“色”以“假名相”之称,在承认色为假有的前提下,通过对色相的观照去参悟“空”的本质。
“色相”映现于山水诗中便是“山水万相”。谢灵运观照“山水万相”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六家七宗之一的支遁“即色论”的影响,支遁主张从现象入手去认识本体,也就是“即色自然空。”[9]69诗人可以通过实际接触自然山水来体物,从中悟出“空”的本体。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诗人便是通过感官对山水的照应去体悟山水,观照色相,并将“即色”的过程完整呈现出来。
(一)多重感官体悟山水
五蕴中的色蕴既包括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即五根,也包括相应的色、声、香、味、触“五境”。因此,“色就在指物质现象的同时,也包含有少数精神现象。”[10]5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玄学的影子逐渐消逝,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也不再是用作比兴的对象,而是悟“空”之净土,诗人徜徉于山水盛景之中,身心都融入其中去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淡远,因此,眼、耳、鼻等五根主观方面对景物的体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视觉去领略风景是诗人最常用的方式,例如:
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11]85(《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11]38(《登永嘉绿嶂山》)
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11]73(《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11]46(《登上戍石鼓山》)
诗人通过视觉去领略风景的角度会随着人与景之间方位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观赏远处的风景用“眺”,观赏低处的风景用“瞰”,观赏后方的风景用“眷”和“顾”,如果风景在侧方,则用“睐”。观赏山水时视觉感受是排在第一位的,谢灵运在诗中采用多个不同的词语去描述眼睛对景物的捕捉角度,可见其对视觉感受是极度敏感的,并且对景物呈现的完美度也有着苛刻的要求,甚至不惜去“扪壁攀枝”,追求完美的视觉享受。
听觉的捕捉往往可以带来视觉和精神的双重享受,因此,诗人也时常会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11]43(《登池上楼》)
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11]50(《过白岸亭》)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11]99(《石门岩上宿》)
诗人钟爱用“聆”表达自己倾听大自然声音时的专注投入,不仅“倾耳”去听,还“援萝”去追寻,因为鸟声、树叶声、风声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稍纵即逝,需要用心捕捉、全情投入地体会。
“即色观空”的理论影响到了谢灵运把握“色相”的方式,而这种多重感官体悟的方式使谢灵运的山水诗极具立体感,眼睛看到的光影与山水、耳朵听到的鸟语与虫鸣、鼻子闻到的花香、手指触到的泉水与香草,共同演化成“声色大开”的山水胜景,也就是谢榛所谓的“造语天然,清景可画,有声有色。”[12]46
(二)“即色”过程的动态呈现
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谢灵运的山水诗:“景非滞景,景总含情。”[13]244是说谢灵运山水诗中的风景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流动着的,具有动态美,这样的景色所蕴含的情感是饱满的。虽然这是一句仅从文学角度做出的评价,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谢灵运在诗中将“即色体物”的过程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其山水诗有着动态的时空关系。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薛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辩。/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11]77
诗人完整展现了他于斤竹涧游览时沿溪而行的路程及边走边观赏到的风景。他在天刚刚亮、夜间的雾气尚未散去的时候进入到山谷里,然后沿着溪水边弯弯曲曲的山路向上走,登上了一座小山峰,随即顺着连绵不断的小路来到山涧,迅速地淌过急流登上栈道,凌空面对着高深的山谷,在这里可以看到溪谷沙洲时直时曲,顺着溪流倒回来转过去,也可以看到水草漂浮在深沉的水潭上,菰蒲从清浅的水泽里伸出枝叶来。最后诗人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稍作休息,在岩石上挺身踮起脚后跟,双手捧起飞流的泉水,采摘含苞半卷的初生嫩叶,尽情地享受山水带给他的这份闲适与安宁,抛开尘世间的各种顾虑,悟出排遣忧虑的方法。
整首诗采取“移步换景”的方式,随着诗人的脚步,新的景色不断的出现。从绵延的山路到湍急的山涧再到凌空的栈道,时空是不断变化的;诗人看到了急流、深谷、沙洲、飞泉、漂浮的水草与卷曲的新叶,景物也是动态的,形态万殊,各呈其趣。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诗人“即色体物”的整个过程如同行云流水般畅快自然。没有预期的路线,自然无法预料接下来将要看到的景色,诗人以一种虚静澄明的心态去捕捉与自然景物相遇时“色”的显现。就如同《游石门诗序》中所说:
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14]1086
在观赏景物之前不带有任何预设的情感,让自然景物吸引自己深入探寻,这样景物才能以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虚静澄明的心态更能体味万物所蕴含的理致。”[15]18谢灵运沿用了佛家的这种观物态度,才会形成其山水诗“边走边赏”的动态写作方式,此时诗中的景物形象“不是简单机械的模山范水,而是经过诗人主观认识,被诗人‘感知’的”[16]66,诗人再通过“感知”后的“物相”去追寻整个即色体物过程的终极目标,那就是“空理”。
张国星说:“恰是由于‘色空不二’之说,才使得谢诗在摹写自然中,通过形象的描绘和自身经验的传达,表现出生动的宇宙‘性灵真奥’。”[16]61在“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影响下,谢灵运在山水诗中通过多重感官体悟自然,然后将这个体悟的动态过程呈现出来,极力捕捉与“色相”遇合的瞬间灵感,去参悟万物“空”的本质,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观照山水的方式。
二、以色观空,寻求境界之空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7]42大乘般若思想的中心观点是围绕着“空”来展开的。根据佛教的缘起论,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无自性便是空。龙树中观学派认为:“所谓性空,不是虚无,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而是对独立实在性的否定,即无自性,自性空。自性空是肯定假有的现象(幻有)是存在的。”[8]176龙树中观学派的思想传到中国后,僧肇受其影响提出了“不真空论”,他认为:“观色空时,应一心见色,一心见空。若一心见色,则唯色非空;若一心见空,则唯空非色。然则空色两陈,莫定其本也。”[9]46不能把色与空割裂开来,在同一时间内,观照色也观照到空,即现象与本体都是空的,强调“真空妙有”的相即不离。
以后人僧肇的佛教思想重新审视谢灵运的山水诗,我们发现,谢灵运的诗中也体现了“以色观空”的方法论,他曾在《辩宗论》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9]222“寂”就是空性,“真知”就是空理。谢灵运便是从自然山水的“妙有”同时照见其中的“真空”,因此他的山水诗有着清丽空灵的风格,而这种清丽空灵的风格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诗人恬静愉悦的精神追求。
(一)清丽空灵的诗风
对“空性”的探寻使谢灵运格外喜好用“水”“月”“云”“日”等意象去表现清新自然之感,如: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11]57(《登江中孤屿》)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11]56(《游南亭》)暝
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11]99(《石门岩上宿》)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11]29(《邻里相送至方山》)
因为“水”本身具有清澈澄明的特质和“洗去尘世喧嚣”的引申意味,而“云”“月”“日”远在天边,不受人为的沾染,是比花草树木还要纯质的自然,因此获得诗人的格外钟爱。此外,水流可以发出声音,山林中的飞禽走兽可以鸣叫,日和月可以发出光芒,照耀万物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所以谢灵运也常常运用“声”“光”“色”去营造诗歌的空灵之感,如: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11]99(《石门岩上宿》)
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11]35(《七里濑》)
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11]96(《登石门最高顶》)
飞禽走兽的鸣叫声向来用作渲染山间的空旷幽静和了无人烟,谢灵运还采用了拟声“活活”与“噭噭”形容水流声与猿啼的两相融合,愈显清幽,这更多的是追求“空”的意蕴。谢灵运在诗中还比较注重对景物色彩的描绘,如:
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11]91(《酬从弟惠连》)
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11]85《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11]30(《过始宁墅》)
谢灵运诗中景物的色彩都是两两对比、相互映衬的:红与紫、绿与红、白与绿,空灵鲜亮,悠然明净,绚丽多彩却不繁杂,色彩的使用为凭借声与光渲染出的空灵平添了“清新”之感,真正达到慧远所说的“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9]98
谢灵运“清气”充盈的诗风来源于其喜好描绘自然山水的浑然天成与清幽肃穆,从而营造一种安谧的气氛,以表现诗人的宗教情绪,即对“空”的追求。而谢诗风格的“丽”则是指他对景象物态的精雕细刻。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诗人详细描绘了他于巫湖山上瞻眺所看到的景观: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荣。/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11]76
诗人用“窈窕”来形容傍山小路的幽深,用“玲珑”形容巫湖中环形岛屿的青翠空明,用词贴切形象;为了全方位的描绘所看到的景观,诗人还采取了仰视、俯视、远眺等多种视角,以求描述的完美与细致,力求全景式地把握山水;为了表现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诗人用新长出的竹丛、刚刚开花的水草、在春风中嬉戏玩耍的海鸥和锦鸡作为意象,并采用植物与动物相结合、静与动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祥和之景,这就是所谓的“穷尽极艳,极貌追新。”[1]191
谢灵运对“丽”的追求一方面来源于当时注重重现山水之貌、巧言切状的文学潮流,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2]694另一方面也是来源于诗人的宗教热情,佛家经常用具体细致的描绘表达对现实世界中物象的态度,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17]318谢灵运想要表达的是,虽然诗中描绘的都是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类看似毫不华丽的事物,但是“心放俗外”、洗尽铅华之后便自会照见这些朴素之物的华丽之处,可见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脱尘世之外、极度空灵的境界。
(二)恬静愉悦的精神追求
“灵运诗中的山水,作为诗人心灵意识的产物,已经不是客观意义上的自然景物了,乃是经过与诗人宗教心理融铸汇合之后,化为表达宗教情感的载体了。”[18]55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谢灵运山水诗清丽的风格与空灵的意境体现出诗人对“空”的追求,而对“空”追求反映到精神层面则是诗人对恬静愉悦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自然源自现实生活的不顺:“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19]1160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时仅仅三十八岁,处于而立之年,本应在仕途上一展自己的才华,仕途上的失意让谢灵运不得不寄情于山水,让自己失落郁闷的心情得以派遣[20]。因此,谢灵运观照山水寻求的是解脱,这与空观中“万物悉无有自性,故不可迷执”的观点相契合,只有看空一切,才能达到精神的愉悦,即“空同何所贵,无贵在恬愉。”[9]69
我们可以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字里行间体会到这种愉悦之情: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滤瞻物自轻,意惬理无违。[11]71(《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11]45(《郡东山望溟海》)
有时候诗句中并没有“愉悦”二字,但愉悦之情处处洋溢: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11]67(《初去郡》)
这种愉悦,既来自于对自然美景的审美快感,也来自于通过“即色观空”得知万物“空不可执”后的释然。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以色观空”这一方法论的影响下,谢灵运塑造了清丽空灵的诗风,同时也塑造了自己恬静愉悦的心境,让内心与诗中自然同时达到致空极乐的境界[21]。
总体来说,般若“色空”观以“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对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产生影响,使其通过多重感官去“即色体物”,以虚静的心态观照山水,将自然山水通过主观的感悟幻化成山水诗中清丽空灵的境界[22],并从中体悟到“真空妙有”的佛法,从而使自己的失落得以排解,精神得以愉悦,达到恬静愉悦的终极精神追求。同时,般若“色空”观的观照也促使山水景物腾升为山水诗的审美主体,以谢灵运为先驱,开创了南朝山水诗的新局面。
[1]刘艳芬.佛教与六朝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孙尚扬.汤用彤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6]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翁虚,等.金刚经今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石俊,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南朝宋]谢灵运.谢灵运集[M].李运富,编注.长沙:岳麓书社,1999.
[12][明]谢榛.四溟诗话[M].宛平,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3][清]王夫之.古诗评选[M].张国星,校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4]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李正香.佛教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6]张国星.佛教与谢灵运的山水诗[J].学术月刊,1986(11).
[17]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8]齐文榜.佛教与谢灵运及其诗[J].文学遗产,1988(2).
[19][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0]刘涛.谢灵运散文撰作探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21]唐爱明.试论谢灵运的悲剧性格[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1).
[22]胡遂,成希.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的比较[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4).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Embodiment of Form and Emptiness of Prajna in Xie Lingyun’s Landscape Poetry
LI Zhen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Mahayana Buddhism and literature permeate each other in Jin and Song dynas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m and emptiness” of Prajna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form is equal to the emptiness” and “visualize emptiness with form”, Xie Lingyun, the pioneer of Landscape Poems of South Dynasty, took the natural landscape as the subject of aesthetics to enjoy the scenery by multiple sensory and calm mood and made an entire record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landscape. He started the clear and fresh style of poem, with which he sensed the “miraculous vacuum” and released himself from the disappointment with his official career. In high spirits he elevated himself to extreme elated emptiness.
Prajna; Form and Emptiness; Xie Lingyun; landscape poetry
I207.2
A
1009-8135(2015)04-0035-05
2015-01-12
李真真(1990-),女,山东青岛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