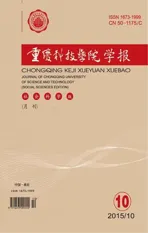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美育思想探析
2015-03-18王玲娟张雨薇
王玲娟,张雨薇
自远古至西周,人们普遍信奉“天人合一”的命运观。然而,由于西周末期周天子政权分崩、安泰局势突变,规律化的节奏被打破,致使天人之道逐渐分离。于是,人们纷纷反思天道,立以人道,至春秋末期各家之“道”歧出。先秦诸子则利用对“道”的隐喻来描绘他们意念中的乌托邦国,从中渗透着他们的美育思想。诸子对“道”的不同阐释,被世人分支别派,最具影响的要数儒、道两家,其次还有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墨家,分派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美育思想也别具一格。
关于“美育”,我国近代首倡美育的教育家蔡元培认为:“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冶的作用,叫做美育”[1],其美育目的仅限作用于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观点不尽全面,或存狭义之解,其等同于艺术教育。我们认为美育是指 “审美教育或者美感教育”[2],它是通过美的形式,在与人的情感相契合的观美、体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以自我审美意识与美感审美判断而形成的个体的审美经验和价值观,以及审美创造。因美的形式纷繁,故美育范畴之广,囊括艺术美、社会美、自然美、科技美教育等。
一、美育理想:和谐美
儒、道两家之鼻祖孔子和老子生活在天子势力被削、诸侯群雄纷争、杀父弑君的先秦春秋末期,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荀子和庄子,亦处在战乱不断、人命如草、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诸子面临生灵涂炭、秩序全无的社会,开始着眼于人本体,欲通过审美活动营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和谐美氛围。
儒家的孔子以“中和”之审美方式促和谐,以社会伦理道德融合人的心理情感。他以“仁”为核心思想体系,攻其内在情理且由内向外,并行礼于外,从而入之以内,以此内外融通改造人的思想与行为,最后趋之于“和”。“孔子出来后,更把这种偏于形式和谐的思想深化到礼与乐、理与情、伦理与心理的和谐结合。”[3]此处的“和”可解释为“合”,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而达到的和谐美育理想。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也谈到,儒家是以“仁”之情理结构造化于人。
首先,孔子论“和”。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就是构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达到人与人平等和睦的博爱境界。其次,孔子谈“中”,即适度。指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主张以‘中’护各维度之‘和’,且育人于中和之美”[4]。 因此,孔子教之:“《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然而,乐与哀是一种原始情绪的体验,即孔子以审美的方式教育人用理性去控制和调节自身情绪,使人的生物性情绪转换为一种社会性情感,从自身和谐达到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礼之用,和为贵”用“礼”促“中”,达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同样,孔子在人与自然和谐中也坚持“中”的原则,要求人不要过度取物,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
孔子的“中和”方法论源于他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不同于孔子的是,由于孟子处于战国时期,氏族宗制全面崩溃,孟子则以“不忍人之心”的王道来构建乱世中的“安和”。 同时,孟子还以“同美感”[5]论和谐,“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同美感的产生是基于主客体的统一,要求客体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不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形成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主体与民族、阶级、地位关系略微,主体“处于共同的历史地位,面对共同的社会矛盾,有共同的政治、经验利益或者改造自然、社会的某些共同的愿望要求,就可能产生共同的心理状态、文化素养、审美观点、审美标准、审美能力,并对同一审美对象产生相近或相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他认为在相同心理根基下人会产生同感,不仅人的感觉相同而且人性也相同。”[6]孟子的以上观点都源于其先验色彩的人格论。从个体差异上讲,此论具有片面性,但从个体对社会美的认同上看则具有一定意义。如果说孟子对“和”的美育理想是从人的感情联结上以致理性上的认同,使之合情合理、情理相通,那么荀子在社会新的体制基础上,更着眼于“礼”的功能性。与孟子相反的是他以外入内,倡导以外在的礼仪来积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只有以群体的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持生存,“礼”则是组建、维持群体和谐的核心。以外入内的方式比孟子更具实践性和时效性。
在乱世,道家以出世隐逸、自保的思想求“和”,置身于世外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与儒家不同的是积极出世、礼乐教化以致和的美育理想。道家首先以“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经第十章》)“坐忘”“心斋”(《庄子·人世间》) 来教诲人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心灵的宁静,以致身心和谐。其次,道家以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经第四十二章》),“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主张以顺其自然育之于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道经第三十五章》),“为无为,则无不治”(《道经第三章》),使人与社会和谐相处。
二、美育原则:真、善、美
从美育原则分析,儒家重善,道家重真,墨家重利。孔子提出了他的美育核心思想“仁”。仁即爱人,则是善的真谛,表现了对“人”的意识自觉。在此基础上,孔子倡导以情育人的方式来改革人性、改革社会。主张以孝悌之情为起点,培养人们的感情自觉,促使人性趋于善。可见,孔子主张以由内至外的方式达到血液性的善,因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主张外在行为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塑造,他要求达到“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集释》《论语补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礼作乐,以致太平,不能有待于后人,故云未尽善。”可见孔子对礼的重视。孔子谈乐,不是单纯论其艺术本体之美,而是以乐来服务于礼,用礼来服务政治和谐。孔子主张先仁后礼,美隶属于善,重视以人的情感为基点,塑造人性之美,以此达到社会和谐之美。因而孔子倡导培养人内心趋善(仁)而美的美育原则,最终为实现礼美、社会和谐之美而服务。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不同之处是,因社会格局的变化,孟子关注执政之道,提出了“仁政”“性善论”的美育思想,同样以善为原则,以善作为美的内容。因此,孟子主张“养气”而达“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其塑造美好人格精神的美育思想是对孔子“仁善”思想的升华,以至尽善尽美。“气质是一个人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7],具有稳定性和可塑性,对人格的塑造极具影响力。孟子强调最关键的是要善于“养气”——“善养吾浩然之气”,使个体人格至于善,即是正义之内在。君王至善至仁也是孟子美育思想的内核之一。孟子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这是孟子教君王以“仁善”之心爱众,体现了孟子以“仁善”为美的美育原则,主张美善统一。
荀子提出的“性恶论”,主张以善育人。荀子说:“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行不胜心,心不胜术。”(《荀子·非相》)心术是指培养一个人的内心品德之善美比其外貌美重要,可见荀子的美育原则也是主张以内善为美。
墨子以能否“兴利除害”的实用性作为其美育原则,主张“节用”“非乐”,反对儒家倡导的繁文缛节、制礼作乐而造成的铺张奢侈。在墨子眼中,“仁善”即是“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法乎天下,利人乎即止。”以是否利民为美育原则,比儒家的美育思想更具有功利性,并带有偏激性。
道家的美育思想也重视内美,但道家的内在美以“道法自然”——保真为其美育原则。老子和墨子同样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然而道家则崇尚自然状态,追求以本真为美。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经第十二章》)他认为礼乐教化会破坏人的本性,世俗的伦理规范会束缚人。所以老子主张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经第十九章》)。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经第五十七章》)充分体现了老子无为保真的美育原则。庄子较之老子,对审美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将老子的“道”由物外转于物内。庄子说:“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庄子·天道》),主张“守本”天然无雕琢,即以“适性”为真美原则。
三、美育途径:乐、礼、诗、技、自然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诗、乐、礼作为美育手段,礼在古代包括衣饰之礼、祭祀之礼、宴食之礼等等,也被视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诗、乐、礼都依附于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理论中礼是服务于政治的,而诗、乐是服务于礼的。孔子首先以《诗经》作为美育的内容,以学诗、颂诗为美育途径发挥个体的认知功能,使人们在学习认知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此为借鉴来构建个体的观念和道德准则。以“心理基膜”[8]的形式在个体的意识中建立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标准。其次立于礼。孔子是一个十分看重礼的人,他不仅教授礼的知识,而且强调礼的实践性,并用以身为教的方式育人。他将个体纳入整体模式化的礼制中进行实践,使个体在礼制的潮流中认同其意识和行为,即达到一种个体规范的同一性。最后成于乐。乐是孔子最重要的美育手段之一,孔子十分喜爱和擅长音乐,他发现音乐能给人极大的精神愉悦和美感,具有熏陶、内导的功能,因此用音乐来触及人们的情感,进行审美教育,强调音乐艺术形式的本体和其内容相统一,并以此由内至外地感人、化人、育人,最终以仁为归宿。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美育手段。首先在用礼方面,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是以氏族血缘的情理结构——孝悌之情教之于礼,而孟子则以人之心性,即以人格美的方式释礼。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发端,且以此“四端”育人。孟子认识到人性的可变性,主张通过学习《诗》《书》保善,以此来练就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内在心性自律进行个体人格美化。其次在利之乐方面,虽然二者都主张通过以乐的审美活动来育人,但实施手段略有不同。孔子遵循先王之乐,以乐附礼,限制乐的内容和形式,重视艺术的教化功能。而孟子却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并不重视乐本身的教化作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从他“与民同乐”的主张可观之,更多强调在审美活动中主体间情感的互动性和感染性,较之孔子更多元、更灵活,更重视艺术的精神愉悦功能。
荀子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主张以礼乐作为美育手段。他在孟子“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反向观点“性恶论”,认为人天生就好利、疾恶、纵欲,“其作为生物的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是人最深层的潜意识存在,是心理系统最根本的动力,即通过生理需要而产生的生理动机”[9]。这被荀子定义为人性本恶,带有一定感性色彩。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强调了乐作为美育手段的本质及功能。乐在古代囊括音乐和舞蹈,“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荀子·乐论》,是说人的原始情绪必然从其声音和行为上表露出来,当个体的情绪发展为稳定的情感,则成为个人品性塑造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以行为心理分析为依据,认为可以从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调和舞蹈的肢体动作来探析一个人的内心性情和情感的变化。“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强调必须以“伪”之,即在洞悉个体内在性情后,以礼乐相济的方式进行引导,转变人恶之性情。相较于孟子的“养心”——由内而外的美育途径,荀子更偏向于外,着重从实用的角度,以礼作为美育手段,“以外部道德的他律性实践方式教育人的认知从感性向理性转化”[10]。同时,荀子在倡导“伪”的美育途径中,认识到质与量的关系,化性则是一个“积”的过程。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他认识到艺术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人的心性。
先秦道家的生命美育思想则以“自然”为其美育手段,此自然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界;其二,是“无为”,道家在美育途径中将二者并趋,首先主张在大自然中审美、虚静、内审。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经第四十一章》),在美育过程中老子教之希声、无形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大美,而至美是存于事物的本质中,在表象的迷惑下不容易被发现。由于人具有认知方式的不同,老子教之“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经第十六章》)。是说只有沉静内心观察其周而复始的变化,方能把握其至美的规律。其次,在美育途径中,老子倡导“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经第二章》)体现“无为”之美育手段。儒、道相比,道家重个体在“自然”的环境下独立感知、内化修其身心,而儒家则重个体通过进入社会群体当中去学习而获得知识经验,在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下修身内化。在美育途径中就培育个体发展而言,道家更尊重个体的自觉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自育的方式自化更具独立性、自由性和灵活性;而儒家更倾向于以美育为手段,将人社会化、群体化。在先秦道家的美育途径中,庄子在继承老子美育思想的同时,比老子更具实用性,他对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极为重视,并将劳动技能作为美育手段,“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技近于道矣! ”(《庄子·天地》)他认为精湛技艺的美能给主体带来自由心灵的享受;其次劳动技能具有实践性,能激发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在技能的提高过程中,还能促进个体审美能力的提高,亦可达到修身之效。
总之,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美育思想是传统美育的开端,它观照个体的修养与发展,通过美育手段使个体得到发展,并以此来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发展。先秦儒、道两家的美育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带有一定的理想浪漫主义色彩,其对当今的美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蔡元培全集:第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0.
[2]彭会资.中国古典美学词典[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69.
[3]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90.
[4]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2007:102-106.
[5]王世德.美学词典[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64.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2.
[7]李新旺.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3-211.
[8]泰勒,佩普劳,希尔斯.社会心理学[M].谢晓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2.
[9]黄金辉,韦克难.实用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98.
[10]保罗·埃根,唐·考查克.教育心理学[M].郑日昌,译.北京大学出版,20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