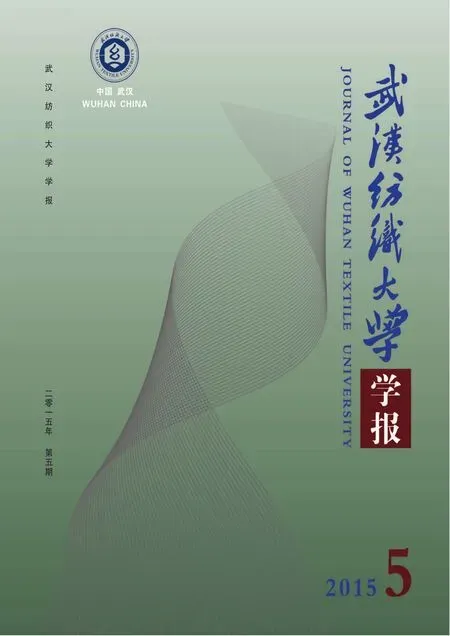民国时期《工厂法》抚恤条款实施状况分析
2015-03-18姜迎春
姜迎春,刘 亮
民国时期《工厂法》抚恤条款实施状况分析
姜迎春,刘 亮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工厂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劳工抚恤的范围、金额等,但法律适用人群有限且保障水平低。施行的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不同经济效益企业,执行力度大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企业中由于受恤人职别、家庭、工作年限的不同,同难不同恤、同伤不同恤的情况大量存在。反映出中国工业化初期,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复杂样态。
抚恤;劳工;《工厂法》;国民政府
劳工抚恤是针对劳工雇用期间因工伤病、残废、死亡的一种补偿,以保障伤者或遗族的基本生存。对此问题,民国时期的劳工问题专家李平衡、陈达、吴至信等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中吴至信还通过对当时国内最主要的40多家工厂资料的分析,说明这一时期的劳工抚恤实际是一种象征性的赔偿,不足以保障受伤劳工或遗族的生活。[1]
1949年以后,劳工抚恤研究再次受到重视,其中以对《工厂法》的研究涉及抚恤制度的内容最多。饶水利的《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彭南生、饶水利的《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安徽史学》2006年第7期)颇具代表性,这些学者深度挖掘了当时法规条文的价值,肯定了它法律上的积极意义,而该项研究中劳工抚恤制度的实际效果的考察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工厂法》抚恤条款实际惠及人数多少?各地区企业的执行状况及在企业中的运行实态如何?本文立足于1927-1937年间该条款施行过程中上述问题的考察,来揭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劳工抚恤制度施行状况及影响因素。
一、《工厂法》抚恤条款的受益人群及保障程度
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1920年现代化生产占工业总产值的10.78%;1936年则升为23.69%。[2]作为一体两面,工业事故发生频繁,劳工因工伤亡人数增加。“国内发生工业灾害在1934年达247O次,伤亡人数5011人,1935年达2655次,伤亡5629人。”①一年时间伤亡人数上涨12.3%。而在1929年以前,劳工抚恤没有引起人们重视。据统计1918到1926年间涉及抚恤的罢工一共有18起,而解决的只有4起,仅为20%。[3]劳工抚恤问题成为当时劳资冲突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第一天就发布《上海劳资调节条例》,“规定因工作而死伤的抚恤金。”②以期能够缓和当时尖锐的劳资矛盾。1929年12月,《工厂法》出台,对因公伤、病、残、亡做了两点具体规定。一是适用范围。第1条规定:“凡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之工厂,平时雇佣工人30人以上者,适用本法。”二是伤亡抚恤标准。“对于死亡之工人除给与五十元之丧葬费外,应给与其遗族抚恤费三百元及二年之平均工资。前项平均工资之计算以该工人在工厂最后三个月之平均工资为标准。”“对于因伤病成为残废之工人永久失其全部或一部之工作能力者,给以残废津贴,其津贴以残废部分之轻重为标准,但至多不得超过三年之平均工资,至少不得底(低)于一年之平均工资。”[4]同时,为了保证法规的运行,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工厂检查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施行条例》、《工会法》与《工厂法》一起配套使用。严格说来该法的抚恤标准和法律配套无可争议,根据参与制定该法劳工官员李平衡的介绍,《工厂法》是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立法成例和国际劳动标准为参照来制定的。[5]其专业性与国际性也许毋庸置疑,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实际效果却难达纸面之意。
首先抚恤条款受益面狭窄。由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工业落后,企业很少能达到《工厂法》规定的30人的规模且使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对全国工厂进行了一次执行《工厂法》情况的检查,全国符合《工厂法》第一条规定的工厂共有1,599家,占23省市工厂总数363,322家的0.4%。 11省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的工厂之工人约有52万人③。而当时全国有1,518,588名工人[6],法定受恤人比例仅为全部工人的40%。
“绥远,工业尚在萌芽,各工厂均不合工厂法之规定;陕西,地处边陲交通梗塞,大规模之机器工厂均未举办,即现有之小工厂,亦系一般手工业,并无大工厂之设立;热河,地处边塞,工业幼稚,尚无各种工厂设立,尤乏工业上之专门人才;吉林,工业幼稚,实少合法之工厂;甘肃,财政困难;察哈尔,经费支细,且无大规模之工厂;湖南,经费支细;……”[7]
其次恤金的保障能力有限。根据慈鸿飞的研究,1927年上海非熟练工人,抚养5口人,最低生活费每月需21.34元,人均4.5元。1930年全国工资标准工人最高月工资为50元,最低为5元。[8]那么按照《工厂法》的抚恤金额的规定,一个因工死亡的劳工最低可以得到420元,最高可以得到1500元的抚恤金。最低的抚恤金够5口之家生活20个月,最高的可供生活60个月。而因伤致残者,最多可以拿到1800元,可以生活90个月;最少只有60元,仅能生活3个月不到。而且不是每个工厂都能做到这一点。“劳工赔偿……大多有厂方决定,而其决定,又多根据于厂方经济情形,……”[9]。可想而知,即使该条款完全实现,也只能算部分保障或不完全保障。可见,冠冕堂皇的《工厂法》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考量,实际作用是有限的。究其原因,诚如王奇生所言:国民党政权就像是一个“夹层面包”。带有现代西方色彩的高层文官整天忙于制定各种法令、计划和决议,不管下层有无承接能力,其结果难免是种瓜得豆。[10]
二、《工厂法》抚恤条款在不同企业的实施状况
然而,在那仅有的0.4%适用《工厂法》的企业中,抚恤条款的落实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的。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对青岛、河北、山东、浙江、陕西、湖南、宁夏、四川、江苏、察哈尔等175家工厂进行调查,工人因工受伤时医疗费由厂负担者26家,酌情给予医药费者4家,无规定者3家,工资照给者17家,工资无规定者16家,占全部工厂的28%。[6]工人残废者,在有记录的12家工厂中,有7家工厂根据伤残轻重和在厂工作时间长短给予4—25.2个月的平均工资,如能继续工作,有5个厂规定工资照旧。工人死亡时,在有记录的23家工厂中,给予20—50元不等丧葬费的12家,有5家规定酌情给予恤金,有4家根据在厂工作年数给予8—36个月不等的工资或根据在厂年数给予50—300元不等工资,或根据《工厂法》45条一次给予恤金300元或2年工资。[6]有记录的工厂基本执行了抚恤条款,但是没有记录的工厂占统计总数的87%,这些工厂至少对该法没有认真实施。其中湖南省符合《工厂法》规定的工厂有12家,实施《工厂法》的仅1家。[11]
到了1937年,经过数年发展情况稍好。吴至信对苏、鄂、豫、晋、冀、鲁等当时中国最重要的5条铁路、9座矿山(其中省营1家,民营8家)、35家厂矿(其中5家国营、7家省营和23家民营)进行了包括抚恤在内的19项调查,涉及工人177510人。其中5条铁路、3座民营矿山(山东、河南、湖北各1座)、21家工厂(7家省营、7家民营工厂未实行)施行了病死恤金,占总数的59%,比1933年提高不少。残废最高赔偿达1500元(上海一卷烟厂)。另有工厂给予公亡葬费50元,恤金300及2年之平均工资(青岛市一棉纺织厂和一制针厂)。因此吴至信认为:“所得印象中其最要者,即今日之我国惠工事业,至少在规模较大或管理比较进步之厂矿中,较之往昔已有相当基础。”[1]
以上两个调查的对象都是执行抚恤条款能力较强的公营企业,故情况较好。而在私营工厂中则差别更大,私营工厂抚恤的厚薄,主要依赖工厂的经济效益。工厂效益较好,对伤残职工的抚恤较为慷慨,少数工厂对非因工致伤病亡也给予救助或抚恤。上海华明火柴厂、第一织造厂、永固造漆公司、东方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河北汉沽渤海化学工业公司对于非因工致病的工人,规定给予一定期间之工资,准予病假,担负药费。而上海东方印刷所、商务印书馆等10家工厂对非因公死亡的工人还给予不等丧葬费和恤金。[6]在经济效益不好的工厂基本施行一费终了。上海印染公司的一名小工整理机器时触电身亡,厂方给予一次性抚恤金420元,而骏昌铁工厂的小工触电身亡,厂方只给抚恤费120元。这些受恤人因厂而恤,所得不一。④吴至信总结道:“其成功的关键,以雇主自觉为重要。”[1]说明法律在不同经营状况的企业中实现程度是不同的,其时的国家强制力又不足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深层次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名为全国政权,但在各个军阀控制的省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够,不足以保证法规的有效施行,而且政权初肇,政府忙于稳定大局,无暇顾及民生。
三、同一工厂抚恤条款的运行实态
《工厂法》在同一个企业中运行差别依然存在,很难达到立法者力求公正的初衷。执行者一方面宣称坚守抚恤标准,以示公正;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用工性质、不同职位、不同社会背景的受恤人,执行者又不得不从人道救助、企业利益、上级意图等因素来考虑,法条的权威在现实的取舍面前很难保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下辖矿山、电厂等企业若干,中央直属企业的背景使其对抚恤条款执行具有模范性,暴露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性。该企业制度规定因工伤亡者主要依靠工作年限和月薪来议恤。服务5年以上就可按月薪的1/4逐月享受抚恤, 5年以内又有3年和不及3年的区别,在一些矿山议恤的年限有所不同。[6]但恤金以月薪为基数,根据服务年数来划分恤金等级的原则是一致的。
但是实际案例反映恤金厚薄取决于5个因素:(1)服务年限;(2)雇佣之契约性质;(3)原来的工资率;(4)残废的程度与经济状况;(5)受恤者的职别、社会背景。前三项客观性较强,容易把握。而后两项则反映出执行者的考量。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地区的旅游体系不健全,在旅游开发和规划的时候缺乏长远意识,没有形成旅游品牌建设,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比较低。景区规划不够专业,经常会出现游拥堵的情况,还有就是大量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旅游经济收益。此外,旅游管理没有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没有将新的旅游信息和行业动态及时发布到网络上,群众基础不够广泛。旅游企业的宣传不到位,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旅游产品,导致旅游业务下降。
如受恤人的经济状况和残废程度。在建设委员会的公报当中经常看到“念其……,特予抚恤”、“特准”、“酌情”等字眼。不可否认,在有些恤案中,这能体现出制度之外人性关怀的一面。如首都电厂电匠吴质庆在工作路上为救落水的小工刘中毙命,本来不能算是因工亡故,但念其“身后萧条、遗有妻女”,优给一次恤金200元和理丧费80元。⑤戚墅堰电厂的公役吴阿锡送递信件,中暑结毒毙命。本来公役死亡,向无给恤规定,而且“电厂工警恤典所载,亦只限于确属因公伤亡之人”,“惟吴在厂服务,已逾数年,平时工作颇为勤苦,……其情不无堪矜之处”,“于是“姑且从宽比照工人抚恤,减等给予1/4恤金,一次发给。”嗣后为怕引起其他工人援例执行,特强调“嗣后概不援此为例,以重恤典。”
同等条件下,正式职员的抚恤金一般是临时雇工的数倍。如首都电厂小工尹仁福属于临时雇佣,服务已逾7年,贫苦堪怜,因公毙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人杰特地批复:“核与抚恤规定未合,姑念其在厂服务已逾7年……,特准从宽发给国币50元,以示体恤。”⑤而同一时期,首都电厂总务课员方遥(正式职员)积劳病故,援照抚恤规则却能被给予一次恤金500元、丧葬费100元。⑤两者相差10倍,可见差别之明显。
事故发生的地点、原因等也能决定抚恤金额的优寡。淮南煤矿局就有案例显示,井下受伤与地面受伤;工作地点受伤与非工作地点受伤抚恤是不同的。孙纪文因推水车轧伤截断脚趾,照章申请恤金50元,但是建设委员会却认为:“查该伙夫系在地面工作,此次因推水车,致伤足趾,由于自不小心,其情形殊与其他地下工人受伤不同,且仅断脚趾两个,乃极小部分略带残伤,嗣后自能另觅相当工作,所请照章给恤之处,碍难照准。”只批准“给予医药费30元。”⑤而该矿的另一拣矸工人汪家贵在洛河岔道(非工作地点)被机车碾毙,该厂代为请恤,建设委员会认为“该工既非因公死亡,自难援照恤典给恤,准除发给棺木外,再给国币20元,作埋葬之用。”⑤
最为常见的是受恤者的职别、社会背景造成的恤金差别。长兴煤矿局局长朱世昀在匪徒袭击矿区时“身亲督警,奋勇抵御,……虽已弹尽援绝,部属皆劝退避而誓死不从,徒手与匪众肉搏,身被八枪四刀,遂□遇害。”建设委员会称朱世昀“任职之忠,死事之烈,固足以矫漓俗而风末世,且功在地方,不容淹没。明令褒扬,俾昭激励。”予以重恤。恤金金额未见记载。直至1932年10月25日长兴煤矿改组移归商办时,其妻请将未拨付的恤金10360元一次拨付,张人杰亲自指示就售煤收入项下一次付清,⑤恤金的数额才露出冰山一角。以朱世昀的月薪和服务年限,是不可能算出一万多元(还不包括已支付的)的恤金的,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厂方“明令褒扬,俾昭激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朱的煤矿局局长的职位使其能够享受特恤,与其同时遇害的一般职员只能按章抚恤,所得寥寥。类似案例在公报中记载比比皆是。究其原因,有学者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工业企业依然没有褪尽封建等级制度的色彩;再加之公营企业中,管理官员掌握着财政、分配的大权,缺乏监督,腐败自然就会滋生。
四、结语
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抚恤条款本身来看,它采自西方成熟法文,具有先进性一面,但是结合中国实际,恤金保障能力有限,其补偿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救济,而且覆盖人群有限,仅为当时工人总数的40%,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劳工游离于法律保护之外,而且鉴于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法规的执行缺乏国家强制力作保证,仅靠企业自觉施行。
在符合施行标准的不同企业中,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效益较好的企业与效益不好的企业,抚恤标准差之甚大。即使在同一个工厂,因人而恤、因事而恤,因地而恤造成同伤不同恤,同难不同恤现象普遍存在。抚恤资源更多地是惠及那些职位高、权力大管理职员,有悖劳工抚恤济弱扶贫的宗旨,反映出工业化初期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复杂样态,说明一个公正、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强有力政府的规划和监督并强制施行,这样不同企业、不同级别的受恤人才能得到有效公正的保障。
注释:
① 见于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局编《国际劳工通讯》,第8号第123一124页;第11号第1一10页。
② 见于《上海劳资调节条例》,《银行周报》1927年第15期。
③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民国二十三年全国工厂检查年报》附录,第40页。
第2步:在第1步录取的数据上,采用本文所述的几种动目标检测算法进行处理,验证动目标检测算法的性能。实验数据的处理结果以距离历史图表示,横坐标表示距离维(单位为m),纵坐标表示慢时间维(单位为s)。
④ 见于《近四年年来上海的劳资纠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国际劳工通讯》1938年第5卷第6期,第30-100页。
⑤ 见于《关于职工考勤抚恤事项》,《建设委员会公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77册第43期第26-30页;第583册第59期第28页;第584册第62期第25页;第577册第43期第24页;第582册第55期第13页;第570册第25期第46页。
[1] 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A].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刊(社会保障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115-169.
[2]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上海:三联书店,2001.105.
[3] 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M].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144.
[4] 邢必信.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M].北平:社会调查部,1931.5.
[5] 李平衡.劳工行政之经过及今后设施[J].劳工月刊,1932,(1):4.
[6] 沈云龙.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辑) [C].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1.281-283.
[7] 王莹.从正泰永和两惨案谈到我国的工厂检查[J].劳工月刊,1933,(7-2).
[8] 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J].近代史研究,1997,(4).
[9] 潘公展.中国创办劳工保险刍议[A].沈雷春.中国保险年鉴[C].南京:中国保险年鉴社,1937(特编).16.
[10]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91.
[11] 实业部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346.
Analysis about the Implement of Pension Provisions of the "Factory Law" in KMT Period
JIANG Ying-chun, LIU Liang
(College of Mar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In 1929,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sued "Factor Act", which made clear the scope of labor pension and pension amounts. But these term were achieved of different level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ue to different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even in the same business, different pension in the same injury or in the same disaster had to be considered by victims' capacity, family, work experience, etc. It reflects the labor pension which is decid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l, different thing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pension; labor; " Factor Act" ; National Government
K252
A
2095-414X(2015)05-0062-04
姜迎春(1972-),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史.
国家社科基金(13BZS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