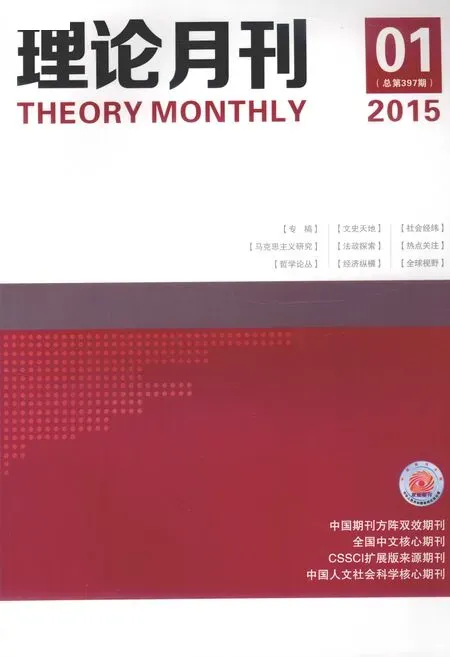儒家向善的三重保障
2015-03-17王治伟
□王治伟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儒家向善的三重保障
□王治伟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人性善恶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扬雄认为人性中善恶混杂,韩愈认为人性分上、中、下三品,李翱认为性善情恶……这些论断都在一定意义上对人性善恶做了思考。儒家一贯秉持性善论传统,然而真正保障人们选择向善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儒家对向善的保障表现在三个方面:性善论为人们向善的选择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利益的鼓励和刺激是向善的积极保障;对恶的惩戒、对他人评判的敬畏是向善的消极保障。
性善;向善;利益;敬畏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扬雄认为人性中善恶混杂,韩愈认为人性分上、中、下三品,李翱认为性善情恶……这些论断都在一定意义上对人性善恶做了思考。然而,从李翱开始,性善论就不再有异议了。他提出的“复性”说,正是把人性看作本来纯善的,于是要恢复到人的本性。宋代学者更是把人性本善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进而提出“天理至善”、“存天理,灭人欲”、“天命之性纯善无恶”等命题。正因为性善,所以性即天理;天理之善既是人性的源头,又是人性的应然归宿。性善论之所以长久不衰,正是由于社会需要正义、需要驱人向善。同时,人们对人性本善的肯定也正是由于现实中人们往往选择向善。
1 性善:向善的内在根据
要保障人选择向善,首先要为向善提供理论根据,即人性本善。由于人性本善,人们选择向善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人性本善,人们选择向善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孟子看来,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并且他用各种方式证明了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的内心本来具有的。在《公孙丑上》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是非”、“羞恶”、“辞让”四个善端。对于孟子“性善论”中的“四端”,杨泽波说:“孟子论四端,大体上有两个角度:一是纵向维的,讲幼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等等。……二是横向维的,讲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端倪,如不忍见牛无辜被杀,不忍见孺子将入于井等等,应当将其扩而充之,不断发展。”[1](P42)也就是说,孟子既是从个人成长历程中来证明善的存在,又是从社会普遍性的角度证明人人都有善性。
从纵向角度来说,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章句上》)。在孟子看来,人小时候就自然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长大后自然知道敬其兄长,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孟子以此来证明人性皆善。
从横向角度来说,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心,孟子先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观点,然后再加以论证。他认为,当人们“见孺子将入于井”,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而这种恻隐之心的产生,并非由于自己和这个小孩有任何的亲情或血缘关系。此外,孟子还用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牛去祭祀,就心有不忍,以此展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中记载:
(齐宣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梁惠王上》)
齐宣王对那头将要被杀的牛产生了恻隐之心,孟子由此证明他本身有善念、善性,这种善性即使自己没有觉察到,在看到动物的恐惧表现时候就能激发出来。其实,无论人们的恻隐之心是否转化成为善的行动,这种恻隐之心都是存在的;即使齐宣王没有以羊易牛,也不能否认他恻隐之心的存在。在这里,孟子只是举出事实,让齐宣王难以反驳、难以否认自己的恻隐之心。
同时,孟子还用“牛山之木”的比喻说明了不善的形成。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孟子认为,牛山之木的原初状态是美的,这是自然物的本性,可是经过人类的砍伐、牛羊的踩踏,最终使牛山之木的美被破坏了,夜气不足以使其恢复原貌。孟子把人性之善比作“牛山之木”的本来面貌,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把牛山之木的意义引向人性本善的证明。赵岐解释说:“言虽在人之性,亦犹此山之有草木也,人岂无仁义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长仁义,平旦之志气,其好恶,凡人皆有与贤人相近之心。”[2](P305)于是,孟子在此不但证明了人人本来都有仁义之心,即善心,而且也指出了不善的来源,把不善与人的本性分离开来。
孟子重视后天环境对人的塑造。虽然人生来是一样的,都是善的,但是环境往往影响到人的为善或为恶。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告子上》)孟子强调上天赋予人的材质是一样的,即都具有善性,可是由于每个人的努力不同,人的具体境遇不同,造成了现实中的善恶分歧。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孟子把善看做一种应当,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人可以或应当为善。于是,善就不必是一种现实的必然呈现,而现实中的不善现象,也不能否定人性应当是善的命题。也可以说,善只是人先天的资质或条件,这并不能保障人后天的作为是善的。所以,孟子的性善论在承认人性具有善质的基础上,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实现它的无限空间。钱穆曾引用陈澧释孟子性善旨意说:“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3](P80)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善只是一种成善的可能性,是善端。也就是说,人们应当为善,并不是说人人都在现实中选择向善或为善。
然而,“应当”并不具有现实的可靠性,人们也未必一定去做自己应当做的。或者我们会说,人们如果为恶了,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为善,就让自己心灵上得到愉悦和解脱。于是,为了求得心安,人们可能会为善。正如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人为恶时应该有羞耻之心,可以用耻辱之心来保障人们向善。可是,这种保障机制太脆弱了,很多时候,人未必一定去做让自己心安的事情。在这里,“人性本善”的价值期待并不构成现实中“向善、为善”的充分条件。那么,孟子的性善论,需要拥有更多的保障因素来维系其被人们认可。人们在现实中为善,绝不仅仅由于孟子告诉大家:人性本善;这里必然有更多因素来保障人们的向善选择,性善论才能长久不衰。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人们向善的更多保障因素,寻找除了人有善的资质之外,哪些因素足以保障人们选择向善和为善。
2 德者得也:向善的利益驱动
在孟子以及后来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到底是什么因素来保障整个社会的向善呢?这应该是孟子性善论本身不能摆脱的问题。也许人性本身无法证明自己的善,而是需要求助于外在因素。
3.1 以德配位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确立了对道德重视的态度。《尚书·蔡仲之命》记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些话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上天只帮助那些有道德的人。《左传》中所说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P1011)把德放在第一位,这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德行的看重。看来,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德行能够被世人认可;同时,拥有德行就可以获得永恒的价值。于是,在先秦思想中,人们已经普遍的形成了“德者得也”的基本认识。[5](P618-622)人们认为,尧、舜、禹等之所以居于王位,首先因为他们是道德模范。由于其本人的德行之善而确立其作为天子的地位,人们普遍把德行的拥有者看作地位的合理拥有者,这就是“以德配位”的思想。
孟子也很看重德行,他说:“……人人有贵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孟子把德行的价值看得高于世俗间的物质欲求,也只有道德才最值得追求。如果国君无德,就失去了获得其地位的合理性,理应受到人们的惩处。《孟子》中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
在孟子看来,国君与平民百姓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遵循仁义,人人得而诛之。国君无天然的合理性。无德则无位,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从此可以看出,孟子重视德行的价值。对于有德者,人们自然应该给他奉上相应的地位;对于有其位而无德者,孟子认为他们应该让出自己的地位。这样,地位与德行之间就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世袭的方式获得地位的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他们的行为更加谨慎、弃恶从善。中国古代不乏“为德舍位”者,正如伯夷叔齐、鲁仲连、陶渊明等人,可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如何就能选择向善,更高地位的诱惑是决然不能忽视的。即使德与位的抗衡和对应不能立刻转变为现实,人们也会把它当成一个普遍价值。于是,“以德抗位”有力的促进了人们向善愿望,激励着人们行善的热情。
3.2 以德抗位
在孟子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要“以德配天”“以德配位”,甚至要“以德抗位”。孟子把德行看作凌驾于现实社会秩序之上的评价标准。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天爵显然高于人爵,在孟子看来,现实中人们官位的高低都要服从于德行的高尚与否,德行在价值上高于世俗的官职地位。而其实,孟子正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有德者才有资格居于高位。德行就意味着你有资格得到一切,有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告子上》)孟子不否认人的欲望,从外在追求的角度来看,人其实是为了得到更多利益才培养自己的善性,坚持向善。人人都想追求更高贵的东西,因而人们才能为了高贵而选择向善。
既然德行成了人们获得更高地位的合理性依据,那么获得地位的权力就被孟子从世袭贵族那里夺了回来。孟子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於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公孙丑下》)孟子并不对国君毕恭毕敬,而是以长者自居、以有德者自居,认为国君应该给予自己更多的尊重和礼遇。
孟子曰:“……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万章下》)
孟子认为君王对待德行高尚的贤者应该恭敬地学习,而不是招来问话。孟子劝滕文公施行仁政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只要坚持仁政、与民为善,想成王于天下者必然来向你学习。孟子把德行看作为师的标准,有好的德行,就可以为师,而圣人正是百世之师。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尽心下》)像伯夷、柳下惠那样的圣人,正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其实孟子也是以师自居,用其德行的地位来和君王的地位相抗衡,甚至居于现实中君王之上。
3.3 人皆可以为尧舜
既然孟子认定普通人与圣贤的区别仅在于德行,那么人就可能通过自身修养,通过善的行为向圣贤靠拢。他声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中载:
储子曰:“王使人矙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告子下》)
孟子认为常人与圣人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常人只要修身敬德,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成为圣人的条件并非出身而是德行。于是,人们都对向善不存在顾虑,在圣人面前也不会妄自菲薄,进而从自身做起为善。
可以说,很多人追慕圣贤品格,正是希冀道德的优势地位,以此拥有获得其他现实利益的正当性。于是,身居下位的民众通过修养自己的德行、“集义养气”,就有机会成为道德模范或圣贤。后来在汉代形成了“举孝廉”、“举贤良”的征辟制度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以是否为善来选择官吏、考察官吏,从一定意义上,正是用官职来诱人向善的具体措施。
总之,孟子的“性善”之说开启了人们成圣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成圣就很难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然而人们追求成圣也只是一个显在的目的,背后总还隐藏着某种利益追求,因为圣人对于几乎任何利益都具有得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性善论就包含了这样的逻辑:正是因为对更高地位的渴求,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为善。一旦你的德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你就将拥有地位、财富,以及其他各种利益。用物质利益的诱导作用来驱人向善,这样解释固然有污道德的至上性和善良品质,物质利益对人们向善的驱动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古人所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后来的科举制度面前,多少士子皓首穷经所追求的,恐怕不仅仅是知识本身吧。
3 敬畏:向善的消极保障
中国人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视角又进一步保障了人们选择向善。对普通人来说,他们拥有评判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每个人都处于评判的角色之中,同时也存在被别人评判的极大可能性。中国古人很喜欢评论别人,也重视大家对自己的评价言论,在《诗经·郑风·将仲子》中说:“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即是后来所说的人言可畏,人们对他人言语的评论有一种敬畏之心。《国语·周语下》说:“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大家的评论可以把金属融化掉。《战国策·魏策二》说:“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人们的评论甚至会无中生有,确实可怕。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中说:“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刘向《新序·杂事三》说:“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逐墨翟,以孔墨之辩而不能自免,何则?众口铄金,积毁消骨。”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对他人言论的重视,都很关心人们如何评价自己。而这种关心,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对为恶的约束力。
《礼记》中记载,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礼记·大学》)他把众人的眼光和评价看作非常严重的事情。人的日常行为都处于别人的视野之中,因此都要格外谨慎。同时,有些人在众人没有看到他时候为恶,可是他们同样忌惮众人的目光。“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礼记·大学》)那些为恶的人在众人的目光中也要把自己的恶掩盖起来,他们害怕众人的谴责。然而,正是这种众人视角,他者的视角对社会上的一些恶性起到了制约作用,进而保障人们向善的选择。
孟子很看重民众的作用,其实也是对他人评判的重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众相对于国君,相对于土神、谷神的祭祀,都处于优先地位。他对民众的重视其实正是对民众目光、民众视野的重视,国君的行为都在民众的目光审查之中,如果有所不当,民众就会表达他们的负面评价。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君的恶行,而鼓励了仁政和善行。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对国君道德高尚的心理期待,和对无德者的心理惩罚、诅咒,都会影响着国君的行为自觉,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君不敢轻易滥用自己的权力。
个人对公众的敬畏之心往往使人们选择向善。人们往往为了得到别人的正面评价,为了在后世留名,甚至可以舍生取义,临危不惧。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作为道德的“义”对于人来说,可能是更迫切的追求,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公众的肯定。“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告子上》)有些人为什么不食嗟来之食,恪守道德和自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希望在公众的评判中毫无瑕疵。在他们的意识里有一种他者的眼光在注视着自己,对他人目光的重视和敬畏,让他们忍受现实的困厄,进而获得公众永恒价值的肯定。有的时候,以身践道、舍生取义正是在众人的视野中才会呈现,众人的目光给了他撑下去的力量,众人的正面评价的可能性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不管是国君还是民众,对公众的目光、公众的评价的敬畏都是客观存在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人们选择向善具有趋利避害的因素。而这里所说的利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与否,而是是否受到公众的口诛笔伐,是否在公众的视野里保持高大的形象。一个人为了不受众人的谴责和惩罚而选择向善,国君也会为了不受公众的谴责、诅咒、甚至戕害而选择向善,即使那些舍生取义的义士,也往往抱着一个青史留名的深切愿望。人性本善的命题需要有他人视野的监督和保障,正因为这样,人们的选择向善才能更具有普遍性。
4 余论
总之,性善论给人们选择向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然而,社会的向善选择也需要利益的激励才能更加持久和有效。于是,社会的向善倾向往往反过来坚定人们对性善论的信念。“人性本善”从价值角度给人设定了一个目标,人们真正地选择向善却少不了社会的功利推动和人们的理性选择。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人们对物质利益过分追逐,就有可能威胁到“人性本善”的命题本身,使“性善论”失去他本身的高尚性和纯洁性,而变成物质利益的附庸。
当代社会,由于人们过分的功利追求,人性本善的价值也正逐渐褪去它的社会和精神基础,人们向善的维护机制也正面临着危险。孟子倡导性善,有德者就有资格得到更多利益,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而当今社会里,“有德”的意义似乎是在淡化其实际能力,德行往往不意味着得到利益的正当性,而更像是不善变通、没有出息的另一种表述。如果人们只着眼于物质利益,而不再关心是否符合道德,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当代社会,人们也不再把他人的目光看作对自己向善的约束力和驱动力,而是看作自己获得知名度的手段,有了名气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为了金钱、为了出名可以无所不为。媒体通过桃色事件来炒作明星,艳照门层出不穷。这些社会现象正是在当代社会消解了传统文化中对人行善的约束力之后的必然产物。
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当代社会的伦理问题,离不开对孟子“人性本善”命题基础的重新考察,也离不开对传统社会维护社会向善的根本利益机制的考察。性善论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陈旧的文化样式,而是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维护方式。重建传统社会对人们向善的保障机制,重新确立人们对公众评判的敬畏之心和对德福一致的信心,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1]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A].李学勤.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钱穆.孟子研究[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
[4]左丘明.左传[M].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06
B222
A
1004-0544(2015)01-0030-0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07)。
王治伟(1979-),男,河南渑池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