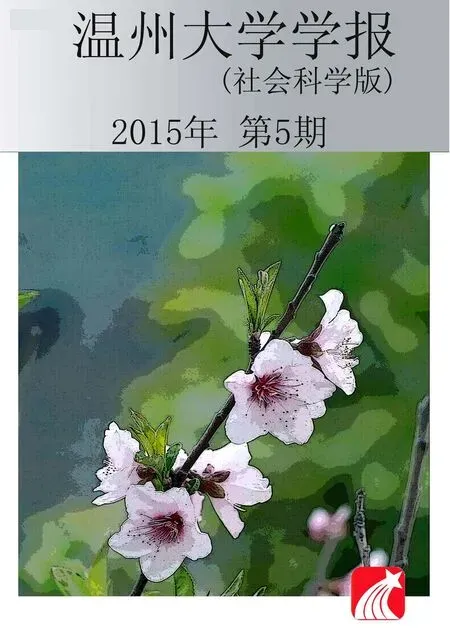林语堂生态美学观念研究
2015-03-17丛坤赤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丛坤赤(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林语堂生态美学观念研究
丛坤赤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林语堂把自然与文化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作为完美生活的重要特征和前提条件。他的生态美学观念包括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科学与人文的完美融合、舒适怡情的生活状态等主要内容。他在一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交汇中追求着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键词:林语堂;生态美学;科学;人文
作为从闽南山村逐渐走向都市乃至海外的大作家,林语堂认为亲近大自然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要求,同时他也并不十分排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繁华热闹的都市中度过。在那里,他会迅速地接纳、吸收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并生活得如鱼得水。他不但没有其他知识分子背弃故土走向都市后无“根”无“家”的矛盾与痛苦,反而在成功与快乐中轻松地成为都市的主人。因此,在设想人类生活的理想家园时,林语堂既没有过度倾心于乡村世界,也没有一味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一面沉醉于自然山野的清新幽静,一面又感受着都市生活的舒适与便捷。在他的心目中,“田园”和“都市”并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它们完全可以融合交汇,形成真正适宜人类健康发展的“田园式都市”[1]生活。林语堂所构建的这种“田园式都市”生活至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
在林语堂看来,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能够使人们充分地感受到人生的恒定性,从而使人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情境中,加强对过去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以便形成达观超然的生活态度,而这种达观超然的生活态度,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避免被机械、金钱等外力所异化的重要保障。
在林语堂看来,最能体现悠闲从容之魅力的城市便是老北京,而老北京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具体表现为空间的开阔与时间的舒缓。
首先从生活空间来看,老北京城的建筑是传统乡村式的平铺展开的格局,而不是现代都市耸立向上的格局。“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乡间的错觉。”[2]211虽然是一座大都市,可是北京城里却“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院落,每一个院落中都有一缸金鱼和一棵石榴树。”[3]在那些院子里,人们可以种树、种菜,也可以养花、养鸟,生活似乎依然沉浸在农业社会的安宁、闲静之中。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宽容大度的人生态度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与极力赞美北京开阔舒适的生活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语堂对那些居住空间狭小逼仄、居住形式呆板单调的都市却极力地讽刺挖苦。比如他描写上海:“我常看见上海的富翁,占着小小的一方地皮,中间有个一丈见方的小池,旁边有一座蚂蚁费三分钟即能够爬到顶上的假山,便自以为妙不可言。”[4]262描绘美国时,他则说:“俯视街道,所见的是一列灰色或已褪色的红砖墙,墙壁上开着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阴暗小窗,窗门半开着,一半掩着阴影,有的窗栏上有一瓶牛乳,其余的窗栏上放着几盆纤弱的病态的花儿。”[4]150-151在《生活的艺术》第十章《享受大自然》中,他更是把城市的公寓比作“看不到行云和花树,听不到流泉”将生命“幽囚到命终之日”的地狱[4]272。从这些充满调侃讥讽意味的话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林语堂对狭小拥挤空间的深恶痛绝和对开阔疏朗环境的倍加欣赏。这种开阔疏朗的生活环境正是“田园式都市”生活的重要基础,它为培养人们优雅闲适的生活心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保障。林语堂认为,要想让人类重返大自然或将大自然依旧引进人类的生活,首先第一步就是要使每个人有很多的空地。在那至少方圆一亩的土地上,人们可以种花、种树,并引来鸟叫和虫鸣,这些真正来自大自然的快乐绝非一笼一羽之乐可比。
从时间来看,林语堂对老北京雍容舒缓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推崇。与许多现代城市里,人们被时间追着跑,几乎要成为时间的奴隶不同,“北京的生活节奏总是不紧不慢。”[2]217最有代表性的应属那些永远从容不迫的前清遗老。他们的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声咳嗽都那么富有韵律和节奏,这种从容不迫的节律既反映了文化的素养,也反映了自信的心态。在崇尚悠闲的同时,林语堂非常反对“速度”。他曾借《奇岛》中的人物劳思之口尖锐、犀利地批判、讽刺了美国社会“完全不对”的生活速度:“美国办公室和商行都不停下来吃午餐,只花半小时坐在汽水自动贩卖机前的高凳上,匆匆啃完三明治,又回去工作了。工作!工作神圣!……一只狗抢到一块肉,还会叼到角落里,舒舒服服吃一顿。……一顿慢慢吃的午餐,就可能表示你被解雇了,或在办公室不受重视,或不被需要……他(指现代人——笔者注,下同)发明省力的机器后,反而比以前更辛苦了。进步的步伐太快,他陷入迷宫里,找不到出路。……人对自己太残酷了。他不再驱赶驴子和马匹,却开始驱赶自己。”[5]247在“人对自己太残酷了”、“我们现在去哪里?”[6]的感叹与诘问中,林语堂指出西方人虽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不懂得如何去享受它,从而并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以及最大限度地了解人生的乐趣。
西方民众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现代社会中那种“完全不对”的速度,破坏了人们悠闲自得的心境,深陷其中的人们成了时间的奴隶,只是不停地向前、向前、向前,却无暇享受人生、体味生活之乐。在《奇岛》中,林语堂借主人公劳思之口指出:“你会承认,在二十世纪急速的进展中,思想是不可能的。人动得太快了。巨大的改变、物质的发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航空缩短了交通,消除了国际界限!——这些改变发生得太快了,人只好被拖着走……”[5]103-104。被拖着走的状态使现代人丧失了自我独立,也丧失了享受生活的优雅心境。因此林语堂推崇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倡导人们以悠闲的态度去看待自然,去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并在自然中自由畅想。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抵御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富足而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二、科学与人文的完美融合
林语堂“田园式都市”生活模式的建立与其力图将科学与人文相交汇、机械与艺术相融合的文化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小接受西化教育,所以林语堂对西方近代科学有着自然而然地强烈向往。他曾自豪地解释说:“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是一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7]林语堂不但在其作品里,以十分赞赏的口气谈到核科学、轮船、电子产品等诸种西方科学成就,他自己甚至还为了研制中文打字机而几乎要倾家荡产。所以他自豪地说:“我嗜科学,故同时留意科学的探究以补救我的缺失。如果科学为对于生命与宇宙之好奇感的话不谬,则我也可说是个科学家。”[8]336林语堂相信,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个人建立一种健全的人生观和人格理想,而且在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当“五四”革命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时,林语堂也顺应时代潮流,极力赞美现代物质文明,欢呼科学时代的到来。在他看来,科学文明在改善民生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物质文明的程度。他说:“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9]3然而与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不太一样的是林语堂在笃信科学的同时,却对科学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恰恰构成了他生态美学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这里的所谓科学主义是指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而逐渐在欧美盛行的一种文化思潮。17世纪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18世纪牛顿的经典力学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使得一种过分相信和推崇科学的思潮在西方社会迅速地滋长和蔓延。强调理性分析,实证分析是科学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本体论上,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主张用科学方法分析哲学问题,完全取消了对世界本源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讨;在认识论上,科学主义推崇理性和逻辑,遵循主客体相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方法论上,科学主义则崇尚论证、推理的方法而反对直观、感悟等人文学方法,认为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统辖所有科学包括哲学和人文学。随着科学主义的滋长,科学所赖以建立的理性精神被无限夸大为足以统驭整个世界与人生的绝对律令。科学这种人类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也因人们的过分崇拜而逐渐成为一种准宗教的信仰,甚至迷信。
林语堂对科学主义思潮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这一思潮的泛滥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主要有两点:首先科学主义的无限扩张,尤其是它对人文世界的侵犯扼杀了人的灵性,使人类的内在自然遭受到极大玷污。林语堂认为“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以及“不加臧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一种罪恶。”[10]105一旦把包括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领域纳入科学范畴,用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人文问题,则必然会导致人的生存价值被遮蔽。因为用数理逻辑构造起来的世界图式只涉及经验事实而排斥价值问题,它往往对富有情调的人文世界的独特性视而不见。正如《奇岛》中的劳思所言:“一旦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介绍到人文学里面,你就会渐渐把无法量度的东西一件一件抛掉——上帝啦、善慈啦、罪恶和悔悟啦,以及艺术创造和高贵的动机等。”[5]212在科学主义的入侵下,以呵护人的道德与心灵为己任的人文学科彻底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因此林语堂把科学对人文世界的干涉视为文化的堕落:“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10]105-106“哲学已成为数学的附庸,道跑哪里去了?谁管?”[10]87
其次,科学主义的迅速膨胀也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看法,自然万物的神性被消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掌控随之日益增强,这一切使得人类社会的外部生活环境急剧恶化,生态灾难频繁发生。在科学主义看来,万事万物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深奥完全可以凭借人类的科技理性进行认知,这就把人类从神性思维的羁绊中彻底解放出来,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自然的主人。应该承认这种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可是同时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也随之消失,人们在享受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丰厚物质财富时,却没有了对自然万物的依赖之情和感恩之心。个人、群体的物质欲望迅速膨胀,宇宙被看作是人类的隶属物,世界变成了人类争夺物质、满足私欲的战场,人类的精神崇高被削弱,人类的意义世界被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
正是出于对科学主义人文关怀缺失的担忧,林语堂提出了将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观点,他说:“科学家应该注意信仰问题,与传教士应该注意科学问题一样,因为两者都在探求人生的意义。当代人第一急务,是利用聪明,恢复人生的意义。”[9]170林语堂将科学与人文相融合所借助的理论资源,既有他深沉的基督教信仰,也有中国儒道互补的古典人文主义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以及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如果说林语堂早期的基督教信仰主要源于家庭的影响,那么成年以后,尤其是当他经过二十多年的叛离又重新皈依基督教时,他的宗教信仰则已具有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内涵。他彻底否定了用科学理性方法阐释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始终把上帝的威严放置在逻辑理性所达不到的境界,坚决捍卫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尊严。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方科学文化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体系。无论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庸见之崇拜,还是老子的相对之言以及庄子的物化之论,都可以对现代科学思想的不足进行有效的外在干预。另外林语堂对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也相当谙熟和崇敬,他敏锐地意识到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桑塔耶那等哲学家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拯救西方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危机的良方。在《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里,他指出“所谓存在主义,或有神论(如Kierkegaard),或明白的无神论(如萨尔忒)……又回到人生切身道德问题,而社会人生良心自由乃成为研讨之中心。他们对人生之负责,如Sartre,Camus虽然是无神论,却能使人肃然起敬。”[10]88另外林语堂还从古希腊文明中汲取人文精华,他尤其对古希腊飘逸洒脱的酒神精神深怀敬意。在小说《奇岛》中,他把人文学科安顿在理性逻辑和科学语言抵达不到的领域里严加守护,让宗教、美学、哲学、艺术完全摆脱旧世界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羁缚,在泰诺斯这个自然风光优美如画,同时又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思想、儒家观念和庄禅哲学融于一体的小岛上得到充分发展。
三、舒适怡情的生活状态
当林语堂在悠闲从容中把科学与人文相互交汇融合之后,他所梦寐以求的舒适而又怡情的生活状态便逐渐显现出来。林语堂热爱自然田园,认为自然田园是都市人生的润滑剂,更是一所永远的疗养院,尤其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4]277但同时他对机械文明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也并不反对。他曾经打比方说:“我总喜爱吃一杯果子汁,而不愿吃由道边潭中取来用一只木碗盛着的污水。”[8]277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度过的。在那里,他享受着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深深的依赖。他承认自己的生活中“总得须有升降机,自动梯,硬木地板,真空拭尘机,良好的艺术陈列所,博物院,以及星象院”[8]277才行。在《抵美印象》中,他介绍说:“美国丰衣足食,诸事安全……美国物质方面,足使人们快乐一生。”[8]276不难看出,林语堂对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先进发达有着由衷的赞叹和喜爱。
不过与一般现代都市人所不同的是,林语堂在享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方便快捷的时候,却没有完全臣服在其脚下,而是敏锐地“深察了这文明的缺陷”[11]。他指出“我尝说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只是你别误会你到Empire State Building去,升降机直送你上云端,就是享福了;或是到Radio City去,你直降到地底深处,就是享福了。这些并不是我所确指的享福。”[8]277-278林语堂认为,真正的“享福”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外,还应具有平和达观的心态和善于发现美与情致的眼睛,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怡情养性”。所以美国虽然有巍峨的摩天大楼,宽阔的高速公路,飞驰的汽车和华丽的商场,是一个机械文明发达、物质生活富裕的国土,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并不见得一定幸福。
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现代人虽然丰衣足食却依然不能感到生活的幸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总是一味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而忘记让心灵保持一份安宁。正是因为丧失了心灵的安宁祥和,所以现代人逐渐被永无止境的索取欲和占有欲所吞噬,并在这两种欲望的驱动下,变得喜新厌旧、贪得无厌。“一般普通的美国人亦与小孩一样,总得要有新花样玩玩才得劲——Radio City也好,马(麻)将也好——过了不久却又玩厌了。”[8]278对此,林语堂曾犀利地诘问,当人们凭借所谓的智慧,以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宇宙,企图建造一个珠玉为门的天堂时,他们究竟是离幸福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如果一个人看到一轮明月而不能感到满足,那么当他看到粉、紫、绿、橙等各色的月亮悬在天空的时候难道就会感到满足吗?如果人类始终以一种“大富豪”的心性来对待宇宙自然,那么“恐怕到了这个珠玉为门的天堂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又会感到讨厌。”所以人类也许根本就不必“徒然地去追寻一个或许只能使上帝满足而不能使人类满足的可能天堂,”其实“我们的地球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星球,”它无需有太多的改变,对于人类来说“最聪明的法子就是:径自去享用这席菜肴,而不必憎嫌生活的单调。”[4]272-274努力恢复领略人生幸福所必需的健康心态,这正是林语堂针对无穷的贪欲——这一现代人的精神痼疾所开出的一剂良方。
林语堂并不反对物质进步,可是他却反对对物质的极端追求。面对充斥着机械崇拜、物质崇拜的现代社会,林语堂特别渴望能在奔流向前的急流中找到一处可以站稳脚跟的避难所,在那里人们可以休息、思想,重新建构起理想的生活模式。在小说《奇岛》中,林语堂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泰诺斯岛塑造成了这样一个避难所。小岛居民把现代化的方便快捷、中国传统的悠闲惬意和古希腊的高贵典雅相融合,过着一种既富足安康,又和缓适宜同时还不乏高雅追求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以美为核心,以保障人类心灵的快乐自由为主旨,具体而充分地体现了林语堂的生态美学观念。
四、结 语
林语堂把自然与文化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作为完美生活的重要特征和前提条件。他既欢呼现代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肯定它们所体现出的人类智性的伟大,又忧虑现代人类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的蛊惑下一天天远离上帝而最终坠入道德的深渊。他自然而然地将道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同古希腊自由奔放的思想相提并论;也有意识地把儒家思想“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2]的理念与基督教对崇高神秘力量的坚决捍卫融合在一起。他不拒绝物质享受,却拒斥物质主义的泛滥,热爱科学却又痛惜科学主义对人文世界和自然宇宙的侵蚀。他叛离基督教又皈依基督教,他坚信人应该有所信仰,却又把天国安顿在凡人的心灵之中,相信人们可以在饮食起居中感悟出美和真义。他力图用心灵去体察自然与社会,对心灵自由有着无限的追求,却又把日常生活作为生命的重心,津津乐道于柴米油盐、吃穿住行。这就是林语堂,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交汇中追求着天人合一的境界,实践着自己的生态美学观念。
参考文献
[1] 王兆胜. 林语堂的文化情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75-220.
[2] 林语堂. 辉煌的北京[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25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3] 林语堂. 讽颂集[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15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4]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21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5] 林语堂. 奇岛[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7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 林语堂.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10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41.
[7] 林太乙. 林语堂传[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29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6.
[8] 林语堂. 拾遗集: 下[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18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9] 林语堂. 啼笑皆非•中文译本序言[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23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0] 林语堂. 无所不谈合集•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C] //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16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1] 施建伟. 林语堂传[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387.
[12] 王文锦. 礼记译解: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778.
(编辑:刘慧青)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Ideas of Lin Yutang
CONG Kunchi
(School of Literature,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250100)
Abstract:Lin Yutang regarded the harmony of nature and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precondition of the perfect life. The main points of h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concepts included idyllic pace of life, comfortable state of life, and perfect fusion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e sought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a kind of mixture of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thoughts.
Key words:Lin Yuta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Science; Humanities
作者简介:丛坤赤(1973- ),女,山东平度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1-18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5.002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01;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5-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