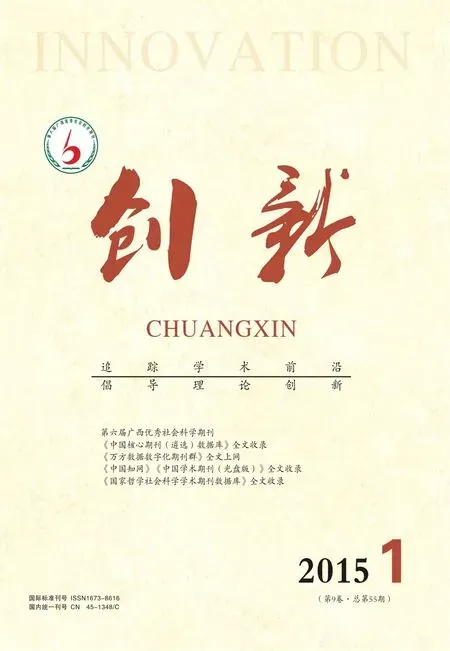利息的来源和性质新解
2015-03-17郑志国
郑志国
利息的来源和性质新解
郑志国
[摘要]商业银行为存款方和贷款方提供双向服务。城乡居民以获取利息为目的而自觉储蓄属于间接投资行为,存款利息是间接投资收益。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的差额是银行服务价值,来源于银行员工创造的价值。存贷双方分享银行服务,按一定比例支付这种服务价值。把存款利息视为货币使用权的价格,可以从劳动价值论得到合理解释。这种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利息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
[关键词]利息;银行;服务;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利息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借贷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割的结果。[1]西方学者对利息有多种解释:从消费角度解释为资本所有者放弃现期消费的报酬,从生产角度解释为迂回生产的结果,从市场角度解释为资本使用权的价格。[2]这些解释有各自的依据,但是不够透彻和具体。笔者主张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利息,但对其的认识应当有所创新和深化。如果把商业银行员工的服务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就可以对利息的来源和性质做出新的合理解释。
一、商业银行的双向服务
现代社会的商业银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它的经营客体是货币,服务对象是存款和贷款两方面的客户,包括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商业银行为存款方和贷款方提供服务,称为双向服务。
经济资源极不均匀地分散于各类主体,为个人、企业、社团和国家机关所掌握。有的主体拥有的货币量多于所需要使用的货币量,形成资金剩余;有的主体拥有的货币量少于所需要使用的货币量,形成资金缺口。商业银行以吸收存款方式将前者的剩余资金收集起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贷给后者,不仅调节了社会资金余缺,而且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
城乡居民和法人实体把资金存入银行既有委托保管的考虑,也有获取利息的目的。银行得到存款后并不是单纯把它保管起来,而是以获取一定的利息为条件贷给工商企业。后者为了得到贷款,愿意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银行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愿意并有能力向储户支付存款利息。这时,城乡居民以获取利息为目的而自觉储蓄成为一种间接投资行为。因为储户不直接将资金投入工商企业,而是以银行为代理者投向可以带来回报的工商企业,银行起着投资中介作用,所以称为间接投资。为此,银行必须充分了解市场信息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选择能保证资金安全、可带来收益的项目发放贷款,并对贷款的使用和效益实行必要的监督考核,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既是向贷款方提供的一种服务,也是银行作为投资代理人向存款方提供的一种服务。把储蓄看作一种间接投资,就可以把利息解释为投资收益和银行向存贷双方提供双向服务的价值。
二、贷款利息与存款利息之差:银行服务价值
对储户来讲,既然储蓄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投资,那么存款利息就是间接投资的收益,来源于用款企业或单位的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用自有货币资本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劳动会创造新价值从而带来剩余价值;企业使用借贷资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劳动同样会创造新价值从而带来剩余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属于生产企业所有;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价值要在生产企业和提供借贷资本的商业银行以及储户之间按一定比例分割。这种分割可以由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得到解释。
当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分离时,它所带来的利润全部属于资本所有者;当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分离后,所有者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凭单纯资本所有权获得部分利润,另一部分利润归资本使用者。这两种权力分别给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收益。其分割比例取决于资本供求关系、使用效益等多种因素。假如货币所有者不以银行为代理人或中介,而是直接将资本借给企业使用,并收取利息,这时利息来源于企业利润,最终来源于在资本使用过程中由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这同马克思关于利息来源于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当货币所有者以银行为代理人将自己的货币借给企业时,通常由企业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再由银行向货币所有者支付存款利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存款利息作为投资收益的性质和作为一部分新价值的真实来源。
贷款利息与存款利息的性质和来源有所不同,前者不完全是投资收益,也不完全来源于在贷款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新价值,而是包含着银行职工劳动提供的服务价值。确切地讲,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剩下的部分是银行服务的价值。银行维持正常的业务活动,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中生产资料主要包括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造币和取款设施、保险柜、账簿、通讯和电脑设备等。这些生产资料价值同其他行业的生产资料价值一样,应当转移给产品,也就是分摊到银行服务的价值中。在银行劳动力通过市场配置的条件下,也会像别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一样发生商品化,其价值会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成为银行服务价值的组成部分。[3]与此同时,银行职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活劳动会形成剩余价值。因此,银行服务的价值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这与一般商品价值的构成是相同的。
假设某商业银行以4%的年利息率吸收1亿元的存款,然后按6%的年利息率贷给某生产企业。一年后,生产企业还本付息,银行不仅收回1亿元贷款,而且得到600万元利息。其中400万元是储户的间接投资收益,表现为1亿元存款按4%的利息率计算的利息,应付给储户。这400万元是来自生产企业的利润,实质上是生产企业职工劳动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剩下的200万元是银行服务的价值,它在数量上等于存贷款利差,但实质上是银行提供服务的收益。假设银行在一年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80万元,劳动力价值为80万元,两项之和为160万元,这构成银行经营成本;剩下的40万元为银行利润,利润率为20%。银行服务的价值由本系统内部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换句话说,银行利润是银行职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而不是来源于其他产业部门或贷款方转让的剩余价值。
商业银行的双向服务不是无偿的,需要得到适当回报。这种服务的价值通常是由存款人和贷款人双方支付的。假设在上述的例子中,200万元服务中有100万元由贷款方支付,另外100万元由存款人支付,双方享受的银行服务各占一半。为了说明双方的支付方式,不妨假设银行只向某一方提供服务。先假设银行只向贷款方提供服务,未向存款方提供服务,这时的服务价值即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的差额完全由接受贷款的一方支付。在接受贷款的企业看来,向银行支付的600万元利息是在1年内使用1亿元资金的成本,似乎都是银行服务的价格,并列入企业外购服务费用。实际上,600万元中的400万元是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属于储户间接投资收益,是对企业剩余价值的分割;剩下的200万元才是向银行支付的服务价值。在银行和用款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银行提供服务,用款企业支付200万元货币(利息)。这200万元才是用款企业外购服务的价值,同企业消耗的其他生产资料或外购服务价值一样,是生产经营成本的组成部分。因此,600万元中的200万元应由生产成本来列支,另外400万元就其性质来说是对用款企业的利润分割。不过,从用款企业角度看,无论是200万元银行服务价值,还是400万元的储户存款利息,都属于外购服务成本,也都是对生产企业利润的扣除。有些工商企业绕开银行,以支付较高的利息为条件,直接向城乡居民集资。这时只需向资金提供者支付利息,而不需要支付银行服务价值。但是要取得城乡居民的信任并大量集资并非易事,往往也要支付许多成本,至少要支付较高的利息才有吸引力;对城乡居民来收,这种集资往往有较大风险,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在金融市场充分发育的条件下,一般情况下工商企业直接向城乡居民集资未必合算。
现在假设银行只向储户服务,这时服务价值完全由储户支付。仍以上述的假设数字为例。当银行得到用款企业支付的600万元利息后,扣除200万元的服务价值,剩下的400万元支付给储户。在银行和储户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银行向储户提供服务,后者向前者支付200万元货币。这种交换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向储户支付400万元利息所掩盖。其实,储户得到的存款利息是一种投资收益,并不是银行的恩惠,只不过由银行转手而已。银行的贡献是自己的有效服务,不仅使1亿元投资如数返还,而且还实现了增殖。根据假设,这时用款企业未享受银行的服务(实际上已经享受,这里纯属假设),600万元贷款利息可以全部看成用款企业向储户支付的投资收益。既然储户独享了银行服务,那就必须用投资收益单独向后者支付这种服务的价值200万元。由于银行提供服务先于储户支付,因此可以说是银行先向储户预付服务,然后从贷款利息中扣除服务价值予以补偿。
事实上,存贷双方都分享了银行服务,所以这种服务的价值是由存贷双方支付的。在存贷业务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由双方对半分摊银行服务价值是合理的。当然,无论是存款利息,还是贷款利息及两者差额大小都允许浮动。当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工商企业经济效益较好、投资需求较大时,利息率可能上升;反之则可能下降。银行也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成本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变化来调整利差,从而调整服务价格。这种调整会改变存款方和贷款方对服务价值的支付比例,影响他们的收益。当存款利息率不变时,提高或降低贷款利息率,意味着提高或降低银行服务价格,从而增加或减少银行收益,相应提高或降低贷款方对银行服务的支付比例;当贷款利息率不变时,提高或降低存款利息率,意味着降低或提高银行服务价格,从而减少或增加银行收益,相应降低或提高储户对银行服务的支付比例;当存款利息率和贷款利息率同时发生同方向或不同方向变化时,储户、银行、贷款方究竟何者受益,取决于存贷款利息率实际变化的幅度。至于贷款方把多大比例的贷款利息计入成本,从理论上讲取决于实际支付的银行服务价值,但在现实中确定这种界限的意义不大。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全部利息都被认为来源于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4]在一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全部利息都被认为是贷款者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存款利息来源于贷款者的利润,它与贷款利息的差额则是银行服务价值,属于贷款者的生产成本。对商业银行来说,借贷资本来源于储户,最终属于存款人所有,存款利息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但是银行利润产生于银行服务,是银行员工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对外部剩余价值的分割。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银行属于第三产业,所创造的价值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此,肯定银行劳动独立创造价值是符合实际的。
三、货币使用权的价格问题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有利息是资本使用权价格的说法。根据前面的分析,存款利息的确可以视为资本使用权的价格;贷款利息由存款利息加银行服务价值构成,不完全是资本使用权价格。借贷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把单纯的资本使用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客体,那么它可以按一定的期限用于交易,利息率可以视为一定时期货币使用权的价格。例如,储户将100万元货币存入银行,年利息率为4%,银行再以6%的年利息率贷给某企业。4%的利息率可以解释为100万元货币1年的使用权的价格,贷款利息率和存款利息率相差2个百分点则是银行服务的价格。为什么货币使用权会有价格?它的价格如何决定?这个问题似乎难以用劳动价值论做出合理解释。
现代货币不是实物形态商品,而是一种交换媒介和价值符号,它本身没有由人类劳动决定的价值,或者这种价值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代货币是国家强制发行和使用的交换媒介,具有可以购买各种商品的功能,这也就是货币的使用价值。当它成为投资时,可以购买任何生产要素,因而成为资源的一般代表。如果货币不能购买商品或生产要素,就不会有使用权价格。货币作为投资的使用权价格实际上是它所购买的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使用权的一种表现,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相关生产要素的劳动决定的,当然也会受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这里以作为生产资料的厂房出租为例来说明货币使用权的价格问题。
厂房本身是具有一定寿命或使用期限的实物形态商品,它的价值由劳动决定,可用于一次性出卖,这时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分离,一次性实现价值;也可用于出租,这时两权分离,分期实现价值,房租是厂房使用权的价格。在一次性出卖中,房主转让所有权,也就转让了使用权,并一次性得到厂房价款;在出租中,房主不转让厂房所有权,而是分期转让其使用权,从而分期得到房租,也可以逐步得到厂房价款。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对厂房使用寿命进行合理分期,由劳动决定的厂房全部价值分摊到历次转让的厂房使用权之中。假设一套厂房的价值是400万元,使用寿命为40年。一次性出卖可得到400万元;如果按年出租,则40年的租金加起来不应少于厂房价值400万元。不考虑维修费,平均每年房租为10万元,这就是一年厂房使用权的价格,它是厂房价值的一种转化形态。
假设一个人拥有400万元现金,考虑两种投资选择:一是存入银行,获得存款利息;二是购买或建造厂房用于出租,获得租金。具体选择哪种投资方式取决于利息和租金多少。假设银行存款年利息率为4%,那么存入400万元1年可获得利息16万元;建造或购买厂房出租的租金按照前面的假设只有10万元,这时选择存款的收益更高;假设银行存款年利息率只有2%,那么400万元1年的利息只有8万元,这时建造或购买厂房出租收入更高。目前国内银行存款利息率较低,一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集资建设厂房出租,收取远远高于存款利息的租金,成为一种致富门路。如果银行提高存款利息率,同时企业对厂房的需求减少,则可能引起变卖厂房,把现金存入银行以获取利息。这种选择变化说明,货币作为投资的使用权价格是实物形态生产要素使用权价格的转化形态。
把存款利息解释为间接投资收益和货币使用权价格并不矛盾,实质上是货币所有者凭其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当然也是货币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一种形式。
四、充分发挥利息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货币是资源的一般代表,利息作为货币使用权的价格,在配置资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这种作用在国内尚未充分发挥,甚至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在利息率基本上由中央银行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长期不变或变化很小,未能随市场变化而灵活浮动。这种做法被认为是银行依靠行政垄断来维护自身利益,结果是用款企业普遍利润微薄,储户作为间接投资者的收入也很低,有的年份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甚至是负利息,银行业却普遍利润丰厚。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长期维持低利息率,另一方面又排斥民营银行发展,最终损害了广大储户作为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商业银行服务独立创造价值,就应当支持和引导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让它们提供双向服务,并允许这些金融机构运用利息手段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以往一些由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宣传把高息揽存说得一无是处,其实高息揽存本身是符合市场价格决定机制的,只不过存在较高风险。储户把钱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固然风险较低,但这是以低收益为代价的,未必对所有储户都是最好的选择。高利息、高风险与低利息、低风险可以由投资者来选择。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应当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如果真正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不论是存款利息还是贷款利息,都应当充分实现市场化。中央银行无疑有权决定基准利率,但是应当允许商业银行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实行存贷款利率浮动。只有完善利息率决定机制,分别发挥存款利息作为货币使用权价格和存贷款利差作为银行服务价格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
[2][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257-265.
[3]郑志国.价值增殖规律探究——献给新世纪[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34-142.
[4]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40-142.
[责任编辑:陈展图]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5)01-0017-04
[收稿日期]22014-08-20
[作者简介]郑志国,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广东广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