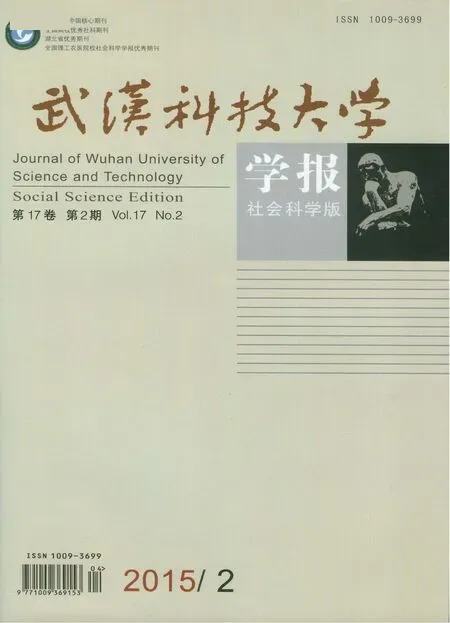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
2015-03-17丁岭杰马兆婧
丁岭杰 马兆婧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教研部,北京 100091)
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
丁岭杰 马兆婧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教研部,北京 100091)
在卢梭的规范主义和韦伯的经验主义的对立与两次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中,民主合法性的内涵渐渐明晰起来。民主的合法性包含了在规范维度上论证民主普遍可欲性的核心价值和在经验维度上承载着民主基本可行性的原则性程序,这两点的耦合形塑了人们对民主的认同和信赖。新兴的民主国家只有建立稳固的民主双重合法性,才能破解民主衰弱和民主化回潮的困局。
民主;现代民主;合法性;核心价值;人权;公民权
一、现代民主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拍打威权国家政治堤岸的声响已不如昔日响亮,但大多数主权国家不管民主与否,都愿意将民主的标签贴于自己的政治体系,以正视听。现代政治日益凸显出合法性政治的面貌,而“民主”这一政治符号似乎就成了合法性最好的栖息地或避难所。
不管在价值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民主”本身就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来源,但民主自身的合法性是什么,该合法性以什么为依据等问题似乎被忽视。胡安·林茨等研究民主化问题的重量级学者将笔墨集中于民主化的内涵、标准、过程,以及影响民主化的变量,而未系统地论述民主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认为,民主本身的合法性早就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英美法大革命中的政治家所证明,其在现代政治中已经成为了不证自明的政治原则,而自己无需再重走先人论证民主的理论之路。效法古希腊先哲,罗伯特·A·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希望以对话体的行文方式阐明民主的伦理依据,他的这一分析似乎可为我们深入探索现代民主的伦理依据打开了一个开端。
现代民主的合法性是民主(化)研究的“元问题”,其直接关涉到人们追求民主、巩固民主和发展民主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现代民主合法性的内涵和流变在政治哲学理论进路——两种阐释合法性的理论范式的对立,以及政治演进的实践进路——在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次危机中渐渐清晰起来。
一方面是两种理论范式的对立。哈贝马斯将解释合法性的理论范式分为两大类别,即规范主义(normativism)范式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前者的开创者是卢梭,其首先提出了按程序办事的合法性类型[1]271。在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共同体的合法性在于共同体本身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契约,并根据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也被翻译成“公意”)和共同利益,借助共同力量来保卫个体的自由和权利[2]。以亘古不变、包容良善准则、统辖世间万物的自然法和由此为依据的自然权利来论证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思想并非卢梭首创。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而后被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法国新教派思想家莫尔内(Mornay)所继承,最后在启蒙思想家笔下发扬光大,并成为批判旧的政治秩序和构建新型国家的蓝图。规范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其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虽然它为彰显至善和正义的政治秩序构建了伦理根基,但是在醉心于“道德星空的璀璨”时,却没有考虑到尘世中的公众——政治的社会根基——能否认同这样的规范性标准,进而依此来评判和影响政治秩序。如果缺少大众认同,再美好的政治伦理标准也只能停留在学者的论著中,而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依据。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合法统治也需要取得支持,否则它也就不能继续存在,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价值已经难以取得信任[1]290-291。
哈贝马斯将马克斯·韦伯定位为经验主义范式的典范作家。韦伯将价值取舍和经验描述加以两分,认为合法性无涉于应然的规范,只体现为被统治和被管理者对统治者和管理者实际而稳定的服从。其以统治权威来定义合法性:“统治(权威),在具体的情况下,可能建立在服从的极为不同的功能之上:从模糊的习以为常,直至纯粹的合理性的考虑。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只局限于判断人们是否认同现存政治秩序和探寻认同的现实来源[4]。韦伯的经验主义范式在阐释合法性上有几大缺陷。首先,其以权威、统治、服从和稳定等来解释合法性,并将这些作为合法性的近义词,这不仅没能清晰地解释合法性的内涵,反而使合法性成为依附于这些词的赘余。其次,经验主义范式虽然探寻了合法性的来源,但是没有深入分析政治体系因价值基础不同而在维系稳定的“统治-服从”关系上表现出不均等的效能。任何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苛求韦伯,因为在他的那个年代,民主的发展并不如当今如此遒劲,独裁和威权政体甚至有时还展现出比民主更好的管制效能。然而时至今日,人类一次次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都证明了,一个政权的价值基础不但决定了其在形态学上的分类,还影响了其维持长久合法性和稳定秩序的效力。最后,秉持价值中立的合法性分析极易产生一种价值选择上的误导:只要能维持稳定秩序的政体都是合法的,都该被认同和服从。这使得该范式不但不能引导人们辨识政权的良莠善恶,反而沦为替暴政辩护的理论工具。哈贝马斯就认为,经验主义范式可以被运用在社会科学中,但由于其放弃了公认的理由的重要性,从而难以让人满意[1]293。
在重构合法性的过程中,为了避开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泥淖,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或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 有一些好的根据”[5]。也就是说,合法性是由良善价值根据和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可组合而成的。
另一方面是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次危机。法国学者罗桑瓦隆(Rosanvallon)认为,分别发生于1890~1920年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现代民主危机,带来了民主理念的重大变革,孕育了实现民主基本价值的新机制,并扩展了民主合法性内涵。
现代民主继承了源于古希腊民主的政治哲学和基本构想(foundational fictions),即整个人民的意志是公共目标的正当性基础。在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中,公民之间没有根本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的分歧,因此多数人原则(the rule of the majority)便可以呈现和代表这种普遍的人民意志。现代民主摒弃了古雅典的直接民主机制,但却以投票选举来寻求集体共识,然而在多元化的现代国家中,那种理想化的共识似乎早就难以寻觅,“多数几乎能代表整体”的合理性和在此基础上选举制度的可行性也日渐微弱。到了19世纪末,公民(主要是男性公民)普选权在欧洲的普及促进了社会大觉醒,但民主随后却淹没在政党和利益集团对一己私利的“你追我逐”中,而且选举政治和代议民主往往难以产生公共理性和呈现公共利益。
在第一次合法性危机之后,建立强大的行政权以扭转民主合法的流失,就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日程。人们认为较为中立的科层机构可以避开党派竞争的干扰,以务实和客观的普遍方式来对公共福利做出积极回应,此时公共行政机构和公民普选权成为支撑起民主大厦的两根顶梁柱。 前者实现了传统意义上民主的程序性、合法性,即权力基于民众的认可,而后者又为民主补充上了实质性、合法性,即权力要能实现预设的基本目标和价值。
民主发展的历程就是价值和机制不断变动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合法性危机带来了新的民主运行机制,然而新机制不但未能解决选举制度的旧问题,反而又为民主的下次危机埋下了伏笔。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多元化继续发展,人们不再将某一政治活动和政治机构中的多数人简单地等同于人民,而是将人民看成是一系列少数人的集合和多个特定历史情境的加总。因而,选举和投票不能为某些政治输出赋予至上的合法性。此外,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这一运动大力提倡社会运转向市场机制回归,并质疑国家在供给公共福利上的权威和效能。
鉴于第二次危机,罗桑瓦隆主张,以消极普遍性(negative generality)、倍增普遍性(generality of multiplication)和特殊关注普遍性(generality of attention to particularity)这三大机制,来促使民主制度在价值、结构和功能上更加复杂和多元。这样的民主不但能在分配公共福利和规范社会运行上做到允执厥中,而且能将公共政策同具体环境中多元主体的特定利益相贴合,从而产生出新的合法性①。
两种范式的对立在横向对比中揭示了民主合法性构筑于应然的价值和实然的认同,而两次民主合法性危机在纵向的政治历史演进中描述了民主合法性在伦理维度和程序维度上的流变,两者都展示出了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因此,本文认为民主的合法性包含了,在规范维度上论证了民主普遍可欲性(desirability)的核心价值和在经验维度上承载着民主基本可行性(feasibility)的原则性程序,这两点的耦合形塑了人们对民主的认同和信任。这里提及的“可欲性”主要是指,某种政治制度由于在构建、运行和改进上符合和最可能符合被哲学与政治经验充分证明为良善的伦理标准和公共目标,而被人类普遍地认可和欲求。
二、民主合法性的第一张面孔:核心价值
(一)人权和公民权: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
“民主”在希腊文中为“δημοκρατíα”,其字面意涵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利”。亚里士多德也以多数人的统治来描述公民政体(类似今天所指的良善的民主制)的外部特征。然而“人民的统治”只是民主运行机制的一般外在特征,不具备独立的正当性,也不能完备地论证民主的基本目标和伦理依据。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区分正义和变态的政体时,采用的就不是统治主体人数的标准,而是公正分配利益的标准②。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人民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也并非总能激起民众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罗伯特·A·达尔认为“中世纪意大利的某些城市国家亦转变为大众政府”标志着民主的一次重大转变[6],但事实上,这些城市国家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而非大众民主制,更为关键的是,普通市民在合法性认同上对“人民统治”并无好感,甚至将其等同于对“多数人暴政”的鼓噪[7]。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大放异彩,对后世的民主与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蒙思想家构想的自然状态是对历史上人类存在和组织形态的虚构,但是自然法理论却揭示了普遍适用的政治判断,即人类(实际或应该)构建、选择和服从某种政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使其能更好地承认和发展人类文明而非其具体的运行特征。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文明的基本目标是约束人的本性,但又保障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从而让人类的理性力量能至臻至强[8]。假设某种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否认文明的目标,甚至异化为野蛮、恐惧和蒙昧的最大制造者,那其存在就不可能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具有独立的和普遍正当性的人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公民权,超越了民主运行的表征,集中体现了文明目标和自由尊严等良善伦理,构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
人权是民主制的终极价值和伦理根基,其体现了制度对所有人的尊严的终极关怀。由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实在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理性与德行的历史性,现代民主主要还是在主权国家的领土之内运行,并依据人权伦理平等地保障广泛的公民权,进而直接以由人权终极价值转化而来的公民权的根本价值来支撑制度的正当性。然而政治运行的现实总是能证明,在宏观的历史跨度上,基本完善的民主制往往能避免大规模的人权侵害,并更能让公民权体系的扩展和政治体系功能的流变趋近于人权价值。
(二)权利价值在目标层面上对现代民主可欲性的支撑
人权和公民权主要在民主的目标层面和主体层面上支撑起了民主的可欲性。
在政治过程维度上,民主的权利目标是,公民(开放的政治身份)能平等、自由、安全和有序地参与政治的输入与影响政治输出,并且能够利用公正的政治法律结构来救济被侵害的权利;在政治结果维度上,民主制的目标是,寻求政治体系、法律和公共政策在最大限度上与最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意志相耦合,并保护公民中的少数派和非公民的基本人权。
实现多数人的利益是民主的原初目的,而保障少数人的人权是民主的矫正性目的,后者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中尤为重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多数原则基础上的政治决定往往不能准确地提炼出公共意志,而且单一的多数原则还会将选举投票中的少数派排斥于人民范围之外。所以,民主制只有以人权为政治底线,才能避免严重偏离公共利益和个人尊严的民主决定,避免削弱民主的正当性。也正因如此,在分析现代民主中“人民”的概念时,萨托利才认为多数人的决定加上少数人权利,才能保障民主真正地成为全体人民的统治[9]。
(三)权利价值在主体层面上对可欲性的支撑
人权价值在终极理想上设想了所有具有参政能力并能承担公共责任的个人都应该成为平等而自由的民主政治主体,这些主体又在民主参与中提高自己的公共理性和政治德性。罗伯特·A·达尔认为人本质上的平等性是民主弱势原则的主要内涵,其无法被其他理论所驳倒,并且使民主具有普遍的可欲性[6]。然而在上述的历史局限性面前,现代民主制往往是在制度可行性上寻求终极目标的逐步实现,即其主要是在主权国家中普遍地肯定成年国民的平等公民资格。
当然,在现实政治中,人权价值并未被公民权价值完全取代,而是在权利主体范围的不断延展中巩固和补充民主的正当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人权价值的道义主张和政治实践的实际困境间的张力,推进民主制度不断向终极价值回归,修正原有的政治体系和过程,从而相应地把原本无法平等享有公民权的国民(如妇女、有色人种、某种宗教信徒、特定的民族和族群)纳入到平等的权利体系中,并更为关注外国人和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保障。美国学者李帕特就分析了一种能保障国内民族集体权的民主形态——协和民主。该民主将国内各个民族作为独立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保障它们推行民族自治和分享国家权力的资格。这一方面补救了历史上的制度性歧视对民主普遍可欲性的腐蚀,另一方面回应了人权价值规定的民主延展性③。此外,在移民问题上,欧美民主国的具体制度和态度不尽相同,并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公共舆论的波动而变动,但是人权思想的启蒙使得政府和公众整体上能尊重非法和合法移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这种包容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外来移民对民主制的认同。
三、民主合法性的第二张面孔:程序基础
权利核心价值在规范的维度上,证成了民主的普遍可欲性,并成为民主与其他制度相区别的伦理标准。然而,如果良善的政治伦理和美好的社会状态只能被部分思想精英主张,而无法借助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从天上降临人间”,那么民主在价值上被设想得越完美,其在乌托邦的泥淖中就陷得越深,就越无法成为被大众普遍信仰的改良政治体系的制度武器。所以民主的合法性不只体现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价值,也体现为能实现某种可欲求结果的效力[10]。从精英的制度理论和大众的政治运行经验中诞生的民主程序基础,通过制度改良弹性、制度可欲性与代理人问题相隔离以及政治过程的非暴力化这三个机制,规划了民主核心价值的实现路径,验证了民主制的基本可行性。
(一)制度改良弹性机制
和其他制度一样,现代民主的存续和功能发挥都依靠于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架构。但民主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必须依据政治生态的变化,调整价值体系和运行过程,以提高自身实现核心价值、回应公众诉求、巩固自身稳定性的能效。民主从歧视性的封闭制度到平等的开放性制度的转变就是对这一改良弹性机制的体现。
一方面,改良弹性机制作用于民主权利外延的扩展。早期的现代民主带有一定种族主义和阶级排斥的色彩,其往往只承认特定种族中有产者的完备公民资格,并且只保障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随着全民教育的普及、大众权利意识的提高、社会底层的经济重要性的增加,工人和少数民族通过利用权利理论和已享有的政治自由,发起了针对歧视性制度的政治抗争,以主张国家实现全民平等的政治权、普惠的社会福利权乃至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和民族自治权。在抗争带来的道义和经济压力之下,民主国家逐渐开放政治过程,将多元的主体和诉求纳入民权体系。表面上,民主制度的内部结构是对立的,其封闭的制度大门反而是被自己信奉的价值和保障的权利所推开的,但在实质上,民主制度内部又是统一的,社会底层对基本权利(即便是不完全不平等的)的享有,以及民主权利的扩展和平等化都契合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并避免了政治转型中的大动荡和大分裂。
另一方面,弹性机制作用于推进民主运行方式的多元化。国家中存在着能被民主程序所提炼的公意,是现代民主从古典民主那继承下来的基础性假设,而且民主国家中的精英和大众又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普遍认为,多数人原则和在此基础上的投票选举是提炼公意并赋予政治行动以正当性的最佳手段,因此,选举投票就成了民主国家最为关键的政治程序。但在多元社会中,投票选举所产生的数量上的多数派并不能在社会学意义上真正地代表公意、公益以及特殊人群的利益,因此,民主不但要构建于奥唐奈所言的“自由投票所呈现出的大众同意”[11]之上,而且还需将罗伯特·A·达尔所阐述的“多重少数人的统治”[12]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基础。
“多重少数人统治”意味着民主运行必须突破投票、竞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和读报办报等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并直面某些特殊群体(如妇女、少数民族、移民族群和社会底层阶级等)的少数派位置被制度固化的问题。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经济发展促使民众越来越关注公正和自主而非单纯的物质利益④,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心理和道义动力。而民主制度中既存的自由开放的政治竞争场域和公民权利体系,既保障了公民与政府可以利用既有制度来进行正和博弈并构建新的政治参与渠道,又为传统民主参与方式与新兴政治参与方式之间的衔接和互补提供了制度框架。这些社会政治条件激活了民族自治、社区自治、社会与政府间的直接合作、公民论坛、抗争政治、司法诉讼和权利的国际救济等有别于传统民主参与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政治输入和输出层面,这些参与方式强化了政治过程同普遍公共意志的契合;在政治发展层面,它们为民主对自身缺陷的修正提供了政治信息反馈机制[13]。美国在经历民权运动后不断加强对黑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加拿大不断完善对魁北克人和土著人的文化权与自治权的保障。20世纪70年代后,在移民问题的压力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相继放弃针对移民的同化政策,转向采取宽容多元移民文化的制度安排[14]。这些都体现了民主制在保障权利上的改良弹性。
(二)制度可欲性与代理人问题相隔离的机制
现代政治在具体运行维度上主要体现为代理人政治。从理论上讲,代理人应该胸怀天下,秉公用权,为民谋利,克己复法,最大限度地与权力所有人的价值和利益保持一致。然而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政体(包括民主政体)的代理人的政治行为和决策结果都可能会与权力所有者为其预设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目标相抵牾,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代理人的经济人特质、代理人的理性有限性、社会文化特性、授权和限权制度不合理、经济和政治波动等。威权和全能主义政权将掌权的代理人与政体相同构,并主要从政绩中获取合法性,由此政权的根本正当性会在权力代理人的失职和政绩的大滑坡中严重流失[15]46-47,而且正当性流失的程度还同公权力的范围呈正相关。
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未来发展的两大程序性支柱,但在国家层面,间接民主还是民主运行的主要制度安排。间接民主也是代理人民主,即公民在自由、开放、有序的政治竞争场域中,辨识、寻找和监督有一定任期和权限的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民主。虽然间接民主也面临代理人和政绩问题,但按照胡安·林茨的阐发,民主程序在民主制和政绩问题间构筑起“绝缘层”,使得民众对民主制度基本认同不被经济衰退所损害[16]52,85。具体而言,有四大限权分权程序通过代理人责任制度化,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分散化,以及政策纠偏和权利救济法治化,破除了政治体系、公权力代理人和社会发展绩效三位一体的同构,从而构筑起了制度可欲性与代理人问题相隔离的机制。
首先是代理人民选程序。此程序虽然在提炼和反映普遍的公意上有弊端,但是自由平等的投票选举制度基本上能实现“政权民授”这一程序正义。其防止政治体系本身因选人用人失察而遭受责任过载,而且保证了代理人的有限任期和新代理人产生的可预计周期,进而以民意基础上的代理人新陈代谢过程,消除了民主政治体系同特定代理人的绑定。
其次是权力制约程序。现代民主绝非要借助多数人原则建立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因此,尽管在公共权力的具体运行方式上大相径庭,但是各民主国家都严格划定了公权力的边界,并建立起了分立权力、制约权力和下放权力的具体制度。这意味着民主制打碎了政治权力汇集而成的硬块,将分散的权力和责任配置于多元的分支机构中的代理人。机构与机构、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制衡避免了“集中权力办坏事”,也明确了特定机构而非整个民主制在政绩问题上的责任。
再次是公民参与程序。民主制的基本特征是“人民的统治”,在现代民主中呈现出两层意涵:第一个层面是公民在公共政治中,决定、影响、认知、监督公权力代理人和公共政策的产生与运作;另一个层面是公民在公权力的边界外,对自身事务进行自主决定和管理。这种多元的公民参与保证了公民能同政府共同分担推进社会普遍福利的权能和责任。而且多元参与形成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带有传感器的预警系,为减少和纠正法律与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偏差,提供了全面的数据支持和强劲的民意动力[17]。多元化的公民参与降低了全国的政绩因某个代理人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生概率。
最后是法治运行程序。现代民主是法治的民主,其原则、制度、程序和演进都被法律所规约。在民主国家中,一方面,宪法规定了民主政治基本原则和基础制度框架,而且这些原则和制度框架只有获得绝大多数公民的同意并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才能被修改。比如在美国,只有当国会的三分之二议员或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认为必要时,宪法修正案才能被提出,而且修正案的生效也需经由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或四分之三的各州国民大会的批准。另一方面,成文或非成文宪法具有实质性的最高法律效力,这意味着政治主体可以通过宪法诉讼和宪法审查或其他司法程序来救济权利和裁断政治争端。比如美国的普通法院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通过宣判法律违宪来终结其法律效力和救济公民的宪法权利。又如,英国虽然没有宪法审查制度,但公民可以通过向法院和行政裁判所提起行政诉讼来限制行政权和救济受行政权侵害的权利。此外,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准司法制度也能代表议会独立地处理行政争议,这些制度都维护了英国的民主法治。
(三)政治过程的非暴力化机制
政治的起源和运行都离不开统治者垄断组织化的暴力和强制力,并以此为后盾来维护制度稳定,引导公共活动,协调利益冲突和惩罚失范行为。但现代良善政治体系不但不以暴力和强制力为自身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基石,而且还要在政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政治结构施加组织化暴力的强度、广度和频度,以达成政治过程的非暴力化。
从政治转型的视角来分析,政治过程暴力化在两大路径中产生和强化。一方面是对暴力的路径依赖。在分析民主转型时,亨廷顿阐发道不管是维护旧制度的权威领袖,还是为新社会开路的民主的反对派,只要以暴力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日后定会对暴力的使用“驾轻就熟”并成为主导政治进程的力量。无论它们哪方得势,政治体系通向和平、包容、妥协和克制的道路就会被相应地截断[15]194。另一方面是镇压悖论。在分析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时,美国学者西德尼·塔罗这样描述镇压悖论:当局的镇压通常不会根除抗争,而只能促使抗争向更隐蔽、更严密,甚至是更为暴力的方向转变[18]。这两个过程构成了一个政治过程暴力化的恶性循环:当权者热衷并熟练地使用暴力促使非掌权主体的政治行为暴力化,反过来,社会运动的暴力化又强化了当权者对暴力镇压的依赖。在民主化中,土耳其当局往往以压制库尔德人的民族文化和剥夺其民族自治权来推行国家世俗化改造,并惯常以武力镇压来应对民族反抗。这些举措一步一步地把普通民族冲突和政治争端转化为库尔德人的暴力民族分裂活动。在克罗地亚独立过程中,作为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人支持克罗地亚人的独立选择并只主张本民族基本的权利,如政治平等和民族自治。但是克罗地亚当局却控制的民族主义新政府在政治参与、就业和福利分配上也施加民族歧视,这些都导致了未来两个民族之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些事件中的民族暴力冲突又都强化了当局对暴力镇压的路径依赖⑤。
民主政治通过构建多元政治博弈系统来破解这一暴力循环。时间维度上的多元博弈表现为自由公正程序所产生的政治获胜者,不无限扩张权力也不封闭政治竞争和政治流动的渠道,而失败者在基本权利保障和下次获胜机会的基础上,认可胜利者在特定时期和权限内的政治权威。空间上的多元博弈体现为,政治主体自由地通过多种政治参与渠道来和平地主张权益和影响政治过程,在不同政治子领域发挥相对的权能优势,并打破选举投票所划定的多(少)数派地位的绝对性。在多元博弈中,理性的政治主体只有放弃极端化的主张以及行为,才能通过争取最多数的中间选民来获得政治资源和道义支持,否则将被政治规则直接淘汰出局。在西班牙的民主化中,苏亚雷斯当局就积极稳妥地推行全国选举,颁布保障民族权利的宪法以及向民族地区下放中央权力。这些都为这两个民族平等地参加全国政治和行使民族自治提供了制度支持,从而强化了他们对统一国家和民主制度的认同,并基本上消除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削弱了民族暴力对政治稳定的破坏力[16]103-120。
民主制度一方面为这种多元博弈搭建了开放而和平的制度化竞争平台,并依靠政治强制力将违背人权底线的暴力主张和行为排除在博弈之外;另一方面,为博弈构建自由平等的权利体系基础,并借助超然于投票选举、政党竞争和利益集团争夺的政治结构(如法院)来公正裁决博弈中的权益争端。多元博弈的良好运行还离不开大众与精英对相关政治规则和结果的信任,菲利普·施米特称这种信任为意见耦合(contingent consent)[19]。从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意见耦合在民主的原初制度中更容易诞生和持续。民主制下的多元博弈实质性地提高了暴力政治的物质和道义成本,并为政治权益的和平实现提供了现实渠道。正如卡尔·科恩所言:“与任何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更有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20]
四、民主的合法性与新兴民主的巩固
从20世纪70年代的葡萄牙 “康乃馨革命”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路高歌猛进,涤荡了一批又一批威权国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浪潮却逐渐偃旗息鼓。从形式上看,非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减少,降低了再出现大规模民主化的可能,但更为关键的是,纷纷建立的选举民主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并未带来权利保障、政治自由和社会稳定。 因此,拉里·戴蒙德认为“民主在第三波后期变得日益空虚”,并认为通过巩固新兴民主来避免民主化回潮是当务之急[21]。
民主合法性的缺失是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普遍问题,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政治精英往往将民主制当成是谋取政治权力(甚至是专断权力)的新路径。执政的政党和政治领袖不是强化专权并谋取家族和利益集团的私利,就是扩大手中政治权力和将政治特权固定化(甚至是宪法化)。南非的国大党在南非民主转型后长期把持南非政权,并日益倾向于以国家公权力来谋求本党的一己私利和以政治社会公正为代价来迎合黑人选民⑥。在巴西、阿根廷和菲律宾,委任制民主大行其道,在此类民主制中,选举产生的总统成为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其按照个人意图行使只受任期和某些刚性制度制约的巨大权力,并将决策失误的重大风险转嫁给普通大众[22]。更为极端的委任民主还表现为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能借助民粹主义的力量来轻易地修宪,从而削弱任期制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撼动。此外,很多在野的政党和集团名为民主的反对党,实为“反民主党”,它们不只是像西方的在野党那样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是为了自己能坐上“民主国王”的交椅,而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来反对当局并腐蚀整个民主制度。普通公民不是成为坐看一幕幕“城头变幻大王旗” 的政治闹剧的“麻木看客”,就是被“裹挟”进各种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精英的鼓动下成为反民主的急先锋。在泰国、柬埔寨和孟加拉,反对党不是通过诉讼来质疑投票,也不是通过议会和媒体来监督执政党,更没有耐心等待下次选举中的翻盘,而是通过街头政治来抵制选举结果甚至是反对整个选举制度⑥。在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对“台湾立法主管部门”通过“服贸协议”的杯葛(boycott 联合抵制),也从议会争执发展为公然支持学生占领“台湾立法和行政机构”。经历了政治主体在民主制下自挖民主墙角的政治历程,民主的核心价值在精英和民众的心中逐渐失去感召力,民主政治竞争场域也异化成了破坏稳定与发展并侵蚀民权与良知的“斗兽场”。这两个相互交织和强化的进程削弱了大众对民主法治的信任与期盼,并极可能导致民众开始怀念原先那个无自由但稳定的威权时代。提出一个巩固民主的具体方案虽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可以肯定的是,无法建立稳固的民主合法性的国家绝不可能破解民主衰弱——形式上的民主制由于行政集权、政治腐败、选举舞弊和街头政治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并且不能公平保障权利和有效规范政治过程,以及民主化回潮——多个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在亨廷顿所阐发的滚雪球效应下接连退回到半民主或非民主的状态。
注释:
①本文对罗桑瓦隆的民主合法性危机理论的阐发参见Pierre Rosanvallon. The metamorphose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impartiality, reflexivity,proximity,Constellations,Vol.18,No.2,2011,pp.114-123.
②亚氏的政体划分理论参见颜一:《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8-89页)。
③协和民主理论参见李帕特:《多元社会的民主》(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④大众需求的转变参见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2,No.4,1988,pp.1203-1230.
⑤关于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具体案例分析分别参见H.Ayla Kiliç.Democratization, human rights and ethnic policies in Turkey,JournalofMuslimMinorityAffairs,Vol.18,No.1,1998;Bo Rothstein. 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No.3,2009.
⑥参见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1]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杨国政,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1-20.
[3]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9.
[4] 张康之.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3):63-68.
[5]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6] 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下)[M].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75.
[7] 约翰·邓恩. 民主的历程[M].林猛,李智,吕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2.
[8]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
[9]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
[10]Sarsfield R, Echegaray F. Opening the black box: how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its perceived efficacy affect regime preference in Latin Americ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6,18(2):153-173.
[11]O’Donnell G. The perpetual crises of democracy[J].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18(1):5-11.
[12]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M]. 顾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1.
[13]理查德·威廉姆逊. 为什么要民主?[M]//刘军宁. 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2.
[14]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M].杨立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7.
[15]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6]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 孙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7]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54.
[18]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 吴庆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14-115.
[19]菲利普·施米特.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M]//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
[20]卡尔·科恩.论民主[M]. 聂崇信,朱秀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27.
[21]拉里·戴蒙德. 第三波过去了吗?[M]//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03,409.
[22]基尔摩· 奥唐奈.论委任制民主[M]//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63.
[责任编辑 周 莉]
2014-05-05
丁岭杰,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博士生,主要从事人权保障与民主建设研究.
D082
A
1009-3699(2015)02-01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