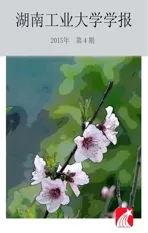翻译的目的之辨与本质之思*
2015-03-17张冬梅
张冬梅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翻译的目的之辨与本质之思*
张冬梅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论文以辨明翻译目的、厘清翻译本质为旨归,指出翻译目的有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两个层次,前者关乎翻译之“本”,是翻译活动本己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目的,具有稳定性和恒久不变性;后者关乎翻译之“用”,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附系于翻译活动之上的目的,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在翻译活动的行为链条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外在目的是通过内在目的的实现而实现的。翻译的内在目的是“使相解”,也应该是、必须是“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让翻译活动“是其所是”的目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础和依据,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内在目的;外在目的;翻译之“本”;翻译之“用”
一 引言
翻译目的问题是每一个翻译实践者或关注翻译实践的翻译研究者在从事实践或研究之前都必须思考的基础性问题。“目的”一词,从字面而言是目光指向的地方,意即企望之所在。人类一切深思熟虑的自觉行为都是有目的指向的行为,翻译也不例外。“对于主体人来说,有了目的才能行动,由现实目的支配的行动才是自觉的行动。目的作为实践活动的支配力量,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始终。”[1]目的是主体的行为指向某种事物或境况的内在根据,翻译目的是翻译实践诸要素、诸方面、诸环节彼此联系的纽带,导引着翻译实践的方向,规定着翻译实践的方式和方法。
翻译目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因答案多元不定而给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认知困惑与选择困惑的问题。当我们读到道安的“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我们似乎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一元的、确定的答案。然而,当我们读到,“在翻译领域中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可能是‘为了谋生’),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可能是‘为了教育读者’),以及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例如,‘为体现源语的结构特点而采用直译法’)”,[2]我们却又发现,翻译目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因人因时因势而异的问题,其答案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那么,翻译目的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是确定还是不确定?上述种种各不相同却又各自成理的翻译目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在翻译活动的行为链条上分别占据什么位置?在翻译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复杂缠绕关系?本文试从区分“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入手,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以期解开由翻译目的的多元并存给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的认知与选择困惑。
二 翻译的目的之辨
“事物的‘开端’,常常也是事物的‘本质’所在。”[3]为了获得对翻译目的的深入理解,让我们从翻译活动的起源开始考察。巴别塔的传说是翻译理论中常见的隐喻性叙事。尽管巴别塔之乱对于翻译活动而言不过是一种“无源之源”,巴别塔之传说也不过是“关于神话起源的神话,关于隐喻的隐喻,关于叙述的叙述,关于翻译的翻译”,[4]然而,翻译活动之产生正是源于人类语言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当是不容置疑的了。“‘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然而,操不同语言的人要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就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5]1尽管翻译活动的确切起源时间如同语言本身的确切起源时间一样不可考,然而“人类之间开始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刻就是翻译实践活动肇端之际”[6]这一论断当没有人反对。诚如谭载喜教授所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7]从翻译活动的起源中我们似乎瞥见了翻译活动的目的。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周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唐朝孔颖达在《礼记正义》[8]中对“寄”“象”“狄鞮”“译”等词一一作了解释:“达其志通其欲者,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晓达五方之志,通传五方之欲,使相领解。其通传东方之语官,谓之曰寄,言传寄外内言语;通传南方语官,谓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内之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在《册府元龟》之《外臣部·鞮译》中,有如下关于周代翻译史实的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9]2翻译活动之产生,正是源于“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源于人类语言各不相同这一“语言殊”的事实;源于在“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五方之民”之间存在着的“达志通欲”的愿望。可以想象,如若没有“语言殊”这一事实,没有在“语言殊”的人们之间存在的“达志通欲”的愿望,翻译活动根本就不会产生。人类通过翻译活动想要实现的最初的和最根本的意愿在道安的“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中找到了极好的表达,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可说是对翻译活动之价值目标的极好注解。翻译就像一座桥,搭起在“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五方之民”之间,通过此桥,人类想要跨越因“言语不通”所造成的障碍,实现“达志通欲”“使相解”的愿望。分析至此,翻译的目的似乎是清晰的、确定的。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之间的复杂勾连时,这一关于翻译目的清晰的、确定的认识似乎立刻变得模糊不定起来。翻译史著作告诉我们,我国早年的佛经翻译是统治阶级为了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5]18徐光启等人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是为了“裨益民用”,[9]44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新民”。[10]翻译理论著作告诉我们,“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构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11]“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可能是‘为了谋生’,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可能是‘为了教育读者’”。[2]27无论是“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还是“裨益民用”“新民”“建构文化”“教育读者”或是“谋生”都是对翻译目的的论述。问题是,这些目的与“换易言语使相解”之间是什么关系?
翻译活动之产生,除了源于言语不通这一事实以及存在于言语不通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愿望之外,一定还有一个外在于翻译活动本身的原因存在。“人们交流都有一定的意向,正常的人际交流不会为交流而交流。”[12]翻译这项应人类文化交流需要而生的实践活动总是为着满足某种愿望或需要而存在,总是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连。诚如蒋百里所言:“翻译本为一种手段,若仅为舌人传递而已,则至于文字之正确精审已达最高点。社会上既无特别反响,而此事业之本身,亦决不会发展。惟其为主义运动也,则为有目的之手段,能于干燥之事实上,加以一种活气,枯窘之文字中,与以一种精神。”[9]246无论是徐光启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须先翻译”,或是梁启超的“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严复的“为了炎黄种族不至沦亡,为了中华古国的复苏而勤奋译书”,鲁迅的“借外国的火,来照明中国的黑夜”“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直接为革命服务”,当代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中的“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所有这些论述中,翻译都是一种如蒋百里所言的“有目的之手段”。
只不过,“强国”“超胜”“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诸如此类的目的都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目的,是论者基于特定需要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利用翻译实现“换易言语使相解”之后希望达到的某种效果。这些外在目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附系于翻译活动之上的目的。它往往是多元的,不稳定的,无常的,变化的,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始终有多种途径可供选择。当梁启超在《论译书》一文中疾呼“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之时,就曾经指出,“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欲救斯敝,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13]可见,在梁启超那里,尽管“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但并非唯一之义。与此相对,“使相解”则是翻译活动的内在目的,是翻译活动本身固有的目的,是翻译活动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的历史使命。要在“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五方之民”之间实现“达志通欲”,翻译是唯一的途径。“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只有通过翻译活动才可以实现的目的。它是一元的,稳定的,恒久不变的,抽离了这种目的,翻译活动本身将不复存在。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不仅是对翻译目的的论述,更是通过言明翻译目的来获得对翻译活动的界定。借用英国哲学家黑尔的术语来说,翻译是一个“功能词”,“为了充分解释这种词的意义,我们必须指出它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它应该去做的是什么。”[14]对于翻译这样的功能词,贾公彦正是用目的或功能来实现对它的界定,说明我们期望翻译在本质特征上要提供什么。
同时,目的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在人类行为的链条上,目的和手段是相互转换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目的总是有限的,相对的,它本身既是目的,但也可以在下一个行为链条中表现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在下一个行为链条中实现了的目的本身又可以成为再下一个行为链条中的手段以导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目的,如此递进,以至无穷。“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就此而论,为了作为手段而需要实现的每一个条件,都是欲望和所期待的结果的对象,同时在实际中已经达到的目的,相对下一步的目的而言,都是手段,同时也是对先前已做评价的检验。”[15]将“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与“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置于翻译行为的链条中观察,我们发现,二者分别处于两节行为链条的末端,这两节链条紧紧相扣,但却分明是两节链条,中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翻译活动的直接目的,位于第一节链条的末端;而“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是通过翻译实现“使相解”之后希望达到的目的,位于第二节链条的末端。“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的实现为“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的实现打基础、创造条件,而“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则为“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的实现提供方向和动力。徐光启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须先翻译”清楚地说明了“会通”这一翻译活动的内在目的与“超胜”这一翻译活动的外在目的之间的层次关系:翻译以实现会通,会通以实现超胜,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之间存在着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三 翻译的本质之思
“一说到目的,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只是指外在的合目的性而言。依这种看法,事物不具有自身的使命,只是被使用或利用来作为工具,或实现一个在自身以外的目的。这就是一般的实用观点。”[16]外在目的强调的是“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适应性”。“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是人们根据某种特定需要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利用翻译实现“换易言语使相解”之后希望达到的某种效果,这种目的并不是翻译本身所固有的,也不是翻译本身所特有的,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机缘而外在地、偶然地附系于翻译活动之上的,其内容变动不居,因人、因时、因势而异。通过外在目的,我们看到的是翻译之“用”,看到的是翻译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联。
内在目的是属于“事物自身”的目的,是本己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目的。“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让翻译活动“是其所是”的目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础和依据。这一目的为翻译活动所独有、为所有翻译活动所共有,是翻译得以区别、独立于其他范畴的最为典型的依据,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是翻译活动据以产生的内在推力,是翻译活动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在地拥有的、恒久不变的目的。这一目的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强加的,也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关系而存在。通过内在目的,我们看到的是翻译之“本”,看到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内在目的关乎翻译之“本”。“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对于翻译活动而言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定性的。换言之,翻译的内在目的是“使相解”,也应该是、必须是“使相解”。如若不然,翻译将不再是翻译,译者也将不再是译者。外在目的关乎翻译之“用”。“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对于翻译活动而言没有规定性。换言之,具体翻译活动的外在目的可以是“强国”“超胜”,也可以是娱乐、赚钱等。对于“强国”、“超胜”等外在目的,译者始终拥有接受或拒绝的选择自由。为“强国”“超胜”这一外在目的而译的是译者,为娱乐、赚钱等外在目的而译的同样是译者。
无论翻译的外在目的如何改变,翻译的内在目的始终不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外在目的对内在目的之实现造成影响或干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在一项具体的翻译活动中,一个译者因翻译之外在目的的需要而不得已选择暂时悖离翻译之内在目的,我们说这是翻译活动偏离其本性的时刻,而绝非翻译活动彰显其本性的时刻。如果在一项具体的翻译活动中,一个译者一开始就不打算通过实现翻译之内在目的来实现翻译之外在目的,不打算在实现外在目的的同时也实现内在目的,我们可以说这项实践活动已不是翻译活动,译者不是在翻译,而只是在利用翻译。正因如此,当梁启超为了“强国”、“新民”的外在目的而将《哀希腊》中的“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I dream’d that Greecemight still be free”翻译成“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将“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翻译成“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时,后世学者将这一做法称之为“意译”风尚、“豪杰译”或“改写”、“挪用”,亦即其偏离了翻译活动的本性。而当女性主义译者为了实现“让语言为女性说话”这一外在目的而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纠正”原文,在原文与女性主义立场相异时以积极介入的姿态改动原文,并在译文的前言或后语中刻意彰显自己对原文的操纵之时,此时的文本实践,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政治目的对翻译的利用。
“对于译者来说,最高的价值是理解——尽管是在一个宽泛而又多变的意义上。所有其他的相关职业价值——真实、清晰、忠诚、信任——都从属于理解。我认为这就是界定译者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以及翻译行为之责任的边界。”[17]“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集中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宗旨与精神,同时也对译者的职业责任产生了内在的规定性。故而,在钱钟书先生誉之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道安就有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在道安所论述的因“时俗有易”、“愚智天隔”所带来的翻译之“不易”与因“名物不同”所带来的翻译之可能的“失本”中,我们读到的,正是那“惟恐失真”、“兢兢于失实”的译者之心,而“惟恐失真”、“兢兢于失实”的背后正是穿越在语言边境线上的译者对“传令知会通耳”“换易言语使相解”之使命的深刻理解和真诚践履。
“通过翻译,作者可以摆脱自身语言之牢的桎梏,但自己的作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如何被接受,却只得依赖译者。在译本的封面上或许有原作者的名字,但封底和封面之间那些实实在在的文字却全是译者写的。”[18]这段来自赫曼斯的引言常被作为说明译者之权力或地位的论据而被广为引用。的确,对于不懂原文的译文读者而言,译文就是“原文”,这一事实的确说明了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生命,说明了译者(文)对于原作(者)在异域文化中的形象、地位乃至命运具有怎样的决定性意义,但从这一事实中折射出的除了译文的价值或译者笔下的能量之外,更有译者的责任。毕竟,如倪梁康所言,“如果我在读昆德拉的小说的话,我想读的是昆德拉,而不是许钧,这是肯定的。”[19]而且,不懂原文的译文读者之所以能将译文当做“原文”,正是因为千百年来人们对肩负“传令知会通耳”“换易言语使相解”之使命的译者的无限信任。
四 结语
翻译目的有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两个不容混淆的层次,前者关乎翻译之“本”,后者关乎翻译之“用”。在翻译活动的行为链条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换言之,外在目的是通过内在目的的实现而实现的。翻译的内在目的是“使相解”,也应该是、必须是“使相解”。这一内在目的是让翻译活动“是其所是”的目的,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础和依据,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人类活动的历史与现实中,翻译作为工具,曾经承载过并正在承载着种种社会文化功能,且这种种社会文化功能及其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曾一度成为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但是,关注外在目的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内在目的,坦承外在目的对内在目的之实现造成影响或干扰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外在目的凌驾于内在目的之上。对于关乎翻译之“用”的外在目的而言,翻译固然是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工具,而是一个有着内在目的性和内在规定性的工具。抽离了这种目的性和规定性,翻译活动本身将不复存在。
[1]张伟胜.实践理性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4.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7.
[3]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0.
[4]Derrida,Jacques.Des tours de Babel[M]//Rainer Schulte John Biguenet.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2:218.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6]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21.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8]阮 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Z].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8.
[9]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
[11]Bassnett,Susan&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X.
[12]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267.
[13]梁启超.论译书[M]//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8-20.
[14]黑尔.道德语言[M].万俊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6.
[15]杜威.评价理论[M].冯 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0.
[16]黑格尔.小逻辑[M].贺 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90.
[17]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M]//Anthony Pym.The Return to Ethics.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1:152.
[18]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
[19]王 宾.翻译与诠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96.
责任编辑:李珂
On the Purpose and Essence of Translation
ZHANG D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Translation purposes exist in two hierarchical levels:internal purpose and external purpose.Internal purpose,purpose inherent in and inalienable to translation,concerns the“essence”of translation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stability;External purpose,purpose imposed on translation by social circumstances,concerns the“use”of translation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On the behavior chain of translation,the internal purpose and external purpose exist in a relationship of means and aims while,the external purposes of translation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nal purpose.The internal purpose of translation is“understanding”,and should be“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is the very purpose that makes translation what translation is,and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ontologically.
internal purpose;external purpose;“essence”of translation;“use”of translation
H315.9
A
1674-117X(2015)04-0105-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22
2015-04-02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断裂与延续:翻译规范的学术史研究”(12YBA114);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忠实’解构论”思潮的学术史反思”(15C0420)
张冬梅(1974-),女,湖南邵东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