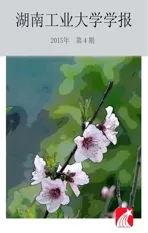在找寻中孤独,在撕裂中前行*
——《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
2015-03-17伍丹
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在找寻中孤独,在撕裂中前行*
——《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
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表明王跃文对爱情婚姻所持的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理想主义态度。《爱历元年》揭示了秩序化的社会道德和理性的婚姻形式下,女性个体存在的孤独本质和对情爱的强烈渴望;展示了在激情的眩惑与理性的撕裂下,现代女性无法逾越的精神困惑和生存无奈。这种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是对现代人生命自由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与超越,它以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欲望书写和属己的生命经纬激发着人们的体悟和反思。
《爱历元年》;女性;孤独;激情;理性
毫无疑问,王跃文是位描写爱情的高手。其新作《爱历元年》中的情爱书写,不但构成了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元素,更呈现了现代人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爱历元年》的男女主人公都在围城之外寻找爱情。中国传统道德从根本上否定了婚外情的合理性,但王跃文却本着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把婚外情写得真诚而动人。然而,王跃文对爱情婚姻所持的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理想主义态度。他从未怀疑过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模式的必然性,其骨子里的归宿意识正是传统文化及其道德观念所提倡的。《爱历元年》的女人在婚姻爱情上的道德选择,正是作者道德评判的显现。当然,王跃文的婚姻爱情道德观念也是矛盾的,他肯定对婚外情缘的追求,表现出宽容的道德意识,但最终仍将道德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让男人女人回归家庭。
“文学的本体是人生的诗意,其本质是推进人的精神、心灵的净化,更是对人的自身道德的提升。”[1]情爱、性爱、欲望书写提供的不仅仅只是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更是一面镜子。《爱历元年》通过人物的内心、语言和行状等揭示了秩序化的社会道德、理性的婚姻形式,和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的情感欲望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现代人无法逾越的精神困惑和生存无奈。《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表明当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依然建构于男性中心,女性缺乏足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她们不是自己的,只有在“她”和“他”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才能确知自我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追求与梦想在男性的操控或背叛中纷纷失落。
一 现实的孤独与寻爱的渴望
“文学作为现实的影像和文化的诗意表现,作家最执著书写的就是代表‘人的文学’基本表现形态的‘情爱与性爱’的永恒精神母题。”[1]王跃文很少如此具体而细致地描写“爱”与“欲”。《爱历元年》的女人们所展现的对情爱的渴求是对平静无欲的现实生活的突围,是对现代人生命自由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与超越,它以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欲望书写和属己的生命经纬激发着人们的体悟和反思。
《爱历元年》对现代人的生存关注是多方面的,它努力描摹当下现实和人的各种生存状态,深入探悉个体存在的孤独本真,实现了向现代人生命本质的逼近。对于执着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和生命终极价值的王跃文来说,现代人的隔膜处境和对生活的失望情绪使其笔下的人物皆处于孤独的生存境地。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人物来说,喜子、李樵和小英都在爱情婚姻中孤独挣扎:在世人的眼中,她们一个冷淡,一个孤傲,一个顺从,她们在社会的世俗压力和传统的道德束缚中孤独地生活,在孤独的生命旅程中寻找自我。
喜子清瘦且少话,冷淡而克制。她爱读书,有独立思想,有成功事业,这是一个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女人;她持家,做家务,和睦家庭关系,这是一个在世俗眼光中也是男性眼光中的贤良妻子。然而,喜子没有朋友,与丈夫缺乏交流,与同事关系疏离,儿子也同她说不上几句话,单调平静的生活就像图书馆的书架,一切井然有序,却也是寂寞的、孤独的。她独来独往,总是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同事聊天,她从不插话,却“留意着窗外的风景,雨中的树叶油亮亮的”。[2]100在欲望横流的商业社会中,距离上的疏离、心灵上的隔膜让现代人不可避免地处于深深的孤独之中。海德格尔等人早已断言技术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终将导致人的物化异化。“在自我决断的制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3]喜子的孤独正是现代人孤独生存的真实书写。青春年少时的理想在冷漠的成人世界已经渐行渐远,现代人在心灵的荒漠上苦苦寻找归宿,最终陷入迷失之中,只能保持孤独的缄默。
当然,喜子们并不像萨特的孤独者终身围困于孤独的境况,独自咀嚼孤独的滋味。她们渴望温暖,试图用爱情来拆解孤独和忧伤。谢湘安直白而灼热的爱让喜子无处躲藏。喜子在这场婚外情中收获了爱情也唤起了全部的生命热情。虽然,一直徘徊在情感和道德的矛盾之中,最终,爱情的诱惑战胜了心中的理性,也将她长期固守的习惯打破。然而,本能和责任、道德与情感始终存在于喜子内心深处,双方在纠缠、对决。小说不遗余力地展现了喜子内心深处的自我冲突与精神困惑,书写的女性的“情”与“爱”,以此延伸的家庭、婚姻等问题,本质上仍是对人的心灵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天性的释放、对人的情感的宣泄,是追求身与心完全自由的象征。
事实上喜子并不了解这个男人,但是男人身上的青春和热情深深吸引着她。与年轻情人那种无忌恣肆的两性欢爱态度不同,已为人妻的喜子迷恋的更多的是对青春流逝的焦灼转而为对青春肉体所发散的年轻活力的羡慕与向往。在肉体的欢愉中,这份迟来的爱情慰藉了喜子心灵的孤寂与灵魂的创伤。当然,“爱情穿越了情欲,纯粹到性的爱情其实也是爱情的外壳,在性里面还有一个核,就是人性为孤独求救。”[4]
李樵是美丽的,初识孙离,她才二十几岁,如兰花般美好,“脸上就像羊脂玉,白嫩嫩地透着亮光”。[2]125李樵是独立的,她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奋斗精神,在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和纲常伦理之下,较之男性,如李樵般的职业女性的事业之路走得更加艰难。然而,现代人的生存不仅要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还要面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自我心灵。李樵结束过一段婚姻,她起伏激荡的内心情感和欲望,作者未着一字,我们却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世界的阴湿和滞重。李樵有着对浪漫的执著渴求,有着敏感细腻的情感体悟,这是女人真实的生命需求。在爱的男人面前,李樵笑起来总是毫无掩饰,犹如孩子般调皮,一次次的性爱,让李樵沉迷于性高潮的快感,也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的生命价值。然而,快乐着,欢乐着,她的情绪突然就不对了,久久不再说话。孙离火一样爱着她,却不了解这个女人。“孙离永远不知道她心里装着什么事,平时只是望着她微微锁起的眉头,听她若有若无的叹息。”[2]123
从李樵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现代女性赢得了事业,追求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却为找寻不到理想的精神家园与归宿而迷茫与失落,显示出女性全面实现“人的存在”的艰难。面对爱人,李樵是孤独的。她努力坚守着人格的独立,捍卫着精神的自由。她和孙离的婚外情缘从不存在任何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他们是彼此肉体的欢愉和精神的吸引,当然也从未有过明确指向未来的目标和道路。
爱情并非虚幻的,作者撕开了爱情的神圣光环,拆穿了爱情神话的虚幻,把爱情从不食世俗烟火的天上拉回了男女相互依偎、扶持的人间。李樵需要的是与相爱恋人的真心相知与永远相守,如一株木棉和他“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她追寻的是精神与现实生存的共同拥有,这也许是作者对女性生命存在方式的探寻,也是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女性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建构。现代女性一直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孤独而艰难地跋涉,也经受着实现“人的价值”的所有痛苦、迷惘与困惑。对孙离的最终拒绝,看似表达出李樵的女性独立意识甚至是女权意识,然而作者也无法为她找到一条证明女性自我价值的康庄大道,只能以离去作为解脱。
小英瘦瘦小小,被父兄视为“物”一般的存在。在小英的故事中,小说为我们展现出了女人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堪和鄙陋。她不聪明,四年级没有读完就被送进城里帮姐姐带孩子,16岁仍背不全乘法口诀。她不懂爱情,却又渴望爱情,这种极度渴望正是个体孤独寂寞的真切反映。她在藕煤炉上烧热了筷子只为卷头发,在懵懂的年龄有了孩子而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早在1792年,英国女权主义者M·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在《女权辩护》中高呼女人的自我发展是比自我牺牲更高的职责。然而,传承千年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让中国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没有担当的男友、专制蛮横的家人让小英如同一件可以随意驱使和买卖的物品。只因1千元的彩礼钱,挺着大肚子的小英被远嫁给一个不曾见过且无法生育的男人。这是一个生于新中国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可怜女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形象,她的命运是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的共同命运。王跃文在现代女性生存与觉醒中延续了这一命题,这是对女性生命存在主题的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
小英的苦难来自于封建宗法思想构筑的社会暗堡和女性本身的弱点自造的黑暗地狱。“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忍受着一切屈辱和迫害,却还要为这种被蹂躏、被凌辱的本身承担社会上的一切罪名。”[5]小英生活在父权文化以及家庭暴力的桎梏之下,在无“情”无“义”的失重婚姻中自生自灭而不为人注意。
多年以后,孙离偶遇小英,长期的苦难生活已把小英打磨成一架机器。在亲情人伦丧失的家庭伦理下,被压迫、被奴役的小英如同裹上了一双无形的三寸金莲,永远走不出如“枷”般的“家”的大门。她是父家、夫家永远的“仆人”,是父家可以换取彩礼的物品,是夫家操持家务的奴婢和泄欲的工具,冷漠和背叛是她的家庭和婚姻的情感标识和行为特征。在小英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被奴化的灵魂,她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和经济地位。她机械地对付着日常的一切琐屑,永无完结地劳作,麻木而认命。她的女性生命意识是缺席的,是被践踏的。她在无爱的悲凉生活中孤独地销蚀着生命,让人绝望,令人同情。
《爱历元年》以小英既无“情”又无“义”的失重生命状态,强烈质疑着居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家庭伦理,这是对阴暗残留的“父兄”“丈夫”权威毫不留情的暴露与批判。小英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是一个女性生命意识被扼杀的一生,这是从情感到心灵,从欲望到意志的全面扼杀。在父权文化烛照下,她一直存活于被挤压、被隔绝的生命状态,自我言说、自我表述的声音被彻底漠视,呈现出无声的孤独景象。
二 激情的眩惑与理性的撕裂
“激情一直是肉体和灵魂的聚合点。”[6]78不能控制和平息的激情使得理智屈从于欲望,而灵与肉的结合最终造就了癫狂。喜子在谢湘安发狂似的性爱中不能自已地混乱乃至癫狂地喃喃自语:“我要死了,我要死了!”[2]152在这里,理性终于丧失或者错乱,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激情的眩惑。理性退缩到黑暗之中,同时也被压制于激情之下。于是,在理性消失于神秘的黑暗之时,喜子也在理性消失的时刻迷失于激情之中。激情过后,平静的面容之下,是心灵无法平复的躁动。这种内心的躁动,仅限于身体内部,在身体表面既没有暴烈的行为,也没有狂躁的哭喊,这是内心软弱无力的癫狂和忧郁。
按照福柯的说法,通常会快速反应并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元气(精神)已被黑暗渗透,变得“模糊、浑浊和幽暗”。在这里,运气传送给大脑的物象会被“阴影”所遮蔽,它们如此微弱,乃至身体不会有任何表征,它们又如此沉重,似同化学黑烟而非纯粹的光影,却又让人无法释然。[6]115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喜子的孤僻和倦怠,却无法知晓其内心的躁动。她神情淡漠,面容阴沉,却毫无泪水。
喜子无法拒绝这份爱恋,甜蜜又充满激情。小安子的出现让她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爱的滋味,爱情的力量让她无法自制和抵抗。然而,喜子的现实世界没有激情的喷发,也没有似水的柔情。婚姻所包含的秩序、责任意味着束缚和枷锁,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不堪承受之重。现实是泾渭分明的必然秩序,喜子必须选择,要么是理智的现实,要么是梦幻的激情。在这里,庄重的现实法则已然受到冒犯,如同激情中的混乱一样,理性和法则也已悄然混合在癫狂的风暴之中。夜里,喜子会突然泣不成声,直呼“饶恕我,饶恕我”,心中却恍惚迷惘。作者触摸着喜子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与肉体的欲望狂欢中,试图通过对“性”和“情”的关注,挖掘人性最深层次的根基。
作为探求人的解放最直接的通道,两性关系是五四文化有关人道主义关怀的重要话题。在喜子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女性经济独立和寻求爱情的个性意识,然而,这种女性意识始终与男权文化规范相伴而行,我们最终看到的依然是喜子向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特质”的回归。婚外情与秩序化的法定婚姻相冲突,选择是必须的,现实终归要个答案:未来在哪里?喜子不得不结束,作者选择让她必须继续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依然站在妻子和母亲的位置之上,为此,作者给了她一个家庭的难题:儿子的出走,让她无暇顾及爱情。最后责任感战胜了爱情:她依然是一个被传统控制的女人。《爱历元年》终究没有表达对婚姻伦理的最终否定,并以这种否定实现对责任义务和固有秩序的消解。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分开是这段激情的终点,回归让矛盾得到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而故事背后情感与道德、本能与责任的两难选择更值得我们深思。
巴赫金说“作品中的每一组因素展现给我们时,已经包含了作者对它的反应……他的思想、情感都加上了自己的语调……”[7]王跃文在《爱历元年》中保持了一贯冷峻的叙事姿态,然而他的态度始终潜沉于故事背后。他没有给读者一个物质至上时代里的爱情奇迹。作品的主人公们爱得浓烈,最后分离,是否相互思念直到老去死去,我们不得而知。最终,喜子是否已经在婚姻内外找到了情感的平衡点,抑或已经屈从或者妥协于现实,小说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
作者只让喜子游离于自我意识的边缘,而她永远无法逾越那个自始至终禁锢她的樊篱。最终,喜子顺应了男权社会主流意识给女性设置的价值定位和“女正位乎内”的传统道德律令。这也再次证明“对男权社会的女人来说,爱情激发的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8]儿子的来信,母亲的喜极而泣成为了小说的尾声,说明在男性作家眼中,家庭依然是第一位的。在男权文化境域中,女性对家庭对孩子是有无限责任的,她的幸福最终来自于家庭给予她的身份认同。喜子的选择顺应了男权社会的暗示,也隐含着作者最终的男性意识:他最终无法跳出将父权制伦理的单一价值观——男性价值标准,强制为女性自我价值取向的做法。在掩卷之余,我们不得不深思:平淡婚姻的现实和个人情感欲望的渴求难道是生活的题中之义?
李樵的出现更鲜明地表现出王跃文男权中心主义立场。王跃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多从男性主体感受方面描写爱情和婚姻,女性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钦羡者与献身者,女性人物的丰富情感和心灵体验被大大简化。“她”的形象,始终带着某种“跨性别想象”,呈现着男性眼中的“她”的女性形象和生命体验。《爱历元年》中的女性群体虽然作为实体被书写,依然是作为欲望化的文学符码被男性所想象和利用,“她们”一直处于被波伏娃所认为的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之上,深深打下了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杰在《观看的方式》中提出的“男性的凝视”的烙印,“她们”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审美的目标和理想的载体。
李樵就是这样一位作为“他者”的“她”,承载着性别的“异己”文化,在寻爱的艰难旅程中,不断处于人性的摇摆和精神的痛苦之中。离异单身的李樵折服于孙离的成熟魅力,被孙离深深吸引。不看重终极归宿,而重视生命过程的声色精彩,这种我行我素的生存状态,只有极少数勇敢女性才能获得并享受其中。这些少数女性所表现出的自主意识成为了更多女性的心之向往,甚至可以说,最终会成为一种时代现象。然而,李樵——这个表现出自强不息的人生姿态的职业女性,因为自认为爱得不道德、爱得无法得到归宿而内心痛苦。李樵甚至没有争取,就已然放弃。不坚持,不争取,甚至没有争吵,离开是她为爱选择的道路。这个世人眼中的现代女性没有表现出挑战世俗规范的叛逆,没有公开表达自己对爱的执着,没有一意孤行地鄙视世俗的看法,在没有非议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之下,她没有坚持她的爱情,她的离去成全了孙离的回归,而这也是作者给孙离预设的必然结局。王跃文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陷人了男性文本的常见情节设置:在两性关系上,有不轨行为的女人的是痛苦的。这既显露了男性文本不能抹去的主流性别意识,也显现出作者面对“女性困惑”的无能为力。
再看小英,身为被侮辱被损害的苦难者,她对男性崇拜、依赖和赝服。作者对她是同情的。在她的故事中,男性的虚荣、男性与对女性的权欲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甚至没有呈现小英苦难一生的的思想动态,或者是有意忽略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欲望,甚至她和让她怀孕的男人之间所谓的“爱情”也因为男人的沉默和她的怯懦而让这段感情在局外人“居高临下”的逼视下,显得猥琐、干瘪。
在王跃文的笔下,女性的命运是和男人、政治、权力、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女性对男性更多是的依附和归顺。在《爱历元年》里,女人虽然争得了更多的笔墨,但其依然区别于张扬女性独立生命意识的女性文学创作,作者的审美视野依然局限于传统观念,男权文化意识依然彰显无遗,女性依然是男性“菲勒斯”或者其化身——权力、地位的囚徒,她们的存在依然可以视为“男性文化秩序”的外化。女性的忍辱负重和爱情坚贞更能获得喝彩和掌声,其生命价值是作为男性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而存在的,实质依然是男性生命的陪衬。但是作为一位写男人的作家,对于展现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现状和困惑,表达女性意识的多样和丰富,我们看到了王跃文的变化。对于年轻女性的爱情迷惘、成熟女性的性欲需求,以及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的道德性问题,作者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也没有直接进行道德评判;对于女性难以言说的隐秘感受和对性的生理需求,他没有笼统地用社会化的个性解放加以解释;他探询现代女性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让“她们”艰难而又尴尬地穿行于女性意识和男权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之中。
王跃文对婚外情的态度是宽容的,在其一贯冷峻的叙事风格之下,他没有对其进行谴责。恩格斯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面对无爱的婚姻,王跃文帮助人物寻找爱情,甚至到婚姻之外寻找爱情。这种对爱情的渴望和积极寻求,表明了王跃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而最后的回归家庭,表明他对规则之外的爱情的回避,其态度不是明确而决绝,甚至可以说是含糊和保守的。这显然与他还没有找到更合理的理想爱情的图式有关,而这本身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爱历元年》的女性刻画虽然都是个体感受,却具有普遍意义,它是绝大多数女性现实生活的真切折射。它所刻画的女性心理虽然多有个体主观性,却代表了绝大多数女性的现实选择和真实表现:“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9]这并非只是喜子、李樵和小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众多女性的现实状态,作品揭露了当代女性普遍存在且难以超脱的精神困惑。这是既有个性也有社会意识的女性言说,她们认同世俗观念和传统道德的个体意识,也因为细节刻画和心灵书写而摆脱了观念表现的抽象化,使得文本的现实主义表现有了某种内在化的特征。
[1]杨洪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情爱、性爱、欲望写作问题(笔谈)——20世纪中国文学性爱与欲望书写的文学史反省[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19-122.
[2]王跃文.爱历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3]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04.
[4]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31.
[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2.
[6]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0.
[8]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85.
[9]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责任编辑:黄声波
Solitude in Seeking,Forward in Tearing——On the Elegy to W om en in First Year in Love
WU D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Tragedies of women in First Year in Love represent Wang Yuewen’s male-centered ideology towards love and marriage.This novel reveals women’s solitude and a strong desire to love in the organized social moral and marriage system.Besides,it depicts the confusion and vulnerability of modern women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By describing the desire and lifestyle of each individual,First Year in Love expos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social order and individual’s desire which are the evidence of human struggle between the eternal freedom and the existing life dilemma.
First Year in Love;females;solitude;passion;rationality
I207.425
A
1674-117X(2015)04-0005-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02
2015-02-06
伍 丹(1981-),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