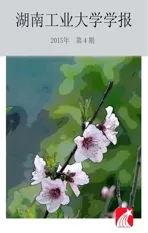现代性的存在困境与自我救赎*
——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浅探
2015-03-17鲍静旗
鲍静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现代性的存在困境与自我救赎*
——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浅探
鲍静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王跃文的长篇新作《爱历元年》,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张弛有度的情节、血肉丰满的的人物形象,从容不迫地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现代社会、一个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小说在还原生活本真的同时,凸显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努力挖掘生命个体的灵魂世界,积极探寻精神危机下的自我救赎之路。
王跃文;《爱历元年》;现代性;存在困境;自我救赎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无比荒芜的状态中。在这个世界中,技术统治着人类,人不知不觉地被技术奴役,不断被物质异化,人逐渐失去了自我,人类面临一种“无家可归”的生存境地。因此,在现代性的生存中,人类不得不考虑“我该如何存在”的问题。
在小说《爱历元年》中,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被物质所异化的现代社会。小说以孙离与喜子的婚姻生活为核心,表现了一群现代人所遭遇的存在困境。她们是现代社会中的群像,是一群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王跃文曾说到:“我的新作《爱历元年》是一部‘无病呻吟,却有大痛’的书。无病之病,是为大病。我想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痛,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1]在这部小说里,除了作者所说的“一起喊痛”,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思考,即在现代性困境中反思灵魂的状态,探寻存在的价值,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本文试图结合小说文本,运用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分析小说的主题意蕴以及寻找现代人的存在价值。
一 现代人的存在困境
(一)如影随行的焦虑体验
现代人崇拜科学与理性,面对利益至上的社会现实,他们将物质利益作为生命追逐的目标,人变得世俗化和工具化。“现代人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焦虑。”[2]而这种存在的焦虑是“个体存在者在异化的实质状态中最为基本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这不是一种病理性焦虑而是生命存在的本体性焦虑。”[3]《爱历元年》的主人公孙离每时每刻都处于这种本体性的焦虑当中。小说将孙离的生活进行散点式的再现,表现他在面对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物质崇拜时,内心的无所适从与忐忑不安。正如小说中写道:“他永远不能像喜子那样沉得下去看书,总让一种莫名的焦虑煎熬着。”[4]34在孙离的生命体验中,“焦虑”一直如影随形。不管是在他与喜子刚结婚的日子里,或是在背叛婚姻后与李樵缠绵时,内心总是会泛起不知名的焦虑情绪。失眠一直困扰着孙离的生活,而失眠正是内心焦虑的一种典型症相。他是一种病态的存在,一种因现代性困境所引发的病态人格。
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蒂利在其《存在的勇气》中谈到“存在性焦虑”,而这种焦虑就是源于对自身异化的焦虑。在孙离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人我异化”,即“人同自我相对立,也同他人相对立。”[5]在小说中,“兰花”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情感意象,兰花象征着高洁与淡泊,它是孙离真实内心的自我映射,是孙离梦想的自我形象。这个象征性意象,一直引领孙离在理性的现实生活中做出感性的情感选择。喜子曾给过他美妙梦幻的爱情,但当他拿到那个红色结婚证的那一刻,在他即将变成一个庸俗而陌生的现代人时,他的梦醒了。而充斥着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现代社会却让梦醒后的孙离显得格格不入。现实的困境让他一直活在个体本身的矛盾冲突之中,使他陷入了无限的存在性焦虑的体验之中,而孙离这种焦虑正是源于他所面对的孤独的存在处境。
(二)陌生与疏离的孤独感
现代的工业文明促进了人类自我力量的急剧增长,在个人意识和理智发展的影响下,人能充分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体以及他人过去和未来的走向,这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状态。正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到:“人类理性的东西越趋于成熟,与原始纽带的关系就越疏远,他与自然世界也就越分离。”[6]16
《爱历元年》中的他们何尝不是孤独的,当孙离拜读了画家高宇的书后,写下了一篇叫做《孤灯秃人》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多伤痛而执迷不悔,世人便多不解,多笑骂。笑骂不解,虽可由人,虽能不屑,心中却仍是觉得孤独凄惶。于是乎,众声喧哗,灯红酒绿之际,仍踽踽畸零人也。”[4]209尽管这是孙离笔下内心寂寞与孤独的画家高宇的形象,但也无疑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孤独感大抵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人与自我疏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孙离和喜子人生追求的不同,是他们产生婚姻危机的重要原因,孙离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淡泊的人生。喜子则不同,她向往的是大城市的繁华与激情,她不安于现状,追求显耀的人生。他们之间是陌生的,也是孤独的。在孙离遇到李樵,喜子遇到谢湘安后,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寻找到了情感的依靠,可是这仍不为能使他们摆脱孤独的困境。小说中多次提到孙离感受到自己与李樵之间的疏离感。“孙离想着李樵虽觉得很亲,却又觉得她离自己其实很远。”[4]186而喜子与谢湘安,同样是孤独者的形象。尽管喜子在谢湘安的身上寻找到作为女人的柔情,可是喜子却对自己出轨的行为充满了恐惧与愧疚,她无法摆脱这样的心绪,谢湘安始终无法真正的走进她的内心。虽然性爱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彼此的心却有着很远的距离。同样处在孤独困境中的还有孙却和小君。孙却作为一个商人,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物质上的富有让他看上去风光无限,是别人眼中的大能人,他也沉溺于这样的物质享受与现实社会的赞誉声中,这使孙却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靠金钱解决,无论是名声、学历,还是权力。然而,生命的变幻无常让这个庸俗不堪的商人看清了现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物质作为基础交换的。如梦初醒的他,方才体会到自己的悲哀与孤独。曾沉溺于物质世界的孙却,不可避免地带给妻子小君同样的生命体验,一种孤独凄惶的存在。小说《爱历元年》中塑造的这些形象既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人,有极度拜金主义者,有急功近利者,也有淡泊清醒者,又代表了相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是寂寞无奈的孤独者。这种相同的生存状态是现代社会所给予他们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人所有的孤独的恐慌和分离的寂寞,都是源自于引发人恐慌和寂寞的外部世界。”[6]14
(三)无能为力的虚无感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7]247这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论断。他认为这种风险源自于不可预测的自然与社会以及知识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的病态心绪,导致人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生存的危机,而焦虑与孤独的精神困境最终让人体会到存在的虚无。尼采曾经悲观的提出:“现代精神已无药可救了。”[8]而尼采指的现代精神的本质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也在其存在哲学中提出:“人被‘抛’到世上,是被抛到一种存在的‘敞开状态’中来,即身不由己地受到他所处生存环境的‘摆布’。”[7]176人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被抛入”的,而在进入之后,却又被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所裹挟,现代人是没有意义的虚无的存在。
在小说中,孙离看到满街夸张的商业广告,内心生出极度的厌恶情绪,无处不在的拜物教让他想逃离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他渴望一片净土来安放自己的灵魂,可是他却无法选择被抛入的命运。小说中写道:“孙离想了想自己写的那些小说,忽然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一种深深的虚无感,重重地压在他的胸口。”[4]126他觉得自己多么渺小,即使用写作这种艺术化的排遣方式也无力改变现实中强烈的虚无感。在这部小说中,主要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两类人,一类是以孙离、李樵、宗教局长马波、画家高宇等为代表一群人,他们看清了社会的真实现状,他们极力地想逃离喧闹而世俗的现代社会,寻找一片精神净土。而另一类则是以喜子、叶子、孙却、小君等为代表的一群人,为了摆脱焦虑与孤独,他们极力寻找一种社会的认同感,渴望通过对权力和金钱的占有来支撑缺乏安全感的自我。无论是欲逃离现代社会的精神至上主义者还是置身于现代社会的拜物主义者,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中虚无的存在者,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时代的精神,在庞大的现代社会面前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二 困境中的痛苦挣扎
现代人被命运无情地抛入到这个精神和道德沦落的物质社会中,忍受着无处不在的焦虑、孤独与虚无的存在困境,现代人无疑是可悲的。但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9]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世界,我们无法选择出生,但却可以选择未来。现代人只有通过后天的行动方能摆脱被物质奴役与压迫的境地。现代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生病的时代,人人都在寻找一种解脱,重新发现治疗现代人类社会痼疾的希望。既然知道现代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取向是被物化,是失衡的,异化的,这就要到人类的本真心灵深处去寻找,寻找早已旁落于人们视野之外的那种精神。”[10]同样,《爱历元年》中的这群现代人,他们亦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地寻找已经迷失的精神家园,而在这条重返精神家园与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误入歧途,在漫长的道路上苦苦地挣扎与抗争。
(一)误入情感的歧途
在早已被物化的现实世界中,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结合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像最初那么密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疏离而陌生。面对越发严重的焦虑、孤独与虚无,人本能地要求改变这种状态。小说《爱历元年》中的他们也在积极地寻求摆脱困境的方法,他们选择了一种逃离现代社会的方式,即寻找情感的依靠。
在小说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感状态便是“出轨”,处在婚内生活中的她们,为了摆脱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困境,他们期望寻找到情感的依靠。正如弗洛姆所说:“人寻找爱情,一种不可避免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躲避孤独的避风港。”[6]118当孙离、喜子、孙却这群现代人发现自己婚姻的对象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时,他们便将眼光投向了围城之外。围城之外的人,带给他们的不仅有精神上的安慰,还有肉体上的依恋。对于孙离而言,李樵这个如兰一般的女人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本真的存在,让他忘却里现实生活的种种烦恼。而对李樵来说,孙离这个比她年长的男人,带给他的并非是普通的男女之爱,更多是源于一种恋父情结。李樵曾对孙离吐出两个字“亲人”,便可以说明。同样,喜子与谢湘安在彼此的身上寻找着一种特殊情感的寄托。谢湘安的出现,带给喜子是一种像父亲又像孩子一般的复杂的情感体验。谢湘安用手绢给她擦汗时,她体味到一种似曾相似的味道。小说中写道:“喜子想起她小时候,有次摔了跤,哭得眼泪鼻涕横流,爸爸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她闻到的就是这种味道。”[4]139而有时喜子看着比自己小十岁的谢湘安的张年轻而稚嫩的脸时,却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亦赤,她不自觉地又母爱泛滥。
除了情感精神上的安慰,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肉体上的依存。小说对孙离与李樵、喜子与谢湘安的性爱场面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绘。通过性爱这种肉体结合的方式,让他们暂时性地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孤独的情绪体验。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揭示了性爱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性爱中的人希望自己同所爱的人等同起来,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自我,通过把一个人扩展成两个人的办法来抵消孤独感带来的恐惧”。[6]76尽管性爱可以让他们体味到结合时自身的存在感,可这种感觉是短暂而易逝的,一旦高潮过后,回到现实生活中,如影随形的焦虑与孤独感将更加强烈。情感与肉体上的慰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他们内心的孤独与虚无,但却始终不能彻底脱离现代社会理性的约束,他们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感到恐惧与不安,这种理性就像一根绳索,当他们逃离的越远,便被束缚的更紧。每次孙离觉得自己越爱李樵时,内心的不安感便越重,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想到了与妻子关于爱历元年的约定。喜子也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每次与谢湘安爱得难舍难分时,她便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挣扎,她哭泣着说:“小安子,我爱你,我没有哪天不在担心失去你,但是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真的不能够!”[4]256他们在情与理、梦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渴望找回真正的自我,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误入信仰的歧途
现代社会是一个丧失了精神信仰的社会,对拜物教者而言,物质是他们的信仰,每一个人企图占有更多的物质来显示自我的存在感。而最终现代人却发现,越来越多的物质生活越发让自己同自然与社会疏离,成为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于是在反思之后他们决定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改变这样的现状。人人渴望得到神的帮助,在神的面前,他们就像神的孩子,可以尽情诉说自己内心的焦虑、孤独、虚无,宗教的信仰让现代人暂时找到了内心情感与精神的依托。
小说《爱历元年》中的现代人,也曾用这种方式试图摆脱纷扰的现实社会。孙离和李樵曾多次前往寺庙,期望躲避世间的无尽烦恼。去到何公庙,熊道长为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佛教讲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是要让人看破虚妄,放下执念。而道家讲三一为宗,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讲一气化三清,长生不死,肉体成仙。”[4]200在何公庙的那段日子,孙离的灵魂得以安放,习惯了失眠的他,竟一夜无梦。之后,孙离又到苍莨寺与妙觉师傅等人一起体味那份难得的脱俗与清净。可是,这种美好状态也只是暂时的,孙离终究无法割舍掉与尘世的种种关系。殊不知这世间的最后一处净土也被庸俗的现实社会所污染。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为了扳倒宗教局长马波,有人利用其妻叶子制造了关于马波与妙觉师父的桃色新闻。现实的权欲和物欲打破了佛门应有的清净,连出世之人妙觉都被无趣的现实世界所打扰,更何况还身在红尘像孙离这样的现代人。当孙离返回到现实社会中时,他内心更是无法平静,反而生出了从未有过的厌恶之感,他原本想逃离丑陋的现实世界,最后却只能在现实的挟持中奋力挣扎,寻找自我真正的信仰。
三 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现代社会中,现代将传统消解,而现实的精神价值却尚未得以重建,于是现代人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们的灵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们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为了改变这样的存在境遇,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般地栖居”。[7]181但很多现代性批判者对他这种存在哲学提出了质疑,“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意义简单的归结为生存,这就非但没有克服虚无主义,反倒埋下了更深的虚无主义的种子,因为虚泛的生存就是意义,等于生存没有意义,这样的生存哲学没有找到生存的真正意义,人生的真正价值。”[7]183的确,海德格尔提出这种救赎方式只能让现代人的精神得以暂时的解脱,却仍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命运。
然而,小说《爱历元年》中的这群现代人,通过自由的选择、积极的行动、对自己与他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情感的体味与珍惜这一系列的动作,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自我超越,他们解决了如何摆脱现代性的存在困境的难题。这种解决方案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自由理论”与“人道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一)自为存在中的自由选择
萨特将人存在的意义看作一种区别于自在存在的自为存在,所谓“自在存在”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而“自为存在”是人用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的一种存在。萨特认为,人应该摆脱自在存在的状态,投向未来,给人以希望和可能,自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要想摆脱现实的困境,人就应该自由地选择生活,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逆来顺受,更不是消极等待。这种自由选择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在世界中自我选择和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小说《爱历元年》中的他们,实现了自由选择,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首先,以孙离为代表的这群现代人实现了自我选择。“虽然有世界的存在,虽然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是我们可以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自己选择做回自己,自己决定自己。不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它都是选择;把我们选择为或伟大和高尚,或低贱和受辱的人,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11]小说中的他们冲破种种束缚选择自己,无视他人与社会的看法。孙离在中学教书时藐视权威,特立独行,坚持写作。喜子不顾传统的社会观念,为了实现自我而选择出去继续深造,他们选择背叛婚姻最后回归家庭。孙却从一个被称为“乞丐”的农村小伙,一步步成为大老板,最后他放弃现实中的一切,回归自然与家庭。孙亦赤从一个个性叛逆的少年转变为一个懂得爱与感恩的青年……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无论这些选择是好是坏,都体现出自由意志。
同时,他们还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正是在超越世界奔赴我们本身时,我们才能使世界显现为它所是的。我们是通过选择我们自己来选择世界的——不是从选择创造了自在,而是从选择给予自在意义的角度论。”[12]人通过自我的选择给予了本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意义是人的自为的存在所给予的。《爱历元年》中的这群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存在的意义。当孙离和喜子选择回归家庭后,世界显现的存在便是温暖的亲情与爱的延续。在孙却选择用金钱获得自我存在感的满足时,世界则是充满了虚伪与拜金的存在。而当他做出远离现实生活,融入乡村和大自然的选择后,他的世界便是幸福与单纯的所在。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自由的选择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他们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者”,而是开始自我干预生命被抛入的轨迹。
(二)积极行动超越自我
萨特认为:“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13]35在自为的存在中自由的选择还仅仅只是自我救赎的开始,他们要使自由变得更有意义,那就需要介入到现实的处境中,让选择的自由变成积极的行动,通过不断的自我设计与自我否定来完成自我超越。这一过程是积极的行动,而非消极的逃避。
小说《爱历元年》中的人物,面对焦虑、孤独、虚无的困境,他们曾采用性爱与宗教这些消极而被动的方式,企图改变苦闷的存在状态,但却使他们越陷越深。而最后通过用自由的选择与积极的行动完成了个体的自我超越,实现了生命的自我救赎。孙却这个曾经的拜物教者,原以为金钱可以摆平一切问题,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后,在他看清了社会的真相,认识到存在和价值的意义后,他积极地寻求改变生活的方式,于是他决定离开尔虞我诈的生意场,回归到大自然中,去洗涤满是污垢的灵魂。这条道路不是孙却妥协后的选择,自由的选择与积极的行动让他重拾做人的尊严,如获新生。
浑浑噩噩过了大半辈子的孙离与喜子,在小侄子的到来,弟弟孙却的经历,亲生儿子立凡病重等一系列事件的促动下,在经历无数次的自我否定与反思后,他们重新发现了生活中本应珍视的幸福。面对共同遭遇的困境,孙离和喜子尝试着去找回彼此的温暖。尽管他们都曾背叛过对方,但最后孙离对喜子说:“我昨天在夜里就在想,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孩子,我们会做错事,但我们都会长大。”[4]337这句话也表明孙离内心的释怀,选择重新和喜子在一起,这是自由的行动,他积极地与妻子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不再逃避现实。
(三)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13]9这说明了个人与他人的密切关联,个人自由的选择,不仅影响了自己也将影响他人。绝对的自由选择与行动并不能完成自我救赎,绝对的自由不能真正得到自由,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我们在寻求自由的同时,应认识到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小说中的孙离、喜子、孙却、亦赤等人,他们曾一味地崇尚自由的选择与行动,而在没有约束的自由下,他们过得并不快乐,甚至遭遇了更严重的煎熬。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救赎后,他们认识到自我存在感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首先,他们开始对自己负责,对自我进行道德与意志的控制,积极地寻找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而非消极的、否定的、痛苦的,不再一味地放纵自由。孙离与喜子逐渐意识到对婚姻的背叛是不道德的行为,每次出轨后,他们都感受到强烈的犯罪感与恐惧感。最后,他们用强大的理性意志来控制不道德的感情。
此外,他们还通过对他人责任的承担来加深自我的存在感。孙亦赤这个叛逆的孩子,一直标榜自我个性、崇尚自由。他曾无视父母对他的关爱,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用音乐把自我同现实社会隔绝开来,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变得冷漠与无情。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孤独的。但最后当他独立行走在拉萨,看见蔚蓝的天空、辽阔的雪山、纯净的格桑花……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他人紧密相关,他决定要肩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当孙离和喜子发现亦赤不是亲骨肉,亲生儿子立凡需要换肾时,孙离决定将肾无私奉献给患病的孩子,生活的磨难让这个曾经犯过错的男人,勇敢地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此外,孙离多次帮助仅有过数面之缘的江陀子,孙离带他离开了寺庙,让他学了一门生存的本领,在得知江陀子挖死了母亲小英时,他连夜赶到事发现场,帮助江陀子处理事故。在我看来,他对这个孩子的帮助,不仅仅是出自一种同情,更多的是源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萨特的乐观向上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人勇敢地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以此来约束个体放纵的自由,达到个体道德的忠诚。
然而,此时自我救赎并没有真正完成,小说中人物告诉我们,只有体会并珍惜美好的情感,方能更长久地获得自我的存在感。在小说的末尾,孙离、喜子等人重新体味了曾经被他们忽视却又值得珍惜的情感,“土豆烧牛肉”“葱煎金钱蛋”“爱历元年”等代表了浓浓爱意的元素都涌上他们心头,勾起过去美好的记忆,他们体味到一种失而复得后的幸福。小说《爱历元年》中的这群迷茫的现代人通过自为存在中的自由选择、积极行动与自我超越,再到对自己与他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对美好情感的体验与珍惜的一系列行动,最终完成了对生命的自我救赎,彻底地摆脱了现代性焦虑、孤独和虚无的存在困境,重新寻找到存在的精神家园。
《爱历元年》是一部关于现代性反思的作品,作家将积聚在内心深处的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痛苦的思考融入到小说之中,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隐忧。在这个充满了欲望的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焦虑、孤独、虚无让现代人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们无奈而艰难地挣扎,寻找失落的现代价值与文明。同时,它还是一部充满着温暖和大爱的作品,尽管小说给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与黑暗,但在最后还是带给我们无限的感动与温暖,这群原本已经迷失的现代人最终找到了现代性存在的方式,使人性得以升华,生命之美拯救了生命之丑,他们拯救了自我,也拯救了他人。
[1]新华网.王跃文谈新作《爱历元年》:无病呻吟,却有大痛[EB/OL].[2014-10-20].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4-10/20/c_127118218.htm.
[2]孙正聿.恢复“爱智”本性的新世纪哲学——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J].江海学刊,2000(1):72-73.
[3]杨经建.从存在的焦虑到生存的忧患——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论之二[J].浙江学刊,2009(5):82-86.
[4]王跃文.爱历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5]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6]弗洛姆.爱的艺术[M].萨如菲,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7]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9.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 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0]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M].苏 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43.
[1]潘志恒.飘荡在虚无中的自由——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的自由理论评析[J].比较法研究,2005(4):133-137.
[2]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95.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e Existence Dilemma of Modernity and Its Self-salvation——On Wang Yuewen's New Long Novel First Year in Love
BAO Jing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Wang Yuewen's new long novel First Year in Love,with plain and simple language,tense and relaxing plots,vivid and true-to-life characters,describes a real modern society and a complex humanistic world by easy stages.While restoring the real look of life,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existence dilemma of modern people,striving to excavate the soul world of individual life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road of self-salvation in spirit crisis.
Wang Yuewen;First Year in Love;modernity;existence dilemma;self-salvation
I207.425
A
1674-117X(2015)04-0010-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03
2015-02-06
鲍静旗(1990-),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戏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