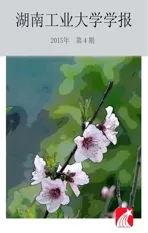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述评*
2015-03-17彭敏哲
彭敏哲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述评*
彭敏哲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旧体诗词”名称及格律问题探讨、旧体诗词的价值认识、当代旧体诗人个案及群体研究等几个方面,其成果丰富,角度多元,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
当代旧体诗词;名称及格律;诗词价值;个案研究;群体研究
“旧体诗词”这个称呼是与“新诗”对举的,在“新诗”的光芒下,旧体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一直比较边缘。当代旧体诗词,是指建国以后(1949年至今)创作的诗词。建国以后的前30年(1949-1979),旧体诗词虽时有人作,却鲜有学者关注。而近30年来,学界开始有人陆续关注到这一领域,并认为这个几乎空白的学术领域是“日渐贫乏的古典诗歌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晋发力点”[1]。本文拟对建国以来的旧体诗词研究作些梳理,以期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些问题。
一 名称及格律探讨
旧体诗词的名称和格律两个问题,一是为它正名,一是为它验身,这是“辨体”的问题。本文把当代人按照古典诗词的格律要求、语言习惯创作的诗词称为“旧体诗词”,但关于这个名称的使用,学界也有争论。目前的称呼有“旧体诗词”“传统诗词”“格律诗词”“中华诗词”“古典诗词”“文言诗词”等等。“旧体诗”这一概念最早由胡适发明,他在1918年给任叔永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称谓。新体自由诗出现后,在体式、内容等方面与其大相径庭的传统诗歌被统称为旧体诗。它含有两包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新体自由诗出现以前,自《诗经》以来的古风、律诗、绝句以及包括词和曲在内的“古典诗歌”。二是指新诗产生后,现代人沿用旧的古风和近体诗等形式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国诗”这一概念,最早始于1932年范罕给《胡先骕诗集》写的序,徐晋如认为“诗、词应该统称国诗,也只能统称国诗,只有这个称呼,才配得上她作为全民族共同诗体的身份,也只有这个称呼,才能把新诗殖民化的本质暴露于阳光下。”[2]张海鸥《关于格律诗词之名称》认为应该使用“格律诗词”这一概念,作者分析了“旧体诗词”“国诗”“传统诗词“等概念的缺陷,认为:“无论诗还是歌词,永远都存在自由体式和格律体式之别。用‘格律’和‘自由’对举,是科学的、便捷的、长久的。”[3]各种意见之中,“旧体诗词”这个概念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也成为了人们的习惯,但是从科学性和学理性来说,“格律诗词”或可取代“旧体诗词”这一概念。
旧体诗词的格律问题,主要集中用新韵还是旧韵上。格律问题上有“守旧派”“革新派”“中立派”,守旧派坚持旧韵,革新派坚持新韵:杨开显《论今日旧体诗形式的改革》认为:“旧体诗为适应现代汉语言文字的变化和发展而应有相应的改革。今人作旧体诗,应废弃入声,按现代普通话押韵,用现代普通话声调的平仄取代古声调的平仄,并且对这种平仄句式允许突破和变通,写出近似古之"变体诗"的今日旧体诗。”[4]周啸天《当代诗词写作中的入声字存废问题》重点讨论了旧韵派和新韵派的分歧点“入声字存废问题”,辨明了两派主张的不同。也有人持中立态度,张海鸥《旧体诗词的韵与命》对新韵和旧韵的主张作了详细陈述,对使用新韵还是旧韵的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姚奠中《有韵为诗,格律难废》认为:“旧体诗词也可押新韵,《诗韵新编》合适不合适,也应经过讨论来逐步达成一致。如笔者翻译古诗是押今韵,写旧体诗基本是押平水韵,这也仅是习惯而已。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必强求统一。”[5]
格律和名称问题,是创作界的争论焦点,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目前争论虽无定论,但这两个问题是对“何谓诗词”的回答,也是辨别诗词体性、判断诗词艺术价值的基础,仍有待继续思考。
二 对当代旧体诗词的价值认识
对当代旧体诗词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旧体诗词是否能够写入文学史,这是对它价值判断的一个关键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学界历经近三十载,经历了三个阶段。
促使研究者对当代旧体诗词产生研究兴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姚雪垠在《无止境斋书简抄》中谈及了对旧体诗的看法,文章认为以旧体诗词蜚声海内外的柳亚子、苏曼殊,以新文学著称的郁达夫、吴芳吉,以及国民党人于右任等人的旧体诗应该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唐弢则明确反对:“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又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6]1984年,谢云的《一个不应忽视的课题:关于新时代的旧体诗研究》指出旧体诗研究已成为必须要正视的课题。倪墨在1985年第5期的《书林》上发表《不应忽视旧体诗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1987年,毛大风相继发表了《旧体诗六十年概述》和《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肯定了旧体诗词的地位。同年,丁芒《从当代诗歌总体论旧体诗词的社会价值》、胡守仁《从中国诗的历史看旧体诗的发展前途》等也参与到讨论中。但这一阶段的讨论,只能说是“旧体诗词入史论”的发端,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合法地位,依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旧体诗是否可以入史的讨论形成了两派意见,李怡提出要将“现代新诗与现代旧诗统一考察。”[7]吴晓东主张:“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中性化的概念,凡是发生在这一时间阶段的文学现象,都列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8]王建平发表了《文学史不该缺漏的一章——论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地位》,钱理群也写就《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正名。黄修己指出:“古典的旧形式在20世纪仍在流行,新文学尚未全部完成取代的使命”,文中他转引罗孚的话“写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却没有人把这一‘化故为新’的文学现象写进文学史中,难道它们不算文学,不能入史?”[9]与此同时,王富仁却表达了不同意见:“在现当代,仍然有很多旧体诗词的创作,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把它们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但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10]这一阶段的讨论让现当代旧体诗词“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地位有了些许改善,一些优秀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并肯定他们的地位,在学术界的重要期刊上展开讨论,让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眉目”和“身姿”都开始清晰起来。
进入新世纪,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再度成为学者的争论点。陈友康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认为:“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11]论文发表之后,反对的声音层出不穷,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从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史现代性观念、经典型原则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现代旧体诗歌不宜入史的主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杨景龙《试论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的负面影响》,吕家乡的《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及《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王泽龙撰文后,刘梦芙发表《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对王泽龙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从现代旧体诗词具备现代性和经典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它可以入史,同时他着重指出了现代旧体诗词“在艺术上在狂澜既倒的大形势下仍然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造精神为古典诗词创作添砖加瓦,献替多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白话倾向’与‘杂文笔法’。”[12]陈友康本人也撰文回应,他对周策纵诗论和诗作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是偏狭的……面对20世纪旧体诗词的客观存在,正确的做法就是就具体诗人、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探寻其‘真美’,而不作笼统肯定或否定。”[13]讨论一再升温,王国钦《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提出:“对旧诗应该消除艺术歧视以期与新诗和谐共存,为当代的诗人词家们争取到基本的艺术尊严。”[14]陈国恩撰文予以回应:“现代人的古体诗词该不该入现代文学史,这是可以讨论的。我主张慎入,是根据文学史的经典性原则、诗词传播接受的大众语言基础、现代性标准和五四传统的意义而提出的,但又坚定地认为旧体诗词在其辉煌的历史上会永远地活着,而且对今人的旧体诗词也要进行研究。”[15]2012年,陈国恩在《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上主持了“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的一次讨论,韩晗、周建华、陈昶、吕东亮、但红光都参与到讨论中。这样的学术讨论层出不穷,往往一人撰文,引起多方的反驳或者呼应,本人又再次回应。其实,对入史持反对意见者多集中在七个方面:现代文学性、文学经典化、语体形式、学术压迫、不宜提倡、进入死亡之旅、能否被替代,而持赞同意见者则从这些方面予以反驳。如此激烈活跃的讨论,正代表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现当代旧体诗词,总的来说,肯定的声音越发坚定有力。
经过这几个阶段的讨论,旧体诗词的价值被一步步重新评估和深度挖掘,它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接纳,从近些年的研究论著看来,这一领域逐渐火热起来,有不少学者都进入这个几乎空白的领域里寻找崭新的选题和研究方向。这一场历时数十载的争论,也让旧体诗词的“朦胧面孔”逐渐浮出水面,确立了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三 当代旧体诗人个案研究
当代旧体诗人的个案研究,是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当代旧体诗人稍加分类,便会发现,创作主力是四类群体:学者、新文学家、革命家和有诗词写作经历的艺术家。这四类群体中的重要个案,为学界所关注。
1.学者诗词的个案研究。当代诗词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应当是学者诗词,学者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主力军,诗词质量也很高。所谓“学者诗词”,是指从事专门学术研究并取得实绩的专家写的诗词。但目前的研究大都因其学术上的成就才关注到他们的诗歌,研究上重其学而轻其诗,对他们旧体诗词的研究夹杂于某些研究专著中,处于附属地位。
进行旧体诗词创作的学者有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其中人文学者主要从事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他们接触诗词的机会较多,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和诗词创作也有某种形式上的相通,所以他们的创作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这类诗词受到的关注也最多,有单篇论文作个案研究。如彭玉平《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邓小军《现代诗词三大家:马一浮、陈寅恪、沈祖棻》、张海鸥《论陈永正的旧体诗词》《试论沚斋诗词》、刘梦芙《名山事业,国学光辉——钱仲联大师的学术与创作成就》、《千秋光焰照诗坛——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的治学与创作》、《浅谈夏承焘先生山水词》、《夏承焘<天风阁词>综论》、陈友康《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等,此不一一列举。一些自然科学学者,虽然研究的领域与诗词无关,但也不乏取得一定成就的诗词爱好者,曾春红在《胡先骕诗词研究述评》一文中列举出不少对植物学家胡先骕诗词的研究专著与论文。
2.革命家诗词的研究。革命家诗词的研究也是当代旧体诗词的一个热点。所谓“革命家诗词”,就是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革命家写作的诗词,这个群体主要包括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他们的诗词在当时影响很大,在学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革命家诗词研究的热点是“毛泽东诗词”,不少论文对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以及对传统诗词的贡献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如龙峰《略论毛泽东诗词对新诗创作的影响》、白明琦《毛泽东对继承和发展中国旧体诗词传统的贡献》、苟国利《熔旧翻新铸伟词——浅论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艺术》等。然而,由于政治因素,对于革命家诗词的研究往往以赞扬为主,未能深入本质,客观评价。革命家诗词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政治背景下,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它们重估价值,公允评判,是目前应当努力之方向。
3.新文学家的创作研究。建国后一批新文学家在新的文学环境下进行旧体诗词创作,这一群体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有关郭沫若、聂绀弩的研究是热点。郭沫若原本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旧体诗词也颇受关注。聂绀弩的诗歌有“聂体”或“绀弩体”之称,甚至影响了一代诗坛。于永森的《聂绀弩旧体诗研究》涉及聂绀弩旧体诗研究的概况、评论、价值等方面,是系统、全面研究聂绀弩旧体诗的第一部专著。李遇春对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有《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论何其芳的旧体诗创作》《论茅盾建国后的旧体诗词创作》《论姚雪垠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身份嬗变与中国当代“新台阁体”诗词的形成——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转型论》《忧患之诗与安乐之死——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田汉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兼论他与南社的诗缘》《性情中人枕下诗——论吴祖光六七十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等论文见诸刊物。
关于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研究,需要注意到的是他们创作过程中的“两面性”。他们一面创作旧体诗,一面又认为旧体诗的文学价值不如新诗,常常把旧体诗当作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文体。这种舍弃与重新书写背后隐含的新旧文化心理,以及他们对于旧体诗词的定位,乃至于旧体诗词创作与新诗创作之间联系,都是个案研究中的特殊之处。
4.艺术家诗词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书画、音乐、戏曲等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不仅在艺术上造诣很高,在旧体诗词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这些人,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书画界的齐白石、启功、张中行、张大千、黄宾虹等。也发掘了一些未曾被关注的艺术家诗人,如《曾景祥诗词审美价值简论》[16]对画家曾景祥诗词审美价值的探索。艺术家的个案研究主要结合其艺术成就,他们的创作也是“诗歌”与其艺术领域相融合的,这也是此类个案研究中的特殊之处。
梳理之后会发现,当代旧体诗人的个案研究其实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且不说许多中小作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是大家之作,也罕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这一方面是源于目前许多文献资料还缺乏整理,诗人别集尚不能搜集完全,枉论对其的研究。李遇春认为:“当前的旧体诗词研究亟需提倡一种实证精神,宏观的论述必须建立在微观的剖析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宏文必须要有坚实的微观个案文章来支撑和建筑。”[17]这是对个案研究的一种启示。
四 当代旧体诗词群体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1949-1979),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和具有创作激情的新文学家是旧体诗词创作的主力,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诉求,1980年代后的旧体诗坛又焕发新貌,发展为“学会诗词”和“网络诗词”两大阵营。关于当代旧体诗词的群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学者诗人群。学者诗人作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主力群体,他们的创作艺术水平比较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陈友康《论20世纪学者诗词》指出学者诗词的特点是民间化、自娱性、专业性和典雅性。学者诗词的价值在于它表现了现代性追求,满足了人的自由需要和社会需要,弥补了新文学的某些欠缺。刘士林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则是对20世纪学人之诗展开了系统的阐释研究,作者把学人定义为“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认为学人之诗有“诗之新声”“学之别体”两重内涵,既对学者诗群的意义作了整体评估,也对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萧公权、吴宓等学者诗人进行了个案研究。他还撰写了《现代学者旧体诗词与其学术关系》《旧体诗词:现代学者的“本体”秘密》《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三题议》《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学人之诗》等一系列论文揭示学者诗词的特点。
2.新文学家诗人群。把新文学家作为整体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成为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一个方面。李仲凡的博士论文《古典诗艺在当代的新声——新文学作家建国后旧体诗写作研究》对建国以后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从中国诗歌变迁的纵向视角作了整体的观照,以新文学为背景,从比较的、共生的横向视角考察新文学语境下的旧体诗写作,又以新文学家的旧体诗为参照系,反思和质疑了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观,可以说是一次对新文学家旧体诗词的有力探索。他还撰写《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的矛盾心态》等文从文学史价值、写作心态等方面考察了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王艳萍的硕士论文《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书写与文化心理研究》主要对新文学家新旧体诗的两栖写作身份背后的写作心理进行分析,也对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写作现象作出思考。曾艳《一人两面:现代新文学家的新诗、旧体诗比较》对新文学家两种精神面貌、语音系统及适用场合进行分析,肯定了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价值。
3.“老干体”诗词。所谓“老干体“,又名“政协体”和“人大体”,是当代诗词创作中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一种诗词体式。“老干体”其实是一个新词汇。这类诗词如同老干部的做人和讲话风格一样观点陈腐、套话连篇,但其创作队伍却不限于这些老干部,许多年轻的诗词爱好者也擅长且钟情此类诗词体式。因此,不仅地方小报有,一些专业诗词刊物也有,网络诗词也不乏正宗“老干体”,俨然成为当今诗词创作的一大流派。杨子怡《古今诗坛“老干体”之漫论》对“老干体”的源流、特征、盛行之原因、流弊及影响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对引导“老干体”回归雅正提出了建议,是目前对“老干体”诗词的来龙去脉、特征、缺陷阐释得比较详尽的一篇论文。
4.网络诗人群。“网络诗词”一词最早由檀作文提出,用“网络诗词”这个概念将新一代的年轻诗人与依赖《中华诗词》等传统官方媒体成名的中老年诗人群区别开来。但现在随着中老年人也上网,网络诗词写手的身份也越来越复杂,现在所说的“网络诗词”应该指当代人自己创作并发表在网络平台上的旧体诗词。它作为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旧体诗词创作现象,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李瑞河、陈建福《网络诗词简论》对网路诗词的起源、发展、特点、不足进行了学理化的探讨,也关注到网络诗词批评的几个特征,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网络诗词的流变及特点。马大勇《第三只眼看网络诗词》认为网络诗词具有“悲悯凝重的人文情怀”“自由多元的思想取向”“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等特点,并认为“网络诗词让我们原本以为早被划上句号的诗词史程正在变成省略号,甚至变成惊叹号。”[18],对网络诗词的未来充满信心。
5.诗词社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基本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诗词社团,后30年诗词社团蔚为丛林。1980年代以来,各地诗社纷纷成立,并形成了目前最大的诗词团体——中华诗词学会及其各省诗词学会。胡迎建《当代诗词社团及其作者状态评述》一文对目前学会团体、高校社团、民间社团、海外诗词社团等做了介绍,兼论社团催生出的诗词刊物、诗集、诗词网站、手机诗等产物,并分析了社团中创作者的基本情况和创作实绩。马大勇《近百年词社考论》一文列入网络时代与词密切相关的几个社团,对留社、甘棠古典研习社、居庸诗社、菊斋诗社、持社等社团作了梳理。
上述是当前研究中比较重点和热点的问题,此外还有关于地域诗的研究、旧体诗词在当代和未来发展问题的探讨、有关于旧体诗词创作的论述等,兹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虽然未成规模,但也是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的补充和深化。
纵观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现状,成果丰富,角度多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学术视野来看,这一领域有现当代学者进入,亦有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研究者进入,各自囿于固有的学术思维,各有所限。从研究对象来看,关注的往往是名家、大家,忽略了大量存在的中小作家群。从群体研究来看,缺乏整体观照,未能从根本上厘清当代60年的诗词创作风貌。从新旧文学关系来看,对新旧两栖作家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创作进行简单割裂。从价值评判来看,对当代旧体诗词作家及作品的评价难免主观好恶,有失公允。
[1]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学评论,2011(6):209-215.
[2]徐晋如.国诗刍议[J].社会科学论坛,2010(15):4-17.
[3]张海鸥.关于格律诗词之名称[N].人民政协报,2012- 12-31.
[4]杨开显.论今日旧体诗形式的改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86-89.
[5]姚奠中,牛贵琥.有韵为诗,格律难废[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3.
[6]唐 弢.唐弢文集·第九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379-380.
[7]李 怡,吴晓东.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5(10):54-77.
[8]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6(1):8-15.
[9]黄修己.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J].广东社会科学,1999(5):129-134.
[10]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55-78.
[11]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5(6):143-154.
[12]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J].文艺争鸣,2008(1):74-78.
[13]陈友康.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J].2008(7):16-22.
[14]王国钦.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J].中国韵文学刊,2010(3):95-101.
[15]陈国恩.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J].中国韵文学刊,2011(2):112-116.
[16]范为超.曾景祥诗词审美价值简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10-112.
[17]李遇春.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亟需实证精神[J].中国韵文学刊,2011(3):97-103.
[18]马大勇.第三只眼看网络诗词[N].社会科学报,2011-12-22.
责任编辑:黄声波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Old Style Poetry
PENG Minzhe
(Chinese Depart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 China)
At present,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old style poetr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discussion of its name and metre,the value congnition of the old style poetry,case study and group study of contemporary old poets and other research aspects.There have been fruitful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studies mad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yet no system has been formed up till now,and many dificiencies still exist in the research objects,research methods and so on.
contemporary old style poetry;name and rules;value of poetry;cases study;group study
I207.2
A
1674-117X(2015)04-0078-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17
2015-01-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14BZW094)
彭敏哲(1990-),女,湖南株洲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20世纪旧体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