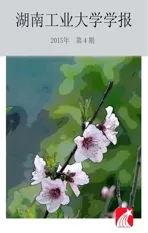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2015-03-17陈天佑
陈天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美术系,湖南娄底417000)
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陈天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美术系,湖南娄底417000)
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宋玉《招魂》所涉之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争议颇多。从礼制入手考辨,可以认定《招魂》系宋玉为招楚襄王生魂所作诗篇,其起因则是楚国举行大田之礼,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慎受惊,故而招魂。
宋玉;《招魂》;魂主;王者之制;射兕;云梦之游;大田礼
学术界关于《招魂》存在着诸多异议。其中,作品中所招魂之生死、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更是争论的焦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将用以礼证诗的方法,通过先秦的礼仪制度来考察魂主之身份,确定诗中所写断非人臣之礼。其次,通过《招魂》的乱辞所述楚王狩猎受惊的情况,结合《周礼》《左传》等先秦典籍记载,可见《招魂》实际上反映了楚国大田之礼的情况: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慎受惊,故而招魂。
一 《招魂》所招魂主辨
朱熹在《楚辞集注·招魂序》中认为,招魂乃宋玉所作,目的在招屈原之亡魂。[1]129事实真是这样吗?
中国古人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能分离的。如《礼记·曲记下》卷四孔颖达疏:“精气为魂,身形为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形。”[2]126并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一魂不守舍则精神不振,二魂不守舍则重病缠身,三魂不守舍则谓之魂飞魄散。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则需要招魂。招魂,是上古时期就出现的一种古老习俗,在部落时代,巫医不分,巫师往往兼有医师的职责,用神秘的宗教咒语治病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招魂之礼,本来既可以用来招亡魂,也能施之于活人之“失魂落魄”者。招魂之礼,在先秦各国皆有,称之为“复”,典籍中也不乏记载,如:
《礼记·丧大记》: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郑注:“复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袭敛,是用生施死,于义相反。”……唯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郑注:“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孔疏:“复而犹望生,若复而不生,故得行于死事,谓正尸于床乃浴袭之属也。”[2]1239-1240
《礼记》《仪礼》中不乏先秦招魂习俗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都属于招亡魂的记载。但根据《招魂》文本中“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1]197-198的这段描述来看,此处招的无疑是生魂。前已述,古人将生病也看作灵魂离开躯体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此处无疑是为病人在召唤灵魂回归,并望其早日康复。虽然从《礼记》关于先秦“复”礼记载来看,其目的亦不外乎“望生”。但毕竟二者性质之别判然。
一般认为,屈原离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8年前后,又根据当前学界对宋玉生年的断限,如公元前300年左右[3]、前298年左右[4]、前296年[5]、前290年[6]等说法。从屈宋的年龄差距来看,屈原离世时,宋玉约20岁。再考虑到屈原晚年长期被流放在外地,两人能够交往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对于屈宋两人的师承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只是认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屈子殁后,宋玉等人方出现于文坛。故而,认为《招魂》乃宋玉因哀悯被贬的屈原而为其招生魂之作,显然失之牵强。
需要交待的是,楚辞中招生魂的仪式为先秦典籍中所罕见,但在民间并不鲜见。朱熹《楚辞集注·招魂序》说:“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7]129他在《辨证》中又说道:“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间风俗,道路劳苦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7]198胡文英在《屈骚指掌·招魂序》中也说:“生人招魂,吴楚风俗有之,谚谓之‘叫魂’,精神恍惚者用之。”[8]为何会有这样奇怪的风俗呢?
如前所述,我们的先民在很早的时期便有了灵魂观念。他们把生病、受惊及死亡都看作灵魂离开躯体的结果,于是便有了招魂之俗。此时的招魂是既包括招生魂也包括招亡魂的。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华夏大地,特别是在周代以降,人本思想日益发展,中原文明的理性精神特质也日益凸显。相比之下,巫的地位大大下降,其原有职能也开始分解,王朝有了专门的史官、乐师和医官。在《周礼》中,王朝不仅设置了医官一职,甚至还出现了明确的医学分科,《周礼·天官》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相关职能的记载;乐师方面,分工更加细致化。《周礼·春官》中记载的乐官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蒙、典同、钟师、磬师、笙师、镈师、韎师等等,他们有的教国子小舞,有的掌四夷之乐,功能不一而足;史官方面,也有左右、内外之分。分科的细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达以及巫觋文化的消退。
社会分工后,招亡魂依然作为巫师的职责被保留,而病人则由专门的医官来治疗。所以,招生魂便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相比早熟的中原礼乐文明,楚国风气则是另一派景象。楚民们“信巫鬼,重淫祀”[9],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楚地祠祀繁杂,巫风盛炽。有了这样宽松的土壤,招生魂这种原始习俗便保存了下来,至今荆楚地区仍不乏实例。
那么这个生魂的魂主是谁?除了先师屈子,有没有可能是宋玉本人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纵观《招魂》全诗,我们发现其招魂之礼不仅与中原“复”礼有性质上的差别,且就形式规模而言,二者亦不可同日而语。总的来看,《招魂》中所反映的楚国招魂礼是一项系统、隆重的国家典礼仪式,集中反映了楚国贵族阶层的建筑、饮食、乐舞、器玩,可以说一首《招魂》就是一场楚国国家级的视听盛宴、狂欢饕餮;也是一部全方位、多层次、高规格地展现楚国宫廷奢华生活的“纪录片”。其宫室巍峨重迭,立于高山之下,曲折的山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宫内外弥漫着蕙与兰的香气;宫殿朱红的大门上刻有精巧的镂空图案,内屋的石室装饰翠羽,墙头挂着玉钩;被褥镶嵌珠宝,罗帐系着美玉。冬有暖房,夏有凉厅,堂高檐深,栏杆环绕,层台累榭,雕梁画栋。层次分明,具体而微,气局不凡,美轮美奂。其它方面如饮食、乐舞、侍女等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凡此种种,很难让人相信其所招对象不是一个君王。试问,在物质生活简单贫乏的先秦时期,还有谁能同时拥有如此巨额的消费资源,享受如此丰富的奢侈体验呢?即使有虚构成分,这也是一个大夫级别不敢想也不该想的美景。这一点,桐城学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三《解〈招魂〉》中说道:“且以为宋玉招师,则中间所陈荒淫之乐,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10]钱钟书先生也认为:“《招魂》所夸宫室之美,声色之奢,非国君身分不办。”[11]姜亮夫先生亦称其为“王者之制”[12]。由此看来,《招魂》一诗系宋玉为招楚襄王生魂而作。
让我们从先秦礼仪制度中再次验证这一结论。结合三礼的内容,我们发现作为文学作品的《招魂》对楚国衣食器玩、宫室乐舞的描述并非完全出于文学的虚构,而是体现了楚国的宫廷礼制。
以饮食为例,《招魂》对古楚美食做了重点铺陈,其中将饮食分为食、膳、羞、饮四类,并逐个罗列铺写。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种美食分类法与中原毫无二致。《周礼·天官》卷四:“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13]79《招魂》中的食谱却有过之之处,食类有稻、粢、麦、黄粱,膳类有牛、鳖、羔、鸿、鹄、凫、鸡、鸧,饮则有柘浆、瑶浆、琼浆等。可见,《招魂》中的餐饮规格比之《周礼》之皇家规格,并不逊色。而这些,也只有尊贵的楚王才可享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招魂》中许多被前人认为是夸张渲染的内容已经随着曾侯乙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一大批考古发掘而得到了新的佐证。总之,大量事实证明,诗中描写的衣食器玩等物品并非“台池酒色,俱是幻景,固非实有其事”[14],而是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一幅“楚宫宴乐图”。
通过以上对古代两种不同的招魂习俗及屈宋生卒年问题的考察,再结合《招魂》文本所反映的信息,我们认为诗中所招之魂应为生魂,再加以《周礼》的旁证,我们可以认为《招魂》系宋玉为招楚襄王生魂所作的诗篇。
二 乱辞中的射兕问题辨
宋玉缘何要为楚襄王招魂?这个问题在《招魂》的乱辞中似乎能够找到答案。乱辞有什么作用?东汉王逸解释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1]47既然如此,众说纷纭的《招魂》主旨应该可以通过乱辞找到准确答案。宋玉在乱辞中写道:“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这一句的解读无疑是很关键的,它交待了作《招魂》诗的缘起,即楚襄王在梦泽狩猎时受到了惊吓。事情似乎并不复杂,但后世解诗注释者却众说纷纭。据《吕氏春秋·至忠》载,射青兕犯了楚国的忌讳[15]。后世许多学者均持此说。那么,先秦时期真的存在这种忌讳吗?
《战国策·宋卫策》卷三十二:“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16]1148
《史记·礼书》卷二十三:“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17]
由此可知,在先秦时期犀兕可算是宝物。除了犀皮可以做铠甲供给军队外,兕角还可以做饮宴用的酒觥。这些物品都是楚国的战略品和消费品。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拥有着这些资源优势的楚国必然会有组织地对犀兕进行捕杀利用,以满足军队的装备和贵族们的消费。所以说,捕杀犀兕之举应当是先秦时楚国常见的“政府行为”。既然如此,此举断不可能是当时的忌讳。不仅如此,射青兕还是楚国王室贵族常常参加的狩猎活动。据《战国策·楚策四》记载,顷襄王之中期,确实常“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16]555-560。这正可成为诗中“君王”射猎云梦泽一事的确切注脚。考古发现也为射兕不犯忌讳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长沙颜家岭三十五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卮上,绘有楚人狩猎的场景,其中便有一头正在逃跑的野生水牛[18]。这更加有力地说明,楚人在狩猎中射杀兕只不过是寻常之事。
由此看来,射兕活动在当时实乃寻常之举。那么,楚王所射之兕与出土漆器所绘之水牛是否为同一物种呢?《说文》曰:“兕如野牛,其皮坚厚可制铠甲。”段注:“野牛即今水牛,与黄牛别,古谓之野牛。”[19]我们知道,野牛是一种身躯高大、孔武有力的猛兽,性情桀骜不驯、野味十足。从上文所载“兕虎嗥之声若雷霆”中也可以想见其威猛。不过,楚国历来尚武,精明强悍的楚国先王在猎杀之余还能“仰天而笑”,而到了国势衰微时期耽于淫乐的楚襄王突然遭遇这样的猛兽,结果受到惊吓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不是每个君王都有“孙郎射虎”的能耐。尽管射兕是一件高危险的游戏,但我们发现,古籍中却屡屡提及楚王射兕的事件。为何楚王们如此热衷于射兕呢?或许有人会立马想到是狩猎、操练或军演兵推,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
据《周礼·地官·牧人》卷十三:“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13]321又《国语·楚语下》卷十八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20]516-519
原来,先秦时国家举行望祀或其它重大祭祀活动时就有君王亲自射杀牛羊以作贡献的传统。君王亲发,以示隆重;而现杀现贡,则取其新鲜之意。由此我们可知,君王亲自射杀青兕是举行国家礼仪祭典等方面的需要。
综上所述,从先秦的礼仪制度来看,《招魂》中衣食器玩、宫室乐舞之规制是依照诸侯级别而来的。魂主为楚王无疑。乱辞中提及的射兕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而射兕之惊纯系简单的突发事件,并非某些学者所说,是犯了忌讳,因为作为犀兕之乡的楚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忌讳。
然而,以上仅仅说明了楚王射兕是出于楚国礼制需要这一推论的可能性。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果说此举属于楚国国家礼仪活动,不习兵革的楚襄王又究竟为行何种礼仪而要去冒险射兕呢?
三 《招魂》的创作动机辨
郑樵《通志·礼略三》云:“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蒐、苗、狝、狩之礼。”[21]蒐,又作搜,有搜索之意。《左传·隐公五年》亦云:“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22]92-93蒐即周之“大蒐礼”,亦称大田之礼。大田礼是古代王朝组织的大规模田猎仪式,它由原始时代部落集体打猎的古老习俗演变而来。后来随着国家的产生,经过三代特别是西周的礼仪规范后,逐渐演变成王朝军事训练的活动。所谓“讲事”即讲武,讲演军事。周代的大田礼每年定期举行四次,即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仲春“搜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车,仲秋“狝田”用网,仲冬“狩田”用车徒列阵围猎。关于搜田之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遂以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13]765-768大蒐礼由大司马主持,军民按实战列阵,经过讲武、貉祭、击鼓等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工作后,就可以用火来围捕猎物了,最后将捕获的猎物在社前祭祀。
两周时期,大田之礼一直是中央王朝和诸侯国的重要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13]466-467先秦时国家有五种军礼,各有作用,大田之礼意在检阅军士和战车,相当于现在的阅兵式。除了阅兵、狩猎之外,大田之礼还有其礼学意义。《左传·僖公廿七年》载:“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22]437-438君主可以用大搜礼来教化人民,这样可以让军民一致,服从指挥,上下一心。又《国语·晋语四》:“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对曰:‘民未知礼。盍大搜,备师尚礼以示之。’乃大搜于被庐,作三军。”[20]363-364至于大蒐礼为何有明礼之用,《左传·隐公五年》记鲁公子彄言:“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22]93-95即举行大蒐礼能检阅军士,彰显车服、旌旗之盛,明辨等级等。正因如此,大搜礼对诸侯国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中原霸主晋国就时常举行大搜礼,徐元诰云:“晋常以搜礼改政令,文公四年,搜于被庐,……八年,搜于清源。”[20]357可见晋国对大搜礼之重视。同时,其它诸侯国如鲁国等也都僭用了此礼。这并不奇怪,一是由于春秋时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二是各国相互征伐,战乱频仍。诸侯们都对军事训练高度重视,个别霸主也有以此炫耀武力的政治企图。在这种环境之下,大田礼有了继续存在发展的土壤。但由于礼制环境的变化,诸侯们在举行蒐礼时便不能完全遵守其中的各个环节了。许多诸侯国按照习惯都对周王朝的大蒐礼进行了相应的改动,楚国素来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其改动也最大。
史书中常常有楚王游云梦的记载,《战国策·楚策》:“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16]490很明显楚共王的这次出游绝非微服出巡或者郊外的寻欢作乐,亦非普通的打猎活动。而是“结驷千乘,旌旗蔽日”的大型国家典礼仪式。“国之大事,在戎与祀。”[22]755能一次性动用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必是国家大型礼仪或军事活动。
楚王游云梦既是楚国的大田之礼,属于国家的重要军礼,而《战国策》中又说楚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将云梦之游看做是冶游,这是否存在矛盾呢?其实,二者并不冲突。田猎之礼形成于殷商,发源颇早,它既有开垦农田的经济需求、训练讲武的军事目的、教化明礼的礼仪内涵,现代学者同时认为,它也还有冶游、逸乐的成分。如陈梦家在考察殷墟卜辞后认为:“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23]可见,大田礼的内涵是颇为丰富的,而究竟以哪一种要求为主,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开拓之君往往会倾向于讲武,守成之主则可能侧重于垦田。然而,随着楚国后期朝政的腐败,襄王昏暗怠政,满朝文恬武嬉,楚国大田礼也逐渐地流于形式,而越来越多地带有冶游的成分。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它作为国家礼仪活动的性质。
《招魂》文本也鲜明地印证了以上论断。宋玉写道:“文异豹饰,侍陂陀些。轩辌既低,步骑罗些。”[1]206这几句常常为人所忽视,其中的信息有几点:首先,侍从武士们身着虎豹纹之装,阵势齐整,其目的在于狩猎;其次,地点在野外的山坡;再次,有骑兵、步兵、车兵等多个兵种。更为清晰的信息在诗的“乱辞”中:“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1]213-214诗人极力描写田猎之盛况,参与围猎的战车竟达千乘,气势磅礴、浩大;狩猎之时,火光冲天;狩猎之法采用步、骑、车多兵种协同配合;骑士们骑术精湛,车手们御术娴熟,步兵们行动迅速;士兵们在广袤的云梦之地施展武艺、争夺头筹;君王亲自进行射兕表演却对青色野牛感到害怕。我们不难看出,诗中所述之狩猎阵势(结驷千乘)及方法(以火搜田)与上述《周礼》《战国策》等记载的情况非常吻合,且多出了不少细节的描述。这说明楚王的云梦之游乃源于中原地区的周礼,系楚国的大田之礼,也有着较悠久的历史,至少存在于楚共王至楚襄王的三百余年间。所以,笔者以为,《招魂》一诗固然有诗人的夸张与想象,但其本事却是真实的,文章的大体构架也是写实的。对此,胡念贻先生也认为:“‘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分明是实写。……作者写他在初春时,曾和楚王南行打猎,车骑随从甚盛。作者同楚王一道直趋云梦,课第诸臣功绩之先后。楚王曾亲自引弓射兕。”[24]而宋玉在《招魂》的后半部分大肆罗列了楚国的美食佳酿,这也与商周田猎活动结束后举行的酒会有着某种暗合。
综上所述,《招魂》的写作背景是楚襄王举行的“大田之礼”,写作原因是楚襄王在狩猎时不慎受惊,故而招魂。至此,《招魂》的礼制追问庶几告破。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礼记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第6册.郑 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金荣权.宋玉辞赋笺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53.
[4]吴广平.宋玉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1:2.
[5]游国恩.楚辞概论[M].北京:述学社,1926:272-274.
[6]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2.
[7]朱 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胡文英.屈骚指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213.
[9]班 固.汉书: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6.
[10]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346.
[11]钱钟书.管锥编: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1:391.
[12]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78.
[13]周礼注疏[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第2册.郑玄,注.贾公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蒋 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36-237.
[15]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 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85:106.
[16]刘 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司马迁.史记: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64.
[18]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13.
[1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58-459.
[20]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1]郑 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592.
[22]春秋左传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第7册.杜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522.
[24]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M].长沙:岳麓书社,1984:443.
责任编辑:黄声波
Interpretation of Songyu’s Soul Ev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iquette
CHEN Tianyou
(Department of Fine Arts,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Hunan 417000,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putes on Songyu’s Soul Evocation,including the identity of the soul owner and the motivation of evoc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iquett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t was written for evocating the soul of King Qingxiang of Chu dynasty,who was frightened in hunting.
Songyu;Soul Evocation;the owner of the soul;the system of the king;shooting the rhino;Yunmeng tour;the Datian etiquette
I207.223
A
1674-117X(2015)04-0069-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15
2014-05-07
陈天佑(1986-),男,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