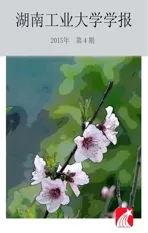城与乡互望中的人性图谱*
——以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为例
2015-03-17张春歌
张春歌
(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江苏常州213001)
城与乡互望中的人性图谱*
——以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为例
张春歌
(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江苏常州213001)
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关注城乡主题时,城市与乡村主要以个体现实处境的空间性而存在,个体生命的无常与人性的深邃在其中充分体现。对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等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个体关注,对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变异的忧思,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发掘,江苏作家主要采取城与乡相互审视的视角,结合个体与存在之间的无限冲突来展现其多种可能的生存状态及人性内涵,力图从人性的凡俗与庸常人生的交织中来发现人性的尊严与高贵,其创作展现出朴素深沉的审美个性。
新时期;江苏小说;人性图谱;城市与乡村
文学是人学,在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对人的精神向度及人性本质的深度探寻一直是优秀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在关注城乡主题时,他们往往将人放置于具体的生存情境中,通过人与生存境遇的相互纠合来展现普通生命的生存状态及丰富的人性内涵,并且对人的本质意义及价值取向进行深度的剖析与追问。人性的演变与丰富的社会现实总是存在必要的关联,这就为文学作品阐释人性的多维提供了诸多可能。从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的创作来看,无论是特定历史下的人性描绘,还是日常现实中的人性发掘,江苏作家都真实展现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现实纠结中的人性图谱。
一 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人性探寻
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1]当江苏作家依据自身的体验、想象与认知对诸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等特定历史进行叙述时,个体命运于历史进程中的堕落或挣扎就汇聚成一种丰盈的存在。对于老一代江苏作家高晓声、陆文夫而言,他们往往将普通个体的人生图景置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框架之下,通过普通人物的愿望诉求与现实的某些冲突来反思历史,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如《李顺大造屋》《美食家》等作品。但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苏童、毕飞宇、韩东、叶弥等这些作家更多地将个体成长记忆融入到作品中,以颠覆或嘲讽的方式于非理性的文化语境中尽现个体人生与时代错位下的精神创伤。尽管叙事角度与表现重心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作家都从某种程度上描写了荒诞的现实与人性弱点相互交织下的普通个体命运的无常与悲凉。
“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2]与力图从文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探究重大现实问题的作品不同的是,江苏作家往往于日常化的历史情境中来展现个体的悲欢与人性的幽微,诸如《怀念妹妹小青》《蛐蛐蛐蛐》《玉米》《玉秀》《平原》《知青变形记》《枪毙》《没有玻璃的花房》《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作品。
第一,庞大生存场域挤压下的人性变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反右等历史在江苏作家的笔下成为巨大无声的钳制力量来掌控着个体的命运,美好生命的无辜消陨(《怀念妹妹小青》),年轻女知青的疯狂(《蛐蛐蛐蛐》),对乡村权力追求中的个体沉沦(《玉米》)等,作家通过这些个体生命的遭际不仅凸显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更充分展现了个体命运在特定历史场域下的无常、偶然与孤寂,以及庞大生存场域力量对个体的牵制所体现的人性的丑陋与悲怆。第二,自身欲望中的人性扭曲。“性的压抑是对人性压抑最彻底的形式”[3],当人的某种本性在特定政治情境下受到压制后,人只能无奈地陷入同自身的战争状态,从而导致人性的病态与癫狂。《平原》中的吴曼玲作为女性对端方爱恋的渴求却因女支书的政治身份对这种本能自觉地禁锢,从而深受心理的折磨,情感的压抑与满足的缺失最终使其在与宠物狗的相互依偎中获得一种扭曲的满足。《知青变形记》中则将这种人性本能的压抑通过知青们对母牛意淫想象的细节中体现出来。江苏作家在人性本能与个体生存状态形成的巨大张力场中充分刻画了无处宣泄的躁动迷茫的精神状态,从而丰富了人性的内涵。第三,荒诞历史下“我是谁”的哲学追问。《知青变形记》的突出之处是彰显了荒诞现实之下个体命运的生存困境。知青罗晓飞被迫成为“范为国”,故事中充满着夸张与传奇,深刻讽刺了特定政治历史的荒诞,更凸显了历史与现实纠合中的群体的存在命题,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蕴。第四,人性与存在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由历史、时代、他人构成的网络关系中,如果平庸的个体与琐碎的生活、特定的政治历史相捆绑,那么个体与存在之间的尴尬与悲剧性的冲突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在文革背景下将少年成长经历中的残忍、暴力、孤独、狭隘、冷漠等精神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充分展现了时代、他人等偶然因素对个体命运的掌控,韩东的《枪毙》《英特迈往》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与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内心世界的透视中,展现了人性与存在之间的无限冲突。
通过这些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毕飞宇、韩东、范小青等这些作家对特定历史的叙述往往在乡村这一主要空间展开,历史并没有作为主要的重心在作品中得以还原,而是成为个体存在的日常化场景,作品的表现重心不再集中于反思历史、控诉苦难等这些现实的表面,而是充分展现普通个体于权力、欲望、政治等多重捆绑下的生存状态与人性内涵。当江苏作家从特定历史情境中转移出来,将视角转入到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时,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与乡村中的个体生命开始在时代的诱惑下呈现出了多种色彩。
二 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变异
当江苏作家关注现实的生活变化时,叙事空间不再是单一的乡村为主,而是在城市与乡村互相渗透中充分展开,叙事视角逐渐采取城市与乡村相互审视的视角,作家对于城乡主题的情感取向也由最初对乡村单一的情感依恋逐渐趋于对城乡平静的对视,由此人在城乡之间迁移游走的悲欢与幽深的人性转变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一直以来,朴实温情的乡村曾作为失意心灵的慰藉之地与美好人性美的承载之处在诸多作品中出现,江苏作家中,汪曾祺建构的诗意的乡村世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即使是范小青、姜滇、储福金等早期的创作,也多以乡村为主要视角来展现农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的自强自立以及乡村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尽管作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文学的现实想象与实际的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是它们叙事的温婉与田园般的诗意呈现充分体现出江苏作家的特色。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与城乡差距的加大,江苏作家在关注城乡主题时不再是单纯的情感抒发与对未来的单一展望,而是从城乡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中来描写城乡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从人生的琐碎中触摸生存的疼痛与人性的变异。鲁敏、范小青、毕飞宇、赵本夫等这些作家都从各种角度描写了这些现实中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城市现代化对乡村各方面冲击之下的人性变异,如《即将消失的村庄》《哺乳期的女人》《颠倒的时光》等作品。这些作品从外到内充分展现了现代化影响下农村的全方位虚空:农民在情感、精神上的日益萎缩,原始淳朴的人性善人情美被逐渐扼杀,人性深处的卑劣与鄙俗逐渐浮现。第二,城市异乡人精神的多重迷惘,如《到城里去》《在街上行走》《城乡简史》《唱西皮二黄的一朵》《梅花开了》《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这鸟,像人一样说话》《带蜥蜴的钥匙》《异乡》等。这些作品或是从进城农民的角度来写城市中的处境,或者以返乡者的身份来写现实故乡的冷漠,都集中描写了农民从外在的生存之痛到内在灵魂漂泊不安的生存处境,人性的善良与温暖在这些作品中被无奈、焦虑、困惑、迷茫、自私、冷漠等所笼罩。第三,对平静、善良人性的坚守。文学的使命是对现实与人精神层面的深度探寻,在诸多江苏作家中,鲁敏的“东坝”系列、赵本夫的一些小说充分显示了在城乡变化中作家对朴实、善良人性的坚守与追寻。
相比较于现实背景下乡村人性的丰富,江苏作家对城市及城市市民的描写内容则相对有些单一。与90年代以后国内多数作家一样,江苏作家也着重展现了物化时代下人的精神世界的迷乱和焦躁,人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性的粗鄙,但他们更将笔触深入到人类终极价值的探求,表现现实状态下人性的焦虑、空虚、绝望等精神困境,尤其凸显人性中的神性逐渐被物质化侵蚀后显露出来的凡俗的一面。诸如《戴女士与蓝》《我爱美元》《尖锐之秋》《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揭示了消费时代下人逐渐被物化而陷入心灵荒芜的生存困境,卑微的个体被无所适从的存在与巨大的虚无感所捕获,从而缺失一种精神力量的指引,自我与现实荒诞纠合中的迷失使个体陷入巨大的精神错乱,欲望、偷窥、隔膜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症逐渐显现。《取景器》《惹尘埃》《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鼻子挺挺》《茄子》《亮了一下》等作品则多从个体的某些病态表现入手来展现自我逐渐消失的人性与人生悲剧,全面描绘了都市人颓废、疲惫、病态的精神世界。尽管如此,某些江苏作家依然力图从人性的平凡与世俗中来发掘诗意的存在,作家叶弥的创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管是早期的《美哉少年》《成长如蜕》,还是后来的《桃花渡》《月亮的温泉》等,这些作品都从过去、现在的时空转换与城市、乡村的空间比照中呈现出对人类精神状态的追问与诗意生活的寻找主题。
从对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关注来看,无论是从外在时代变迁审视个体生存境遇,还是从个体生存状态来展现丰富的精神世界,江苏作家总是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从个体与周围生存场域力量的牵制中来表现个体的可能性存在,采取向内的叙事视角来探寻个体生命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主体的生存与精神空间,在城市化背景下的互动交流中势必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冲突,江苏作家在平静地呈现个体的生存境遇时总是力图从人性的真善中来捕捉共同的人心向往。这也是江苏作家用文学介入现实的独特所在。
三 城乡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多元
日常化的生活视角,是江苏作家一贯采取的写作视角。即使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探求、经济时代的人性展现,江苏作家也并无意于凸显时代或政治的背景因素,依然立足于个体的人生体验来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当一切都转入平庸的日常状态,人的表现也就具有了浓厚的生活意味。作家迟子建曾说过:“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甚至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我们只有在拥抱平庸的生活时才能产生批判的力量。”[4]
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现代化的推进,城乡空间的重组正改变着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也在城乡空间中的频繁流动中感受着生活的巨大变化,城市与乡村,已不再是单纯的地域空间,而具有着无限丰富的隐喻内涵。第一,对城乡日常生活空间进行隐喻式呈现,表现现代人性的各种病症。在格非、戴来、朱文、韩东等作家的笔下,中巴车、轮船、卫生间、酒吧、KTV包厢、麻将房等这些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经常构成小说的叙述空间,作家通过对这些生存空间的展现来揭示欲望化的社会生活中人被各种欲望所奴役的现实困境,于是婚外情、师生间的畸形恋爱、暴力、人性深处的怯懦等就成为作家努力捕捉的人生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描摹来把握都市人难以捉摸的情感内心,传达生活深处的某种寓言和象征。正是这种人生的无意义状态才使得文本中的形象显得焦灼、无奈与绝望,于是人性的病态表现诸如偷窥、嫉妒、冷漠、报复等就自然地得以表现,诸如《茄子》《甲乙丙丁》《亮了一下》《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等作品准确揭示了现代人的各种病态情绪。相比较于城市空间,范小青、鲁敏、姜滇等作家笔下的乡村空间则多是学校、乡间小路、蔬菜大棚、墓地、船等,作家敏锐地捕捉住了城市化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全面影响:乡村主体的集体逃离、乡村留守人员的精神孤寂与焦虑、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失范等。尽管“‘城’‘乡’的存在不仅是地域性的区分,更是交织着权利话语与经济社会形态的空间存在”[5],在众多描绘城乡主题的作品中,往往存在着文明与落后、富有与贫穷等的强烈对比,但是在江苏作家的作品里,没有城乡强烈的对比,只有城乡平稳琐碎的人生常态以及这种常态人生下的人性的滞重与淡然。朱文颖、魏微等作家的作品,侧重于对普通都市人生命过程中物质与精神逐渐游离致使自我迷失与混乱的隐秘心灵的透视,如《高跟鞋》《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猛虎》等作品。而范小青、鲁敏、赵本夫、毕飞宇等作家的作品,则主要将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充分融合,于柴米油盐、细细碎碎中来展现一种民间的、世俗的、普通的人生形式,从日常细微处来捕捉一种朴实的感动与高贵。他们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多是一些卑微的小人物,如乡村裁缝、瘫痪在床的女孩、农村老人、乡村教师、继父、城市拾荒者、进城务工青年、小偷、盲人等,他们对爱情的固执与坚守、对庸常人生的静默等待、对善的维护、对曲折命运的挣扎等无不令人动容,作家对他们并没有过多地施以怜悯或同情,而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他们的现实困境、情感世界进行阐释,体现出一种日常的尊严与温暖,诸如《人情》《幸福家园》《请你马上就开花》《我们的朋友胡三桥》《在街上行走》《豆粉园》等,这些作品中没有诗意的温婉,只有庸常人生中流淌出来的平淡、微妙、宽容的人性。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江苏作家对于人性的关注和生命的书写无不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深切眷怀。无论是对文革、知青等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个体生命的关注,或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变异的忧思,还是对城乡日常生活中的多元人性的探微,江苏作家往往通过普通生命与周围生存场域力量的纠合、无常命运与世俗琐碎生活的捆绑来尽显人性的深邃,并依据自身的生命体验表达着对现实的理解、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城市与乡村在江苏小说中也主要以一种个体生命现实处境的空间性而存在,所以小说中人性的善良、卑微、陌生、粗鄙等世俗性的一面就与琐碎庸常的现实境遇契合在了一起,小说中没有描写超然的神性人性,只是表现世俗现实基础上的朴素人性。这其实也是江苏作家一直以来平淡深沉的审美个性体现。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
[2]严歌苓.穗子物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3]陈晓明.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评东西的长篇《后悔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4):44-47.
[4]迟子建.女人的手[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0:133.
[5]姚海燕.现代生活的叩问:论万宁小说中的空间生存与想象[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2-37.
责任编辑:黄声波
Humanity Atlas in the Mutual Insp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ing the Jiangsu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for an Exam ple
ZHANG Chun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zhou,Jiangsu 213001,China)
Since the new period,Jiangsu writer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City and country have mainly existed in the spatiality of individual reality situation,in which the transience of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deep humanity are embodied.With individual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ducated youth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worry about the humanity vari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and the humanity excavation in daily life,Jiangsu writers mainly took the angle of mutual insp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displayed many possible survival states and human nature combining the endless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xistence,trying to find out the dignity and noble of humanity from the mundane and mediocre life,thus their novels show a simple but deep aesthetic personality.
new period,jiangsu novels,humanity atlas,city and country
I207.425
A
1674-117X(2015)04-0065-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14
2014-11-23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中的城乡关系研究”(2013SJB750006);江苏理工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中城乡关系的文化探析”(KYY12073)
张春歌(1977-),女,山东定陶人,江苏理工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