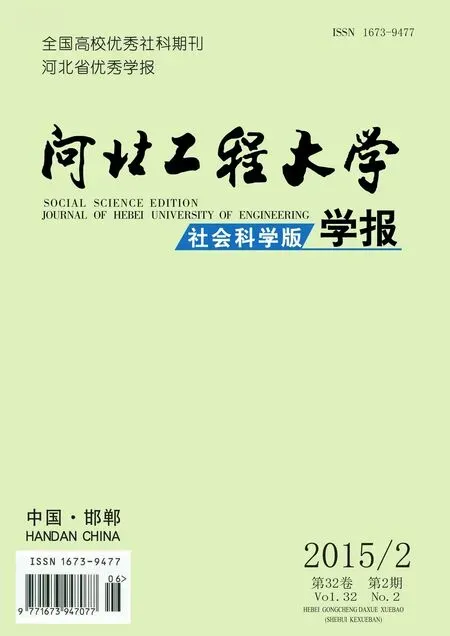民国《良友》画报与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
2015-03-17满建
满建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文学史给予且的定位是现代通俗小说家,但他最初却是以随笔散文为读者所熟悉的。1943年,谭维翰在《记予且》一文中回忆十余年前对予且的印象时写道: “‘予且’两个字,我最初发现它大概是在《良友画报》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我并不懂什么叫做文学,可是‘予且随笔’却使我在课余得到不少的喜慰;只是每当我看得起劲的时候,底下没有了,我常常问自己,这样好的文字为什么不多登两段呢?”[1]这段话道出了予且早期散文的魅力,凸显出了散文以系列形式发表的吸引力,以及《良友》画报之于予且散文传播的意义。那么,《良友》画报和予且散文有着何种的偶合?予且早期散文以什么样的特色引起读者的兴致,对海派文学及中国现代散文又有何贡献?
一
予且的早期散文,最初发表在赵家壁主编的《中国学生》月刊上。该刊创刊于1928年11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主要面对大学生,介绍全国各大学学生校刊及优秀作品,因此在文学界的影响有限,存世也不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刊。
1931年9月,予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良友》的第61期上。其时适逢《良友》创办六周年,该刊为了提升自身的品位,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刊登比重。梁得所在该期《编后记》中介绍到:“文字比前约多三倍,因为每月只出一期的刊物,应该较为充实。本期所刊,予且先生的《饭后谈话》共分六段,每段一题,将按期发表。”[2]这组散文发表《良友》第61—66期上,分别为《饭后的脸》(第61期)、《吃饭的艺术》(第62期)、《何以解忧》(第63期)、《淡巴菇》(第64期)、《茶之幸运与而厄运》(第65期)、《司饭之神》(第66期)。此后,予且相继在《良友》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作品还有《福禄寿财喜》(第 67期)、《龙凤思想》(第 68期)、《酒色财气》(第 69期)、《天地君亲师》(第70期)、《予且随笔》(包括《坐》、《甜蜜的家》2篇,第143期)等。从发表时间来看,除第143期的两篇散文发表在1939年外,其余诸篇均发表在1931—1932年间,正值予且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些散文作品在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迥异于表达文人抱负或情致的传统散文,具有浓厚的市民趣味,适应了《良友》画报的刊载需要。
《良友》画报创刊于1926年,30年代初期已成为上海、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界最受欢迎的画报,素有“《良友》遍天下”的美誉。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和其趣味化办刊宗旨是分不开的。该刊第2期的卷首语曾谈到:“做工作到劳倦之时,拿本《良友》来看了一躺,包你气力勃发,作工还要好。常在电影院里,音乐未奏,银幕未开之时,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四面顾盼还要好。坐在家里没事干,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拍麻雀还要好。卧在床上眼睛还没有倦,拿本《良友》看了一本,比较眼睁睁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还要好。”[3]这种趣味性的办刊追求,迥异于严肃性社会政治宣传刊物,极易受到读者市场的欢迎。作为图文兼重的画报,它不仅仅表现在刊登的图片所展现的色彩斑斓的都市时尚图景上,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上。该画报在第61期的宣传栏中写道:“本刊以后增加有趣味有价值之文章,使读者除领略美术图片之外,复得有实际的知识文字,读之有味,手不肯释,材料异常充实。”这一点是和予且的散文追求不谋而合的。在《说写做》一文中他谈到:“人生出来只有哭、笑、睡觉、更无所谓庄严”,“我们的文章是用笑脸写出来,方才有趣味,趣味便是文章的灵魂。”[4]对于趣味化的共同追求,使得予且散文能够在《良友》画报上频频亮相。
二
1934年末,《良友》第100期纪念特号刊登了一组“本志读者一斑”的照片,展示了该杂志读者遍布的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公园的游客等等。为满足画报市民读者的阅读需要,予且早期散文所写的都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话题,所表现的是普通市民的趣味。
予且的散文表现出对市民价值观念的认同。他曾这样自陈过:“这种表只要一块八毛钱一个,坏了我便丢了它,也不拿去修理,然后再买一只新的。就算一年换两个表,也花不了四块钱,而且我可以随时地用新表”[5],体现的是市民阶级只追新潮不求永恒的价值观念。予且为《良友》画报写作的散文处处都表现出他对市民价值观念的肯定,在《吃饭的艺术》一文中写到:“食是吃饭,色是性欲,二者同等的重要。因为不吃饭就饿死,无性欲就没有家庭社会”, 强调了食色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一些散文中,他还通过生活具体情态,来消解宏大的主题,反映市民阶级的趣味。对于萧统《陶渊明传》中描写的“葛巾漉酒”这一表现文人洒脱的逸事,他用世俗化的笔法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一个穷苦的老头子,在烈日下拄着拐杖奔赴友人家,用沾满了油垢和汗渍的头巾滤酒喝了,再把湿漉漉的头巾戴上(《何以解忧》),在对生活细节的还原中,消解了陶渊明真率超脱的诗化境界。
予且重视市民日常生活的意义,并能从中挖掘出趣味来。在《饭后的脸》中写到:“我看见过一个刚吃饱了奶的小儿,真可爱。又看见过一个餐后闭目养神的老人,觉得人类真是美的,虽老而不衰。又看见一群商人,醉饱之后聚谈,令我觉得大地春回,生气蓬勃。又看见主人请客,亦醉亦饱,宾主尽欢,笑态可掬”。接下来,他谈到,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小孩子的鼻子上有许多青筋暴起来,老人脸上的皮如同桑树皮,商人的脸上有着市侩气,请客的主人满头是疮、客人中有流清鼻涕的——不在于日常生活本身如何,而是如何去看待它,不同的目光注视下,会有不同的景象和境界。予且在对市民日常生活细致入微观察后升华出浅显的生活哲理:“社会上许多好东西,因为认真一考察,便毫无趣味了。一个美人脸,显微镜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着皮,就不说显微镜,看久了也是生厌的。”[6]
予且所谈对象都是发生在普通市民身边琐屑小事,无论是谈吃饭(《饭后的脸》),还是说抽烟(《淡巴菇》),抑或是论喝茶(《茶之幸运与而厄运》),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市民趣味。予且对都市世俗生活和市民的人生满怀着热情,因而能对市民生活有着细密的观察和体悟。他用无数逼真的细节来丰富其散文内容,生活色彩浓厚。在《吃饭的艺术》中,他举出某人用筷子的技术极其高明:“他在一桌筵席上,一样菜有一样菜的夹法,从没有失着,滑的,粘的,硬的,大的,箝挟起来,无不称心如意”,他写不善用筷子者的狼狈心理和动作:“他改挟的时节,心里是老大不高兴,他偷偷地四面一望,恐怕有人笑他夹不起来,末了他发现着人家都在高谈阔论的没有注意到他,他方将那一块低等的菜,放入口中,也陪着大家一下”[7]。他又用简单的语言,传神地写出囚犯、电影上的男女、小孩子、学生、教员、孀妇、义赈会里的人、乞丐、病人、兵队、送行者、街上的男女等等不同人吃饭的不同方式。没有对市民生活极大兴趣和倾心的融入,是无法写出来的。
三
在开始刊载予且散文的第61期的《良友》编后记中,梁得所写道:“消解生活的枯燥,是《良友》的一种责任。善意的建设,也是我们的主张,增长知识和辅助修养的图画文字,用趣味的方式来发表”[8]。予且早期发表在《良友》画报上的以“市民趣味”为表现对象的散文作品,在艺术形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这些作品体现了予且的连类无穷的生活想象力,由此及彼,由一及多,由具象而抽象,给读者以无穷的艺术享受。 在和予且有着密切交往的谭维翰看来,予且谈锋很健,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就是在连续谈论两三个小时的话后,自己和谈话对象都不会感到厌倦。予且的这种谈话风被他运用到了散文创作中。他的散文多为议论性的随笔,形成杂谈式的文体风格。
金克木认为中国人思维多是线性思维,他说:“就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说,思维往往是线性的, 达不到平面, 知道线外还有点和线也置之不顾。只愿有一,不喜有二,好同恶异”[9]。予且的思维方式却是发散式的,他具有联类无穷的联想力,由某事物生发开去,向日常生活散开,呈现出无所不谈、纵谈无穷的特点。在《吃饭的艺术》一文中,予且放谈“吃饭”这门艺术。针对有人认为吃饭就是简单地张开口塞进食物再咽下去,而无艺术性可言,予且指出,如是这样便不会有破唇破舌烫嘴的细节了,进而写到人之吃东西不是蛇之食蛙,蛙之食虫,牛之食草,再进而指出牛之食草的“反刍”也有艺术意味,接着联想到其他脊椎动物,比如猫吃老鼠就是意味深长。他还继续谈到,说到吃,就会联想到嘴,进而联想到牙齿,联想到舌,进而联想到小儿的舌和老人的舌,进而联想到狗舌。接下来,他谈到:“吃,是一个行为,而且一个复杂的行为。这繁杂的行为,有属于外部的,有属于内部的,讨论的范围,是从手中得物时起,送入口中,嚼后入胃为止,做食品的方法不在内,得食品时之状况不在内,食品入口之次序也不在内。”[10]在予且看来,吃这样的“艺术”如果不划定范围就无法谈下去,话题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尽情而谈,无休无止。在《淡巴菰》中,他仅从“淡”、“巴”、“菰”三个字眼借题发挥,就能生发出关于香烟和生活的无穷联想。
其次,予且散文趣味性以丰富的日常知识作为基础,因而并不浅薄。予且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教育背景,知识渊博,中西皆通,这就使得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管什么话题,都能谈论自如,无论是福禄寿财喜,还是天地君亲师,龙凤思想,酒色财气,他无所不懂,无所不谈。尤其是在市民日常生活题材作品中,他也能够自如地运用自己了解的知识、典故、风俗、轶闻等去进行比照。如在《吃饭的艺术》一文,在谈到有人不善用筷、只好吃筷子上的余沥时,他以日本故事中的大神伊奘那岐伊奘那美用长矛在太平洋中蘸水、滴成日本的高山做比喻;在谈到将吃饭作为艺术来学习时,他列出了学习书法和学习小提琴的种种复杂的技法;在谈到用手拿食物的时候,他剖析了中西吃饭分别用箸和刀叉的心理根源;他谈到了内地老板以让出首座辞退店员的习俗、旧式婚礼媳妇到婆婆家在中堂坐席的习俗,谈到中国和罗马的新娘新郎都有将共食的一晚称为团圆饭的风俗等等。予且散文中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其用意并不是炫耀高深,而是融入到世俗话题的议论中,拓展了生活的维度,增加了散文的可读性。
第三,予且散文的趣味性以日常智慧作为调适,在肆意放谈中生发出智慧的闪光,使得散文妙趣横生。他认为书这一人类表现思想最高深、最久远、最完全的东西,一大半都是为了混饭吃而编而用而读的,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书籍,还是国文百日通、自荐尺牍、商人秘笈,以及生利指南、发财新法等书均是如此,甚至还有人用圣经佛经拿来混饭吃。当然,教人禁绝烟火者和白日飞升者除外。这些即兴发挥的议论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但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又有一定的道理,因此能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天地君亲师》所谈的是对被人供在中堂永受香火的所谓“五大”的种种不同解释。前两种解释虽然庄重且冠冕堂皇,但作者都在质疑后将之推翻。最后是作者给出的解释:针对学生不长进,老师解释说,“天地君亲师”五者中自己被排在最后,责任最小。这种出乎意料的解释属于神来之笔,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能让人忍俊不禁。
四
《良友》画报为予且提供了作品发表的园地,予且则以其散文对市民趣味的体察和表现,加强了《良友》画报对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良友》画报上刊载予且的“市民趣味”系列散文,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体现了海派文学精神的整体性和前后一贯性。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以使用现代主义手法表现目迷五色的都市新感觉而著称,40年代的海派文学则转向了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表现。事实上,现代都市上海作为多面体,其摩登光鲜的一面和普通日常的一面是同时存在的,对其表现也应该如此。《良友》画报的图片在展现爵士乐队、摩天大楼、赛马场、赛狗场、回力球场、电影海报的场景及声光电化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也有“人行道上的上海”的组图,铺排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良友》画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既有穆时英的《黑牡丹》、叶灵风的《朱古律的回忆》、施蛰存的《春阳》等新感觉派的摩登小说,也有予且对普通市民生活的情趣的表现。予且散文的这种审美维度,展现了海派文学丰富性,是40年代海派文学表现市民生活的先声。
其次,予且的“市民趣味”散文,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中国被称为散文大国,散文具有悠久的创作传统。从功能上看, “文以载道”的观念根深蒂固,散文长期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多表达宏大严肃的政治主题。从传播角度来看,古代散文主要用于上奏朝廷或是在文人之间小圈子流传,其读者对象是达官贵族、文人名士等。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有人指出,“现代传媒对于作家的写作的意义在于,使他们通过报纸期刊真正面对了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对象,从而改变了散文作家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散文文体的文化功能,使散文成为现代报刊的特殊文体类型”[11]。刊载在《良友》画报上的予且散文一反传统散文的惯例,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市民日常生活一面,以其较强的市民趣味适应了市民读者对象阅读喜好,从而拓宽了我国散文的表现领域。《良友》画报其时“每期印行四万份,每月读者五十万人”,无疑对具有浓厚市民气息的中国都市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许道明先生在谈论到予且散文时指出:“无论怎样,‘趣味’还是他的中心,他的那条风景线是属于市民的。市民惯常的兴趣,街头巷尾的情调和茶馆酒肆间的意兴,养就了他的作风。”[12]予且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趣味是和《良友》画报“藉趣味的取材,作阅者之良友”的宗旨相一致的。这些散文都是用平常话写的平常人事,并不能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受,但真切的生活感及其蕴含的趣味性,却能和《良友》图片一道,给市民阶级以某种消遣性的满足。
[1][5]谭维翰.记予且[J].天地,1943(1):22.
[2][8]梁得所.编后记[J].良友,1931(61):2.
[3]卷首语[J].良友,1926(2):1.
[4]许道明.海派文学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12.
[6]予且.饭后的脸[J].良友,1931(61):44.
[7][10]予且.吃饭的艺术[J].良友,1931(62):44.
[9]金克木.蜗角古今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5.
[11]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8:342.
[12]许道明 冯金牛.潘序祖集:饭后茶余[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