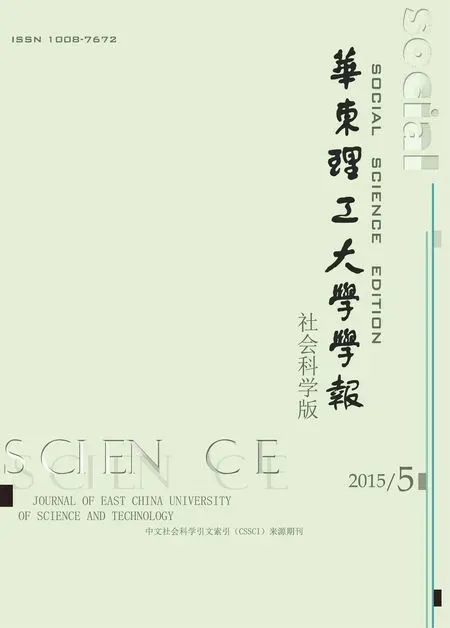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2015-03-17曹锦清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最近几年来,与中国极具相似之处的印度是以中国为标准,把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作为观照他们现实的尺度。印度学者以中国为背景,认为中印两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主要源自于两国不同的土地制度。中国自1950年开始实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并用革命、阶级的叙事割裂了与传统的联系,减少了现代化的发展阻碍。与此不同,在印度,与种姓结构、村落制度纠缠在一起的土地制度,使得它的现代化的道路极为曲折。因此,中印两国土地制度以及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的比较,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土地制度现代化道路中印比较
2015年3月我们一行四人赴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了几天的调研。以下是从印度回来后的一些感想。①本文根据曹锦清教授讲座录音整理,除对个别过于口语化的词句进行调整之外,文章忠实于讲座原文。对印度的关注大概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在国内学术界,我大概还算比较早的一个。大家知道二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两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这些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如果要比较的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当然是一个比较的视角,那么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那就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同。所以十几年前,我一般主要是纸上谈兵了,多次想要到印度去,没有机会,就找了凡是翻译过来的印度的著作大体上都看了,所以对书本上的印度知识,我大概有一点。这次去看,只是跑了一个中南部的海德拉巴,而且只是里面的一个点。信息非常有限,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第一个,三天会议当中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在最近几年来或者宽泛点十来年形成的,因为印度讨论印度问题原来也是以西方为背景,而中国讨论中国问题永远是以西方为背景,我们不会有印度的视角,这是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这里是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所以,参加会议虽然我不动声色,却心中暗喜,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尺度。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确实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却以西方为尺度。聪明伟大如毛泽东,他也是把马列主义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以西方的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更何况一般的学说。那么最近二十几年来的变动是,当马列主义的尺度衰微,自由主义的尺度就要在中国争夺它的普世话语权,作为唯一的尺度。会后的交谈里面确实隐藏着印度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他的自尊心绝对不亚于我们,但是在中国的同行面前,他的设定是明确的,即多讨论中国这个标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们中国这六十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一般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信息,当然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从关注问题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六十年来的实践,那就大逆不道了。所以,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西方的现实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最突出的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在印度学者讲中、印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他们的论点,尤其是最后一个总结发言的(因为他的发言时间最长一个半小时,一般我们的发言时间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就是他是一个权威,而且他长期从事中印比较研究,对中国很熟悉,在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印度的学术界把他当做权威请来作最后总结发言),他的题目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他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印度人讨论印度问题,来设定中国北京的时候,把视线投向了前三十年,所以这个教授发言完了以后,要我们给出一个评论。我的评论是,他的发言放在中国的当代的学术环境里面大体上是左翼观点而会受到右翼的猛烈的批判,但是印度学者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就是前后三十年的连续性,以及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奠定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大概是印度学术界的一个小共识吧,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本人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所以,关于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对后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建国后,中国是1950年开始进行土改的,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为后来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影响,那么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声音就是说,你把一个乡绅阶级消灭了,因而把传统给消灭了,然后由一批地痞流氓来执掌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是极右翼的观点,然后传统被共产党给彻底割断了,给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道德失衡问题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这是右翼的叙事。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那么印度的左翼,就是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印共,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就是马列就是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它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几个邦还长期地执掌政权。毛派的那一些就在东部的那些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然后还是顽强地坚持土改,那么作为印共,属于印度要剿灭的。至于海德拉巴,他认为是第三派,是继承马列毛的这个派别,他们的观点是(当然不是学术会议上的观点,学术会议上一般比较温和),就是印度海德拉巴这个派别,他们更强调土改的问题,就是印度没有实行土改。这个话当然也有些问题,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一些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因为历史上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那种土地制度不可能了,所以采取限田制。在唐以后这个限田制不断地出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然后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那么印度采取限田制,他们的判断是失败了,当然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就是没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分掉了是有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实行,是实行过的。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因为我提出来他们都笑了,只能得到极差的地。所以它的这个土地制度没有改革。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因为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1927年到1937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就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里面是这样的,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在印度当中,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了以后,原来的这个结构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这个和中国建国以后的领导力量的转变(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批人),整个的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在印度没有发生,所以它的整个传统保留下来了。我们除了见到印共海德拉巴的主席,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印友好医疗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习主席去年访问印度的时候,还给他颁奖了呢。因为印度大家知道有一个名声仅次于白求恩的人物,大家知道叫什么?柯棣华,这个人在印度也有点名气,在中国的名气仅次于白求恩。在他们的叙事里面,在1947年他们解放就是独立,之前也有一个激进的叙事,他们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那个种姓结构。因为它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这样来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实现。他们一直认为,印度所出的问题(我讲的是印度海德拉巴的)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中国开始土改了,他们没有土改,这样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要按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因为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这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这个传统割断了,在这里割断了联系。虽然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的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我以为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印度只是一个农村存在,他们说不,也是一个城市存在,蔓延到城市里面去了。而且有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后来,我回来以后在查一些和印度有关的史料,才发现确实如此。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面叫做士农工商,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这个商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不是说他们集聚财富的能力也弱于农民,所以实际的地位是平衡的。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他们也问我们中国整个类似于种姓结构的,我的回答是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陈胜的故事,陈胜是一个雇农,在为地主干活的时候他发了一句牢骚,这个怎么是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种”可以理解为种姓,就是说固定化的等级制度,对不对,没有种,那个时候没有种,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的是想对抗这个种姓制度,所以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退出?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我这次第二个深刻的领悟,是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倡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那种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到了几百年以后,它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十、十一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当然伊斯兰教后来以大规模的入侵传播到印度去。第二个故事,我就讲宋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和均役的单位,出现了民谣,“千年田,八百主”,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这个流动,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第三个我讲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第二部《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两个确实与印度反差很大。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我们参观的那个农户,他的妻子是个婆罗门,是个高种姓的,所以他原来有二十一英亩的土地,中大的地主了。那个规模也不算小,一百二三十亩地。这个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在印度教里面,我还研究了一下,等级的分配就是它讲的婆罗门是宗教第一,然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叫刹帝利吧,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婆罗门是经商的,所以印度的商业历来很发达。自古以来从印度、马六甲海峡一直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那一带,那个时候这一带都活跃着印度商人的影子。所以印度的佛教向整个东南亚传播主要靠商人,而不是军队。后来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到缅甸,然后覆盖到整个印尼进入菲律宾,而且主要是靠商人在那里传播。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所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比如说焚化尸体、宰牛做皮革的,就是有一类的这个工,手工业那种的极大部分,不是低等级,都认为不是低种姓,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种姓就是贱民来承担。这样我们说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印度学者讲的,不是我们掰出来的,就是说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它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这是印度学者的观点,对不对由他们来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么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因为报酬低所以它比较贱,因为报酬高所以它比较贵。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我以后有机会去还要研究一下,你可以用这样的西方语言来讲,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体会。这是最大的两个体会,我回来又花了三天时间总结了一下。
第三个是水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这样的一个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要。这里指的就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地表水的储存就是搞水库了,当然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北方平原大量还是利用地下灌溉,我讲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那一带,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利用池塘什么的。那么建国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的发展就更厉害,建议各位以后尤其是安徽的,去大别山看看那五个水库,我讲淠史杭的整个灌溉系统,是建国以后花了十年功夫我们建立的特大灌区,就是一千万亩以上的特大灌区。全中国有三大灌区,第一大灌区秦汉就开始了,我这里指的是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第二大灌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不断进行的就是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千万亩以上;第三大灌区是建国以后为了治淮而建立起来的淠史杭灌区。为什么1950年我们把土地分掉以后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过程,就是以集体化的名义进行集中化过程?原因种种,其中有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观点是农田水利建设。五十年代初有几场大的水灾尤其是淮河系统,因为淮河和运河系统的常年失修,一百多年了,晚清想搞没有力量,北洋政府也想搞,没有力量,国民政府建立的牌子搭起来了,组织班子计划都有了,所以建国以后的基本主架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不要忘记的,它的规划也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第一个就是,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都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你看明朝初年的朱元璋,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因为战乱,水利失修,土地没有办法种。
共产党起身于农民和农业,所以,更重视这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个农田水利建设就直接地关涉地表的土地地权,尤其是和小块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的冲突,你要开河开沟,谁家的土地让你开掉,你要开沟引水,如果说小块土地所有制,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储水灌溉。当然,如果战乱以后重建一个王朝,大规模的人口消失,无主的土地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以国家级的工程进行水利建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后就不可能了,因为土地都有主了,而且土地都细碎化了。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土地的细碎分割特别严重,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后来查下来土地集中确实和水利建设是有关系。还有一个把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就是把7亿亩地富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就等于把7亿亩的地租(这里指的是粮食)也交给了农民,所以每个农民稍微超好一点,就把7亿亩的地租吃掉了,因此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粮食一共就三百亿斤左右,缺口四百亿斤左右,这就要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要把这个粮食从税收以外的系统就是统购统销系统重新集中到城市,来支援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个个分散的农民,挨家挨户地要,不鸡飞狗跳来才怪呢,而且征收的成本高、风险大。你集中起来通过公社早就把你拿走了,拿走以后集体再拿走一块,然后集体再来分啊,这个征用成本是很低的,就这样悄悄地,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所以,我讲的两个理由,水利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正因为这个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公社时期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要忘记了三级所有的公社是社队合一的,它的顶端是和国家合一的,所以农民长期保留的一个观念是土地是国家的,虽然法律规定是集体的,但是集体本身的规定是模糊的,公社这一级是集体还是小组这一级是集体,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就帮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虽然土地分掉了,还依然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提是土地的地权实质上的国有,所以现在我们要在第三世界推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光征地就要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了,没那么容易。印度要搞一个高速公路谈何容易,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我们要搞一个高速公路一般要六十米左右的,有的要八十米的还有绿化带,如果六十米的话那你110米就是一亩地啊,那是良田啊,照样征到,我们原来是双向四车道后来是八车道,你看看那个开封到郑州的十二车道还要豪华。当然反过来讲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中国要征地,个别钉子户把它一拔就拔掉了,当然这几年也不允许乱拔钉子户。
印度由于土地的私有制以及人口繁衍以后土地更加细碎的分配,导致它长期以来不能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它的降水量不低于中国,但是存蓄水的能力很差,南北方基本上以井灌为主,这里才明白,印度以井灌为主,而不是以地表灌溉为主,中国的南方以地表灌溉为主,井灌为辅,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包以后,南方的井灌也发展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用井灌再加上印度尼赫鲁的向农倾斜的制度,就是电价极低,就比城市价格低,这个价格几十年不动,因为农民不许它动,他们的客运政策也是尼赫鲁定下来的,那个时候通货膨胀也不受影响,这两个对农民优待的政策反过来成为印度最大的头疼的问题。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是有21英亩地吧,那个农场种水稻的,一年两熟,他打井,那么问他交的税费,半年一交,一百二十个卢比,等于十二块钱,一年就是二十四块钱,他21英亩土地的灌溉,而且水井很深,你看看用电量多少,就等于电是白送给他的,只有一定规模的富农以上以及地主才有可能打深井,深井而且这个水又这样用,用了以后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原来二十米的没水了就废掉了,他又没有能力再去打井,这样大量的中小块的土地靠天吃饭。这次我才明白,解决了我一个心中的困惑:印度的可耕面积占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印度的国土面积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它的耕地面积大概维系在21亿亩左右,那么中国的土地最高面积达到20亿亩,由于二十几年来我们退耕还林了一亿多亩,我们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又一亿多亩,现在就是大概只有18.23亿亩,总而言之中印的耕地面积差不多,但是你查印度的粮食总产,我讲印度从1947年解放从来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的百分之五十,这个很奇怪。当时我以为是他们的土地质量比较差,或者他们受季风的影响,印度洋的季风和我们太平洋的季风有差异。当时我估计,要不他们干旱和水害比较多了,一般来讲太平洋的季风稳定能力要比印度洋的稳定,不要忘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季风国家,第二个是雨热同期的,从南方到北方如果是均衡分布的,历史上叫做风调雨顺,结果必然国泰民安,天下寺庙上的那些字最频繁出现的必然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长期滞留在南方,那么北方旱,南方涝;如果一下子越过了淮河进入到黄河流域,那么北方水灾南方旱,所以中国一般的形式是三年一小灾,六年一中灾,十二年一大灾,当时因为中国大,害了北方有南方,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的话,粮食调配的能力比较强的话,饥荒一般不会发生。印度的季风情况,我们没有研究过,地表储水能力绝对比我们差的,必须利用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地下降,和我们最近二十年的状况差不多。共产党有办法,就是用南方的水补调北方,现在我们有两条水,东线的水早已经开通了,我这次专门跑到东线调水的末端就是通州去看了,那个水质还不错,能灌溉用,能不能吃我没有问过他们。然后我们的整个中线的调水已经完成了,北京市民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饮用水吃到我们南方人的水了,丹江口的水调过去了。你要搞那么大一条运河过去,要多少动拆迁,征多少土地,印度不可能完成。那么中国有能力完成,当然了从学者来看你还有动拆迁不好的,乱动拆迁的,那我们哇哇哇叫起来也是应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工程的正面效果,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制以后,就把地表的最后一百米的支渠和斗渠的灌溉系统在南方大规模地毁坏了,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下来的5.8万个水利设施。在南方你看看,最近我特别关注云南,云南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地方,为什么稍微一晒,就干旱了,你看看云南的水库运行了三十年以后怎么样,原来水库是一个网么,常年不修的话不就水库淤积嘛,现在一晒就干旱。如今才注意要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农田水利主要由国家支付,主要是中西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是这种转移支付下去被腐败的可能性居多,被包工头以及那些水利局的哥哥弟弟搞掉了,拿去一百万就干了十万的事情。这个问题大家要特别地研究一下,就是共产党给钱要给出坏事,原来问农民要钱也要出事情来。这是第三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感觉。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个别的小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中印的六十年的差别。我说我的判断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从事了土改,印度基本没有土改;第二个是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印度就不可能、也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对第一个都肯定,说你做对了,对第二个是怀疑否定态度的。对于计划生育,整体来说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假若没有计划生育,那么我们同印度比较一下。印度1947年解放独立,1950年从事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1951年公布了1950年的普查数字。印度当时把巴基斯坦、孟加拉搞出去了,版图总人口为3.2亿,我们1950年人口多少呢?因为我们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近6亿,然后推算到1950年大概5.5亿,据说这个数字出来以后整个中共的上层都大吃一惊,那年开始提计划生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1957年反右斗争就终止了,毛泽东原来的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稿有一段是讲计划生育的,发表的时候已经反右了,把那一段取消了,后来就没有搞计划生育了。那么印度1950年人口是3.2亿,去年公布的是12.2亿,按照它的增长率我们现在人口是多少,大概要超过20亿,将近21亿,而我们现在公布的人口大概是13.6亿,减一减,计划生育就少生了6个亿,这6个亿一定还在那个地方排队还排着呢,对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们就业怎么解决?不可能!即使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农村依然沉淀大量的剩余劳动,中国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就过了刘易斯拐点是不可能的,而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这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个点是最难过的。但是他们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数,你中国因为搞计划生育所以未富先老,后面的问题严重着呢!现在我们也有点忧虑,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这二十年过不了,你搞了计划生育,后面有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老”是不是个社会学定义,你60岁为“老”?还是65岁为“老”?你稍稍改变定义,劳动力就丰沛起来了,其实欧洲早就这样干了,德国的“老”定为67岁,那么企业和国家就少付你七年的养老金了,你还可以为国家多干一些年。现在上海比如说平均寿命82岁了,定位70岁为“老”也没有问题,因为当年的那个俾斯麦定义“老”的时候就问当时德国的平均寿命是多少,60岁,就将“老”定为60岁。现在年龄大起来了,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值得担忧?现在还是要解决年轻人的就业,像我们不退休,把你们堵住了,我退休,就可以退掉一个教授的职位供你们上来。现在到底是照顾我好呢,还是照顾轻人好呢?那么要照顾年轻人了,回头把年轻人变成不满者,网上负面信息的发布者,那就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生育率的自然的递减率,我就问他,你城市化了以后生育率的自然递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农村人的人口还在不断地产生,进城了以后生育率降低了,还有很多没有进城的人呢?在农村里面地那么少,没事干就生孩子。这是一个问题,印度也搞过几次计划生育,罚很多东西吧,印度也不知道罚什么东西,但是印度学者认为会自然地下降的。印度的自然增长率曲线最近五年确实是向下弯的,在下降,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东西,中国在城市推行计划生育是在1979年,农村大规模推动是1985、1986年,在1990年达到峰值,整个农村也搞得鸡飞狗跳,我是那几年经常往农村跑,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尽管如此,我们看农村产业的就业人口就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虽然城市化率在不断提高,农村的比例在下降。如果我们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就算做城市人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了,但不要忘记,这个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农村的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持续上升,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下降?我们五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也就2.4亿多,然后不住上升,到2002年达到了峰值,大概是3.8亿劳动力,2003年以后开始绝对值下降,正好和刘易斯拐点同时下降。这个特别重要,过了这个坎,然后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逐步地推行。怎么把那么多的农民工稳定地有保障地装在城市里面,这当然是我们以后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总的意思就是说,中印的某一些比较,通过印度来反观哪些事情做对了而又有哪些事情做错了,有一个明显的认识。另外,传统纠缠于现实,对这样一个议题,历史对于当代的影响,中印的近代对比,中国的几场革命,尤其包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那个作用,就截断了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全盘地西化了。以前我对那场运动越来越采取否定的态度,经过印度之行,我相信我会修改一些观点,原来我是崇拜鲁迅的,后来我又否定他,现在我觉得对那一场运动,又有一个新的反思。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它和传统的东西割断,有它的必要;然后当传统不再纠缠于我们现代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就是大规模的传统被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的一种符号,这就是共产党当下所干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不纠缠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传统的文化,我们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最后一个观点,就是事实上近代中国在观念上割断了传统,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然后1949年又是一次隔断,彻底地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割断,这三刀切下去,所以,中国的历史要进行平稳的叙事,就特别得困难。那么有些传统事实上是观念上否定,虽然否定了但仍然顽强地存活着。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郡县制就顽强地存活着,这是反传统的毛泽东公开承认的。百代践行秦政制,而且郡县制在中国的完成是从秦开始,大规模的推进从晚清开始,北洋民国加剧,而后到共产党的1965年,建立最后一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正式完成。把郡县制推广到周边地区去,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是1965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在我看来,党的领导核心在哪里,是对这个传统的守护,如果在中国的现有的宪政体制里面,把这个拿出去,它是一个完备的宪政体制,各级地方选举各级人大,各级人大选举各级政府,那不是一个完备的宪政框架嘛!这个框架如果没有郡县制的保护,它就散掉了,这个框架是彻底颠覆传统的郡县制,因为现在的框架是对下负责的,郡县制是对上负责的,所以如果把这两个体制有效地结合,同时各级政府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那么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在座的搞行政管理的老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向诸位汇报以上几点。在中印两国的比较当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发展当中的某些东西。
(责任编辑:徐澍)
On Sino-Indian Comparison after a Visit to India
CAO Jinqi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In recent years,Indian scholars started to take China as standard to reflect up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ia.They think the different modernization pathways of India and China stem from the different land systems of these two countries.The collective land system since 1950 has la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fter the opening and reform.Besides,the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severed China’s connection with traditions,and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o modernize.In India,however,the private land ownership,together with caste and village systems,has made their path of modernization a tortuous one.The Sino-Indian comparison in terms of land systems,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urrent realities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flect upon China’s situation.
land system;modernization path;Sino-Indian comparison
曹锦清(1949-),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C912.82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
1008-7672(2015)05-0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