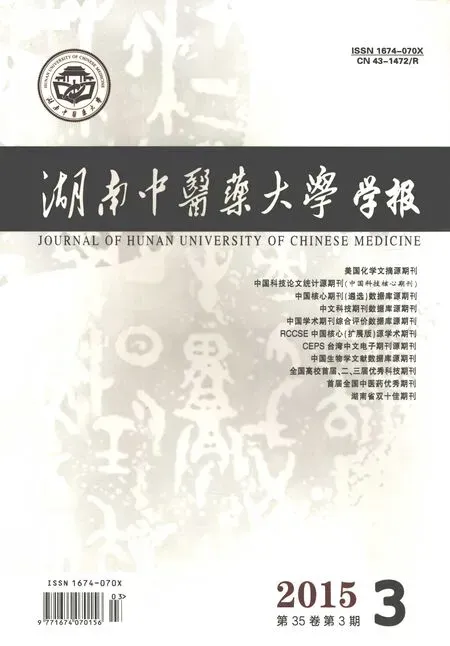浅谈人体科学“三分法”
2015-03-17曾逸笛周小青
曾逸笛,周小青*,周 昊
(1.数字中医药湖南省高等学校2011 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长沙410208;2.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208;3.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5)
纵观古今中外,存在着一个“三”的法则,因“事必有三”。 三分法代表着一种全面、深刻、深思熟虑而又有着简明扼要和说服力极强的思想内涵。 因说服力和简洁共存而引人注目的状态。 《说文解字》云:“三,天地人之道也。 从三数。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此处“三”并非实指“3”这个数字,而是指由两个对立的方面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第三者,进而生成万物。 同时结合其下文提到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理解为“阴阳二气互相作用交和而成为均匀和谐状态,从而形成新的统一体”者。 我国古代学者常在阴阳二分法的基础上进行三分,如中医的三阴三阳学说,在经络学说以及六经辨证当中均有所应用,“太阳、阳明、少阳” 即“阳”的三分法,“太阴、厥阴、少阴” 即“阴”的三分法。 人体科学从“三分法”角度进行解析,是否将能更全面描述人体的各功能、形态、特征,更有利于开展人体科学相关研究,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服务。
1 身体健康状况三分法:健康,疾病与亚健康
对于人体,最容易引起人们重视、人类科研投入精力最多的是疾病与健康的研究。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中就给出了人类“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免于疾病,而且是保持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好状态,1989年修改为: 包括身体的、心理的、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1]。 但若教条主义式照搬原文, 对人体进行简单的 “健康”与“疾病”的划分,就容易落入机械行事的陷阱,犹如“加到第几粒米才能称为一堆米” 的难题, 面临着“若遇到难以客观量化的不适, 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之为疾病”这一窘境。 幸好,很多学者注意到了人体的健康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一特点,很早就模糊地提出了“第三状态”、“潜病状态”、“灰色状态”等词来形容[2],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由王育学首先提出了“亚健康”这一概念,用来概括这种“不黑不白”的中间状态,并得到了广泛沿用。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 《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给亚健康下的定义是:“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 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诊断标准。 ”[3]
其实, 简单的三分法已经在临床中有所展现,如正常人的生理状态皆为一定的范围值,超出或低于此状态皆视为异常、病变,类似的指标有:高血压、低血压、正常血压;心率快、心率慢、正常心率;基础代谢率过高、过低、正常,等等。 但在这正常生理状态之中又可再使用三分法进一步划分,如同样是正常血压、正常心率、正常基础代谢率状态的人群,根据体质强弱、偏颇,仍可进一步区分出阴脏、阳脏、平脏之人。 这样说来,正如在正常高血压范围值内还能再细划分出理想血压值一样,经三分法划入正常状态的人,并不代表一定此人的身体状况处于理想状态,但此时又与疾病尚有一定的距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比“非黑即白”两分法的健康/疾病人体状况描述,充分肯定“亚健康”这一概念的“疾病/健康三分法”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医学对人体认识发展的主流。 此为人类身体健康状况中的“三分”人体科学。
2 人体体质三分法:平脏,阴脏与阳脏
体质学说五花八门,仅古代就有诸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将人的体质分为5 种大类:木、火、土、金、水,各自再推演出5 种亚类,共25 种:“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元代朱丹溪提出痰湿体质,《格致余论》:“肥白人多痰”; 明代张景岳将人划分为阴脏人、阳脏人、平脏人;清代章楠《医门棒喝》提出4 分法:阳旺阴虚,阴阳俱盛,阴盛阳虚,阴阳两弱。 再随着加上近现代学者对体质学说深入研究,又有匡调元将人体分为:正常质,晦涩质,腻滞质,燥红质,迟冷质,倦白光质[4];王琦将人体分为:正常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气虚质,瘀血质[5];田代华将人体分为:阴虚型,阴寒型,阳虚型,阳热型,气虚型,血虚型,血瘀型,津亏型,痰湿型,动风型,蕴毒型[6];何裕民将人体分为:正常质,阴虚质,阳虚质,阴阳两虚质,痰湿质,瘀滞质[7],等等。
如此纷繁复杂的体质学研究角度,均各有各的优势与侧重点,不能轻易取舍,但又很难同时驾驭。反观同样浩帙的中医诊断学辨证理论体系,虽亦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等多种方式,但各版教材、不同老师,都会强调最为提纲挈领、最为全面的辨证方法只有八纲辨证, 它虽然不够深入与细致,但只有它方能统领各类证型。 同样的,各类体质学研究均有根有据地提出了自己分类的方法,有的已经形成了切实可行的临床量表,但缺乏一个最具有纲领性的、公认的人体体质分类纲领,那么明代张景岳提出的阴脏人、阳脏人、平脏人的分类应当列入考虑之首。 《景岳全书·传忠录》写到:“阳脏之人多热,阴脏之人多寒。 ”这里的阴脏阳脏,既可单纯指寒与热,又可似八纲辨证当中的阴与阳,将其余病邪统领进来,如痰湿、血瘀质可纳入阴脏人当中,而燥红质、蕴毒质可纳入阳脏人当中,至于平脏人,即大致对应上文的健康人,如此,方可化繁为简、执简驭繁。 此为人体体质的三分人体科学。
3 人体形态三分法:解剖,体质与状态
来看人体本身,存在解剖、体质、状态这三种不同的情况。 解剖学当中对人体的定义有中西之别,历来有不少争论, 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殊途同归,均是从不同角度窥探、 分析人体这一复杂的巨系统,同时也是认识人体最基础、最稳定的环节,所描述的大多是现实可见的人体脏器、组织结构,除重大的疾病、手术等病史外,出生后一般难以改变,可视作人体观三分法层次当中的基石。 体质的稳定程度次之,体质的不同既有先天条件的差异,又有后天环境的影响,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想要改变人体的体质也并非一粥一饭可撼动之。 同时,相对于人身体解剖关系,人体质的可塑性又大得多,饮食、方药、导引、情志等等均可在假以时日之后对体质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至于前文尚未提及的同时也见诸报端甚少的状态人体学,则明显带有可变、多变、易变的特征。 “状态”在《辞海》中解释为:“在科学技术中,指物质系统所处的状况。 ”吴承玉[8]说:在医学范畴中,人体某一时间的全身机能状况,称即时状态,简称“状态”。也即,除体质外,其他对人体产生能够反映在外表现的因素都归属于中医状态人体学,如情绪、饮食、疾病等,甚至可包括由于年龄、性别不同所带来的人体状态上的差异。 因此,如将解剖、体质、状态这一三维角度比作金字塔,那么位于基底部的必然是解剖学, 在解剖学基础上方能展开体质学的研究,而位于塔尖、最为精细的状态学,不可否认其还有很多部分的研究尚处于空白, 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去发现。 此为人体形态的三分人体科学。
4 人类年龄三分法:儿童,成人与老年
除了人体状况、体质、形态的研究,另还有时间的三分研究角度。 现代临床医学,连同现代化的临床中医学,对人群健康研究的划分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的趋势,例如临床科室从以前的大内科,划分出现在的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肾病内科等,甚至根据医院人才资源的不同,在内部进一步细化为各有侧重的不同病区,这也同体质学研究一样,呈现出前述纷繁复杂的趋势。 另一方面,尽管病变、功能减退的器官、组织有所不同,但患病人群仍有其很大的共性,其体现在生理功能、储备能力、特殊综合征以及对心理、精神、社会等影响的反应上,带来这一共性的最主要因素可以说是随着时间增长的年龄,分为老年医学、成人医学和儿科学。 关于儿科学与成人医学,各方面研究体现出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老年医学还有待加强。 随着我国人口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很多医院开始兴建以前尚缺的“老年病科”。 而将老年人这一人群作为整体研究的老年医学紧迫性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09年,被誉为 “老年医学之父” 的美籍奥地利医生Ignatz Leo Nascher 在美国西奈山根据拉丁文geras(老年)与iatrikos(治疗)创造了现代老年医学(geriatrics)词汇,并开启了老年医学的先河[9]。 我国于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华医学会老年学(gerontology)与老年医学学术会议,该会议对我国现代老年医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老年医学专业的首次建立[10]。针对老年患者发病的特点,现在有学者提出老年医学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 老年医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2)老年病诊疗的连续性;(3) 老年病诊疗需多学科协作;(4) 老年医学更需社区医疗与社会服务体系[10]。这对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树立起对老年医学的正确认识,开展我国的老年医学教育和医师培养模式,完善人群观之三分法,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
“生命之源”水有三态;人亦有三态。 水之三态气、液、冰,在自然界中缺一不可,相互转化才有这大千世界;人亦有三态:三分法的健康观、体质观、形态观和年龄观,在人体科学中缺一不可、相互转化, 充分而简洁地概括人体本身所有的生命活动。在此提出的三分法之人体科学,基本全面地囊括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人体本身, 更有利于整体把握、开展人体科学的相关研究, 并应用于教学与临床上,也更有利于缜密思维的培养,其目的是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服务,促进医疗水平不断向前发展。
[1]刘伶燕,陈一民,刘东海.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健康定义重建[J].教育教学论坛,2014(44):76-78.
[2]蓝毓营.”治未病”源流述略[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5,39(9):38-39.
[3]范延妮.中医“治未病”思想对亚健康防治的启示[J].西部中医药,2014,27(12):37-39.
[4]周狮驮,匡调元.匡调元辨质论治临诊经验实录(一)——总论[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247-250.
[5]靳 琦.发微于理论体悟于临证——王琦教授辨9 种体质类型论治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5):284-288.
[6]田代华,吕明伟.论体质与证候[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3(1):86-87.
[7]何裕民,王 莉,石凤亭,等.体质的聚类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5):7-9.
[8]吴承玉.中医学对人体状态的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0,15(6):25-26.
[9]冷 晓.美国老年医学理念与实践[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1,31(1):31-33.
[10]张 华,吴利平,王晓明.中国老年医学发展与老年医学教育的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8):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