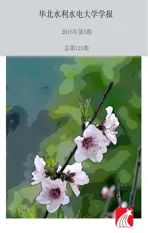贾平凹笔下“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
——以《商州》《秦腔》为例
2015-03-17黄鋆鋆
黄鋆鋆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贾平凹笔下“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
——以《商州》《秦腔》为例
黄鋆鋆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疯子·女神·城里人”是贾平凹乡土小说中所开创的一种独特模式。寄寓着乡土之美、传统文化的女神,在代表乡村非理性、丑陋一面的疯子和“农裔城籍”的城里人之间进行的选择,也是现代社会中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城乡所进行的自觉的价值选择——抛弃乡土、入赘城市。这一选择所面临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根和失落。这不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乡土和文化本身的悲剧。
贾平凹;女神;城乡选择;农裔城籍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中最贴近“中国之心”和“中国精神”的作家,也是一位不断超越自己,永远在探索和前进中的作家。他的乡土书写为我们提供了真实乡村日常生活的盛宴,把乡村的存在和可能性展示给我们看,并在此间将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人性)融为一体,向乡土中国的精神内核无限靠近。但在多产和探索中,他的创作常出现某些固定的模式,比如女性形象的单一化、情节结构的定型化等。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一女二男的叙事结构。而在一女二男中,又以“疯子·女神·城里人”最为典型,也最能表现贾平凹对乡土之根寻找的失落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漂泊、无根无依的状态。
《商州》是贾平凹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分为乡土文化和乡土选择(即地方志与故事)两部分,呈现出寻觅乡土之根的焦虑和失落。在其新世纪的大作,被誉为“乡土文学的绝唱”《秦腔》中,乡土的衰落和故乡的丧失让“农裔城籍”的知识分子呈现出更深的绝望和更大的悲剧感。毫无例外,这两部作品的悲剧感与乡土社会没落的无奈都间接地由“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隐现出来。女神对男性的选择也成为乡土文化的美神对乡村与城市的选择的一种隐喻。
一、“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
女神的形象是贾平凹笔下不变的坚守,也是他“地母情结”的一种显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师娘(《天狗》)、小水(《浮躁》)、珍子(《商州》)、白雪(《秦腔》),都是乡土培育出的美的精华,作家把自己心中所有关于美的定义统统赋予她们,她们“都有美丽而博大、神圣而苦难、平凡而难以企及的特征,是男主人公为之奋斗的动力和苦难遭遇的避风港。……她们是贾平凹创作中的生命力显示”[1]。“疯子”们则是土生土长、又有缺陷的一群农村人,严格来说,他们并不都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却都有着疯狂和痴傻的特质,是原汁原味的、非理性的、甚至是丑陋的乡土的孩子。至于城里人,则是一群非城非乡,表面打着城市标签的精神漂泊者。他们或被城市放逐,或被乡村驱逐,成为无根的一代,也是“农裔城籍”的作家的化身。
这三种形象构成了三角恋的结构:疯子痴情地追随女神,而女神所爱的却是优越的城里人。但最终,女神的选择并未给自己带来幸福,传统文化也终究在城市和乡村的选择中陷入失落和无奈。
(一)《商州》:秃子——珍子——刘成
在《商州》里,贾平凹沿着河流地势,从根上梳理了故乡所在的商州地区文化,然后向着省城西安返回。虽说是寻根之旅,可作家所托身的“后生”走的却是一个“离城——去乡——回城”之路,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城市。刚刚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从农村走出,在向往的城市安身立命,
久之,便成了圈在笼中的鹰,即使被放归,也不能在天空中获得归属感。那么,抛弃故土的知识分子就真的能寻回自己的根吗?
在作家和读者皆为之痴迷的商州,贾平凹构造了一个秃子——珍子——刘成的三角恋爱故事。我们以为商州的乡土人文风情就是贾平凹寻到的根,但他却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写了一个“不相干”的故事。在这故事中,城与乡的对比在人物角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刘成担当起从城里归来的“农裔城籍”的城里人角色,与返乡的“后生”脚步相接,也是乔装的作者本人。他有钱、帅气,但也冲动、缺乏原则。与之相对的,是来自农村的秃子,丑陋、猥琐却痴情、无私。他头上鲜明的癞疤正如乡土之根的皴皮。这又老又丑的秃子却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珍子,为保护搭夜车去城里找刘成的珍子,他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伴侣——黄狗。女神珍子来自自古出美女的山阳,集天地灵秀与传统文化于一身,面对秃子和刘成,她的选择是明晰而决绝的:从始至终,她都只爱刘成这个城里人,对痴情付出的秃子却只是由讨厌到怜悯。女神的价值选择也代表了这一阶段作者本人的立场,不论故乡多么美好,一心向往城市的知识分子却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安排了一个别具深意的结尾:刘成和珍子在城乡交界的华山落脚,准备开始幸福的生活,但一场洪水毁了所有,刘成和珍子双双死去。来自城市的追捕力量和来自乡村的追求力量间接参与了对二人的谋杀。作者有意告诉我们,刘成和珍子在死之前并未达成身体上的结合,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与乡村之美是难以真正结合的?城里人和女神的结合以死告终,躯体留在了乡土。而作为根的乡土有的却是深深的无力感,留不住孩子的心,只能留住冰冷的躯壳。于是,寻根之旅最终在死亡面前失败了,作为根的乡土也开始了溃败的历程。城市与乡村的争斗,最终是没有胜者的。
(二)《秦腔》:引生——白雪——夏风
《秦腔》可谓是实实在在的乡土的硕果。作者回到生活的原点,从最琐细的日常生活入手,在一砖一瓦中建构了乡土,又解构了乡土。城市此时已成为巨大的乡土舞台后不可遮蔽的背景,它以强大的力量压迫着古老而虚弱的乡村,让乡村传统的长老统治在政治权利的挤压下先溃败后灭亡。“最后一个农民”夏天义的死成为乡村失去自我的标志,乡不乡、城不城。乡村最终沦为城市的一个附着物。
“疯子·女神·城里人”的模式在《秦腔》的时代呈现出了更大的悲剧意味。在这场追逐中,三人都没有幸福可言,甚至连精神的结合都不曾有,唯有肉体的结合给他们带来“怪胎”的后代与最恶毒的诅咒。所有的结合都面临无根的结果,乡村不仅失去了孩子,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疯子引生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承担起“作家、隐形叙述人、叙述人、小说人物”的四重角色,“生活是由他结构的,同时也是由他解构的”[2]。作为乡村的代言人,他不仅早早失去了和女神接触的资格,还在开篇不久便自残阉割了自己的生命之根,让乡土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有了缺陷。而夏风这位“农裔城籍”的城里人彻底被乡村放逐,他的活动舞台更多是城市,他在乡村的身份成为一种虚无、罪恶和权力,同时也是“负心汉”和“不孝子”。雪随风而舞,风却弃雪而走。坚守和游离成为白雪和夏风之间最大的鸿沟。两人面临着较珍子和刘成更为失败和痛苦的结局,精神难以结合,身体也难以归根,因而他们的后代只能是畸形儿。
在这部小说中,对城市与乡村的抉择于女神来说更为悲痛,新世纪城乡关系也较之20世纪80年代更为紧张和特殊。乡村对美的追求已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而女神对城市的攀附也了无希望。乡村与女神最终面临的都是失落,而乡土的生命和美也就此无处安放。
二、三角恋里的城乡抉择
一女二男的叙事模式是贾平凹富有寓意性的设置,男女的感情不但牵涉爱情婚姻,更影射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转变。创作兼具数量与质量的贾平凹,既能保证情节的生动有趣,又能达到艺术的高度与深度,往往是既讲了故事,又讲了道理。他笔下的女神形象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女神表面是勤劳美丽的农家少女,内在却有乡土中国的符号意蕴。女神的选择也成为透视作者本人城乡抉择的一扇窗口。
(一)女神的寓意
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原型一般有三类:地母原型,如母亲、女神等;寡妇原型,如狐妖、妓女等;恶妇原型,如后妈、巫婆等。贾平凹的女性书写中以女神型为主,而像石华(《浮躁》)、黑娥、白娥(《秦腔》)、唐宛儿、柳月(《废都》)此类女妖型仍在少数,且不够成熟。作为女神的珍子、白雪,因地母的原型被赋予了乡土的根性与生命力,她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希望和根本。反过来,她们又给予乡村根的给养和美的净化,乡土只有在她们的存在和庇护下才能保持生命和发展。
但不幸的是,女神们在依附城市的努力化为泡影后,不仅让乡土的根性和生命难以维系,也把自身污染了。引生总说白雪从城里回来后脸变黄了,即是表明最纯洁的白雪已经污浊,乡村的美和生命又如何维系?因此,疯子引生在超现实的言说中对乡土之根、对乡土社会的命运发出了最大的哀嚎和忧虑:乡土到底能不能存活下去?
传统文化是女神的另一重身份。珍子和白雪不无巧合地都是地方戏曲的演唱者和传承者,她们都是戏曲的象征。作为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晶——戏曲,实则是乡土中国的文化之根。从这一层面上,女神又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贾平凹的创作也就不仅是乡土的挽歌,更是文化的挽歌。在《秦腔》中,文化与乡村成为并置的两个维度,“最后一个文化人”夏天智在清风街、在夏家无疑更具有长老的资质,是比夏天义更为强大和厚重的存在。然而,两个“最后一个”终究都逝去了,希望就落在了无血缘的女儿白雪的身上。相比于乡土的失落和消逝,贾平凹显然更忧心文化的没落和丧失,这一点在《秦腔》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小说借助秦腔长歌当哭,为乡土和文化的消逝而哭。正如陈晓明所说:“原来的那个宏大的乡土叙事,具有历史发展方向和愿景的乡土中国正在走向终结,并且携带着它的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3]因此,《秦腔》相比贾平凹以往的乡土写作,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以及文学史的地位。
(二)女神的选择与作者的城乡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全方位、深入、主动地融入现代化的大潮,也是这现代化带来了城乡的二元对立。在现代化对乡土中国的全面进攻中,农村和农民也在不可遏制地发生着质变。从《浮躁》里的人心不古,到《商州》里工业化、商业化对农村的渗透,再到《秦腔》中“最后一个农民”的逝去,乡村早已不是知识分子传统思维中的桃花源、乡土乌托邦、精神家园,就连被称之为根的土地也在修路、建厂中一点一点地退守底线,而这底线能不能守住,仍是一个未知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贾平凹所做的选择也正是无数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抑或乡土中国人们的选择,具有时代的代表性。
从《商州》到《秦腔》,女神对男性的选择总体上都是择“城里人”而弃“疯子”,向城市靠拢的趋势和心理是不变的。一边是繁华、光鲜、发达、优越的城市,一边是土气、丑陋、落后、卑微的乡村,不论我们嘴上、心里多么热爱乡村,实际上却都是心照不宣地选择城市。历史再次把国家的命运寄寓在女性的身上,古老的乡村和文化多么希望抓住现代的契机,不遗余力地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传统和现代作为异质性的二元存在,一方向另一方的靠近也就意味着自身的消泯甚至灭亡。
作为城市的媳妇,乡村的女儿,女神们选择了城市却仍旧离不了乡土。她们的活动场域从来没有真正走入城市,大多是在城乡之间徘徊。乡土仍是她们想要降落的地方和精神的家园,她们作出了时代的选择,但充满焦虑和失落。
农裔城籍是贾平凹非常突出的身份特征,他同女神一样选择成为城市的入赘者,但却始终不敢忘却自己的乡土之母。在明确了走进城市的无根焦虑和死亡威胁之后,贾平凹们仍怀着一颗乡土之心,向着乡村深情地回望,企图在这里找到赖以生存的根系和信仰。但这转身亦是一种徒劳和悲剧,他们的乡村已经质变,他们自己也已质变,被城市放逐的“他者”只能再次被乡村放逐。寻根的结果是无根,于是,无根的一代只能继续漂泊、流浪。
[1]张学昕.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2006(3):53.
[2]阎建滨.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贾平凹创作深层魅力新探[J].当代作家评论,1991(1):10.
[3]陈晓明.他能穿过“废都”,如佛一样——贾平凹创作历程论略[J].延河,2013(5):74.
(责任编辑:王菊芹)
The Narrative Mode of“the Madman,the Goddess and the Oppidan”of Jia Pingwa——With Shangzhou and Qinqiang as an Example
HUANG Yunyun
(College of Art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The madman,the goddess and the oppidan is a unique mode of Jia Pingwa’s local novels.The goddess of the local beau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gives a choice between the madman which represents the irrational,ugly sid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oppidan of"city of agricultural origin",which is also the conscious choice of the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Jia Pingwa when faced the value choi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own initiative:leave the country and enter the city.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hoice is no root and lost,which is not only the tragedy of this generation intellectuals,but also it is the tragedy of native and the culture themselves.
Jia Pingwa;goddess;urban and rural choice;city of agricultural origin
I206.7
A
1008—4444(2015)05—0125—03
2015-08-28
黄鋆鋆(1992—),女,河南平顶山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