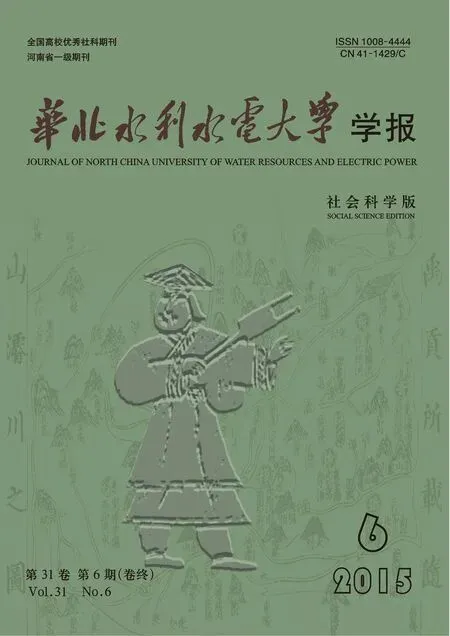严歌苓笔下女性的卑微与顽强
2015-03-17王改宁
王改宁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严歌苓笔下女性的卑微与顽强
王改宁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严歌苓以西方价值观重新看待中国的革命史,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塑造出富有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在沧桑、厚重的历史中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的一群。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忍受着命运的残酷作弄,表现出女性生存的艰难和身份的卑微。但女性的卑微并不表明她们是生活的弱者,严歌苓同时也写出了女性在巨大的生存困境下表现出的坚忍与顽强。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卑微;顽强

一、历史叙事下的女性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潮流来看,言说“历史”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写作方式。以《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1]94。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说教作用,而“新历史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限制与束缚,以一种新颖的叙事视角和艺术实践来展现历史语境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严歌苓的小说也可归为“新历史小说”的范畴。她用独特的艺术想象将小说中人物的传奇经历和历史的宏大叙事相结合来进行文学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亦是如此。战争年代的凄苦、文革十年的不幸,以及平淡岁月的琐碎,这所有的记忆都揉碎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带领读者走进那些过往岁月。海登·怀特说过:“历史叙事不‘再现’其所形容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对这些事件应该朝什么方向去思考,并在我们的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感情价值。”[2]171严歌苓的小说也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叙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特殊体验,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
严歌苓不着重建构宏大的历史史诗,更多的是以个体在历史中的成长与发展为主线(这种成长与发展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个人进步史),以个人历史的角度来展开叙事。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具体的历史场景和历史风貌是个体生活的缩影,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多样而丰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崇高”与“庄重”被消解殆尽,而建构小人物的平凡历史则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九个寡妇》沿袭了这样的创作特点。这部小说取材于河南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严歌苓通过艺术加工塑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寡妇——王葡萄。在小说中,王葡萄有一双“不避人、不惧怕”的眼睛,有一颗面对人事变迁而不改初衷的真心,有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原则。小说开篇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对于葡萄,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听人们说:‘几十万国军让十万日本鬼子打光了,洛城沦陷了!’她便说:‘哦,沦陷了’。”王葡萄是普通的乡间村妇,在她心中没有什么抗日豪情和民族大义。
在《小姨多鹤》中,十六岁的日本女孩竹内多鹤一出场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她以“不善跑的两腿”疯狂地奔跑,在小女孩心中这是一场生死赛跑。她要将村长们的“决定”告诉邻村人,让这些来“满洲国”垦荒的日本村民在“好死”之前能多一些选择。幸运的多鹤最终成为代浪村为数不多的生还者,后以七块大洋的价钱成为老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多鹤就这样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以“小姨”的身份在张家卑微地生活着。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事件都囊括进文本中。严歌苓曾说:“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3]文学要表现人性故事,而只有当人性体现为一种故事状态时,它才能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大是大非,没有那么多的豪情壮志,也没有那么崇高的革命理想,她只是用自己的历史故事讲述着小人物的悲喜,并试图去揭示极致环境下人性的本质。她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作家的审美判断来重新看待中国的革命史,在多变的时代中塑造出富有人性魅力的人物形象。
二、卑微存在的女性
严歌苓描写了许多在极端境遇下艰难生存的女性,悲惨的遭遇和不幸的命运让她们成为“卑微”的一群。学者徐虹说:“严歌苓似乎总是乐意用一个女孩的命运列车,装下对生命的伤感和叹惋,也擅长将这个卑微的个体命运,放在广阔而惨烈的社会大背景中。”[4]
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南京城为背景展开叙事,为我们重述了一段惨烈而悲痛的历史记忆。《金陵十三钗》不像其他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它没有全景式地展现日军的侵华罪行,也没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场景,小说不着重凸显中日敌对双方的仇恨,而着重书写人性在战争中的表现。严歌苓以一个十四岁并具有“黛玉般小女儿情怀”的回忆者——书娟的晚年记忆重述了在沦陷的南京城中的威尔逊教堂里,十三位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为保全纯洁天真的教堂女学生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小说中的女性身世悲苦、身份卑微。身为青楼女子的豆蔻只有十五岁,她本是凭着打花鼓的手艺讨饭的淮北人,却被拐走最后卖进窑子,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人生的苦楚。豆蔻是一个“心不灵口不巧心气也不高”的女孩,这样的女子若是生在太平年月的普通人家,应该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而秦淮河的头牌名妓赵玉墨则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她读过四书五经,也通晓琴棋书画,只是由于家道中落而不幸被堂婶卖到了青楼里。
在小说开篇,当玉墨和她的姐妹们十分卖力地翻过教堂的围墙,狼狈地来到避难所时,她们便与教堂的女学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英格曼神父虽勉强同意她们暂时留在教堂,却把教堂的院子划分为两半,让玉墨和其他姐妹住在仓库的北角,任何女学生都不得接近她们,也不允许她们出现在仓库附近。南京城内的炮声中止了金陵城里的春梦,但却没有中止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妓女即使是在神父和学生眼中也永远是肮脏、卑微的存在。而对玉墨和她的姐妹们来说,她们也已经习惯了以风尘女子的生存策略来应对简陋环境带给她们的不适。所以在小说中,红菱会去勾引教堂的陈乔治从而让他说出神父藏酒的地方,豆蔻也会由于无法忍受寒冷而偷偷溜进神父的住处,而在仓库里秦淮名妓摆弄的妖娆舞步也会让纵情声色的受伤士兵忘却身体的疼痛而沉浸在这轻歌曼舞之中。在戴教官他们眼中,玉墨她们是身份低贱之人,除了充当男人的玩物似乎也别无它用,所以,在炮火中能寻得这片刻的娱乐和消遣也是极为珍贵的。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对十三位风尘女子卑微形象的刻画是较为成功的。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男权话语中是身份卑贱的玩物,在社会话语中又是不知廉耻的女性,这样双重话语的指责让我们不禁哀叹这些女子的悲戚与不幸。
三、反抗卑微的女性
在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柔弱与卑微不是其创作的目的和根本,无论是命运的不幸还是身份的卑微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反衬,从弱到强的身份逆转中高扬的女性颂歌才是作者的意图所在。因此,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她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用笔下女性在反抗卑微时所表现的坚忍与顽强,证明女性并非是弱者的代名词。
在《金陵十三钗》中,当日本大佐在圣诞节的夜晚向教堂的女学生发出“请柬”时,当士兵与神父无法保护单纯弱小的女学生时,救助“战争中最娇弱”生命的任务便落在了这十三位只谈风月的青楼女子身上。玉墨和她的姐妹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在夜色的衬托下,她们俨然就是一群单纯无邪、纯洁善良的女孩。在女学生身份的掩盖下,她们每个人都揣着牛排刀、水果刀和发钗,试图在日本兵“享用”她们时,扎瞎他们的眼珠,从而用青楼女子的绵薄之力来保全他人。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让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变得高尚起来。她们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只会抚弄琵琶、弹奏靡靡之音的轻浮女子,而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张艺谋将影片《金陵十三钗》翻译为TheFlowersOfWar(《战争之花》)。的确,这十三位女性在承受战争伤痛时绽放的人性之花散发出了温暖的气息,她们的存在也让阴霾的历史天空抹上粉红的色调,尽管看起来有些惨淡,但却足以给艰难行走在历史隧道中的人们以灵魂的感动和精神的抚慰。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通过寡妇王葡萄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一种属于女性的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寡妇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潮流来看,这一群体总是以悲苦、阴鸷、幽怨的文学形象留存在读者心中。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怀着恐惧死在漫天飘雪的祝福之夜,单四嫂子怀着对明天的无限期许等待宝儿的归来;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用尖酸阴毒的病态心理成功拆散了子女的幸福。然而,在严歌苓这里,同为寡妇的王葡萄却是仁爱的代名词,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寡妇。她不再是柔弱、幽怨并屈服于环境的女性,而是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爆发出顽强生存能力的生活强者。
在孙家做童养媳时,面对繁重劳累的家务活,葡萄没有任何怨言,她尽心尽力地按照婆婆的吩咐做事,让家人对她另眼相看。葡萄帮二大搞定各种难缠的赖账者,是二大身边优于男性的得力助手。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婆婆死于战乱,二大被错划为恶霸地主并判处死刑,二哥少勇因革命成为逆子……这些打击都没有打垮王葡萄,即使没了依靠,她依然不失勇敢生活的信心!她到河滩上认领尸首时发现二大还有呼吸,当天夜里便将他背回家中,替二大清洗伤口,敷上白药,缠好绷带。为了保全公爹的性命,葡萄将他藏在红薯窖里,这一藏便是二十多年。小说细致而真实地写出了二十多年间王葡萄保全公爹性命的过程,表现了女性柔弱外表下的生命韧性。在世俗人的眼里,王葡萄只是一个早年丧夫的不幸女子,而在失去丈夫之后,一连串的不幸遭遇接踵而至,她的肩上承担了太多的苦难,但重重的苦难面前,她却以强者的姿态乐观视之。王葡萄在史屯用自己的生存策略勇敢的生活着,她的坚忍、执着让她成为严歌苓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同时也以女性的顽强来反抗自身的卑微。
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以“自己的房间”作喻,指出女性不仅要有居住和生活的空间,还要有女性自己独立的文学空间。对严歌苓来说,她的房间是以厚重沧桑的历史为外墙,而行走于房间中的女性,虽身份卑微但却不屈地面对生活的考验与磨难。无论是平凡普通的乡村妇人,还是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无论是为获得绿卡的少女小渔,还是渴望回城的知青文秀,她们都是严歌苓笔下光彩照人的女性。她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5]73。在严歌苓构建的女性世界里,男性不是征服者,女性也不是他们的战利品,让女性回归到最本真最质朴的品性上是作家的意图所在,而女性话语的独特魅力也在于此。就是这样的创作意图才让她们完成了从卑微到反抗卑微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显示出的是女性生命力的执著与顽强。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01-29.
[4] 徐虹.严歌苓:隐身在传说中[N].中国青年报,2011-09-06.
[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菊芹)
Talking about the Females’ Humbleness and Tenaciousness In Yan Geling’ s Works
WANG Gaining
(College of Arts,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Different from contemporary feminist body writing, the females in Yan Geling’s works are those who lived humbly and tenacious in the history of vicissitudinous and thousands years. Yan reconsidered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value; therefore she could mold female images full of human depth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era. In her works, the women always bear cruelness of fate, which shows arduousness of the females’ survival. However, women’s humbleness doesn't mean that they are the weakness of life, and Yan have shown their steadfast, perverseness and tenacious personality.
Key words:Yan Geling;female images;humble;tenacious;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5)06—0130—03
作者简介:王改宁(1990—),女,河南巩义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