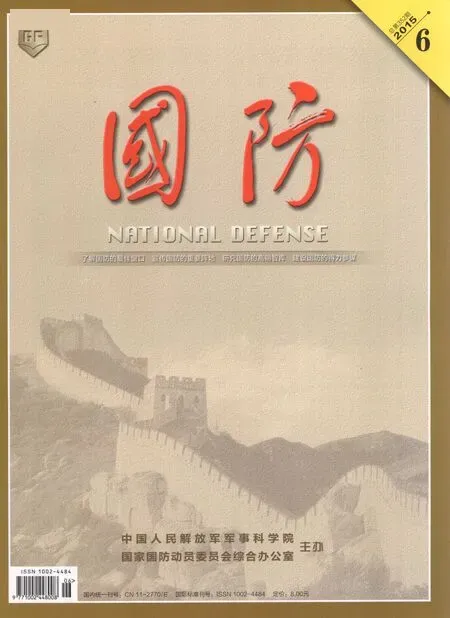同仇敌忾之六两次随枣会战
2015-03-07周晓玲
康 昊 周晓玲
同仇敌忾之六两次随枣会战
康 昊 周晓玲
关键词:军事历史 抗日战争史 随枣会战 枣宜会战
作者:康昊,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综合计划部助理研究员,中校;周晓玲,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讲师,专业技术9级,少校
1938年10月,日军虽然夺取了武汉,战略上却陷入不利:一方面,日军希望通过夺取武汉,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投降的企图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经过一年半的全面战争,日军不仅伤亡惨重,大量部队被消耗,而且国家财政也陷入危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动像武汉会战那样持续数月、进击千里的大规模进攻,只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部分优势兵力,对一些重点地区进行扫荡式进攻。为巩固武汉外围、打击中国军民抵抗意志,1939年4月和1940年5月,日军先后对随县、枣阳和宜昌一带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荡式攻击,史称两次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亦称“枣宜会战”)。
一、初战随枣,日军铩羽而归
在放弃武汉之后,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以武汉西北方向的大洪山、桐柏山为依托,扼守通向川东地区之门户,并对平汉线形成持久威胁,加上在大别山区的游击部队不断袭扰日军后方,让华中的日军如鲠在喉。1939 年4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了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共1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装备火炮200余门、坦克装甲车100余辆。其意图:沿襄(阳)至花(园)和京(山)至钟(祥)公路并肩西进,形成中央突破,直扑第五战区防守的核心区域,先夺占随县、枣阳,再转向襄阳、樊城、南阳一带,围歼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
自台儿庄战役以来,第五战区各支部队经一年多的血战,兵力消耗巨大,虽有几个集团军的编制,但普遍只有满编时的一半,总兵力不过10余万人。更为严重的是,部队在撤退过程中,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火炮等重武器损失、遗弃殆尽,甚至川军某部两个团的“重火器”只剩下4挺老旧的马克沁重机枪,缺乏对抗日军坦克的武器装备。
不过,第五战区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和主攻方向早有察觉,并事先做出部署:第八十四和六十八军防守日军正面进攻的随县—枣阳一线,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防守大洪山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北麓的南阳、唐河到桐柏一线。长江沿岸的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部(不归第五战区统率)负责。为弥补第五战区兵力的不足,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5个师从江南北调增援,于4月中旬在桐柏山南麓一带展开,伺机攻击日军侧后。
4月30日,日军沿襄花公路向西发起攻击。沿途地势平坦,便于日军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设防的中国军队只能凭借勇气,以血肉之躯与日军坦克搏杀,有士兵甚至攀上坦克,向坦克内投掷手榴弹。在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之下,日军进攻十余日,被牵制在随县一带。5 月5日起,日军改向中国军队两翼发起突击,左翼以骑兵部队沿襄河攻击,并于5月8日占领枣阳;右翼自信阳向西,攻陷桐柏、唐河;左右两翼会师枣阳,对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形成包围。
为应对危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从豫西向南突击日军侧后,5月11日收复新野,对日军形成反包围的态势。5月15日,中国军队在全线发起反击,日军开始撤退,主动放弃了枣阳,退守随县。由于缺乏攻坚武器,中国军队不得不在随县之外与日军对峙。
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毫无战果,还损失了数千兵力,被迫退回进攻出发线。
二、再战枣阳,张自忠英勇殉国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军队利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之际,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多个方向上发动了“冬季攻势”,皆有斩获,让日军遭受不小的损失。特别是在广西南宁的昆仑关,赢得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攻的胜利。
日军认为,中国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抗战意志和一定的战斗力,必须“给予更大打击来解决中国问题”。
1940年2月,日军第十一军即开始制定会战指导纲要,企图从5月上旬发起攻势,作战目标指向宜昌。日军认为,进攻宜昌不仅可给包围武汉地区的第五战区部队以沉重打击,又可夺占进入四川的门户,对中国的“陪都”重庆构成直接威胁,进而对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日军第十一军除留下少量守备部队外,集结了7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并得到从第十五、二十二师团抽调来的2个支队以及海空力量的加强,总兵力约20万人、坦克200余辆。这是武汉会战后,日军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
接替冈村宁次担任司令的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为两步:先歼灭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再渡襄河攻击宜昌。在作战方案上,日军摒弃了第一次随枣会战中简单直接的中央突破战法,决定先由北、南两翼分别沿信阳—唐河一线和汉水东岸向枣阳地区攻击,待突破第五战区防御体系、切断向北退却的交通线、形成包围时,再从中路进攻枣阳,围歼第五战区的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为迷惑中国军队,还命令长江南岸各部在第十一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向各自正面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对外则宣传日军此次进攻的目的与前次随枣会战相同,扫荡过后即撤回。为此,日军还制造了一份假命令以迷惑中方情报机构。
日军的隐真示假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然早在3月就得到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情报,但一直判断日军进攻的目的只是“寻歼中国军队主力”,而没有对宜昌方向的防御做特别部署。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起进攻,在突破第五战区第一线阵地后,以每天30~40公里的速度突进。5月7日,日军第三、第十三和第三十九师团分别抵达唐河、王集、随阳店,从北、南、中三个方向对枣阳形成合围。日军虽然攻势凌厉,但各支部队间隙过大,并未实现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不仅如此,中国军队在跳出日军包围之后,开始积极部署反击。第三十一集团军从南阳地区南下,5月12日,将日军第三师团包围于樊城附近。第三师团所携粮弹消耗所剩无几,又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分割,在第十一战车团的支援下才突围而出,伤亡惨重。
南线的反击由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实施。其部署是:由集团军主力东渡汉水,在枣阳以南截击日军第十三师团。为了抢夺战机,张自忠亲率第七十四师、骑兵第九师和总部特务营抢先渡河,在方家集一带截断日军退路。然而,由于能够投入的兵力过于薄弱,虽然达到战役目的,却形成孤军深入的不利态势。
张自忠将军在渡河前给集团军副司令冯治安的信中说:“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日军通过无线电侦察,截获了中国军队的电报,掌握了中方部署,遂集中第十三、三十九师团的兵力发起反击;同时,日军情报部门通过电台呼号和电波方向测知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电台位置,进而获悉了张自忠所在地点,随即调集5000多人的兵力向该地区发起猛攻。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5月16日,在与突入阵地日军的作战中,张自忠将军死战不退,终“身受七伤,腹为穿”,以身殉国。当夜,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奋力抢回张自忠的遗体。随后,张自忠将军灵柩被运往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有10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3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军民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日军对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反击得手后,乘势北上,跟踪追击。5月21日夜,日军在偷渡白河时遭遇猛烈射击,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300多人毙命,第十一军随后下令停止追击。枣阳一带的作战随即结束。
三、宜昌失守,长期相持
日军未实现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目的,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已疲惫不堪。面对进退维谷之战局,日军指挥官认为,如果此时放弃进攻宜昌的任务,就意味着此前作战遭到失败,将影响该军统帅的权威和天皇对该军的信任,遂决定继续向汉水以西的宜昌发起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前期判断失误,宜昌方向兵力大多被抽调到枣阳一带,设防极为空虚,摩托化行进的日军得以乘虚而入。5月31日发起进攻,6月3日即突破中国军队防御,占领宜城。6月10日,日军抵达宜昌外围,在近百架飞机的支援下,以3个师团兵力猛攻宜昌城,并多次施放毒气。6月12日,中国守军撤往山区,日军开始长据宜昌,并从黑龙江抽调关东军第四师团协助第三师团防守宜昌、安陆一带。自此,第二次随枣会战结束。
两次随枣会战期间,中国高层出现了汪精卫建立伪政府的事件,军队中也出现了一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失节者。但是,更多如张自忠一样的中国军人,以自己的热血和勇气坚定地履行守土卫国的职责,以低劣的武器装备积极主动抗击日军,使日寇虽然占领我大片土地,却不得不处处收缩、处处防守,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加入德国法西斯团伙去瓜分世界。中国军人以自己的坚毅和牺牲,不仅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也为世界人民的反抗法西斯、争取解放的正义事业赢得了更多宝贵的时间。
参考文献:
[1]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抗日名将张自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3]薛岳等.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何 荷)

中图分类号:E296.9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ISSN1002-4484(2015)06-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