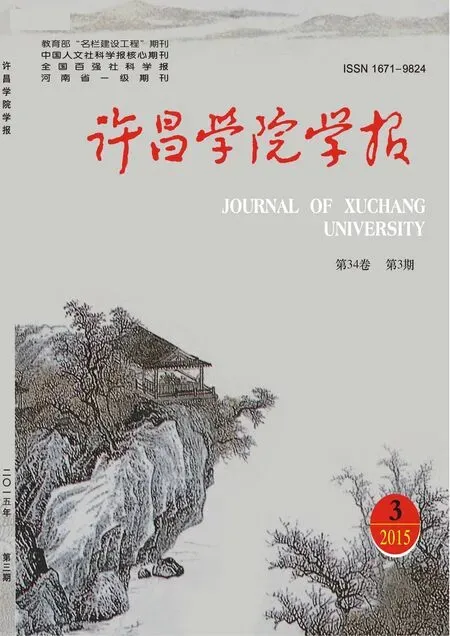丰子恺漫画的艺术特质
2015-03-01孔静
孔 静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河南 许昌 461000)
丰子恺漫画的艺术特质
孔 静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河南 许昌 461000)
丰子恺作为著名的漫画家,长久以来受到人们持续的关注。从笔法和意旨两方面入手对丰子恺漫画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特别的诗意、自然朴实美以及古典韵味等艺术特质。
丰子恺;漫画;艺术特质
丰子恺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画家、散文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其艺术生涯是从漫画创作开始的。中国现代的“漫画”这一称谓就来源于1925年他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从诞生之日起,丰子恺的漫画在当时的上海就极为流行,说其风靡一时,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毫不为过。当时上海的杂志界有所谓的“四大权威”,即《小说月报》、《语丝》、《国学周刊》和《新女性》,丰子恺的漫画在这四种刊物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丰子恺的漫画之所以能够被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丰子恺的个人特质。朱自清称他为“从头至踵,浑身都是一个艺术家”;日本的吉川幸次郎把他誉为“中国现代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对于其漫画作品,郑振铎说:我的情思却被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俞平伯说: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朱自清则称之为“带核的小诗”。丰子恺漫画的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容的微笑
对于漫画丰子恺这样说:“漫画二字只能望文生义。漫,随意也。凡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如果此言行得,我的画自可称为漫画。因为我作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1]388这段话很好地阐释了丰子恺的创作心态。漫画一词来源于日语,对译于西方的cartoon和caricature,指称的是一种“讽刺”、“幽默”的小画。在今天一般的英语词典词条解释中,cartoon是指幽默的、往往是讽刺世事的画作;而caricature主要指对对象、尤其是人物颜貌特点进行夸张表现,且具有喜剧效果的画,也可用来表示政治讽刺画。主要是嘲讽性质的“笑别人”。而在丰子恺的漫画中,这种嘲讽性质的“笑别人”我们几乎看不到。我们所体味到的就是一种随意的从容,一种悠然的微笑。
丰子恺的漫画借鉴了日本“浮世绘”的创作方法,以人生日常琐屑生活为画材,描写世态人情。在作画时,丰子恺不是一个处于高势位的“解剖者”、“看客”,他以一种不关心的、非同情的态度,捕捉一种相对的距离感。他自己也说,他喜欢观察和描绘日常生活中为人之经验和欲望遮蔽的“美”,并反复强调要与对象保持平等、亲切的关系。所以他那些最具个人特色的作品,总是会给观者带来一份从容的微笑。
比如他的《花生米不满足》,一个儿童因为自己的花生米少不满足而哭闹,这种情景在图画中由作者信笔拈来,丝毫看不出那种成年人对于哭闹孩子的反感和批评,作者所传递出来的感情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对于天真幼子的喜爱之情。我们大概可以体味出画家作画时嘴角那种玩味的笑容。还有《初步》,画面中母亲搀扶着学步的孩子,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除了孩子蹒跚学步的可爱之外,画面中年轻父母那种“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喜悦之情也表露无疑。[2]35-38
二、特别的诗意
丰子恺出生在清末,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丰子恺精通中国书法与绘画,也喜欢吟诵中国诗词与曲赋。1925年出版的《子恺漫画》中大部分都是古诗新画,可为佐证。然而丰子恺漫画中的诗味更多地是隐含于画作之内,不在画作中的诗本身。他能够用诗意的方式审美地批判和赞扬所处社会的真实场景。在世俗的、日常的景象之中,丰子恺总能挖掘出特别的“诗意”。画面既亲切生动,又不失含蓄隽永。其情趣大致可用“雅俗之间”来形容。
在《取苹果》中,一个小小的孩子,身高还没有桌子高,却想拿到桌子上的苹果。她把抽屉每一只都抽出来一点,在下面的抽出来最多,最上面的抽出来最少,这样抽屉就变成了孩子的楼梯。虽然我们在这张画中看不到孩子的脸,却能从孩子弯着腰探着头好像刚刚要迈步走上台阶的姿态看出一个可爱的儿童形象。尤其是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孩子那种“仿佛在做一件大事”的那种严肃认真,这种特别的诗意,既亲切又生动。
丰子恺在作画时总希望一张画在看看之外又可以想想,他要求自己的画兼有形象美和意义美,形象可以写生,意义却需要寻找,他的找寻原则就是,倘若看到的形象没有丰富的深刻意义,无论形状色彩何等美丽,也懒得描写;即使描写了,也不是得意之作。?曾有人指着丰子恺的漫画批评道:“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而丰子恺的回答是:“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所得的体感,我是现代人,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他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喜爱而把画画的模式化,而是处于对描画对象的热爱,亲近,深入的理解,设身处地的体验。比如《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中解决凳子“四只脚”的难题时,阿宝的果敢、大方;《瞻瞻的车》骑着两把芭蕉扇做成的脚踏车时,小儿的快意与满足;《三娘娘》中“打棉线”时那俯仰得宜、妙合自然的身姿;《挖耳朵》《剃头担》中挖耳朵、剃头小担上顾客的巍然不动和担主的悠然自得等等。[3]56
三、自然朴实之美
丰子恺的画使人有“一想之美”,意思在画外。他的画就像伸出了一根指向天空的手指,指给你看天上的月亮。而这“月亮”或是你往日的经历,或是你向往的场景,正是在每一个看画人的心中。这种“一想之美”是自然而然、油然而生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丰子恺作画时平易的写法。
丰子恺笔下的画作都是日常所见、所闻的。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现实基础:从他们所穿衣物看,男人的衣着或是长衫、马褂、瓜皮帽;或是坎肩与短裤;或是受欧美服装影响的西装、皮鞋,配上圆镜片的眼镜与拐杖;女人则是上衣、下裙和旗袍,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衣摆则有方圆与宽瘦长短的变化。他有一类画作被称作儿童漫画,主要内容是儿童天性中的“真”与儿童生活中的“趣”。这“真”与“趣”也可以延伸到丰子恺的其他画作中,构成了一种平实,一种自然,美就从此产生。
比如他的“瞻瞻”系列,在他的笔下,瞻瞻看见天上的月亮会认真地要求父母捉下来,见了已死的鸟儿会认真地喊它活转来,一只藤椅子可以认真地变成黄包车,戴上铜盆帽就认真地变成新官人,为看见爸爸被人又割脖子又捶打而痛哭失声却被众人不解而伤心等等,瞻瞻的纯洁和真诚都历历在目。[4]126比如他的“乡村大娘”系列,以丰家的“三大妈”为原型,《人造摇线机》记录了大娘们普遍的一项家庭生计:搓线纳鞋底;久雨时节,为家庭成员缝缝补补是大娘们的另一项女红,在《久雨》中,丰子恺让妻子和岳母做了正在从事这项劳作的大娘们的代表;《巷口》和《锣鼓响》中的“李大妈”与其说是丰家帮工,不如看作是许多江南乡绅家庭的帮工;像丰子恺的邻居莫五娘娘那样粗暴地对待自己孩子的大娘,被丰子恺速写在了《感同身受》中;有些大娘很有才干,被丰子恺留在《五娘娘》中。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美。这与丰子恺作画时的心态有关,丰子恺作画时,与西方人在和儿童说话的时候常常要蹲下身子的行为很相似,既不讽刺,也不幽默,令人“一想而美”。
四、俭省的笔墨
丰子恺在《我与〈新儿童〉》中说: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不知几百十次了。这体现了丰氏的为人,简单而质朴。同样的,在作画时,他自然不自然地把这种为人特质也渗透到了画作上。他的漫画像他的人一样,只是“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用笔简洁,但内涵很丰富,只能让人觉得“奇怪”却不会让人大失所望。
丰子恺早期作品中在画没有五官的人的时候喜欢在眼睛的位置上画两条平行于眼睛的横线,如《指冷玉笙寒》《明月窥人人未寝》《买粽子》《畅适》等。这种习惯是丰子恺学习速写“炭笔画”的时候留下的。但是后来这“两条横线”在他的画面里逐渐消失了。但这种没有五官的人的表情却更加生动了,给了读者无比巨大的想象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1923年的《阿宝赤膊》。这时的阿宝只有三岁,可能是刚洗完澡,腰上套了一条小裙子,赤裸着上身,阿宝歪着头,双手交叉挡在胸前,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因为害羞,阿宝的脸被省略了五官,甚至被省略了脸的轮廓。但是每一个看画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阿宝的表情。
另外丰子恺也擅于简单地通过画题表达画面的内容。比如《守得三天生意好,与尔买条小抱裙》中,一位设摊的妇女抱着赤裸下身的孩子,摊前不见一个买主;女摊主的心理活动就在画题中。其生活窘迫的形象跃然纸上。与此类似的另一幅画:一位正在喂蚕的村姑,头扎三角巾,衣衫褴褛,脑海里想象着来年春游的情景,题曰:于蚕匾中窥见明年春游的服装。一幅抱裙,一件新装,这就是终日萦绕于乡村妇女脑际的理想和追求。
这种笔墨的俭省是有意为之,丰子恺的艺术是理想中的艺术,追寻一种艺术的美。他自己对此是这样说的:“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自己想象出来。这正与平剧的表现相似:开门骑马、摇船,都没有真的门、马与船,比实际的美丽得多。”[5]358
有人曾经说丰子恺的漫画“不要脸”,其实是在说丰子恺所画的人物,往往只有一张脸的轮廓。没有五官。这样尽管不完整,但观者却能感觉到一张完整的脸。”这正符合阿恩海姆谈到格式塔心理时所提出的视知觉的基本规律,也体现了虚与实的辩证统一,虽然没有画完整,但却完成了艺术的表现,形成了艺术的美。如漫画《阿宝赤膊》中,阿宝的脸只画了轮廓和头发,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简化掉了,小阿宝只穿裙子,上身赤膊。藕节似的小手护住前胸。只是简单梳篦画出了阿宝不必要的娇羞。最有意味的不是脸而是她的手,让观者一眼就能想象出小孩阿宝娇羞的小脸。
弦外有余音,这种含而不露、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正是艺术家所追求的。比如《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画面简洁生动,但是简洁中却不简单,阿宝衣服上装饰性的线条,在纯黑的头发与只有轮廓线的阿宝的裤子和袜子之间,起到了呼应和连接的作用。丰子恺完全领会了孩子的心思,他用最简化最准确的绘画技巧把孩子的世界再现了出来。
五、书法与画法相得益彰
丰子恺最初的小画以毛笔线条勾勒而成。这也可以说是子恺漫画与西方、日本近代漫画,以及中国近、当代绝大多数漫画创作最直观的区别。后者多以炭笔、钢笔而成。表面看来,这只是用具上的差别,但对于绘画这种造型艺术而言,这种差别却可能是关乎根本的。在《我的画具》一文中,他讲述了自己在绘画工具方面的“挑剔”。反复比对,他发现最好用的,还是“平常写字用的毛笔和纸”。[6]38这一方面是因为,漫画创作对于丰子恺而言,主要还是一种率意而为的、非专业性的活动。而毛笔“伸手可及”,兴到便能下笔。用它作画不仅不可修改,甚至不可犹豫,挥洒由心,落纸即成,“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丰子恺本来就是在用写字的笔法作画。丰子恺自幼便苦习书法,后来更是得到李叔同、马一浮等大家的指点,其书“出于北魏,涉及隶草,遒密劲拔,质朴奇拙”,在当时颇负盛名,只是后来为其画名所隐。很多见过其书、画的人,都发现其画中笔法与书无以异也。所以丰子恺每当在绘画方面有所窒碍时,便开始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发见画就有长进”。
除此之外,在丰子恺的画作中,有大量传统的风俗场景。丰陈宝对此就有专门回忆:“现在我还可历历地回忆:玩具,花纸,吹大糖担,新年里的龙灯,迎会,戏法,戏文,以及难得见到的花灯……曾经给我的视觉以何等的慰藉,给我的心情以何等热烈的兴奋。”[1]340比如《贫女如花只镜知》中画面右侧从上面挂下来一根绳子,绳子下端的钩子上挂着一只篮子。这种篮子叫做“饿杀猫篮”,是一种竹子编成,四周有孔的竹篮。食物放在竹篮里,挂在从梁上顺下来的钩子上。这样既能保鲜食物,猫儿又吃不到,所以叫“饿杀猫篮”。这种画作中的传统物品也增加了其趣味性。
总之,丰子恺的漫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它如一坛好酒一般,愈久弥香,在欣赏之余带给人更多的艺术享受。
[1] 丰陈宝等. 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2] 丰子恺. 丰子恺儿童漫画选[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3] 丰子恺. 护生画集[M].北京:龙门书局,2009.
[4] 丰子恺. 华瞻的日记[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5] 丰子恺. 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6] 丰子恺. 丰子恺的漫画人生(精选)[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4-10-16
孔静(1979—),女,河南许昌人,讲师,研究方向:动漫艺术。
J205
A
1671-9824(2015)03-00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