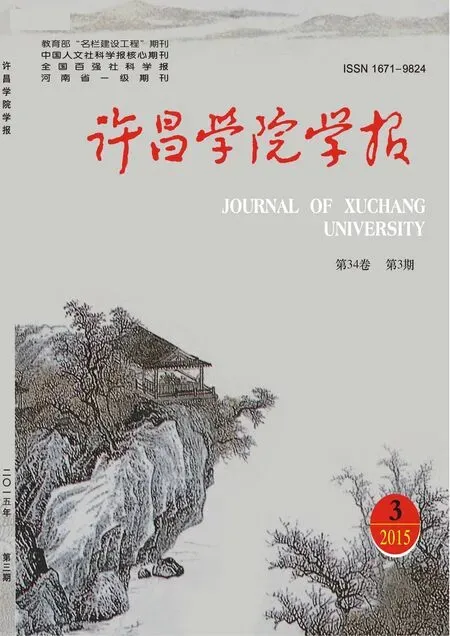乱世人生中的忙里偷闲
——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2015-03-01王哲谦
王 哲 谦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乱世人生中的忙里偷闲
——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王 哲 谦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于质朴平凡的生活中取材,以平和的心境品味世界和人生,潜心营造闲适幽默的境界,表现了作者欣赏人生的超然态度。《雅舍小品》写于抗战时期,其创作也可以说是他在乱世人生中的忙里偷闲。
梁实秋;雅舍小品;超然态度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于1940年至1943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期间,作者因避战火而到了四川的北碚,借居在一所十分简陋的房子里,梁实秋给它取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雅舍”。后来,他应邀在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写专栏,以《雅舍小品》为栏目,以笔名子佳发表。处于大动荡时代的梁实秋,虽说也关注时势,有一定的爱国情怀,但由于个人自由主义思想,他力图超然独立,寻求心境的平和豁达,不想过多介入现实纷争。在《雅舍小品》中,他回避时行题材,专注于日常人生的体察与玩味,着眼于人性的透视和精神的愉悦,潜心营造闲适幽默的境界。试图通过琐碎平凡的小素材、小情调、小理趣以达到自我的怡情悦性,可以算作是梁实秋在乱世人生的忙里偷闲。
一、从质朴平凡的生活中取材,折射出智慧的哲思
梁实秋主张散文应该“崇真实,尚个性,贵简单”[1]194, 《雅舍小品》常取材于平凡而细小的生活,在生活细微处去发现人生的智慧。在男女老少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中,梁实秋回避重大题材和现实热点问题,力图将文学与政治分开,专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寄托情感和趣味,寻求悠然闲适的小理趣。
送行是人生中常见的事情,作者在观察中看到,中国人的送行多与吃相连。他在《送行》中写到:
送行既是人生中所不可少的一桩事,送行的技术也便不可不注意到。如果送行只限于到车站码头报到,握手而别,那么问题就简单,但是我们中国的一切礼节都把“吃”列为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一个朋友远别,生怕他饿着走,饯行是不可少的,恨不得把若干天的营养都一次囤积在他肚里。我想任何人都有这种经验,如有远行而消息外露(多半还是自己宣扬),他有理由期望着饯行的帖子纷至沓来,短期间家里可以不必开伙。还有些思虑更周到的人,把食物携在手上,亲自送到车上船上,好像是你在半路上会要挨饿的样子。
请客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作者看到了请客不只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其实也有很多无奈。在《请客》中作者这样写:
常听人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请客只有一天不得安,为害不算太大,所以人人都觉得不妨偶一为之。
作者历数了请客吃饭的种种麻烦与顾虑:要请一次客,请客的人选,待客的菜肴,宴席的喧闹,酒足饭饱后的高谈阔论,而后主人疲乏无比还要收拾杯盘狼籍。
睡眠是每天都会进行的,对于睡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梁实秋在《睡》一文中先描写了睡眠的一般现象:
都是说心里本来平安,睡时也自然塌实。劳苦分子,生活简单,日入而息,日出而作,不容易失眠。听说有许多治疗失眠的偏方,或教人计算数目字,或教人想象中描绘人体轮廓,其用意无非是要人收敛他的颠倒妄想,忘怀一切,但不知有多少实效。愈失眠愈焦急,愈焦急愈失眠,恶性循环,只好瞪着大眼睛,不觉东方之既白。
结尾又从中看到了睡眠的另一种作用:
睡也可以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在这个世界活得不耐烦而又不肯自行退休的人,大可以掉头而去,高枕而眠,或竟曲肱而枕,眼前一黑,看不惯的事和看不入眼的人都可以暂时撇在一边,像驼鸟一般,眼不见为净。
梁实秋写作《雅舍小品》何尝不是一种战乱时期的一种睡眠呢?
理发也是人生常有的,对于理发,小孩子特别害怕,而对于大人也有很多的不适应。他在《理发》中写理发时的感受:
椅子前面竖起的一面大镜子是颇有道理的,倒不是为了可以显影自怜,其妙在可以知道理发匠是在怎样收拾你的脑袋,人对于自己的脑袋没有不关心的。戴眼镜的朋友摘下眼镜,一片模糊,所见亦属有限。尤其是在刀剪晃动之际,呆坐如僵尸,轻易不敢动弹,对于左右坐着的邻坐无从瞻仰,是一憾事。左边客人在挺着身子刮脸,声如割草,你以为必是一个大汉,其实未必然,也许是个女客;右边客人在喷香水擦雪花,你以为必是佳丽,其实亦未必然,也许是个男子。
人生中由于太过看重自己的私利,往往就错过了很多的风景。理发时担心自己的脑袋,所以不敢也不能看到周围的情景。
《雅舍小品》从日常生活入手,从洗澡、理发、下棋等生活琐事中发幽探微,点出其中的闪光点,让读者在人人都有的生活小事中引起心理的共鸣,悟出人生的小道理。
二、于人生百态和社会世相中,呈现普遍的人性人情
由于在美国学习的经历,梁实秋深受他的老师白壁德的影响,倾向于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应当描写永久的人性,表现不变的人情,反对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人、看待人的生活。为此他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应该说在当时的语境中,梁实秋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平和的时代语境中去读《雅舍小品》,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们看《女人》、《男人》、《握手》、《衣裳》、《信》等文章,便可发现《雅舍小品》多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百态信手拈来的现象,这些人们熟悉的种种现象,在梁实秋的笔下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
关于女人,梁实秋在《女人》一文让人看到梁实秋观察的细致。先是说女人的说谎:
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艳羡汽车的女人常常表示她最厌恶汽油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适。一个女人馈赠别人,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总之,女人总欢喜拐弯抹角的,放一个小小的烟幕,无伤大雅,颇占体面。
接着说女人善变:
女人不仅在决断上善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三张沙发,能摆出若干阵势;几根头发,能梳出无数花头。讲到服装,其变化之多,常达到荒谬的程度。
再说女人的哭与笑:
一旦精神上再受刺激,便忍无可忍,一腔悲怨天然的化做一把把的鼻涕眼泪,从“安全瓣”中汩汩而出,腾出空虚的心房,再来接受更多的委曲。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驻在女人脸上的,这笑脸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护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了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淌眼泪,以至于翻斤斗!哀与乐都像是常川有备,一触即发。
另外,还有女人的啰嗦、女人的胆小等,梁实秋的描写都能够让人不断地点头称是,不说不明白,一说句句在理。梁实秋对女人的了解和分析似乎让我们看透了女人的一切,但我们不能绝对的看问题,只能说梁实秋看到了一般女人的一般特点,对于不同的女人不同时期其实还应该有着不同的特点。
梁实秋在《男人》中,对男人的种种丑态进行了细致的描摹。他这样写男人的脏:
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土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黏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
这样的男人其实并非少数,读者往往也会联想到自己,说明梁实秋的观察是真实的。
男人不仅脏而且懒,尤其多半自私:
2.2.2 护理质量关键要素控制 第一,患者安全质量控制,护理管理者聚焦重点科室、重点环节,对频发事件分类先提出控制策略,如高危患者的安全控制,对每位患者入院时压疮、跌倒、导管滑脱等高危因素进行筛选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降低风险。另外建立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设立护理安全质控员,实时采集患者不安全因素,构建患者安全管理屏障。第二,患者服务质量控制,根据患者需求及护理工作专业的要求,制定护理服务流程和护理服务评价标准,随时了解患者对护理工作的建议,掌握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结果,研究护理服务失效补救系统,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观中有一基本认识,即宇宙一切均是为了他的舒适而安排下来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向人奴膝婢颜外,他总是要做出一副老爷相。他的家便是他的国度,他在家里称王。……他不高兴时,他看着谁都不顺眼,在外面受了闷气,回到家里来加倍的发作。他不知道女人的苦处。女人对于他的殷懃委曲,在他看来,就如同犬守户鸡司晨一样的稀松平常,都是自然现象。
梁实秋对男人丑态的描写,很明显是对男性世界的批判,这一点表现了梁实秋有反男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比较进步的。对男人丑态的描写也是对男人劣根性的挖掘。虽然梁实秋没有从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进行更深入的解剖,但也可以看到梁实秋对人性认识的深度。
梁实秋对孩子的观察也是比较细致的,他在《孩子》中描写一个顽皮的孩子:
一个母亲带孩子到百货商店。经过玩具部,看见一匹木马,孩子一跃而上,前摇后摆,踌躇满志,再也不肯下来。那木马不是为出售的,是商店的陈设。店员们叫孩子下来,孩子不听;母亲叫他下来,加倍不听;母亲说带他吃冰淇淋去,依然不听;买朱古律糖去,格外不听。任凭许下什么愿,总是还你一个不听;当时演成僵局,顿成胶着状态。
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也确实让人可气。梁实秋逼真的描写之后,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孩子中之比较最蠢,最懒,最刁,最泼,最丑,最弱,最不讨人欢喜的,往往最得父母的钟爱。”梁实秋告诫人们,虽然新的时代要求人们解放孩子,但还需要严格的管教。解放不等于放任。此外,梁实秋还在《握手》中通过握手的方式来揭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势利;在《信》里,他看到了“信里面的称呼最足以见人情世态”;在《衣裳》中提出了女装的自由与多样是一个社会开明民主的反映等。梁实秋尽可能在对生活中某一事物某一特点的描绘中去寻找普遍的人性。
梁实秋说:“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因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各个时代的深度的优秀作品永远有知音欣赏。”[1]202梁实秋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也说出了文学带给人类的永恒的价值。
三、在闲适幽默的审美追求中,寓含旷达的人生态度
梁实秋殷实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生活上少了鲁迅因家庭败落而带来的生活困顿,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人性的恶,西方贵族文化的熏陶,使他总是超然在人间苦之上。回到故国的梁实秋,面对兵荒马乱和一时的生活困境,也没有让他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他总是以绅士的姿态俯瞰人生。“既充分享受物质生活又不过分沉迷;既追求高贵的生活品味,又认同凡俗的人生,寓雅于俗。在这种人格理想指引之下,梁实秋形成了既认真执着于人生又洒脱豁达于人生之外的性格。”[2]2走进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读者在轻松与闲适的描述中,能够真切体会到作者谐趣横生、风雅幽默的美学风格。请看开首的描写: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
人生最怕年老,年老总有很多不便。梁实秋在《老年》中先是说到老年的特征:
老的征象还多的是。还没有喝忘川水,就先善忘。文字过目不旋踵就飞到九霄云外,再翻寻有如海底捞针。老友几年不见,觌面说不出他的姓名,只觉得他好生面熟。要办事超过三件以上,需要结绳,又怕忘了哪一个结代表哪一桩事,如果笔之于书,又可能忘记备忘录放在何处。大概是脑髓用得太久,难免漫漶,印象当然模糊。目视茫茫,眼镜整天价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两耳聋聩,无以与乎钟敲之声,倒也罢了,最难堪是人家说东你说西。齿牙动摇,咀嚼的时候像反刍,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戴围嘴。至于登高腿软,久坐腰酸,睡一夜浑身关节滞涩,而且睁着大眼睛等天亮,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但梁实秋却未并去悲叹老年的无用,而是用一种超然的心情说到:
老不必叹,更不必讳。花有开有谢,树有荣有枯。
他反对有些人怕老的做法:
有人讳言老,算起岁数来斤斤计较按外国算法还是按中国算法,好像从中可以讨到一年便宜。更有人老不歇心,怕以皤皤华首见人,偏要染成黑头。半老徐娘,驻颜无术,乃乞灵于整容郎中化妆师,隆鼻隼,抽脂肪,扫青黛眉,眼睚涂成两个黑窟窿。物老为妖,人老成精。人老也就罢了,何苦成精?
他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待年老的超然心态:
人生如游山。年轻的男男女女携着手儿陟彼高冈,沿途有无限的赏心乐事,兴会淋漓,也可能遇到一些挫沮,歧路彷徨,不过等到日云暮矣,互相扶持着走下山冈,却正别有一番情趣。
对待人生的发展应该是顺其自然,有这种超然的心态自然让人赞赏,但梁实秋当时还不是很老,真的到了他老年的时候,其实他也未必都能够做到他所说的,这可能不是局中人的原因吧。
在《雅舍小品》中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千世界的人生百态图,他总是用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审视社会世相,社会百态,又以一种幽默,闲适的心态冷静的审视玩味平常事,并不指手画脚,但总能搔到生活的痒处,寓庄于谐,娓娓道来。他的幽默虽也有讽刺的成分,但又透露出温和善意,还能使读者获得丰富的启迪。虽然不能激发当时民众抗战的激情,却也给苦难的人们偷得半日乐趣。
梁实秋在《雅舍(代序)》中对雅舍的描写很让人回味: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读着这样的文字,仿佛置身于雅舍之中,感受着雅舍不同时间、不同氛围中的情调,品味雅舍带给人的浓浓的情意,那样惬意、那样自由、那样充满诗意。如生活在世外桃源,给人无穷的遐想。生活在战乱时期的人们,饱受生活的多种磨难,能够找到一个让心灵暂时得到歇息的地方是多么难得啊。特别是当苦难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梁实秋的“雅舍”确实可以算作暂得栖肩之所。
[1] 梁实秋.偏见集[M].台湾:台正中出版社,1984.
[2] 刘勇等.安放人生的雅舍[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4-09-28
王哲谦(1990—),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I207
A
1671-9824(2015)03-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