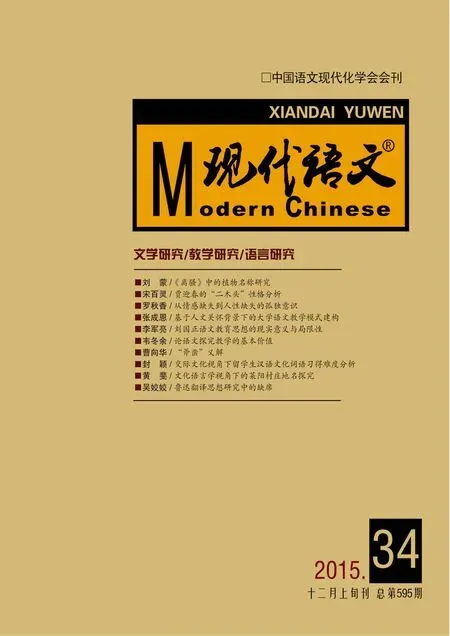由《忆菊》初探闻一多诗歌创作的潜质
2015-02-28○白玉
○白 玉
由《忆菊》初探闻一多诗歌创作的潜质
○白玉
摘要:《忆菊》一诗是闻一多的早期诗歌代表作,写于1922年重阳节前一天,当时作者正求学于遥远的美国。作者在描绘菊花的各类形态时,表现出非凡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论者以此为起点,探究这首诗的艺术品质,这些品质影响了闻一多后来的诗论及诗歌创作。
关键词:闻一多《忆菊》创作潜质
《忆菊》一诗是闻一多的早期诗歌代表作,写于1922年重阳节前一天,当时作者正在遥远的美国求学。正值传统重阳节,他远眺祖国写下了这首《忆菊》。那时他刚接触白话诗歌,刚开始对诗歌创作进行思考。提及此诗,难免要提及这首诗的种种艺术长处,然而这只是其中要义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此为起点,探究这首诗的艺术品质,因为这些品质影响了闻一多后来的诗论及其诗歌创作。
一、完成“诗画同质”说的传承
闻一多诗歌理论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诗的格律》中,其中讲到诗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而这首《忆菊》作为他的早期诗歌代表作品,还没有充分体现他的“三美”理论,只充分体现了“绘画美”。在古诗理论中,“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的“诗画同质”说提出时间很早,指诗与画在本质上相通,只是表现手段、表达技巧不同而已,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表达倾向、共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精神。诗画同源理论在新诗最初的实践中并没有过多涉及,闻一多是明确提及此理论的第一人。1926年5月13日闻一多于《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发表了《诗的格律》,这是诗人经过长期实践,思索新诗诗学缺失,根据新诗创作现实而提出的论断,目的在于纠正诗歌创作时弊,也在于指引当时诗歌创作的艺术趋向。当然这一诗论的形成需要加以逐步推断,闻一多早在评论郭沫若的诗歌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要关注地方色彩和东方神韵,“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1]闻一多以一种世界性的思维,暗示中国要想建设具有世界意义的诗学,必须要融和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色彩,而具有中国传统性的命题之一“诗画同质”便在主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思考这一问题是有自身优势的,闻一多本人便是学美术出身,对事物的颜色、外形、情态格外敏感,加上某一时刻特有的感怀心绪而完成此诗,正如朱光潜在《诗论》中论述:“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从此出。”[2](P102)由此得出,诗人在创作此诗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饱和的情趣,并通过饱和的意象来完成诗画合一的境界,完成现代诗学在诗画同源这一根基上对古典诗学的继承。
用文字进行描绘是完成诗画同源这一传统创作技巧的最重要的方法,闻一多在《忆菊》这首诗里便借助能够表现形色的语言体现诗中的画面感,通过语言特有的意义,间接作用于人的思维,依靠想象完成构图。比如作者要描绘静态菊花的形象,就要依靠绘画的手段,绘画重在表现事物的外在形状和色彩,尤其是在写实的画中,通过能够表达形状和色彩的文字完成对实物的描绘,通过人的视觉这一感官调动平时的观赏体验,作用于人的大脑,调动想象空间,完成完美画面感的呈现。为了使画面具有反复推敲的立体感,作者再次借助自己独特的诗人兼美术家的双重身份,把菊花存在于空间中的形色和存在于时间中相承续的动作符号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呈现出菊花不同时段的开放姿态,具有动作的延续性,展现出菊花依次开放的状态,化静为动。这既暗示了菊花在空间中的绵延,也暗示了一种情绪的延续,但绝不是呈现一种抵达顶端的状态,如果抵达顶端,那便是一种极致,定然会阻断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便不能在获得最初印象之外再前进一步了,也便削弱甚至丧失了诗的激发功能。
二、对传统诗歌表现方式的变异
闻一多《忆菊》一诗有与传统诗歌精神一脉相承之处,除上述论证的“诗画同质”之外,还有古韵,古色古香、古典古雅、古意古蕴古趣,这是对古代文人之士的重要的审美习惯、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的继承,代表的是中华诗歌的一种难以消磨的文化痕迹。但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的格律诗咏赞菊花,已经很难超越,因为古诗千万遍地吟咏过菊花开放的气象和境界,新诗诗人们如果再在旧有的形式和题材中挖掘,很难再挖掘出让人兴奋的东西了。另外,古诗的精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很难再前进一步的境地,闻一多选择了菊花这个古老的传统的审美意象作为抒情的对象,可以说是对传统精神的承继,但是要想有独创风格,一定要重新定位一种新的样式,也就是说,给古老的菊花穿上时髦的新的外衣。于是作者呼应着新诗的涌动,采用白话诗的形式描摹菊花的现代样式和传统诗趣精神,由此也可看出闻一多身上一种难得的品质——善于求新变异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也是闻一多所呼唤的20世纪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也可以看出闻一多具有敏锐地处理古老与现代的承继改革的能力,这种能力便是闻一多提及的对中西艺术创作技巧的借鉴能力,“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么,里边可以有李白,有杜甫,有陶渊明,有苏东坡,有歌德,有济慈,有莎士比亚;……”[3]因为有了这些最基本的对诗歌表现方式的认知,闻一多便采用了融合的方式书写《忆菊》,像是散文诗,但是却用了分行的形式;又像是俗歌,但没有押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候的闻一多写诗时走的是“欧化”的路子,完全不同于旧诗中所使用的语词、表达方式、意蕴气度。作者很好地运用了一个美术家的眼睛进行了绵密的观察,然后采用文学家的笔墨和表现方式从容地书写每一朵或每一簇菊花的姿态,又用了象征的手法表达作者远怀祖国的情绪,这种诗歌的包孕能力是古典诗歌所不具备的。尽管现代的读者看《忆菊》会发现一些缺陷,比如散文性太强,比如没有适度的格律,比如缺少诗歌应有的品质,等等,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否定这首诗的理由,因为它是闻一多最初的实践,有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
三、结语
作者写这首《忆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菊花”这一文学形象唤起对祖国文化的倾慕和赞赏,是为了让读者在欣赏“菊花”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引申到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叹服之中,是通过对“菊花”如数家珍似的细致描绘来表现对祖国的深切思恋之情。层层叠叠的铺叙,最后的落脚点便是两个大字,那就是——祖国!这是闻一多爱国情怀的体现,而爱国之情始终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在以后的诗歌写作当中爱国情怀是其不灭的情怀,永远年轻绚烂,也永远感动着千万后来人,作者景仰的英雄便是拜伦式的民族英雄,他在后来的诗论中也反复提及爱国情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比如他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爱国精神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4]闻一多不仅直接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而且还在思索着如何表现这种爱国之情,让诗歌中的言语不至于落入空处,一个切实可行亟需实践的办法是把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结合起来,如果它们分道扬镳,爱国运动的收效不会很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会极为有限,切切之情在这些言语之中得以充分表现,这也是我们在很多年以后还能仰视这位诗人、诗论家、民主战士的一个重要缘由。
注释:
[1]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第5号。[2]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闻一多:《诗与批评》,火之源文艺丛刊,1944年,第2、3辑合刊。
[4]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第1号。
(白玉延安大学文学院7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