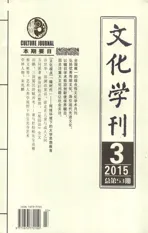三国蜀汉辞赋再考
——兼与杜松柏先生商榷
2015-02-27田鹏
田 鹏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三国蜀汉辞赋再考
——兼与杜松柏先生商榷
田 鹏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蜀汉辞赋和类赋之文内容的贫乏和数量的凋零反映了蜀汉人才选拔标准以及其他政治因素对蜀汉文学的影响。前人的研究存在诸多盲点和偏差。蜀汉辞赋不兴的根源在于蜀汉政权偏重军事政治方面的人才,不以文学为能,且对有辞赋创作传统的巴蜀文人实施了一定政治压迫,最终导致蜀汉辞赋在创作动机上的衰微。
蜀汉;辞赋;类赋之文
一、蜀汉辞赋的研究现状
辞赋是现存蜀汉文学作品中所占比重较小的文体,学界对于三国时期蜀汉辞赋的研究较少,相关的论文有杜松柏先生的《三国蜀汉辞赋考论》和两篇研究蜀汉文学的硕士论文:朱贤高的《三国蜀汉文学研究》和戴智恒的《三国蜀汉文学研究》。在蜀汉辞赋数量的统计标准和结果的问题上,以上两篇硕士论文完全采用了杜松柏先生的观点。
钟思远在《论蜀汉归晋后的士情与文情》一文提出了异议:“考《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籍所存目,蜀汉诗赋类作品亦为数不稀,只是声名广播者不多”,至于作品失传的原因,钟思远将之归结于“(蜀汉归晋时)正值巴蜀学统文脉代谢承替之际,却被迫中断于国丧士徙之间”。实际历史情况和钟思远所述恰恰与之相反:蜀汉归晋时不仅有谯周、郤正健在,而且陈寿、李宓、王崇等蜀地文人都得到了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政治地位相比蜀汉政权时得到了一定提高,却仍然没有更多的辞赋创作,其中另有隐情,而且钟思远言及的“诗赋”并不完全指的是文学体裁,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将“名文名论”和“书信或疏奏,笔墨也不乏出彩之处”归为“诗赋”的能力,并没有明确分析辞赋的创作状况及其原因。
邓超的《吴蜀辞赋观念述论》将吴蜀辞赋一并研究,以吴国辞赋为主,对蜀汉辞赋一笔带过,也有可供研究的材料太少的缘故。程章灿先生著《魏晋南北朝赋史》中将“吴蜀赋”合并研究,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将吴赋作为研究重点,对于蜀汉辞赋重视程度不够。其他涉及蜀汉文学的专著还有傅德岷的《巴蜀散文史稿》、谭兴国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李大明的《巴蜀文学与文化研究》和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这些对于巴蜀文学的通论在论及三国巴蜀文学的时候,只提及了秦宓、谯周、郤正、李宓等人,缺乏对政治和文学立体关系的解读。
二、蜀汉辞赋数量问题再考
对于蜀汉辞赋数量的问题,学界目前有两种结论,对于“辞赋”这一文体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标准:
其一是上文提到过的程章灿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对于“辞赋”这一文体的要求很严格,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蜀汉作家作品中只有三篇列席:[1]

作家 篇名 出处文立 蜀都赋 《文选》卷四《蜀都赋》注 《三国志·谯周传》裴注引《华阳国志》谓“文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郤正 释讥 《三国志·郤正传》 按本传,此文效崔骃《达旨》,是对问体,又所著诗论赋之属垂百篇。陈术 释问 《三国志·李譔传》 按本传,《释问》七篇,当是对问体,如七体八段称为八首,今姑附此。
实际上,除了郤正的《释讥》尚完整保存下来,文立的《蜀都赋》仅存残句,陈术的《释问》已亡佚。
程章灿先生的统计和他对这一段文学的评价是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他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讲论“吴蜀赋”,并将这一章命名为《倾斜天平的这一端:吴蜀赋》。他转引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至于东吴、蜀汉,以地理父系,文风不过曹魏远甚。其以经术擅长者有之(如虞翻、陆绩),以著述见称者有之(如韦昭、薛综),以政事见长者亦有之(如诸葛亮),独以诗赋名家者则未之或觐也。”这是对蜀汉文学的客观描述,却建立在对吴国辞赋的倾斜之上,只收录三篇蜀汉赋的统计标准有失偏颇。
其二是杜松柏的《三国蜀汉辞赋考论》作出的统计,他将蜀汉辞赋分为两类:
1.辞赋
(1)存全文
秦宓《与张温对问》、费祎《啁吴群臣》、杨戏《季汉辅臣赞》、郤正《释讥》、谯周《仇国论》。
(2)存残句
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
(3)存目
陈术《释问》七篇、费祎《麦赋》、李赐《玄鸟赋》。
2.类赋之文
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秦宓《答王商书》、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李密《陈情表》。
以上十一人十三篇。[2]
杜松柏先生的统计的材料更为丰富,他的观点也被更广泛的接受了。上文提及的两篇硕士论文都采用了杜先生的观点。但是,杜先生所分的存全文的蜀汉辞赋数量过多,标准放的过宽,其中有秦宓的《与张温对问》不具有一般赋体的特征,因此不应录入。
《与张温对问》是发生在吴蜀两国外交场合的一次辩论性质的对答,核心在于讨论两国孰为正统的问题:
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於西。”[3]
这段对话与两汉辞赋中“主客问答”的叙述传统在形式上很相似,但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政治场合实际发生的口头辩论,后者是文学家在作品中虚拟成的文学套路;前者是两人唇枪舌剑、暗藏机锋的外交对峙,后者是制造氛围,用以铺陈排比的写作形式;更重要的是,秦宓与张温对问的这段话并不具有“辞赋”这一文体所要求的文采和韵律美,大量的引用其他作品,上下句参差不齐,缺乏逻辑联系。这一段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辞赋。
在《三国志·秦宓传》中有另外两段秦宓与客的对答,其一为《报李权》[4]:
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其二为:
“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5]
这两段文字文采斐然,和同时期的作品一样具有赋化特征,而且论及了政治上的王道与霸道、文学中的文与道的关系,与同时期魏国曹丕《典论》“诗赋欲丽”的观点相映成趣。秦宓的这两段话和他的《答王商书》一样都能代表三国蜀汉辞赋的发展水平,应当归入“类赋之文”这一类。沧海遗珠,不知为何杜松柏先生没有将之收录。
这些作品在篇幅和功用上和东汉的抒情小赋一脉相承,相比之下费祎《啁吴群臣》更加短小精悍,只有区区十六个字:“凤皇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6]如果这也勉强算作是辞赋的话,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短的辞赋了。不过综上所述,已经能看出前人的对三国蜀汉辞赋的统计研究上存在文体定义标准不一问题。
杜松柏先生在《三国蜀汉辞赋考论》一文中又考证了四十三位蜀汉作家,因为“以上诸人著作篇数都在数十以上”,因此论证“他们在蜀汉辞赋数目当不止一篇。”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以四十三人平均每人可能作数篇计,即西晋初年蜀汉辞赋总共篇目当在百篇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较为可观了。”杜先生在文中也总结到“统治者对蜀汉辞赋的态度、政策”、“入晋后蜀人身世沉沦与作品流传”等等主客观原因,但是忽视了对辞赋发展起决定性原因的是蜀汉的人才选拔标准和政治原因。
杜先生观点成立的基础是:每位蜀汉作家都曾创作过数篇作品,而实际上,辞赋这种文体在蜀汉政权统治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极其衰微,正史所载的人物不可能创作如此可观的辞赋数量。
三、蜀汉辞赋数量稀少的缘由
蜀地在汉代就有辞赋创作的文学传统,西汉四大赋家四有其三——司马相如、王褒、杨雄。《汉书·地理志》对巴蜀文学的这一黄金时期形容为:“文章冠天下。”晋人常璩评价这一段时期:“汉征八士,蜀出其四。”[7]“汉具四义,蜀选其二。”[8]但是到了三国蜀汉时期,辞赋这一文体一度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写作的作家和传世的作品寥寥可数。
关于三国时期蜀汉辞赋不兴的问题,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认为是“主要是由于两汉以来中原与南方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平衡所造成。”[9]但是“益州疲弊”并不应当是决定文学衰颓的决定性原因,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乱世或困苦的状态下写成,即使是同一时期动乱的吴国,也有许多辞赋作品传世,同时还出现了经学大发展的文学现象。杜松柏先生认为,入晋以后,“能文之士凋零散落,作品不易流传和保存”是蜀汉辞赋散佚的重要原因。但这些解释均无法解释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清代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录的蜀汉其他文体的作品并不像辞赋那么少,还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许多使用“前朝称谓”的表章都保存了下来,为何单单亡佚了杜松柏先生统计的“一百多篇”赋?
第二,如果说是因为晋朝“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10]是巴蜀文学作品保存不利的成因,那么终蜀汉刘备刘禅两朝,刘氏代表的“流亡北士”一直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对蜀人在政治上一直采取怀柔加防范的策略。而在入晋之后,司马氏将刘氏一派势力尽量迁回北方,还政与巴蜀当地士人,大大缓和了了巴蜀政坛两派政治力量对峙多年的紧张气氛,提高了蜀人的政治地位。为何在此之后蜀汉辞赋仍未大量传世?
要解释蜀汉辞赋衰微的问题,并合理估算当时蜀汉辞赋的数量,关键在于蜀汉的人才选拔标准和政治原因。
(一)人才选拔标准
“夷陵之战”(公元222年)是蜀汉人才政策收紧的一大里程碑。“夷陵之战”之前,刘备和诸葛亮共执蜀汉之政,蜀汉核心集团的人才除了黄权、费诗、杨洪等寥寥几人之外,几乎全部是刘备集团发展前期的旧部或荆州降将。刘备发展前期是在中原地区勉力存活,人才核心多是北方人和荆州人,尚权谋而轻文学,均不似益州士人有辞赋创作的传统。北方和荆襄士人好谈辩议论,品评人物的习气(如徐靖的“清谈不倦”和简雍的“优游风议”)也极大的冲击了益州文人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入川以后,益州交通不便,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环境非常封闭,人才选拔的标准和文坛主旋律就更不容易发生改变。
史书上很少见到刘备和诸葛亮对于辞赋这种以铺张扬厉为美的文体的看法,但是,总结严可均《全三国文》和陈寿《三国志》中刘备、刘璋父子和诸葛亮的文学作品,基本以诏令、表章和书信为主,应用文体一枝独秀。
先主刘备的文化水平一般,在蜀汉后期实际掌权的诸葛亮也并不长于辞赋。陈寿评价诸葛亮:“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说明了诸葛亮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与之前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相比,诸葛亮身上缺乏文学家的浪漫主义气质,相对于辞赋,他更重视应用文体,在其作品中看不到夸饰的言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刘禅举荐人才:“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11]对于诸葛亮所推重的这几位人才,不但都延续了刘备时期的选材标准,而且都看不到史书上对他们精于文学的记载。这就造成了“蜀罕以诗赋擅称者,故不逮邺下之盛”[12]的文坛局面。蜀国选拔的人才以勤于军政的实用性为标准,文学能力不仅不被作为参考,反而成为一种赘余。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到诸葛亮舌战群儒,斥责寻章摘句的文人为小人之儒:“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此可作为印证刘备集团人才选拔标准的旁证。
(二)政治原因
在人才选拔的政治背景问题上,“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任蜀国丞相并开府,具有更大的权利选擢人才,但是也面临战后蜀国国力衰退更加严重,刘焉、刘璋的旧部心怀不满,借机蠢蠢欲动的现状。这就更加需要倚重入川时所带的流亡北士。这间接的造成了蜀汉后期人心向背,既要反对北伐,又想谋求统一,那么投降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谯周(巴西西充国人)的《仇国论》就折射了巴蜀当地文人的这一心理状况:“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对于战争,他认为:“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13]
杨戏的《季汉辅臣赞》[14]列举了刘备政治集团几乎所有活跃的核心人物,一一加以赞美或批判,其中大多是刘备入川之前的旧部。反倒杨戏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这篇赋如果是出自流亡北士或荆州旧部之手,就有自称自赞之嫌,但是出自巴蜀之人的手笔,这篇文章就对刘备集团有了宣传上的政治意义。
因此,三国蜀汉辞赋传世数量少的决定性原因在于蜀汉的人才选拔标准和制度,这造成了“作家少,创作空间小,缺乏创作动机”的独特文学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文献辑佚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作品统计方面“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情况,即取得的信息仅仅来源于幸存者(淘汰后的结果)的时候,对此信息的分析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好比有人想通过研究大学生来挖掘高中的教育问题,却忽视了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人才是高中教育中真正出了问题的人。目前对蜀汉辞赋研究的症结就源于这个“幸存者偏差”,只通过现存的蜀汉辞赋来估算其创作与发展情况是不够的,根据现存的文学作品来还原文学史是片面的,想要尽量真实描绘文学史的演进过程,就必须将与文学密切联系的其他历史因素纳入考量。
四、蜀汉辞赋统计与分类
《中国文学大辞典》对赋的定义是:“文体名。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最早出现‘赋’名的是战国时荀况的《赋篇》。至汉代形成固定体制,称为‘新体赋’‘汉大赋’。后演成‘俳赋’‘律赋’‘文赋’等类。讲究铺陈描绘、词藻华丽,又注重韵节严整。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见,‘赋’于‘体物’之同时,亦‘写志’。”
辞赋与类赋之文必须满足两大条件:相对于作品本身,必须在形式上“铺采摛文”,句法上骈偶错落,音律上参差有致,在形式上过于简短、松散和简陋的不能被归为赋;相对于作家创作,必须是作家有意识以某文学体裁为目标或模板进行的创作,才可以被归类于此。如费祎的《啁吴群臣》,与其说是赋,不如说是口占的四言诗更为恰当,但是它又同时具有骈四俪六的特征,因此由杜松柏先生所归类的“辞赋”移到“类赋之文”。
根据辞赋与类辞赋之文在文体上的特征和作品创作的实际情况,兹将三国时期蜀汉辞赋进行重新整理并作统计和分类如下:
1.辞赋
(1)存全文(3篇)
杨戏《季汉辅臣赞》、郤正《释讥》、谯周《仇国论》。
(2)存残句(1篇)
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
(3)存目(9篇)
陈术《释问》七篇、费祎《麦赋》、李赐《玄鸟赋》。
2.类赋之文(7篇)
费祎《啁吴群臣》、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秦宓《答王商书》《报李权》《论文采》、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李密《陈情表》。
根据《三国蜀汉辞赋考论》中所列举的四十三人中,除王崇和陈寿有明确记载确实创作有辞赋作品,其余作家都缺乏相关佐证。因为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以朴实无华,质朴无文的应用文体见长,结合上文论述的相关人才选拔的标准和政治原因,保守估计蜀汉辞赋总量不会超过五十篇。

泥模艺术——探母回令
[1]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09.
[2]杜松柏.三国蜀汉辞赋考论[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5):102-105.
[3][5][6][11][13][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581.580.844.548.610-611.640.
[4][清]严可均.全三国文(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11.
[7][8][10]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任乃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8.620.2.
[9]王林.六朝辞赋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95.
[12]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40.38.
【责任编辑:周 丹】
I207
A
1673-7725(2015)03-0082-06
2014-01-14
田鹏(1987-),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