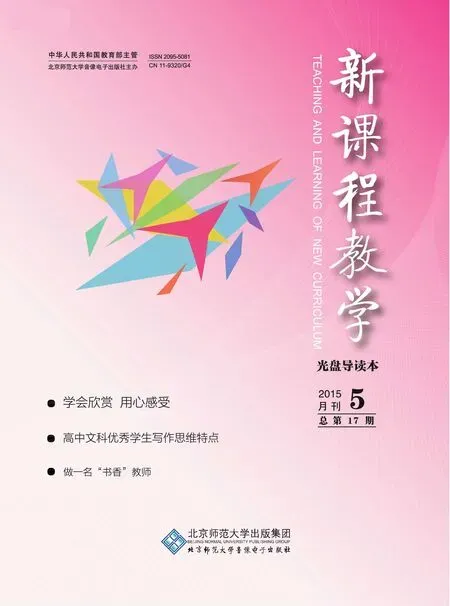变“官方的课程”为“教师的课程”1——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与政策”为例
2015-02-27沈为慧
沈为慧
(江苏省昆山中学,昆山 215300)
美国课程专家古德拉德提出,课程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理想的课程”,它是由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所倡导的课程构想、建议和计划组成的.第二个层次为“正式的课程”,也称“官方的课程”,即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第三个层次为“领悟的课程”,即任课教师所领会、创生的课程.第四个层次为“运作的课程”,即课堂上实际实施执行的课程.第五个层次为“体验的课程”,它是学生实际体验到的课程,也即学生学习的结果.[1]学生学习的结果,取决于体验课程的深度.而对课程体验的深度,往往取决于能否把“正式的课程”转化为“体验的课程”,以及如何把“正式的课程”转化为“体验的课程”的.而实现这种转化的主体是教师,只有通过教师的理解和运作,才能把官方的“正式的课程”(即“官方的课程”)变为教师“领悟的课程”(即“教师的课程”).但是,“教师的课程”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使之成为可在课堂上实施执行、运作的课程,只有这种课程才易于让学生体验、理解、掌握,成为“学生的课程”.
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曾指出:“学生学不好某门学科的知识,并不是他没有能力学好知识,而是他不能学好以某种特定方式教授的知识.所以,要树立所有学生都能学习的新的学生观,就意味着要研究适合每个学生特定学习能力与学习特点的教授方式,使课程、教材、教法的设计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和灵活性.”[2]为此,就需要把“官方的课程”变为“教师的课程”.日本课程专家佐藤学认为,所谓“教师的课程”,指的是被每一个教师的意图、解释、构想、设计所演绎的课程.[3]可以说,“教师的课程”是“官方的课程”与“学生的课程”之间的桥梁.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搭建这种认知的桥梁呢?下面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为例作简单说明.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与政策”,中学教科书是这样介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激烈斗争,成为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
新中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诞生.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新中国都愿意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毛泽东形象地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4]
重点介绍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方针,以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个形象化的方针.但学生很难理解这一外交总方针和三个形象化的外交政策,这就要求把“官方的课程”转变为“教师的课程”,以搭建便于学生进行体验的认知桥梁.在搭建这一“桥梁”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结盟”无疑可作为最重要的“建材”.
为了促进中苏两国结盟,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不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在两个领导人面前,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即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联使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为保障苏联安全的一个广阔地带;同时,苏联还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两港口的特权,从而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了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但是,如果不收回东北主权,中国的新政权就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解释采取“一边倒”的合理性.
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便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可是,两人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分歧太大.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毛泽东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致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告诉罗申:最近几天,“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苏联从中察觉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新政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第二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毛泽东处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的意见.
在中苏举行条约问题谈判时,苏联情报部门又得到消息:美国决定“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这使苏联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在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因此有人说,美国成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谈判的结果是,1950年2月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中国收回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中苏结盟的实现反映了新中国执行了“一边倒”的政策;结盟过程中,收回东北地区的铁路、港口,则体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1945年的中苏条约,则是对“另起炉灶”政策的具体实施.践行三大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外交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二是巩固新生政权.近代中国的外交往往受控于他国,新型外交必然要追求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前提条件是,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只有得到国际承认和外国援助,中国才能恢复经济,安全才能有所保障,新政权才能巩固.借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结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与政策进行解释,使这一抽象性、概括性很强的学习内容变得更加具体、有针对性,从而易于学生认知.
在教学实践中,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与政策”的内容还有很多.“官方的课程”是制度化的产物,它“强调课程的间接性、简捷性和引导性,忽视课程的亲历性、自主性和方法性,过分强调知识经验的普遍接受和共同感觉,忽视个体经验、感受的差异性”.[5]“官方的课程”又是“由外部专家开发的一种体系化、概念化、抽象化了的课程”,它“相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是间接的、外在的和客观的,是远离教师和学生生活的;其知识呈现的形态往往是结论式和结果式的,因而是非过程性、非情境化的”.“官方的课程”还是“各种外在于教学情境的专家经过选择和抽象化了的智慧经验”,是“远离学生心理顺序的,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客观性的特征,是大多数人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想方设法使“这种抽象化了的内容生动起来,简化了的内容丰满起来,统一的内容个别化起来”.[6]
课程不能“仅仅是静态的书面文件(教科书、教学指南等),而是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情境中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经验”.[7]因此,教学中应将抽象性、概括性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具有过程性、亲历性的课堂知识,与教师、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的实践知识,从而将“他的课程”变为“我的课程”.
[1]施良方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9.
[2]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35.
[3][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9.
[4]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①(必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08.
[5]石鸥.在过程中体验[J].课程·教材·教法,2002(8):10-13.
[6]陈家斌.论教师课程运作的机制[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24-26.
[7]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