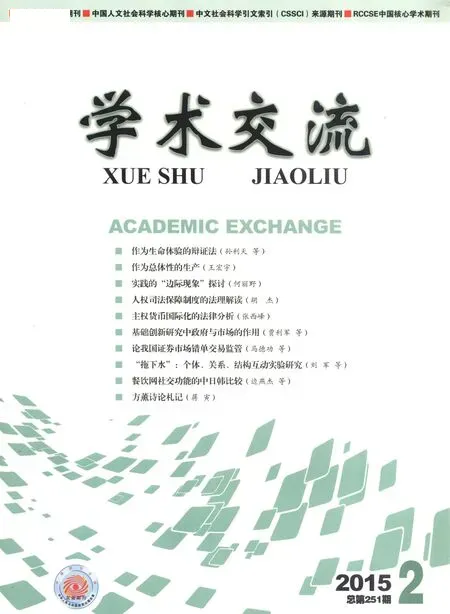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 ——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
2015-02-26李光杰,崔秀兰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研究”(12BYY075)
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
——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
李光杰1,崔秀兰2
(1.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长春 130024; 2.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清末民初是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构成的重要时期。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是以幽燕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外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而构成的。清朝末年,随着东北地区满语的衰落,通过由使用满语到使用汉语的转化,实现了幽燕方言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满语并未消失,而是同其他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作为底层词遗留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历史上国内外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大量国内外移民的涌入,形成了东北特有的语言接触现象,使以山东方言为代表的各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迅速汇入到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最终形成创设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移民;词汇系统;定型期
[收稿日期]2014-12-31
[作者简介]李光杰(1968-),男,黑龙江安达人,博士后,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汉语史、东北方言研究。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2-0171-05
清末民初,由于国内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广泛聚集的特有区域。随着各民族的互相接触、互相融合,在东北地区就产生了十分丰富且极为罕见的语言接触现象。这一现象为最终形成多元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满语的衰落为现代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主体转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我国东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自古以来,满、蒙、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先人,就世代生活在这里。而这些民族的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从唐代契丹、靺鞨经金元两代女真直到明末形成的满族,历代在东北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用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因此,古代东北地区原来很可能是以阿尔泰语作为通行语言的。”[1]112可见,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对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当属满族语言。
满族的先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称呼。商周时称为肃慎,汉时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黑水靺鞨,辽、金、元、明时称为女真。
满族的语言是金代女真语的延续和发展, 清朝入关后称做“清语”,通常称为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在清朝前期曾盛行一时,在清朝中期主体地位受到汉语的冲击,逐渐丧失主体地位,清朝末期则完全衰落。
较早进入东北地区的汉人以幽燕地区的居民为主,以后的各个时代,关内北方各省汉人流入东北的数量不断扩大,明清之际形成了较大规模,最高峰则是在清末民初。
由于先期流入东北地区的汉人多数是幽燕地区的居民,所以他们所操持的汉语应以幽燕方言为主。“在辽太祖阿保机时期(907-926),所俘虏的大批幽燕地区的人分布在东北各地,和当地各族不断交往,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幽燕地区的方言。”[1]113在东北,直到清前期,以满语为标志的阿尔泰语系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幽燕方言为标志的东北汉语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才得以完全改变。
(一)清东北地区通用语的使用情况
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也是满语使用时间最久的地区。这里居住的满族人口,多数分布在乡村,语言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时,东北地区相对关内地处偏远,吉林,特别是黑龙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语言受到冲击的因素少,语言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东北地区成为全国范围内满语使用时间最长、转用汉语时间最晚的地区。
1.清前期东北地区以满语为通用语。 1644年入关前,满语几乎是满族人单一的语言交际工具。“入关初期,八旗人员的绝大多数不通汉语文。‘开国之初,综满洲、蒙古、汉军皆通国语。’清仁宗说:‘满洲人才,并未娴汉文,不能汉语。’”[2]28为解决满汉官员语言不通的问题,满族统治者专门设立了汉语翻译“启心郎”一职。“设启心郎是因满族人不通汉语,裁撤的原因之一是满族人渐通汉语。满族人入关前自然是使用满语,彼时纵有通汉语者亦属个别,决非普遍。”[3]67由此可见,满语在清朝入关前后一直是东北地区的唯一通行语言。
2.清中后期东北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为满语汉语兼用。 清中后期东北大部分地区开始了由使用满语向使用汉语的转化进程。由于东北三省是满族的发祥地,因此转用汉语的进程比较复杂,大体上是由南向北、由城镇向乡村呈现缓慢延伸的发展趋势。
清朝中期,清政府对东北已经实施了长达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但由于关内北方各省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及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迫使大量流民冲破封禁进入东北寻求生存,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满语因此受到强烈冲击, 使用趋势减弱,并逐步被汉语所取代。在城镇的满族已多改用汉语,出现了满语汉语相互共存的局面,“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到乾隆末年,连盛京的满族官员都不会写满文了”[4]67。 但这只是局限于城镇,在东北,聚居在村屯中的满族仍在继续使用满语交流。“辽宁省满族使用双语到转用汉语,情况极为复杂。城镇中满汉杂居,转用汉语的时间要早一些;聚居在乡村的满族,学会汉语并转用汉语要晚一些。总体上说,辽宁的满族大约在清代中后期陆续转用汉语。”[2]31
3.清末期东北地区的通用语为汉语。 清朝末期迁入东北的移民据统计有1000余万人,大量的移民涌入,对于使用满语的满族来说无疑是产生了巨大的稀释作用。使用满语单纯的封闭性的语言环境遭到破坏,更多的满族人受到这种语言发展趋势的影响而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开始操说汉语。清末,除黑龙江少数偏远的满族聚居区仍然在使用满语外,东北全境几乎全部实现了由满语到汉语的转换,汉语成为通用语。从黑龙江《呼兰府志》中可知当时满汉语言之间的转化情况: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皆用清文。同治以后,满汉文俱有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满语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满语者,则千中之一二人而已。
在吉林地区,汉语使用情况非常普遍,《双城堡总管衙门档案》曾记载当地“以清语相问答者实不多见”。由此可见,“吉林省的满族应在清中后期始用满汉双语,大约在清末民初完成汉语的转用”[2]32。
对于清末民初的东北地区来说,大量移民的涌入,使汉族与满族开始了大范围、多角度的广泛接触。这种接触使满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乃至于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最终导致了满族文化的迅速变迁。这种接触同时也改变了东北地区原有的人口数量的比例结构,使较为封闭的语言环境受到挤压,以至于破坏了以满语为通用语的较为平静的语言环境,最终通过激烈碰撞满汉语并存,转化为汉语替代满语而成为通用语。
(二)东北满语衰落的原因
满语作为通用语在东北从使用到兴盛再到衰落,最后由东北汉语所取代,历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1.满汉语言差异是满语衰落的客观原因。 一种语言如果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它的语言结构功能就会逐渐退化, 需要借用其他语言来满足人们的交往功能。
满族对于汉族来说是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满语与汉语相比,满族的语言体系不够完善,语言功能不够完备,具体表现在语音标识受到限制,词汇系统不够丰富,语法结构过于简单。因此,满语在很多方面,还很难详尽地表达出应表达的内容。
汉语经过长期的自身演化以及不断吸收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极为成熟的语言。因此,汉语能够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现象迅速作出准确而详尽的表述。正是因为汉语具有极强的语言表达功能,自然使自身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满语最终走向衰落。
2.满汉社会文明程度的差异是满语衰落的内在动因。 满族是新兴的少数民族,是一个刚刚从以渔猎经济为主走向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民族,其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随着关内移民的不断涌入,满族的人口数量与汉族相比已经处于劣势。在人口分布上形成了东北土著少数民族与汉族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尤其是满汉两个民族开始了大面积、多层次的接触。在与移民接触的过程中,满族需要学习汉人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文化知识以及管理经验。这种心理需求是导致满族主动放弃自己语言而转向学习使用汉语的直接内在动因。
满语由清初的通用语到清中后期开始衰落,再到清末几近完全转用汉语,这个过程不是满汉两种语言的一个简单转换,而是实现了阿尔泰语系少数民族语言向以幽燕方言为主的东北汉语的转换。这种转换确立了幽燕方言在清末民初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东北汉语始终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的局面,对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构成的次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东北汉语方言词汇系统从此形成了以幽燕方言为主,东北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的格局。
满语伴随着满族的昌盛及清王朝的兴起,曾经兴盛一时,成为东北地区长期使用的通行语言。由于大量汉人移民东北以及满语自身的局限性,满语逐渐走向衰落,但它并未消失,而是作为底层语言遗留在东北方言中,成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语对东北方言的影响,最集中体现在词汇方面。满语中的许多词汇已进入东北方言中。较为典型的满语词有嘎拉哈(一种利用猪羊等足关节骨做的玩具)、哈拉巴(指肩胛骨,一般特指牛的肩胛骨)、靰鞡(满族发明的用皮革制成的鞋,里面垫靰鞡草,也作“乌拉”)、哈喇(油质或油质食品放置时间过长而变质,产生异味)、磨叽(不厌其烦地央求别人)、秃噜(事情没办成)。
其他的少数民族语在与汉语接触融合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词语作为底层词留存于东北方言之中。如蒙古语“把式”,也作“把势”,指专门精通某种技术的人。“老嘎达”排行最小的意思。此外,还有锡伯语,“卡伦湖”,为边防哨卡之意。
二、国内移民为现代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外省方言词
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生存条件较为艰苦,但这里却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关内北方各省因土地兼并、战乱侵扰、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关内北方各省向东北移民的历史较为悠久,但最高峰却是在清末民初。据统计,这一时期从关内移民东北的人数就达2 300多万,这在我国东北移民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清末东北人口情况
清末是形成东北移民高潮的重要时期,东北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清朝末期满族统治每况愈下,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清政府被迫在东北采取“开禁放垦”政策,以缓解经济压力。咸丰十一年(1861年)首先在黑龙江地区开禁放垦。清人徐宗亮在《黑龙江述略》(卷六)中描述当时移民的情况是:“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生动反映了开禁放垦时期流民奔向东北的真实情况。关内各省的流民络绎不绝地奔向黑龙江,是形成清末东北地区移民高潮的前奏。同时,清朝中后期积贫积弱,成为俄国不断蚕食的对象。“移民实边”也是为抵御沙俄入侵。此外,1897年沙俄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是造成东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的另一主要原因。
清末东北人口迅速增加,1861年(咸丰十年)清政府正式在东北局部地区弛禁放荒。据赵英兰统计(《清代东北人口的统计分析》2004年)当时人口为3 707 820人,到1900年的39年里,人口就上升至12 000 000人,而到1911年人口又上升至19 964 226人,50年中,东北人口翻了近六倍。而在这些人口当中,除去当地人的自然生长,移民占据很大比例,根据以上数字判断,至清末迁入东北的移民至少有1 000多万,这是清朝东北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民初东北人口情况
民国初期,东北移民数量较清末有了快速增加。这是因为一方面民国政府及东北地方政府继续沿用清政府开垦东北地区的政策,积极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地区,另一方面民国初年关内北方各省军阀连年混战,加之这一时期天灾异常频繁,使得关内民众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选取东北作为谋生之地。
因此,民国建立以来,东北移民有增无减,在民国前期的20余年中,约有近千万人出关谋生。据宋家泰先生统计(《东北九省》1948年版)辽宁省人口由1 000万增至1 600万,吉林省人口由400万增至730万,黑龙江省人口由200万增至360万。依据陈彩章先生《中国历代人口之研究》(1946年版)我们可知:仅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就增加了一倍多,达到近3 000万人。民国初期的短短20年,东北人口数量由于移民的原因,至少又增加了1 000多万。
据上述材料,清末民初关内涌入东北地区的移民至少约有两千万,使东北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外省词在东北方言中的存留
东北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征,形成了东北方言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受此影响,大量的东北方言来自关内北方各省。其中,以山东人占绝大部分,河北人次之。
据何廉先生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1932年)调查,“1927年,关内北方诸省迁赴东三省之移民,其中87%来自山东,12%来自河北,1%来自河南。1928年迁赴东三省的移民籍贯变化不大。1929年,移民中山东人口占71%,河北人口占16%,河南人口占11%,其他省份的占2%”。从这一移民籍贯的统计调查,可以看出山东、河北人在移民当中占有绝大多数。这说明由于以山东、河北为主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东北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与数量比例,在东北方言形成的过程中,就必然吸收山东、河北等地的方言,如来自山东方言的刀鱼(带鱼)、炮仗(鞭炮)、嫌乎(嫌弃)、厌恶(不满意)、单饼(用面粉烙的薄饼)、恶应(恶心),来自北京方言的开瓢儿(砍或打破脑袋)、鲤鱼拐子(小鲤鱼)、猛住了(愣住了)、够个儿(达到或超出一般程度)、稀溜儿的(稀稠度略稀的)、溜够(足够),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方言词汇构成系统。
以山东为代表的外省方言词随着移民进入东北,与东北方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外省方言词被东北方言不断吸收,成为东北方言词汇构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的要素,增加了新鲜成分。
三、外国移民为现代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形成注入了外来语
东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我国京、津地区的天然屏障,还是进出亚洲东北部的重要门户。因此,沙俄、日本一直想吞并我国东北,将其变成它们进一步征服整个中国的基地。在清末民初,伴随着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政治上的窥视、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侵略外,还主要进行移民侵略。与俄日两国不同,朝鲜向中国东北移民主要是因为本国的残暴统治、自然灾害与日本入侵所导致。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日、朝三国民众纷纷涌向中国东北地区,致使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俄国、日本、朝鲜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最高潮。据统计,清末民初日本、俄国、朝鲜向东北地区共移民就达190万人之多,这无疑对当地的语言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一)俄国移民及俄语借用
1.俄国移民情况。 清末民初是俄国移民我国东北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形成了俄国人移居中国东北的高潮。主要原因是中东铁路的修建。
中东铁路于1897年开始修筑,干线与支线合计长达2 420多公里,由于工程浩大,所以急需大批人力资源。因此,这一时期有大量与中东铁路有关人员涌入东北,形成了历史上较大规模的俄国人移居中国东北的现象。此外,流亡东北的俄国侨民也是东北移民增加的原因之一。据《东北俄侨社会人口状况》(1900~1944)统计,1900-1910年,在东北的俄国人人数达5万。1919-1920年间,达15万人。1930年,在中国东北的俄国侨民人数为11万人。
2.俄语借词。 我国东北地区真正接触俄国语言和文化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营运开始的,这时期铁路为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文化历史背景下,俄语与东北方言进行了接触,大量俄语借词作为外来语被保留在东北方言词汇当中,如笆篱子(监狱)、班克(装酒油的方桶)、布留克(蔬菜名,块根可腌咸菜)、布拉吉(连衣裙)、马达木(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马神(缝纫机)、喂得罗(上大下小铁皮桶)。
(二)日本移民及日语借用
1.日本移民情况。 由于日本是岛国,同时又具有地狭人稠的特点,这就使日本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侵略与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贯主张。
通过移民达到侵略的目的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从清末民初,即从1906年开始到1937年始终向中国东北移民。这一时期,日本最早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标志是1906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建立,1915年进行了最早的农业移民。据1928年统计,当时在东北定居的日本人总数近20万,其中农业移民仅1 061户,约3 000人,仅占1.5%。[5]这一阶段移民的整体分布,大部分集中在北满三江省和滨江省一带。
2.日语借词。 为达到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从1906年开始以铁道移民、农业移民、武装移民等形式向中国东北移民。大量日本移民的涌入,必然使日本人与当地居民在居住环境、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引起语言方面的广泛接触。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强迫国人说日语,这为东北方言中日语借词的迅速产生提供了外在动能。东北方言中的日语借词有咕噜玛(在铁轨上运行需人力控制的小型板车)、马葫芦(下水道)、榻榻米(床上的草垫子)、瓦斯(煤气)、邮便(邮件,常说“打邮便”)等。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语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
(三)朝鲜移民及朝鲜语借用
1.朝鲜移民情况。 中朝两国陆路接壤,交通便利,为朝鲜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末民初是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时局动荡,外患频生,防务管理松懈。因此,物产丰富、地大物博的我国东北地区对于此时处于国内政治、经济严重危机中的朝鲜移民来说,无疑是生存的最佳选择。此外,日本驱使朝鲜移民中国东北也是形成这一时期朝鲜移民最高峰的原因之一。
1860年到1870年间,朝鲜北部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批灾民涌入中国东北。从1840年至1880年,定居东北的朝鲜人有20 000左右。[6]961881年以后,清朝有条件地向朝鲜贫民推行了一些意在吸引其迁入东北的优惠政策。1894年东北朝鲜移民已达65 000人,到1909年增至210 000左右。[6]97从1910年至1930年期间,朝鲜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情况是:1910年,东北朝鲜移民约有220 000人,1917年达358 000余人,1920年达459 427人,1930年达607 000余人。[6]97-98
2.朝鲜语借词。 朝鲜语作为借词留存于东北方言之中多数是以地名为多,且多存在于吉林省东部地区,仅吉林珲春境内的朝鲜语地名,现留存的就约有60多个。东北方言中从朝鲜语中借用的较为典型的词汇有朝鲜族传统食品冷面(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做成的圆面条,煮熟后经冷水处理,加入牛肉片、西红柿、糖醋及老汤而成)、打糕(把糯米煮熟后捶打后,将其切成小块,拌花生粉等佐料食用)、辣白菜(用大白菜、辣椒面等原料腌制而成,口味辣脆酸甜),还有众所周知的花名金达莱,以及现在仍沿用的“唧个啷”(争辩、吵嘴)等。
总体来说,朝鲜语借词在东北方言的词语相对于俄语、日语借词数量较少,但作为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的特征之一,仍然发挥着积极的语言交流作用。
从清末民初开始,东北方言中大量吸收了周边国家的部分词语。这些词语作为外来语曾在东北地区长期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交往之中,成为东北方言词汇中的重要补充成分,这些外来语丰富并发展了东北方言的词汇构成系统,使东北方言更具区域性与独特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是一个体系开放的、动态的系统。
四、余论
清末民初是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东北区域已经完成了满语与汉语的转化,幽燕方言取代阿尔泰少数民族语言确立了在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中又大量吸收了外省方言词、增加了外来语的借用。正是因为构建了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这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此时的东北方言词汇构成体系要素已经完备,东北方言词汇构成体系已经成熟。
东北方言词汇构成系统的形成确定在清末民初,对于正确认识东北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东北方言影响的不断扩大,对于东北方言的研究也将不断地深入,东北方言多元的、民族的、区域的内在价值将体现得更加鲜明。
[参考文献]
[1]林焘.北京官话溯源[J].中国语文,1987,(3).
[2]季永海.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J].满语研究,2004,(1).
[3]爱新觉罗·瀛生.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J].满族研究,1987,(1).
[4]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J].北方文物,1995,(1).
[5]赵力群.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J].社会科学辑刊,1992,(2).
[6]金元石.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责任编辑:曹金钟〕
语言文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