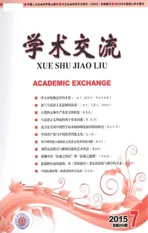沙夫异化概念中的矛盾
2015-02-25塔杜什布克辛斯基TadeuszBuksiski
[波]塔杜什·布克辛斯基(Tadeusz Buksiński)
马建青 译
(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专题·
沙夫异化概念中的矛盾
[波]塔杜什·布克辛斯基(Tadeusz Buksiński)
马建青 译
(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沙夫著作中的异化概念结构复杂且充斥着矛盾。从异化的主体方面来看,异化表征为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又积极献身。从异化的客体方面来看,在何种意义上客观因素促成了异化的主体态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种主体态度是社会结构异化的根源这一点并不明晰。本文试图阐释亚当·沙夫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并追问是否可能避免异化。
沙夫;异化;主体异化;客体异化;人
在波兰之外,沙夫被视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他被视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斯大林式解释的哲学家。关于这一点,只需列出沙夫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出版的著作的标题便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62年),《人的哲学》(1961年,1965年),《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1965年),《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1978年,1999年)。20世纪60年以后,人(man)的问题和人类(human)的哲学地位问题在沙夫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波兰,沙夫常常被认为是一名正统的,甚至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亚当·沙夫是在苏联科学院的哲学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而且他讲授的主要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其次,他在政治上一向是积极的,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的。再次,他于1959年加入波兰联合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人们常常认为,他应该对将苏联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强加给波兰人民负责。最后,沙夫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人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学而非哲学观点,因为它研究了社会范畴中的个体,却忽视了该问题的形而上学维度。
一、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
亚当·沙夫最重要的和最具独创性的学术成就之一便是提出如下观点:异化是马克思哲学最根本的主题,它——或明确或隐晦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所有研究成果中。这种观点与一些马克思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主张相对立,在后者看来,异化只出现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重要的是,沙夫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有力的论证。因而,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作品成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异化理论。一方面,沙夫再现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另一方面,他对这些异化思想进行了分析,辨识出潜在于异化概念中的价值论假设并根据20世纪的经验将之重释。在此意义上,沙夫超越了明显地存在于马克思作品中的有关文献和论点,无论如何,他都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并运用它来分析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象。
亚当·沙夫所提观点的一个关键点是他对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的划分①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Warsaw 1999,KIW[first edition in German,1978],pp.97,142.。这种划分是独创的,它使作者能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沙夫区分了客体异化的三种基本类型:经济异化,社会-政治制度异化和观念产物的异化。在此总体框架之下,他又指认出许多类型。比如,在沙夫所提出的体系中,经济异化包括的子类型有劳动产物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经济关系的异化以及工人自身的异化。社会-政治制度异化包括国家、法律、政治机构、行政制度、政党、地方政府和整个政治生活的异化。相应地,观念产物的异化主要指宗教、意识形态、语言和整个文化的异化。客体的经济异化被认为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类型,它是所有其他异化类型的根本原因或根源②Ibid.。
与马克思作品的字面意义和本质精神相一致,亚当·沙夫将客体异化界定为一个过程,通过此过程,人与他们的活动和产物相疏远,他们的活动和产物独立并与人相敌对。因而,人的产物和活动获得了功能和意义,这些功能和意义不同于——有时是根本不同于——作为它们的创造者的人有意分配或试图分配给它们的功能和意义。比如,产物根据其定义是用来满足生理需要或社会需要的,遵从市场法则,市场为其定价。然而,它们的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生产者很难甚至不可能购买他们的产物。工人的生活需要商品:他们的劳动产物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而不是中立的。然而,这些商品是难以企及的,甚至被认为是敌对的,因为它们是作为一种由市场法则所支配的独立的和无法控制的力量与它们的创造者相对抗着的,并且作为一种压迫的要素限制了人的自由、行动的机会和生活的潜能③Compare K.Marx,Zeszyty Filozoficzno-polityczne,in:K.Marx,F.Engels,Dziea[Works],vol.1 Warsaw 1961,KIW,p.578.。
这样,客体异化,特别是如上强调的作为其他异化的基础和原因的经济异化的原因和根源这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沙夫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异化的直接根源包括资本和雇佣劳动,而这些是受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制约的。这些要素导致种种发展的动态过程,结果使人们丧失了对他们产物的控制进而变成它们的附属物④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p.98-106.关于这些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被提出的观点,沙夫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Warsaw 1965,PWN)一书中也进行了简要的阐述。。然而,这种说明并不能满足波兰哲学家,他们认为这种说明不够清晰。沙夫争辩说:如果所有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异化过程的真正必要条件,那么废除它们应该就能消除全部异化。尽管如此,与这种期望相反,客体异化仍然存在于现实社会主义之中。因而可以断定,马克思为异化所列出的先决条件应被逻辑地解释为异化产生的充分条件,或者,充其量是导致异化过程的条件。
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关于异化产生原因的说明,便会产生疑问——其他支撑这种过程的要素是否也可能是异化产生的原因。于是,沙夫又开始探讨独立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劳动分工。它既受社会阶级结构的制约,又有相对独立的起源和特征。劳动分工使得消除异化这个问题复杂化。很显然,不可能消除劳动分工,因为它是技术进步的诸多表现之一。即使沙夫确实认为通过将新机器引入生产从而消除分工是可能的,但他似乎并不重视这些假定性的想法⑤Ibid.and 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p.102-105.。列宁曾声称,在未来(比如,在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机构将消亡,即使普通的清洁工也将能依其意愿改变职业,担任指导的、政治的或其他管理的职务。事实上,当列宁如此说的时候,沙夫指责列宁天真。然而,既然技术进步需要日益强化的专门化,人就不可能随意改变职业: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多个领域都是精通的①Ibid.p.109,compare Lenin’s Państwo i rewolucja[State and Revolution]in:W.Lenin Dziea wybrane[Selected Works],vol.II.Warsaw 1955,KIW.pp.144-146。
沙夫也列举了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中客体异化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对特定商品的市场垄断、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职业化②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p.113,129 and 195.。
客体异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历史发展动力论。动力既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一个结果,也是强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活动的长期结果大多数是不可预知的,而且通常相悖于最初的意图。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的活动结果要么是不可知的,要么是无法控制的。这导致很多现象和状况独立于人的意图和目标之外,并常常使人们遭受严重的危险,它们表现了异化过程的某个方面。尽管如此,动力的价值论地位仍非常模糊。因为消灭分工这个动力将限制自由的范围,因而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们至多能限制一些动力形式:短期来看,这明显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然而,规划主要的科学或技术发现却是不合理的③Ibid.p.98 and the following pages.。
主体异化也被称为自我异化,它被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划分为个体和社会、制度、文化、劳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异化。事实上,主体异化可以被视为对客体异化的一种具体扩展。主体异化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是个体将自己从他的产物、劳动、制度、活动以及他“自身”中异化出去(而不是相反);其次,个体的“疏远”是由某种特定的参照系,比如,个体所信奉的标准、价值和观念造成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个体的方法以及他自觉的和主体的态度。这种异化在其内容上和“指向”上都不同于前者。如果个体——通常有意地和自觉地——决定不介入他的产物或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客体领域中,他也就能不和它们发生联系进而对之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和疏远的态度是由客体异化所导致的④Also ibid.,pp.143 and 200.。
二、异化理论的价值论假设
一般来说,马克思和沙夫都将客体异化视为一种否定的现象:在道德的、人类学的和历史的范畴中。相比之下,沙夫却是在少的可怜的范畴中来阐明他的主体异化观的。他善意地评价了它的一些形式,因为异化态度使得对有害于个体的社会现象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最终支撑着革命态度)是可能的⑤Ibid.,p.66.。
这些被详述的否定性评价含蓄地假定了某种状态:肯定的理想或肯定的评价目标、能力或价值。因为这些状态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异化状态,而且通常是与之相对立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异化的分析中被发现或创造出来。因而,在未异化的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大规模的私有制,制造能力为全部生产者或整个社会所掌握。劳动不是艰辛的,它是创造性的和令人愉悦的,并不限制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事实上,劳动是由劳动的需要所激发的。未异化的制度关系以承担为全体公民服务、向他们开放,并密切关注他们的兴趣的责任而闻名。简言之,行政管理应是友好型的。相应地,在制度关系之外的,自我和他人以及自我和自我的关系中,没有异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精神进步,具有创造力,自我认同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意味着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和无私的、友好的关系。这种状态中没有妒忌、怨恨、欺骗、讨厌或敌对。不难得出,没有异化的社会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⑥A.Schaff,Marksizm a jednostka ludzka[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op.cit.,p.120 and the following pages.。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理想的哲学地位和方法论地位。沙夫反复强调,马克思批判19世纪西欧的资本关系,并创造出他的理想和完美关系概念,与他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形成对抗之势。然而,这种解释引起了如下问题:马克思详述的价值论的和社会的理想是永恒的吗?如果是,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是永恒的?如果它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考是基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和经济环境,)那么在有效性方面它的哪些规范性特征是有限的?如果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价值论图景只被视为它的时代的产物,那么它的有效性便会受到时空制约。在另一个时代,在一种不同的文化中,其他品质、需要和价值将代表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并被用来作为评价他们生活境况的标准。
在沙夫那里,客体异化理论所包含的价值论理想的有效性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个问题既未被详细地加以阐述,也未被深刻地加以分析。另外,沙夫反复强调决定思想和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以及它们的可变性和相对性,而这些主张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陈述性的和概述性的。与作者的意图相反,客体和主体异化理论似乎具有了一种世界的实在结构。毕竟,未异化的存在和现象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它们的存在和运行与它们自己的本质或本性相一致。异化歪曲了这种本质并阻碍了它的实现。比如,只要劳动是创造性的和出自内在需要的,当劳动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并反映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旨趣时,它就是未异化的①A.Schaff,Filozofia czowieka[The Philosophy of Man],Warsaw 1965(1stedition–1961)KIW,pp.164-171; and A 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192.。这是劳动的本质,它似乎是普遍有效的,也就是说,它不受资本主义时代或社会主义时代的限制,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被视为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国家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对立面的社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考察作为价值论理想的个体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沙夫采取了一种似乎相当随意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从未赞同过永恒人性(或人的本质)观,或者,这种观念从未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沙夫坚决主张,人性是被历史和可变因素塑造的②Ibid.,pp.62-63 and 184-18.。然而,这种信条源自沙夫的偏爱,而不是对马克思作品的谨慎分析。沙夫公然宣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思考,这也就是如下事实的原因:他与任何此类观念保持距离并试图证明它们也是马克思的作品所缺乏的。他写道,说人有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明显带有一种形而上学意味。可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非人化问题,换言之,马克思肯定性地描绘了某种“总体的”人的图景,这种人以一种自由的和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即使这种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但对于所有人——无关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来说,它仍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理想。思想家将人置于动物的对立面,并从道义上对那些将人降低为动物存在(生殖、吃、生理需要的满足)的行为进行谴责③K.Marx,Zeszyty filozoficzno-ekonomiczne[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op.cit.Schaff proposes putting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man ad acta-compare A Schaff,Marksizm a jednostka ludzka[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op.cit.,p.80.。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考察主体异化,即该词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异化或疏远的假设。一般来说,它假设和客体异化一样的理想和价值。然而,它们的内容更为多样,因为主体异化的形式是多样的,而且必须指明的是,这种主体异化依赖于个体的情感、经验和态度。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主体异化的形式可能或多或少是极端的、碎片化的,也可能或多或少是相对的,它们的全部都是在适当的参照系统中获得表达的。例如,某人可能在经济领域中是异化的,但在政治领域中却未被异化。相对性和碎片化使得自我异化及其价值论假设变得含糊不清。关于某特殊现象或对象而形成的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态度都可以是自我异化的表现形式。例如,自我异化的其中一种形式与主体对产物的疏远感相关,也和不能将此产物看作是他(或她)的产物的无力感相关。与之相反,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对作为商品的产物的崇拜并认为它有特别的和非凡的价值。后者也指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作为一种现象,指个体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财产(比如,他们的汽车、房屋等)等同起来,并且无法看到他们的“崇拜物”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两种自我异化形式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的物化。因此,人们倾向于将他人和自己视为可操纵的对象而不是视为人类。这两种现象都导致个体从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人类“本性”中分离出去,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劳动活动中。无论对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庸结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是过分积极地投身于工作之中,都是自我异化的表现形式①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73.。
沙夫也强调文化世界中的异化。其中,沙夫提到文化价值、文化规范和文化财富的分离,比如,文化财富是以一种不介入文化活动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另一方面,他勾勒了非批判地介入特定文化事件的情形,这些文化事件使个体丧失了恰当评价他们试图强化的文化的判断力,因此也使个体丧失了他们自身而片面和非批判地献身,比如纵情于一种盲目的爱好。上面提及的文化上的漠不关心则表现为纵酒、无政府主义、犯罪等②Ibid.,p.175.。这两种文化异化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可以找到。文化上的漠不关心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职业重负,时间不足,使用文化财富的不可能性,文化规范与人们的心智和特性或他们所接受的传统的不一致。这个问题既是微妙的也是矛盾的。文化异化的消失,比如文化适应的消失不需要消除异化,因为它也代表着自我异化:当个体的活动遵从现存的规范和社会期望但又与他们“自身”、他们的观念以及他们自己的期望相抵触时,这就会发生③Ibid.,pp.180-187 and A.Schaff,Marksizm a egzystencjalizm[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Warsaw 1961,KIW,p.79 and the following pages.。
三、人的概念
再次回顾亚当·沙夫关于人类个体概念的系统性解释似乎是恰当的,因为这是理解异化概念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兰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关键。沙夫认为,人类个体这个规范性概念是详细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全部作品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基础。马克思形成了他的人的哲学,论证了作为个体的人所遭受的不幸的本质——此种不幸的起源和克服它的方式。由此看来,即使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看起来也更像是伦理学研究成果而不是经济学研究成果。相应地,异化理论能澄清使人不适的关键方面和社会机理。这些信条成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沙夫在所有他出版的前文提及的研究成果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题,沙夫认为他的人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们对人类个体概念的探究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或者揭示(如前所述的)异化理论的价值论前提,或者使用马克思研究成果的明文(expressis verbis)之中的信条。这两种研究方法沙夫都采用了。让我们来更详细地分析沙夫对马克思关于人作出的明确论述所进行的解释。根据马克思的作品,沙夫将人的特性区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首先,人被视为在生物学层面具有一系列类特征的物质存在,这些类特征将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这列类特征包括:爱的能力、直立的姿势、发达的上肢、复杂的大脑,等等。沙夫假定,这些特征是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它们显而易见,但哲学观点对此并无特别的兴趣。其次,作为个体的人具有独特的、唯一的和不可仿效的特性,比如,他们对生活意义的独特理解,对生活中他们的价值或他们的特别使命的认识。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沙夫肯定性地评价了围绕人类的独特性展开的相关问题,但并不能将之归为存在主义者所阐明的观点,因为在存在主义那里,这些特性在个体的生活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⑤A.Schaff,Filozofia czowieka[A Philosophy of Man],op.cit.,pp.132-138 and A.Schaff,Marksizm a jednostka ludzka[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op.cit.,pp.32-33.。最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个论题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思想。正如沙夫所主张的,它是对人作出的最恰当的定义⑥Ibid.;also compare K.Marx and F.Engels,Ideologia niemiecka[The German Ideology],in:K.Marx,F.Engels,Dziea[Collected Works],vol.3,Warsaw 1961,p.11 and the following pages.。然而,它为多种解释留有余地。一方面,人们可强调人类固有的普遍的社会特征的重要性,比如,生产劳动、制度结构和政治结构(zōon politikon)的建立,在共同体内独特的人类关系的创造,等等。另一方面,人们也可强调可变性,强调人具有不同的自然和文化需要以及受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制约的期望和观点也是变化的。沙夫一贯地坚持后一种人类观念⑦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48.。
此外,他将这种对个体的理解与另一论点结合起来,这种论点假定个体依赖于社会关系而且社会对个体有塑造作用。这些论点贯穿于沙夫的主要作品中。不幸的是,它们只是笼统地被谈及,而且有时还缺乏一致性。因而,沙夫关于人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首先,如前所述,关于人的本性或存在是相对的或可变的这种主张是武断的。其次,只要对被视为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先在于人以及与人共存的条件,它们客观存在且独立于具体的个体)产物的人类个体的特性与不受这些条件制约的个体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问题便会出现。沙夫强调,个体服从于不受他们影响的客观规律①A.Schaff,Obiektywny charakter praw historii[Objective Nature of the Laws of History],Warsaw 1955,PWN.Schaff never abandoned the theses laid down in this book.。尽管如此,他认为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人类历史)是人的产物。例如,正是创造政治制度并影响历史进程的个体组建成共同体。沙夫已经意识到这种矛盾并试图通过使二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历史化来加以解决。于是,他声称,即使历史规律本质上是客观的,它们的客观性也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它们通过人而起作用,比如通过他们的意志、需要、态度、期望和行动起作用。而且,作为社会和历史存在的人类始终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已然固定的和继承下来的历史境况中,他们将此境况假定为活动的起点。它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处于主导地位的态度、适当的标准、社会和制度结构,等等。通常,个体在改变已确立的条件和创造新环境方面的可能性已经受到限制。只有在这种特殊境况对人们不利时,他们才可能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求更激进的变革。上面提到的特别情形包括战争、危机、饥荒和贫穷,它们作为刺激因素,会激发社会抗议和社会革命,促进已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激进社会变革。
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是合理的,可被描述为辩证的,然而它不能解决由此产生的全部问题。局面并不明朗,因为矛盾是双面的。它不仅相关于事实层面上社会与客体领域和个体与主体领域之间的矛盾,而且相关于事实性现实和人的规范性与价值论维度之间的冲突。规范的和价值论领域(价值、目标、规范、生活理型和理想)相连于物质和社会领域(生存条件、生理需要、激情和它们的实现)。然而,它能否被正当地认为是后者的结果?当然,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似乎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有时可视为是辩证关系。然而,沙夫并没有充分阐明潜在于这些关系之下的逻辑。他给出的唯一陈述是,这种关系和不同类型的活动形成一种环境,在此环境中,人们改造客观实在并将自身塑造为社会存在。
四、消除异化如何可能
沙夫认为,两种异化类型的原因最终是相同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并且客体异化先于并制约主体异化。他的论点似乎表明这样一种信念——客体异化既是决定主体异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假定接受这种解释,那么通过消灭客体异化便可消除主体异化。如果不根除客体异化(比如,对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主体异化的逐步消除便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论点似乎过于武断,并且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作者自己无法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他也认为主体异化态度可独立于客体异化而产生,表现为个体的特性或心理特征的结果。而且,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废除了全部私有制和为私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仍然存在这两种类型的异化,而且它们不应被压制。这种观点表明,客体异化事实上并不是主体异化的必要条件。在别处,沙夫坚决主张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是相互关联的②A.Schaff,Alienacja jako zjawisko spoeczne[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op.cit.,p.200 and the following pages.。由于未给予清晰的说明,人们可以在研究这种关系时主张一种适度的、温和的解释,也就是说,认为客体异化是促进主体异化产生的一个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上面所提的适度的解释在理解“反作用”,即主体异化对客体异化作用的类型和范围时也存在问题。因此,尚不清楚的是,人们是否应该立足于日常基础来与异化作斗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斗争。当然,人们可以消极忍受异化,眼看着它加重到无法忍受直到触发革命的地步。或者,人们可以持续不断地与异化展开斗争——通过消灭现存的剥削形式,争取更好的劳动和工资条件,要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等方式。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参考中东欧和西欧国家过去十年间的经验。异化仍然存在于这两个地域中,尽管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彼此不同。而且,中东欧和西欧一直努力通过如下方式来减少异化效应:在无视剥削的经济关系甚至反对国家和政府所实行政策的人们之间建立非正式合作关系,创建不受主体异化和客体异化影响的恰当的共同体(家庭、朋友、邻居);官方对异化的谴责和为争取限制异化的法律而作的斗争(比如,环境保护条例或法律能保证劳动的安全)。异化不是命运之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客体异化也依赖于人们的态度、愿望、意图和价值观。人们可能更喜欢某种价值观(自由、私有制),因而也就能容忍在实践这些价值观时产生的后果,即某些形式的异化。尽管如此,与异化作斗争无需被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革命的准备和阶段。它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对极端异化形式的持续谴责、某种真正态度的培养以及减弱异化的改革的推进。
存在于客体异化和主体异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现象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权者采取的手段往往变成国家通过客体制度对公民进行压迫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公民异化的原因之一。操纵选民、裙带关系和腐败扭曲了国家的功能,国家成为权势集团掌控的工具,从而导致公民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冷漠。这种异化并不总是否定的,毕竟,它可增加政治异化集团的经济活力(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①M.Weber,Etyka protestancka a duch kapitalizmu[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Warsaw 2010,A letheia.,减弱与人民相敌对或压制人民的政策的影响,或者为由人民构成的自主公民组织(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Polish Solidarity])奠定基础②J.Tischner,Etyka Solidarno ci ihomo sovieticus[Ethics of Solidarity and Homo Sovieticus],Cracow 1982,Znak.。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在形式上认可现存状况(比如通过参与选举)对于界定异化的程度和类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亚当·沙夫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依存关系的复杂性:除了强调主体异化对客体异化的依赖,他也列举了一系列实践手段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非异化(职员轮换,对当权者的社会控制,公意的养成,减少党政机构运行的财政津贴③Ibid.,pp.129-134.)。相信这些手段的有效性意味着这样一种信念:个体能有意地和自觉地影响平时日常状况中——不仅仅是危机、战争和革命时期——客体异化的范围和严重程度。受存在主义启发,沙夫在他晚期作品中越来越强调道德和道德责任在个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自由的重要性。他写道:尽管接受了存在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但他拒绝他们的解决方式④A.Schaff,Filozofia czowieka[A Philosophy of Man],p.12 and the following pages.。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拒斥存在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因为在存在主义看来,个体是完全“自主的”、孤独的和命中注定的,然而他对整个世界负有责任。个体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活动,但这种自由受到它们作用生发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制约。因而,个体的责任始终是部分的和情境性的。它依赖于环境和某种具体环境中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赋予个体的自由和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是变化的,因为它们一方面依赖于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依赖于生活条件。上面这一系列论点再一次揭示了受制约的社会存在这种状况和人的条件的创造者这种状况之间的具体辩证关系⑤Ibid,pp.104-114.。沙夫并未更深入地探究这种辩证关系,而且也无从知道这些关系是否适合被精确地描述出来。
〔责任编辑:余明全 曹 妍〕
B513
A
1000-8284(2015)07-0006-07
2015-06-16
塔杜什·布克辛斯基(Tadeusz Buksiński,1942-),男,波兰人,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ń)政治与社会哲学系教授,从事当代政治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历史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马建青(1982-),男,山西和顺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