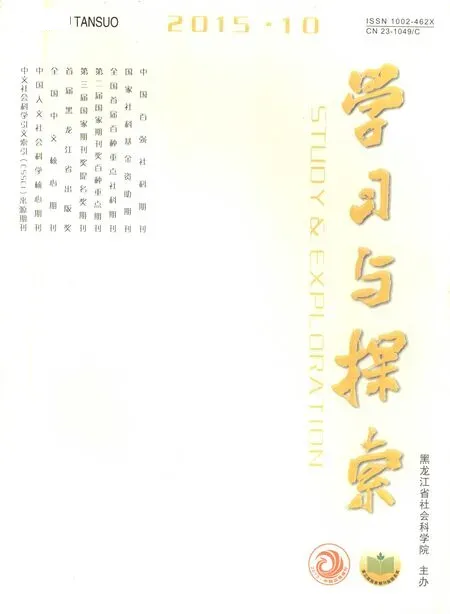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历史演变分析
——基于人类生存辩证法的视域
2015-02-25穆艳杰
陈 柯,穆艳杰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130012)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历史演变分析
——基于人类生存辩证法的视域
陈 柯,穆艳杰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130012)
从生存辩证法的视角来分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历了两种形态,当下即将进入第三种形态。三种形态分别是: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直接同一的肯定性关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的否定性关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辩证统一的否定之否定关系。这三种形态的历史演变构成了人类的生存辩证法。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理依据就是上述三种形态历史演变构成的生存辩证法。
生存辩证法;生产方式;自然生态环境
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其中,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本文将立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来探索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直接同一的肯定性阶段、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独立的否定性阶段、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辩证统一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一、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直接同一的肯定性阶段
近代工业文明以前,人类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人类依靠农业劳动来保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处在天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所谓和谐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完全处在自然生态环境提供的条件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完全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自然生态环境从来没有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因而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单纯的肯定性。自然生态环境从不否定人的生存,从不构成威胁生存的否定性力量。当然,这里讨论自然生态环境是否对人类造成生存的威胁,其实隐含的前提是:人类本身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促使自然生态环境反过来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否定性力量,实质是由人类自身对象化活动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相反,如果不在这一前提下,纯粹的来自自然生态环境的对人类生存的否定性力量,就只剩下“天灾”。而这是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之内的。因此,考察自然生态环境是否对人类本身构成生存威胁和否定,其实质是以人类自身的生产方式是否触动自然的反作用为标准的,而不是从自然本身的“天灾”来说的。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人类创造的生活资料来自于自然,主要是土地。人类依靠农业耕种获得大自然提供的果实。人类的生活资料全部是从农业产品中获得的。而且,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数量,是与大自然(土地)所能够承受的生产力相一致的。人类从来不会强迫自然(土地)生产出超出自然界限的更多的果实来。虽然人类也在探索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手段,比如灌溉技术、施肥技术、播种技术,但这些技术尚没有进入工业生产方式,仍然是在自然的界限之内展开的。这与当代的农业技术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当代的农业技术比如肥料技术、农药技术、嫁接技术、转基因技术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然本身的界限。这些技术意味着让自然生产出超出它天然具有的能力的果实。这种超出自然天然的能力,是由人类的智慧强行追加给自然的。比如,在自然中,植物是不会自己发生嫁接的,植物自己也不会有目的地改变自己的基因的。自然进化中的基因变异,只是潜在于自然中的一种特例,自然物基因变异并不影响自然自身的生产能力。人工创造的化学肥料,也不是天然的土地生产力。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通过使用自己的智慧,强行改变了自然(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显然是对大自然来说的“勉强”行为。可见,人类的智慧具有超自然性,它能够强行改变自然的生产能力。而这一人类行为必然促使自然反过来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而相反,在人类没有强迫自然提升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是保持原始的高度同一性的。
此外,人类的生产活动的节奏是随着自然的节律展开的。比如,对节气的划分,是与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紧密相连的。在哪个节气开始播种,在哪个节气开始收割,这都是与自然节律紧密相连的。与此相关,人类的饮食也是随着自然节律的变化而变化的。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季节性食物。人类的饮食从来不会出现“反季节”的情况。这就说明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的节奏是完全同步的。
人就其本性而言,首先是一个自然物,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作为自然物显然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个成员,因而按照这一自然性来说人类与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区别,他的自然生命一定要服从自然法则。这里暂且不论人类必须要通过社会性生产来实现生命的持存,单就其作为自然生物来说,他的自然生命应该以服从自然法则作为生命延续的第一法则。因此,我们把直接服从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称为直接性的肯定性关系。人类的农业生产行为是与自然法则保持同一性的。而在这种同一性中,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行为被保持在了自然生态的天然界限之内,因而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同一性关系。“出于这个阶段的人类不仅身受自然原因造成的灭绝威胁,而且深受大量未知恐惧的困扰。简单的生活没有产生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之外的剩余。无论是物质进步,还是智力进步都不明显。”[1]48这就需要人类进入新的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
二、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对独立性的否定性阶段
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生产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超出了农业生产的范围。这是一次生产方式乃至文明方式的巨大变革。其发生的条件主要有两个。
其一,这是以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条件的。在西方,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以此为基础的技术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在工业文明中才显露其巨大的力量的。在农业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发生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此时科学技术才上升到了空间的规模,并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手工业的时代很快进化到了大机器时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无疑提升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当人类开始使用科学技术以获取自然能源媒介创造工业产品的时候,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了自然生产力的限制。自然生产力只是农业生产力,虽然人类要通过劳动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全部农业生产都是自然自己的生产。人类并没有参与到自然生产的内部活动当中,充其量是自然生产的外部要素而已。农业生产实质是一种自然生产,自然生产就是在生物学的自然法则下运行的。人类并没有干预到内在的自然生产活动。我们把这种农业文明的生产称为“自然生产”。自然生产是按照自然的生命有机体的法则从事的生产,它完全遵循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的“自然法则”。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和西方道德学中所提出的自然法则具有不同的内涵。这里的自然法则是指自然界生物按照生命的规律而存在的秩序。而西方道德学中的自然法则指的是内心的理性之光。“这自然法则可以被描述成能由自然之光来识别的神圣意志的律令,它指明了何者与理性本质一致,而何者与其不相一致,并因这一理由而命令或禁止。”[2]
然而,在工业生产当中,打破了农业文明的自然生产而变成了一种“人工生产”了。在上述科学技术引入的背景下,实现了从“自然生产”到“人工生产”的转变。可以说,工业生产是人工生产,它与农业生产不同。人工生产当然要借助于自然提供的资源和能源,因为没有资源和能源就没有工业生产的可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然而,“工业化使得世界人口无约束地增长。人口的物质需求也在同一时间加大。因此,即使工业生产可以极大扩大,满足人类需求的机会从人均来说也在恶化。”[3]此时,自然能源变成了生产的外部要素,而人工活动则变成了生产的内在要素。所以,人工生产和自然生产是性质恰好相反的两种生产活动。人工生产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智慧,去创造自然所不能直接给予的生活资料。其中主要通过人类理性的设计、人类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以自然提供的能源为支撑而从事的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创造。自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必须通过人类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这样的生产行为就属于“人工生产”。
当然,在人工生产活动中,我们也强调要利用自然规律,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才能创造。如果人工生产也要服从自然规律的话,那么,这种人工生产是否在根本上仍然属于自然生产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自然生产,是指按照自然生命有机体的生物法则所从事的生产。而人工生产所利用的自然规律,并不是自然生命有机体的法则,它已经超出了生命有机体的界限。比如,万有引力虽然是自然规律,但如果我们运用万有引力作为动力学的原理去创造某种生产机器的行为,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然生命有机体的界限,因为自然界不会自己产生“机器”。也就是说,如果背离自然法则,这一物种就会违背生存。其他的动物显然是没有超出自然法则的能力的。因为能够超出自然法则的行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原因是人类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物,他具有了理性的智慧。理性的智慧意味着它能够超出自然的界限,凭借自己的理性创造出自然所没有的产品,即“人造自然”。比如,自然界是不会自己生长出“复合化肥”的,只有人类通过智慧才能够生产出“复合化肥”。
其二,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是通过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表现出来的。“资本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所建构的生产方式,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商品的交换而促成的资本运行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对这种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与马克思关注的不同,我们所关注的是,在这种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所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我们把这种变革称为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的确立。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在本文的生存辩证法的视角中,我们把资本逻辑统治的人类生存命运概括为“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说来的相对独立性”。
20世纪的西方生态学,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已经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根结底是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现象,把它概括为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机制就是:当人类进入资本逻辑的秩序当中,实际上是被资本逻辑所固有的内在交换价值的规律所支配而生产方式不再与自然的生态法则相协调,因而构成了一种独立于生态法则的相对独立的生产法则。而这一生产法则不是别的,就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这就意味着,追求私人财产利益的最大化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内在规则。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意味着生产的扩大化,这种扩大最根本的就是跨越自然生产的界限,或者说,摆脱自然生产的界限而进入人工生产的无限扩张。然而,人工生产是有条件的,它的科学技术条件是属人的条件,因为只有人类自身才能创造科学技术。但是,人工生产的物质条件,则只能来自于自然界。这样,自然界就变成了人工生产的物质资源和能源的储备库。这显然超出了自然生产的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逻辑支配的生产方式中,通过前文所述及的人工生产,使生产方式摆脱了自然生命有机体法则的限制而进入了相对独立的生产关系当中。
当进入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的时候,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不再是从前自然生产中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直接同一性了,相反,人工生产在资本逻辑的秩序中,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独立出来。当然并不是说人类的生产可以完全摆脱自然的依赖,而是说,这种生产超出了自然生态的生命有机体法则,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产法则。这就导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人工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人工生产越是强大,自然生态环境就越遭到冲击;而生态环境越是遭到冲击,则反过来越威胁人类的生产生活。当这种冲击突破一定的界限的时候,于是就发生了生态危机,进而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我们把这种因为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环境反过来制约人类生存的现象,称作是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否定关系。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着一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处在一种对立的否定性关系之中。这一矛盾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最大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状况,自20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都开始高度关注人类未来的生产方式变革问题,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环境问题,关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克服这一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的否定关系而重新进入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同一的生存方式呢?
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辩证统一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现在,我们开始探讨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我们将诉诸当代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来探讨这一问题。
追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存主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问题,是基于人类已经发生了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和谐这一事实而提出来的,即前文所讨论的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的否定关系。如果要突破这一否定性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重大问题。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在生产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的道路,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秩序仍然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因此,对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同一问题,仍然处在理想的“应然状态”。这样,本文也只能先诉诸于观念上的变革,以及学理上的“应然”的反思,来探索实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道路。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要适应世界资本逻辑的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重建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在逻辑上是否是可能的?这就需要引入能够凌驾于现有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一种力量,来对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加以限制。而这种东西如果暂时还不能找到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手段,就只能从学理上做初步的探讨。人类以外的任何一个物种都不会出现自我否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个物种都不会在自己的生命逻辑中否定自己物种的存在。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是通过客观的“生态圈”的自然法则得到维持的。比如,一个物种如果过度繁殖,因为食物链中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因此该物种的一部分就会被自然淘汰,以保证该物种的延续。食物链是物种得以在自然生态圈中平衡存在下去的客观限制条件。然而,对于人类来说,因为人类具有智慧,这使得其具有了超出自然生态圈限制的可能性。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人类遭遇生存危机,与其他物种相比较,人类反倒是最危险的物种。其他的物种除非遇到自然环境的巨大变迁,比如地震、气候突变,才被迫遇到灭亡的危险。否则,物种的存在是安全的。而人类反倒不如其他物种更安全。因为人类具有的智慧本性,具有超出自然生态环境界限的能力,这就将使自身遇到自我毁灭的危险。因此,说到底,人类的生存危机不会来自于人类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而只能来自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只能够自我毁灭的物种。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如果是自我毁灭的,那么拯救人类的责任也只能由人类自己来承担。这样,在根本上,人类自身必须要对自身的生存行为包括具体的生产方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人类不能等待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否定,而是在此之前,就应该自己限制自己的生产行为,从而使人类的生产方式不至于突破自然的界限而发生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重新同一,就只能诉诸人类对自身生产方式的限制。如果人类自己不限制,则自然必然会以否定性的方式对其加以限制。由此可知,人类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的重新同一,是需要通过人类对生产方式自身的否定的方式实现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否定。其一是人类对自身生产行为的限制,这是第一个层次的自我否定。其二是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否定,这一否定推到极致就将是人类的毁灭。因此,我们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第一个层次的自我否定,从而消解第二个层次的否定。这是我们当代探讨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重新同一的唯一出路。
[1] 洛克.论自然法则[M].苏光恩,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8.
[2] 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3] 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6.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5-05-08
陈柯(1971—) ,男,博士研究生,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穆艳杰(195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变革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B1
A
1002-462X(2015)10-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