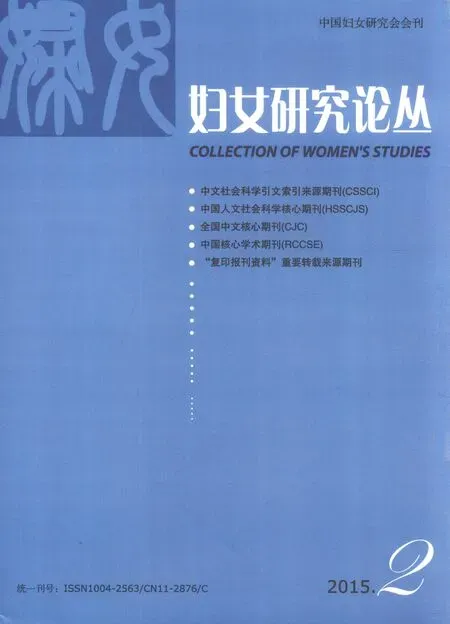始信英雄亦有雌
——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
2015-02-24黄华
黄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始信英雄亦有雌
——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
黄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秋瑾;装束;易装;性别操演
文章从秋瑾的照片入手,结合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秋瑾装束的记载,讨论易装在秋瑾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分析秋瑾女扮男装的行为动机及其投射出的深层文化心理。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有一定的出入,来自异域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印象中单一刻板的秋瑾形象。根据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秋瑾的女扮男装可以被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个人反抗形式。秋瑾从最初自发地反抗家庭中的夫权压制,到自觉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活动,直至为国捐躯,在此过程中,不仅摆脱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更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蜕变。
谈到中国近代女英雄,人们头脑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应该是秋瑾(1875-1907),因为镌刻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有她慷慨激昂的诗词,更有她舍生取义的事迹。一个女子能够像男人一样写诗填词、跨马扬刀,甚至以血警醒世人,不要说在近代中国,即便在世界也堪称罕见。然而人们都相信这位女英雄的事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史料,而是来自照片。这些照片不仅直观地将秋瑾的音容笑貌印刻在民众心中,而且将一位易装的女子推到世人面前,与她留下的诗词、中外学者的相关著述形成呼应。本文选取秋瑾的四张照片,希望从中窥视到这位巾帼英雄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一、秋瑾的照片
秋瑾存世照片中有四张珍贵的独照,照片上人
物的容貌变化并不大,最明显的区别是每张照片上的不同服饰装束,从穿传统中式女装,到男式西装、和服,再到长袍马褂的中式男装。秋瑾似乎有意穿着这些不同的服饰拍摄照片。依照当时的设备、摄影条件推测,这些照片显然是留影者专程到照相馆拍摄的,留影者背后相似的道具布景、稍显僵硬的表情,都表明了这一点。在晚清,对普通民众而言,照相应该不算一件小事,是留影者比较在意的日常生活事件,摄影时所着服饰自然也无法忽视。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秋瑾的留影似乎有着特殊的含义,是为纪念人生的某次经历?还是为赠送友人,抑或为了向世人展示其成长变化的过程?当然,也不排除为流传后世而摄。总之,拍照属于留影人自我展示的产物,通过现代技术将一个客观真实的自我呈现给世人。那么,秋瑾期望通过照片告诉人们什么信息呢?
第一张照片上的秋瑾是一位身着传统中式女装的闺中少妇。头戴软帽,帽前正中镶有饰物;上身穿斜襟低领滚边的半大长衫,宽大的袖口遮盖至手背;下身穿曳地长裙,双脚被裙子盖住。秋瑾端坐椅上,左手扶椅背,右侧手肘轻轻靠着一个圆几,几面上摆放着一瓶花。照片上秋瑾的神情拘谨,额前不见一丝乱发,向后的发髻全部被帽子遮住,从发式上推测,应该是她婚后在外省居住时所照,有名门贵媛的风范。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秋瑾,祖父、父亲皆为举人,母亲单氏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秋瑾,聪慧灵巧,富有才情,逐渐养成开朗、豪爽的性格。秋瑾十三岁时,便“偶成小诗,清丽可诵”[1](P113),擅长女红,“尤擅刺绣,虫鸟花卉,阴阳反背,自出心裁,靡不毕肖。顾性不乐此,旋即弃去,时复把卷伊吾如宿儒”[1](PP113-114)。读书和女红是秋瑾待字闺阁时的最爱。一首《踏青记事》描绘了秋瑾少女时的装扮:“女邻寄到踏青书,来日晴明定不虚。妆物隔宵齐打点,凤头鞋子绣罗襦。曲径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红送落红!”[2](P60)脚踩镶有凤凰图样的绣鞋,身穿锦绸剪裁制成的襦裙,与女友携手走过芳草萋萋的曲径小桥,长裙拂地发出“珊珊”声。诗中充溢着小儿女的欢快与温婉之情。《杂兴》中有“瓶插名花架插书,数竿修竹碧窗虚”[2](P58)等诗句,勾勒出一幅闲适优雅的隐居生活画卷,与照片上的背景形成呼应。这样一位“才女”可惜嫁给纨绔子弟,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出身商贾,见识平庸,与秋瑾琴瑟不合。婚后秋瑾写下“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2](P76)(《谢道韫》)的诗句,借以抒发心中的郁闷。照片中的秋瑾,眉宇间透露出些许幽怨。如果秋瑾一直居住在南方,可能仅仅就是一位闲来写写闺怨诗的才女,但后来到了京城,她的视野和命运随之转变。
第二张照片中的秋瑾穿男式西装出现。头戴鸭舌帽,穿着一件宽大的西服,左手掐腰,右手持一根细细的文明棍,神情怡然。肥大的裤脚下赫然露出一双男式黑皮鞋的宽鞋头,推想起来,秋瑾应该是有意为之。因为按照清末的传统,出身名门的女孩自幼缠足,秋瑾也不例外,但她后来放了足。有意显露的皮鞋鞋头,与上一张照片被裙裾遮盖的双脚形成对比,很可能是向世人彰显她那被解放的双足。
那么,从何时起,秋瑾改穿男装了呢?这要从秋瑾的丈夫王廷钧进京捐官讲起。1902年王廷钧捐官任户部主事,秋瑾随之赴京。京城里变革求新的氛围影响了秋瑾,她结识了女界精英吴芝瑛,与之结为金兰姊妹,通过吴芝瑛,秋瑾又接触到不少新派人物,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原本就有嫌隙的夫妻关系因而变得更加紧张。根据秋瑾挚友徐自华的记述,秋瑾首次穿男装出现在社交场合是1903年中秋。秋瑾身着男装到戏院观剧,轰动京城,招致王廷钧的一顿打骂,秋瑾怒而出走,在泰顺客栈住下。显然,女扮男装公开亮相是夫妻冲突的主要原因。也许秋瑾之前在家中扮过男装,大家不以为然,以为玩耍罢了,但为何那晚秋瑾要穿男装公开亮相呢?这缘自王廷钧的一次失约。那天,王廷钧原说要在家中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王廷钧被人拉着逛妓院、喝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想外出散心,就第一次穿男装,带上小厮去看戏[3](P14)。事情的经过与是非一样明显,可男尊女卑的纲常礼教站在丈夫这一边,任凭妻子有百般委屈。秋瑾写下《满江红·小住京华》一抒愤懑,其中有“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2](P105)的诗句。是年,距秋瑾与王廷钧结婚整八
年,“歌残”“破楚”暗示了诗人对这段婚姻的彻底失望,词中还表达了“身”与“心”分离的激烈冲突,暗示自己渴望冲破女性身份束缚的决心。王廷钧第二天让女佣捎书信给秋瑾,劝其回家,但被秋瑾拒绝。王廷钧只好央请吴芝瑛把秋瑾接到吴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后又搬到南半截胡同同乡陶大钧家中短住。在陶、吴两家的暂住,秋瑾有机会读到当时的进步书报,对秋瑾的思想影响很大,坚定了她摆脱旧式家庭束缚的决心。这张着男装的照片应该摄于那一时期[4],它象征着秋瑾与女性社会身份的决裂。因此,这张照片可以看作秋瑾冲破家庭束缚的标志,其不再以女性的社会身份自居,而力图向世人展示着男装的秋瑾。另外,秋瑾还有一张头戴鸭舌帽、着男装的半身侧面照,应该也摄于这一时期。吴芝瑛在《纪秋女士遗事》一文中提到“其在京师时,摄有舞剑小影”[1](P71),其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一文中也提及“尝摄舞剑小象”[1](P116),可惜今不知所踪。
第三张照片是大家熟知的秋瑾穿和服的半身照,该照是秋瑾1905年12月归国前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时年30岁。照片上的秋瑾梳日式高发髻,穿一件翻毛黑白条纹和服,右手横握一柄出鞘的倭刀,刀刃上的闪闪寒光映衬着秋瑾冷峻的目光,神色端庄。穿和服对于留日的秋瑾不难理解,但为何手持利刃?这要从秋瑾的留学经历谈起,1904年秋瑾写下“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2](P85)(《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的诗句,与旧传统诀别,投向新生活。秋瑾在日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她加入旨在推翻满清政府的“三合会”,组织“演说练习会”,参与创建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性团体“共爱会”。秋瑾曾两次东渡求学,历经坎坷,但事与愿违,1905年10月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公私立学校接纳清国留学生的规定》,即后来通称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起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为此留学生中分为两派,周树人(鲁迅)、徐寿裳等主张继续学业、暂缓回国,而秋瑾、陈天华等主张集体罢课回国。12月8日陈天华跳海自尽,秋瑾主持了陈天华的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等人“死刑”,并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5](P17)随后,秋瑾等指挥留学生分批归国,写下“曰归也归何处?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6](P331)(《如此江山》)饱含悲愤的诗句。回国前,秋瑾特地到照相馆,拍摄了这帧穿和服、手攥倭刀横置胸前的照片。
第四张照片是一张穿传统汉族男装的全身照。照片上的秋瑾,梳男式长辫,穿长袍马褂,脚蹬官式皂靴,左手倒持一把雨伞。身后是画有亭台的布景,右侧圆几上摆放着盆栽,神情凝重,双目威严。与和服照相比,少了几许豪气,多了几分悲怆和肃然。这帧照片摄于1906年农历正月,是秋瑾归国后特意在绍城赴仓桥街蒋子良照相馆(今绍兴市红旗路284号)拍摄的。此时的秋瑾虽然未能忘却陈天华之死及留学种种往事,但她决心从悲痛中走出,脱下和服,改换汉式男装,以此表达自己投身反满革命的志向。但救国之路在何方,照片中秋瑾凝重的神情暗示了她后来不平凡的起义之举。
四张照片展示出秋瑾不同时期的装束和形象,从拘谨的闺中少妇,到女扮男装的西装革履,再到身着异域的和服,最后定格于长袍马褂皂靴的中式男装,风格迥然。我们关注秋瑾的服饰,并不是想证明秋瑾有追求时尚或易装的嗜好,因为下面使用的材料将表明,秋瑾服饰装束的改变不仅代表个人对社会性别气质的挑战,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着装风格作为个体思想意识的表征,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要起到身份认同的作用,例如,在公共场合,如果要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国籍身份、知识文化背景乃至思想政治倾向,经常会根据其着装来加以判断。服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文化的基本观察点之一。外在的服饰成为秋瑾表达社会身份和内心夙愿的工具,也成为探究秋瑾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
二、中国人笔下秋瑾的装束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深受民众推崇和研究者青睐。然而在现有研究中,有关秋瑾照片、服饰的记载却失于零散且不受重视。笔者摘录了一部分有关秋瑾生前装束的记载,分别来自秋瑾的至亲好友、革命同仁以及国内学者三个视角,这些记载多集中在对秋瑾女扮男装的关注上。
现存资料中,与秋瑾交往最密的两位女性好友是吴芝瑛和徐自华。秋瑾的结义金兰吴芝瑛在其就
义后,撰写了多篇文章以纪念秋瑾,文中数次提到秋瑾为留学东瀛“脱簪珥谋学费”[1](P68,P71)。吴芝瑛将秋瑾遗留的《兰谱》并一封书信寄给筹建秋社的徐寄尘,信中提及二人结义时(1904年)秋瑾赠送女装的情形:“烈士于人日写盟书一通以来曰:吾欲与姐结为兄弟。……越日:烈士作男子装过我,并赠七律一首,媵以自御之补鞋一、裙一,曰:此我嫁时物,因改装无用,今以贻姐,为别后相思之资,……烈士自改装后,即摈满清衣服不御。此物尚存,足为烈士脱离满人羁勒之纪念;”[1](PP55-56)吴芝瑛将秋瑾的易装视为脱离满清民族立场的表现,这与当时的民间舆论方向大致相同。当时的报刊、舆论普遍为秋瑾鸣冤,认为该案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疑点,反映了满清政府的专制腐朽,借“秋瑾案”为推翻满清政府在舆论上造势[7],吴芝瑛当然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为秋瑾鸣不平。
与吴芝瑛对待秋瑾女扮男装所持的宽容态度不同,秋瑾的另一位挚友徐自华(号寄尘)并不支持秋瑾的易装。除去上文提到的徐自华记录秋瑾首次穿男装亮相的经历,她还在《小说林》第7期(1907年)上发表了《秋瑾轶事》,其中有一段女扮男装的情节:
女士自诩乔装,人难辨别。余哂曰:“丰神态度,毕竟不同,乌有不能辨别?岂人尽无目者!”女士曰:“子勿如是言,我明日倩数人易钗而弁,一试法眼。”翌晨星期,约数女生男装,偕至易园摄影,倩余品题。余曰:“小淑文秀,惜少潇洒;希英魁梧,而无跌宕;薪苹则软弱,浑似女儿腔矣;数子之中,自然是君英爽倜傥,最占优胜,亦乔装日久之效果也。”女士大笑曰:“好月旦,面首三十,只中一人耶!我与若姊妹共摄一影若何?”余曰:“君如此装束,不便奉陪。”女士笑骂曰:“迂腐顽固,真不可教者。”[1](P65)
这是一段秋瑾在南浔女校任教期间的生活琐事记录,生动地再现了秋瑾对易装的浓厚兴趣。她不仅在好友面前夸耀自己乔装打扮的本领,更付诸行动。女教员(秋瑾)约上一群女学生穿上男装,到照相馆摄影,再由女校长(徐自华)对众人的扮相一一评鉴。尽管徐自华认为其中秋瑾的扮相最佳,但仍拒绝与改装的秋瑾合影,这表明时任南浔女校校长的徐自华并不赞同秋瑾的易装。秋瑾在后来的《柬徐寄尘二章》中写下“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2](P93)的诗句,表达自己期望好友觉悟,加入革命斗争的心愿。1907年夏,秋瑾为筹军饷来找徐自华,自华捐出所有首饰。为感激好友倾囊相助,临别时秋瑾脱下自己佩戴的盘龙双翠钏相赠,并以“埋骨西泠”的旧约相嘱[1](P93)。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推想起来,秋瑾扮男装已久,这副翠钏应该是秋瑾身边最后一件值钱的女性饰物。此时,距秋瑾就义不足一月,皖浙起义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秋瑾已经暗暗下定以身殉国的决心。后来,徐自华将翠钏返还秋瑾之女王灿芝,并作《返钏记》。
同样对秋瑾易装印象深刻的还有近代女词人吕碧城。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任编辑时,在《鸿雪因缘》中记道:“犹忆其名剌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某役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瑾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于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1](P273)秋瑾在赴日留学前曾拜访吕碧城,劝其随自己东渡。两人通宵深谈,尽管彼此契合相得,但仍各择其路。
秋瑾异母弟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一文,从家人的视角,回忆了秋瑾不为外人知的一些生活细节,特别是服饰上的变化。他记录了自日本归国后秋瑾服饰的改变:“姊返自东瀛,着紫色白条棉织品之和服,宽襟博袖,盘髻于顶,乍见几疑是客。姊笑抚余首曰:‘弟长大成人矣,犹识阿姊否?’予闻语恍然,惟牵衣憨笑。姊既归,乃弃和服不御,制月白色竹布衫一袭,梳辫着革履,盖俨然须眉焉。此种装束,直至就义之日,迄未更易。改装伊始,曾往越中蒋子良照相馆摄一小影,英气流露,神情毕肖。”[1](P119)秋宗章记录了秋瑾第四张照片(见上文)的来历,关于秋瑾穿和服装扮的描绘又与第三张照片形成对应。
在秋瑾的男性朋友陈去病、陶成章、冯自由等人笔下,较少谈及秋瑾的服饰装束,他们着重记录了秋瑾参加会党、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过。陈去病称秋瑾“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1](P77)。冯自由在《鉴湖女侠秋瑾》一文中提及秋瑾在青山实践女学校时,“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1](P95)。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节录)》中记录了1906年冬秋瑾到杭州发展光复会时的装束:
“秋瑾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绉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青年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1](P230)朱赞卿在《大通师范学堂》中也有类似记载:“她的身材不高大,高鼻梁,时常梳一条辫子,着一件鱼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缠过,但着一双黑色皮鞋。所以有人说她是男装到底,但是头是不剃的。”[1](P237)朱赞卿认为秋瑾给自己起别号“竞雄”和着男装的行为,是因为愤激于男女不平权。
中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范文澜1956年应《中国妇女》约稿,撰写《女革命家秋瑾》一文,描述了童年印象中的秋瑾:“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1](P3)更重要的是,因其胞兄范文济曾是大通学堂的学生,范文澜以亲历者的口吻从侧面记录了秋瑾被害的过程,还原了秋瑾被捕当日的场景:“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被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地奔过我家门口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1](P4)作者的身份及其家人的亲身经历成为人们信服的重要理由,该文也因而奠定了秋瑾女革命家的历史形象。后来的国内学界多沿袭这一说法,努力建构秋瑾女革命家的形象。
国内有关秋瑾服饰及装束的记载总体来说并不详细,也许大家对于秋瑾的易装嗜好有意采取忽视态度,或避而不谈,或在不得不谈时,赋予其反抗民族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革命意义。这与晚清的时局和舆论需要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同裳”的礼教传统相关,更与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解放、妇女地位的提升有密切关系。人们致力于在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内建构秋瑾女革命家的形象,对其易装行为采取了有意忽略的态度。
三、日本人笔下秋瑾的装束
因秋瑾曾留学日本,不少日本人对秋瑾十分推崇。秋瑾就义后,一些有关秋瑾的日文文章、文学作品问世,主要来自与秋瑾相识的日本友人及后世日本作家,前者如服部繁子、松本龟次郎等,后者有日本作家武田泰淳、永田圭介等。与中国人笔下强调的秋瑾着男装、具有女侠气质不同,日本人笔下的秋瑾形象更趋日常化,装束也更丰富多样。
服部繁子是时任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她对秋瑾赴日留学、到实践女学校就读起到重要的引荐作用。她著有《回忆妇女革命家王秋瑾女士》一书,这里引用的资料来自她在日本《中国语杂志》上发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文中多次提及秋瑾的穿着装束。秋瑾给服部繁子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辨不清男女的怪异装束:“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青年。”[1](P171)繁子无法辨别眼前人是男是女,等吴芝瑛介绍是“王太太”时,才明白原来是女扮男装。在随后的交往中,繁子逐渐喜欢上这个有个性的中国女子。第二次相见,秋瑾穿的还是那身宽大的蓝色西装,但繁子显然对其有了好感。在繁子眼中,秋瑾有着林黛玉一样苗条的身材,越看越像一个南方的娉婷美人。繁子问秋瑾为何男扮女装,她认为其女扮男装的行为“有点孩子气”,并以“男女平权”的思想劝说秋瑾。但秋瑾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向繁子抱怨自己的家庭“太和睦了”、希望丈夫“强暴一些”等,让繁子认为秋瑾是家中的“女神”[1](P174),对其夫王廷钧反倒升起同情。第三次见面是在秋瑾北京的居所。繁子来到秋瑾家中,见到女装打扮的秋瑾,黑上衣,灰色裙子,下蹬一双绣花鞋。繁子还见到白脸皮、很少相的王廷钧,印证了自己的猜测。秋瑾跟繁子谈了自己打算去美国留学的想法。第四次见面,秋瑾穿白色水手服来看繁子,显得英姿飒爽。她改变了想法,请繁子带她去日本留学。繁子起初拒绝了秋瑾的请求,但架不住王廷钧的登门拜访和央求,最后同意带秋瑾去日本。文章第五次提及秋瑾装束是二人同行启程去日本。秋瑾随服部繁子一道赴日留学,在船边与家人告别,王廷钧和两个孩子前来送行。秋瑾没穿男装,穿浅蓝色朴素的衣服,短发用帽子拢住,告别的场面温馨而伤感。到日本后,应秋瑾的要求,服部繁子推荐她入读实践女学校。
起初,服部繁子的这篇文章在中国并不受重视。
一则因为繁子笔下有关秋瑾夫妻关系的记述,完全不同于秋瑾对丈夫王廷钧的描述,也与国内其他资料的记载截然不同。中国读者很难接受秋瑾笔下“禽兽之不若”“天良丧尽”[2](PP36-37)(《致秋誉章书其三,其四》)的王廷钧与服部繁子眼中“腼腆”“俱内的小丈夫形象”[1](P174)之间的巨大反差,想当然地认为来自异域的记述不真实。一则这与日本妇女恭顺谦卑的行为方式有关,日本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较中国更为盛行;二则繁子的叙述立场很让人怀疑。身为日本官宦家眷的繁子,尽管主张男女平权,但完全否定秋瑾的革命思想,认为秋瑾同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患了流行的“革命病”[1](P175),时常担心秋瑾留学期间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繁子对秋瑾的态度是敬佩、尊重、疑惑与责备共存。
但近年来,服部繁子的文章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也许由于“他者”的记述没有落入“革命话语”的窠臼,显得相对更客观、真实。夏晓虹的《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易惠莉的《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马自毅的《秋瑾夫妇关系考辨》[8]等论文将服部繁子的文章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无论怎样,这是一篇记述秋瑾装束风格最详细的文章,生动立体地呈现了1903年冬到1904年春秋瑾在京期间的日常生活,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秋瑾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的穿着又是怎样呢?我们可以从日本人撰写的文章中找到相关记载。松本龟次郎的《中华五十日游记》中有一篇文章《秋瑾女士墓和我的回忆》,其中提到秋瑾初到日本在留学生会馆学习日语的情形。1905年松本龟次郎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任教,曾教过秋瑾日语。在松本的记忆里,秋瑾“白皙的皮肤,柳眉,身体苗条,体态轻盈,黑色花纹的和服上衣,配一件当时流行的紫色裙子,小脚,日本发型,莲步蹒跚。每天来校从不缺课,回答问题清楚,提问也很尖锐”[1](P246)。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特别指出“小脚”“莲步蹒跚”,这是中国女子区别于日本女子的主要特征。尽管秋瑾梳日本发髻、穿和服,但蹒跚的莲步还是在日本教师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无法将心中柔弱的女子形象与革命英烈联系在一起,故留下“飘然紫色裙,轻盈金莲脚。平常凡女子,刚烈显英杰”[1](P246)的诗句。
当代日本建筑学家永田圭介,由一次偶然的绍兴之旅,激起他对秋瑾的无比崇敬,他历时三年撰写完成了《竞雄女侠传》一书,该书于2004年出版。永田圭介选择秋瑾穿和服的照片作为封面。因为搜集了大量有关秋瑾的中日文献,故书中有不少关于秋瑾服饰、摄影等生活细节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基于史料和合理的文学想象,即史料加虚构组合而成。例如,该书开头便详细记述了秋瑾5岁缠足的经历,并根据秋瑾后来28岁放足的经历,指出秋瑾饱受“缠足和放足两重痛苦的煎熬”[9](P8)。作者描述道:“秋瑾很喜欢拍照”[9](P96),“平时总爱把自己喜欢的照片配上镜框保存起来”[9](P250)。“相片(作者按,指穿和服照)洗出后,秋瑾加洗了几张,将相片镶在椭圆形镜框里,分别送给即将回国的朋友。”[9](P209)永田圭介在小说末尾特意指出孙中山为秋瑾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中“巾帼”的含义,巾帼原指中国古代妇女的头饰,借指妇女,自中山先生为秋瑾题词后,巾帼英雄便成为秋瑾的另一称号[9](P332)。由此可见,服饰对于确定秋瑾身份的重要性。
因为深受武田泰淳以秋瑾为主角的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影响,永田圭介在《竞雄女侠传》中时常与之进行比较,借以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个人理解。在武田泰淳的启发下,永田圭介在“尾声”部分把秋瑾之死与耶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并详细进行了阐释和对比,将一心想致秋瑾于死地的贵福比作犹太教大祭司该亚法,将始终怀有愧疚感的李宗岳比作彼拉多,把清兵赶来时一直纠缠秋瑾的蒋继云比作叛徒犹大,将获悉徐锡麟被害后秋瑾的独自痛哭与耶稣在橄榄山独自承受悲痛相比……小说以1987年6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中文版刊登的美国女诗人阿格尼丝的《秋瑾英烈》一诗结束全书。“秋瑾秋瑾/绍兴的巾帼豪英/我们唱一支颂歌/献给您短暂的一生……”[9](P337)永田圭介以此来彰显秋瑾作为古城绍兴历史人物代表的意义。
从服部繁子、松本龟次郎、永田圭介等日本人笔下,我们读到了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秋瑾。说熟悉是因为秋瑾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说陌生是因为透过异域“他者”的眼光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有着喜
怒哀乐、英勇刚强但带着更多无奈的秋瑾。
四、易装背后的文化意义
中国人笔下的女革命家秋瑾与日本人笔下的秋瑾形象构成了一定的反差,我们无意探究哪种记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是聚焦于已经超越了国界的秋瑾研究,在跨文化的视域下探讨易装在秋瑾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先对比中日两国学者有关秋瑾装束描述的差异,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来自异域的记载纠正了国内许多资料带给读者的秋瑾着男装的刻板印象。这些记载表明自1903年秋瑾首次着男装公开亮相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地穿男装,而是如常人一般时常变化。如服部繁子提及的秋瑾着中式女装、水手装,松本龟次郎印象中秋瑾着日本女装等。
第二,秋瑾装束的改变,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另一方面也未免要受到当时潮流(即今所谓“时尚”)的影响。如当秋瑾期盼赴美留学时,曾身着白色水手服来见繁子,借以表达对远航留学生活的渴望,水手服在当时应该是很时尚的穿着,也符合时人对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美国的想象。又如,在日本期间,秋瑾一直梳日式发髻、穿和服。按照秋瑾的个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身居东瀛、入乡随俗的表现,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穿和服的留影,如章太炎、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周作人回忆留日生活时曾谈及当时穿和服的风尚:“章太炎先生初到日本时的照相,登在《民报》上的,也是穿着和服,即此一小事可以见那时一般的空气矣。”[10](P616)从松本龟次郎的记载来看,秋瑾在日本时穿和服女裙,即一般女子的平常装束,在服饰上未有任何偏激的表现。可见这一时期的秋瑾心绪平和,尽管服部繁子对秋瑾的革命思想心怀忐忑,但秋瑾还是遵照两人的约定,选择进入实践女学校读书。如果不是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秋瑾也许会在日本完成学业,但她愤激冲动的个性使她无法接受屈辱性的条件,只能拂袖归国,投身于更激烈的革命起义。
第三,服部繁子文章中谈及秋瑾在家着女装,在外着男装,这表明秋瑾在塑造、改变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秋瑾有意在公共空间内改穿男装,在私人空间内保留女装的做法,是身份政治的表达,即一种政治立场的反映。借用当代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社会性别操演理论来解释,性别并非如服部繁子劝导秋瑾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扮演和操练来建构的。巴特勒提出:“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事件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11](P184)秋瑾希望通过以男装示人的做法改变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期望拥有男子的社会性别身份。秋瑾自己的话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繁子问秋瑾为何穿男装又是西服时,秋瑾答道:“在中国是男子强,女子弱,女子受压迫。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先要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留辫子是异族人的习俗,不是中国人的装束,所以我穿西装。”[1](P173)
秋瑾希望通过穿男式西服,实现对自己女性身份的逾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僭越不同于西方后现代性别理论中所强调的僭越,因为它是双重僭越。第一重是性别身份上的僭越,秋瑾女扮男装,希望能够扮演像男子一样的强者,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利,如社交自由、受教育权等;第二重是民族国别身份上的逾越,体现在服饰类型的选择上,秋瑾特意避开满清男子的装束,借以表达自己反满的政治立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女扮男装的奇女子,花木兰、娄逞、黄崇嘏等,但着装的标准无非是比照身边的男子,从未超越国别的界限。作为户部官员家眷的秋瑾,居然身穿男式西装,公开亮相,在当时的京城可谓大胆之举!不过按照秋瑾的逻辑推理,男强女弱,西(方)强中(国)弱,模仿自然要模仿最强者,故秋瑾要穿男西装。这反映了她向往男女平权、期盼改变中国贫弱现状的心理。这是秋瑾区别于花木兰的重要之处。因为无论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是才高八斗的女状元,女扮男装都只为躲过眼前的家庭困境,易装动机并不违背中国封建纲常,都是为了尽孝尽忠,但秋瑾的易装却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革新之举,目的是为了拯救被压迫的中国妇女和被列强欺侮蹂躏的国家。例如,秋瑾在同吴芝瑛谈及留日学习
科目时,提到她不学师范,不学医学,因为她认为这些科学,不能增长她救国家、救二万万同胞的本领[3](P17)。又如,秋瑾在日本与陈撷芬组织共爱会,其宗旨是爱国、自立、学艺、合群,其目的为“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学问”[3](P18)。可见,秋瑾的易装,并非为一己、家族之私利,而有着更高的民族国家的追求。
来自异域的资料对国内的秋瑾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纠正和丰富的作用。在同时代的日本人笔下,我们读到的是对这位奇女子的敬佩和感动,正如松本龟次郎所说:“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壮烈的革命先驱者。”[1](P246)京都产业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也称秋瑾的事迹“在东亚成了精神交流的媒介”[9](P2)。
如果将秋瑾的易装行为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嵌入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内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易装——这种身体行为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把身体描述为文化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11](P169),即身体被理解为一个媒介,更确切地说是一页白纸,文化持续不断地在身体上施加作为,个体身体上便留下了历史文化的烙印。秋瑾的女扮男装最初源于对家庭内夫权的反抗,后来其通过留学、参加会党、组织留学生运动、担任学堂教习、筹备起义等活动,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也许起初的易装只是一种转换身份的策略,后来女扮男装久了,秋瑾便跳出中国传统妇女的社会性别规范,开始自觉承担起男性角色的社会责任,尤其担起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在此过程中,秋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早年的“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2](P57)(《题芝龛记》),到庚子国变的“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2](P62)(《杞人忧》)。直至绝笔信中的“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2](P26)(《致徐小淑绝命词》),秋瑾始终心怀民族、国家大义,但不免偶尔因易装产生自我的幻觉,这在她的《自题小照(男装)》表现得最为明显:“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身悔寄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2](P80)这是秋瑾唯一一首照片题诗,也是唯一有关易装的诗。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的操演性“推到极致来说,它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果”[11](P9)。秋瑾的《自题小照》正是易装行为幻觉效果的反映,因为此时刚从日本回国的秋瑾,仍沉浸在悲愤、挫败,有时不免精神恍惚的情绪中。但根据照片和秋瑾后来的行动,我们又可以推断出:秋瑾脱下和服,换上汉式男装并摄影留念的行为,带有明显地宣称改变身份立场的意味。
尽管外在服饰的改变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正是从日常生活的冲突之中产生更大的总体性社会冲突”[12](P45)。晚清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新与旧、西洋与本土的多种政治文化观念激烈交锋。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穿西装、穿制服、易装等行为都带有强烈的立场宣示和身份认同的意味。而摄影技术的介入,充分发挥了服饰的象征功能和审美功能。于是,不难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身着特定服饰在相机前做出各种造型动作的意义。这些照片通常登载在报刊上,借以宣扬他们的理念,而公众也惯于通过着装风格来辨识其立场和身份。秋瑾穿和服手攥短刀的照片即刊登在《中国女报》第二号(1907年3月4日发行)上,卷首同时刊载了秋瑾的《勉女权歌》。显然,秋瑾试图用自己的诗词和照片来激励中国妇女。
秋瑾的女扮男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身份立场的表达,这一方面基于中国文化中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传统,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亟须变革的社会需求。借助外在服饰的变化,秋瑾跳出了传统女性规范的束缚,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最终为国捐躯。正是这种“始信英雄亦有雌”[2](P57)(《题芝龛记》)的震惊和感动,使秋瑾成为近现代亚洲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代表。
[1]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2][清]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夏晓虹.北京时期的秋瑾——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J].社会科学论坛,2007,(23).[5]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年表(细编)[C].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6]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7]夏晓红.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J].近代史研究, 2004,(2);马自毅.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J].安徽史学,2005,(2).
[8]夏晓虹.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4);易惠莉.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J].社会科学,2012,(2);马自毅.秋瑾夫妇关系考辨[J].历史教学问题,2005,(1).
[9][日]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10]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A].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八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2][匈]阿格尼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含章
HUANG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Qiu Jin;outfits;cross-dress;gender performativ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Qiu Jin's choice of outfit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r revolutionary pursuit,analyzes the motive of her choice of outfits and the deep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bedded in it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her portraits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cords of Qiu Jin.Notably,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about Qiu Jin's outfit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cords,the foreign records renewed Qiu Jin's stereotyped image in Chinese people's impress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th Bulter, gender is the result of performativity.Qiu Jin's cross-dressing outfits can be viewed as a personal rebellion in her daily life.From her spontaneous rebellion against her husband to her conscious devotion of her life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 government,Qiu Jin managed not only to escape the constraint of the traditional female role but also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social identity.
I206.5
:A
:1004-2563(2015)02-007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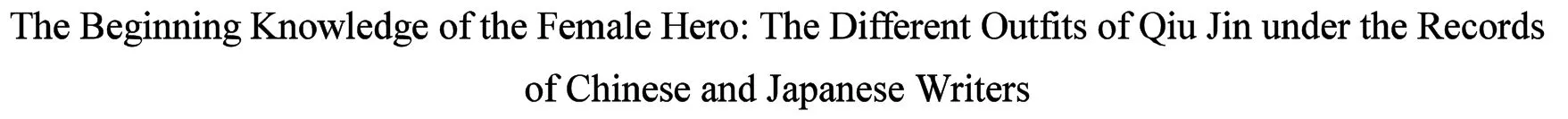
黄华(1974-),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女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