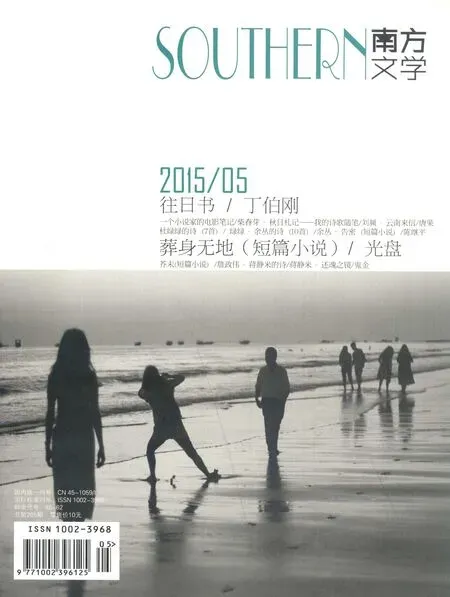一个小说家的电影笔记
2015-02-24text柴春芽
text_柴春芽
一个小说家的电影笔记
text_柴春芽

电影的真实有时会超越现实的真实。
我所热爱的,是具有内省气质的欧洲电影。
电视的出现宣告了电影将死的危机。
1989,没有记忆的一年。
父亲归家,而大雪苍茫。
暴雨将至。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善讲故事的人。
新的蜂王诞生了!
对于我的视觉映像的记忆而言,1989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是不定期的流动电影,在此之后,则是电视。按理说,社戏和皮影表演也应成为我视觉映像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社戏和皮影在我的视觉记忆里却难以构成某种暴烈性的事件。这或许是因为社戏和皮影太过古老和陈旧,从而难以刺激人对新鲜事物的惊讶。我还记得平生看过的第一场电影吗?在那个夏天闷热的午后,乡政府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我们的村庄。等不及天黑的人们,决定借用粮管所储存小麦、玉米和薯干的仓库来播放电影。粮仓的门窗被紧紧关闭,几乎全村的人拥挤在空气污浊的粮仓里。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和粮食的霉味混合在一起,使得好几个孕妇哇哇呕吐。于是,粮仓那污浊的空气里很快便混入胃酸的气味。柴油发电机的轰响和黑白战争片里的炮火交织在一起,轰炸着人们的耳膜。等我随蜂拥的人群踉跄步出粮仓,午后的积雨云正酝酿着风暴。从黑白的梦境一脚踏入坚硬的现实,这使我许久分辨不清虚假与真实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不知是因为愚钝还是因为聪明,当电影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时,人们仅仅是感到好奇,因而并未表现出过于冲动的举止。而在1898年,法国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一边惊呼:“着火啦!着火啦!这是巫术!”一边纵火烧毁了卢米埃尔的放映棚。当然,我故乡的人们第一次面对电影时所展现的那种较为平静的表情,或许是因为电影的真实性。长时期被社戏和皮影那种虚假的表演所蒙骗,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解放军战士骑着“真实”的马在“真实”的原野上奔驰。人们第一次发现,社戏中骑士手中用来隐喻马的那根马鞭显得非常荒谬。当然,社戏和皮影里人物的唱词也在电影的相形之下显得非常荒谬,因为现实中的人绝不会用唱腔交谈。
电影是属于大都市和机器文明的产物,但它很快便超越孕育它的“母体”,从大都市的影院进入农村的戏场,从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发展到世界各大洲。
电影令人着迷,因其“真实”的故事。从此以后,我便跟随已届成年的小姑姑和她那些处于青春骚动期的伙伴们经常性地翻山越岭,在或是漆黑一片或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追随着电影放映队。少年丹巴是否也曾像我一样,跟随八月去看露天电影呢?直到有一天,少年丹巴是否和我一样,对电影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呢?因为我在观看译制片时,发现金发碧眼的老外居然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再接着,我发现电影里的人物从来没有大小便。终于,我明白了,电影是个谎言。多年之后,我在维姆·维德斯(Wim Wenders)导演的电影《大路之王》(Kings of the Road,德文名为Im Lauf der Zeit,直译过来就是“时间之旅”)中看到主人公在拉屎。那是一个远景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车司机布鲁诺蹲在白花花的沙地上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屎。这一幕令我印象极其深刻。
电影的真实有时会超越现实的真实。对于性交和排泄这种动物性的举动,人们一直采用的是遮掩。当然,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对邪恶与丑陋的遮掩更是屡见不鲜。但是,电影要揭开这层遮羞布,让我们看到赤裸裸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如果没有日本导演大岛渚电影《感官世界》里对性爱的真实映现,如果没有文德斯电影《大路之王》里那一段排泄的场面,我可能会对电影失去热情。
电影的超现实美学(或许可以叫作梦境美学)是牢牢建立在细节的真实性之上的。
大多数好莱坞电影的肤浅就在于这种细节真实性的丧失。它们只讲确定类型的故事,它们已经放弃了在类型化的电影之外体验事物(生活)的真实,其结果是,美国电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不断地在弥补这种不可信的漏洞。美国电影不可能带我感受个人化的体验,因为好莱坞采取的是由制片人、导演、编剧等组成的制片厂系统的集体创作。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他的世界,他的经验,全都是由他童年看电影的经验所组成;对他自己而言,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滥觞于195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是对好莱坞电影的一次反动。作者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化而非类型化的真实经验。当然,如果虚假与肤浅已经成为某一类人的性格症候,那么,作者电影便会与其格格不入,而好莱坞电影则会与其相得益彰。污油怎能与清水相溶?维姆·文德斯从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转变为一个电影学院的大学生时,不也在拒绝《假面》(Persona)以及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所有的作品吗?那时候,他迷恋着美国电影的“物质特性”,而反感着欧洲电影的“深度”。只是,当文德斯终于混入“电影天堂”好莱坞之后,他才发现美国电影的“物质特性”的表层显得多么平滑,多么坚硬,以至于在其后面隐藏的只是思想的贫瘠。十年前他所鄙视的“具有内省气质的欧洲电影”——譬如后来令他潸然泪下的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The Cries and Whispers)——如今则像是失而复得的家。
1
电视的出现宣告了电影将死的危机。1947—1953年,从美国出现然后迅速遍及西方的电视机,使得电影观众大为减少。虽然声音、彩色、宽银幕和3D技术被纳入电影,但是,一度辉煌的电影——人类的第七艺术——仍旧日薄西山。
逐渐地,电影看起来愈来愈像是为电视而拍,不管是光线、取景与节奏方面。看起来电视美学大有取代电影美学之势。
许多新电影不再指陈电影之外的任何真实世界——它们代表的只是包含在其他电影里的经验——好像“生命”本身不再为故事充实材料。
电影是拍得愈来愈少了,其趋势是愈来愈多的超级大制作以牺牲小成本制作机会的姿态而出现。
很多电影很快就发行录影带上市。这个市场在急速扩张之中,很多人宁愿在家里看电影。
所以,我的问题是,电影是否会变成死掉的语言,一种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艺术?
2
如果要我现在回答,我会说,电影并不会死亡,或者应该这么说,构成电影的物理技术肯定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有所更替,但是,电影美学不会死亡,就如同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小说的发展,但却并没有消泯诗歌。录音技术(留声机→录音带→CD→随身听)的日新月异也没有扼杀音乐。摄影技术从胶片到数码,但也没有让摄影消亡。电影一旦成为第七艺术,它就拥有了永恒性的生命,因为人类的梦想不会枯竭。
但是,对于少年时代的我而言,1989之后,电影死了。
流动的露天电影消失了。人们全都躲在家里,因为有了电视机。
我们村庄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粮管所主任那贴满标语和革命导师画像的办公室里。那是粮管所的上级主管部门作为一项福利,发给这个偏远农村的粮管所员工的。农民要在每年的冬天到粮管所缴公粮(农业税),如果适逢大旱之年,农民实在无粮可缴,那就改缴钞票。很多农民不得不去城市乞讨,或者去河西走廊的产粮区乞讨面粉,然后再将面粉卖掉,以便回来补缴农业税。贫穷阻挡不了人们的好奇。我们这群少年尾随着大人,到处寻找电视转播信号。几个壮汉轮流背着电视机和柴油发电机,另外几名壮汉轮流扛着电视天线。人们先是在宽阔的打麦场上找信号。电视荧屏上由于电磁反应而出现一片雪花状的斑点,偶尔会有声音传来,间或闪烁出几个人影。最后,有人建议,如果要避免四周群山对电视转播信号的阻挡,必须得去各个山头。于是,人们浩浩荡荡,日复一日地在各个山头上辗转。就在人们快要失去信心的那一天,离我们村庄不远的乡政府安装了一个电视信号转播台。村里比较富裕的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每个夜晚,拥有电视的人家便早早关门。我们这些贫穷家庭的少年不得不在各个拥有电视的人家门前盘旋,一遍遍祈求,最后愤愤地冲着紧闭的大门撒尿。
可以通过电视记忆真相的时代,我却因电视的迟来而忽略了1989年。1989,没有记忆的一年,集体遗忘的一年,成为我视觉印象中的一个盲点。可是,此后很多年,我却不断地与1989年遭遇,在中国西部一个小县城的角落里,在巴黎的一个旧货市场上,在温哥华的电影节上,在台北布拉格酒吧……这些不断的遭遇抵抗着遗忘。
身陷在1989巨大的空白里,我无所期待地活着。早恋,学跳霹雳舞,逃学,打架,课业荒芜……突然有一天,我母亲用她那女巫般的口吻命令我去村委会取信。“谁的信?”我问道。“你阿爸的信,”母亲回答。“不可能,我阿爸早就死了。”“不,他还活着,昨天晚上我梦见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坐着火车正要回家。这是来信的梦兆。”
“你居然相信梦!”“人可以骗我,但梦不会骗人。”
果然,父亲在消失三年之后写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约定,今年春节,他将回家与我们团聚。他在信中的口气那样轻松,你简直会以为他只是个结束了短期旅行的人,仿佛他只是去贩运了一趟木材或是羊毛。我在他乘坐绿皮火车抵达县城火车站的前几天就骑着那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离开村庄,住宿在首阳镇的二姑家等待。父亲的出现令我有些错愕。三年时间的打磨,使他变得格外陌生。我甚至有些无法接受他还活着这一事实。有很多人传言说他已客死异乡。我的祖母每晚哭泣,终于在第三年哭干了眼泪并哭瞎了眼睛。我的祖父每晚以一场咒骂儿子的咆哮表达丧子的悲痛。
父亲带来了很多礼物,包括一台12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他是那样归家心切,以至于那些堆满了一架板车的礼物被他抛在二姑家。他和我分别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寒冬风雪的黄昏从首阳镇出发。夜幕很快降临。白雪照亮了崎岖不平的土路。我们骑行15公路,终于抵达家门。我在推门而进的那一刻大喊一声:“我阿爸回来了!”我祖父从炕上一跃而起,径直从厅房里奔出。秋风落叶般的雪花纷扬而下。我看见我祖父和我父亲紧紧握着手,眼里噙满了泪水。那时候,已经怀抱着文学梦想的我,想要在多年之后,把这一幕写进小说。而现在,我多么想把这一幕拍成电影。但是,我电影中的少年丹巴并没有父亲。他无法像我一样目击风雪之夜里一对曾经怨仇的父子握手相泣,但他目击的一幕,将比我所目击的一幕更为惨烈。
夏天的第一场暴雨凶猛地到来。猝不及防的蜜蜂在匆匆回巢的途中被疾来的雨点打落在地。养蜂人忙着护理蜂巢,用麦秸编织的雨披一一覆上。哗哗的雨水顺着雨披直直地流下。丹巴赤身裸体,在大雨中奔跑,呐喊。自从去年夏天以来,这是丹巴第一次洗浴。大学生K正要推开草料房的小木门走进院子,随着一声霹雳,哐啷一声,大门被撞开了。一群男子抬着一张门板。门板上躺着八月。她左手腕上缠着的纱布已经被雨水浸湿。人们把门板放在地上。丹巴停止了奔跑,呆呆地望着。养蜂人走过去,俯身凝视着八月。八月闭着眼睛。雨点击打着她那满是青紫伤痕的苍白的脸。
“亲家们,这是……”没等养蜂人说完,一记重拳便落在他的脸上。他沉沉地仰躺在泥泞里。八月的丈夫扑过去,一阵气势汹汹的拳打脚踢。他有着难以发泄干净的怒火。他有着难以言说的屈辱。
丹巴依旧呆望着。抬着八月进门的那些人和丹巴一样呆望着。草料房里的大学生K隔着门板上的缝隙,同样呆望着。这一切来得太过激烈,使得丹巴和大学生K不知如何反应。
养蜂人在泥泞里翻滚。
八月的丈夫一边殴打着养蜂人,一边用他愤恨的声音喊道:“是谁把你女儿睡过了?说呀,你说呀,是不是你把你女儿睡过了?你这老不死的混账……”
大学生K背靠着小木门。他扭曲着脸,无声地哭泣着。他想冲出去。他想对那些人说:“是我,是我,这一切都是我干的……”他想紧紧地抱住八月。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受苦。“上帝啊,我是个罪人……”
院子里的咒骂声戛然而止,只有滚动在天边的雷声和哗哗的雨声。
大学生K赶紧转过身去。通过小木门上的缝隙,他看见赤身裸体的丹巴手握着一把刀子。在丹巴的脚边,八月的丈夫捂着肚子,想要站起身来。可是,在他快要站起来的时候,重又沉沉地摔倒在地。窒息在他喉结下的叫喊,随着他的挣扎,此刻便响亮地迸发出来。他像一头被阉割的公牛那样叫喊着。
谁能想到,不是别人,而是丹巴,这十四岁的痴傻少年,竟会杀人。
此刻,一层虚构的帘幕隔在我与丹巴之间。我在长久敲击电脑键盘的写作之后,透过窗外那陈年鸽粪般灰白的雾霭,依稀看到丹巴的眼睛。他是那样镇定,以至于刚才冲锋而来接着拼刀而上时的那股凶狠显得多么陌生。
大雨滂沱。持续不断的雷声在天空中翻滚,闪电如同皮鞭,抽打着伤心的土地。
关于1989年的夏天,我所能讲述,唯有这场大雨,而我不能讲述的则是:苏联自1917年以来,实行了最自由的选举,其后不久,这个超级大国一夜崩溃;近半个世纪作为东西方冷战标志的柏林墙倒塌了,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相聚在一起,举行狂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魁辞职,作为政治犯被囚禁多年的48岁的剧作家哈维尔当选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匈牙利举行了42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
如今想来,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善讲故事的人,绝对不是。我童年的伙伴中,不乏真正天才的小说家。即使过去了30多年,那些天才小说家当年讲述的故事,如今依旧历历在目。他们的故事未经书本的污染,因而具有真正的原创性,就像各个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印刷术和影像技术的发达,使得世界各地的儿童轻易就被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海洋所淹没。孩子们只会复述千篇一律的故事。只有少数天才儿童,才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里旁逸斜出,开创一点小小的发明。当我回顾贫瘠年代里的童年,竟然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孩子全然出自本能地冲动,虚构出无比瑰丽的故事,并以极其生动的语言将其讲述。我愿意将那些铭刻在我脑海中不曾被多年阅读的知识冲刷变淡的奇异故事列举如下。
大约在小学二年级,一个阴郁夏天的午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围着想平娃(多年之后我祖父想要杀死他),骑坐在一棵古老榕树裸露而出的虬结的根系上。想平娃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从绕过太阳的遥远星球赶来拯救人类的英雄,他那又粗又长的阴茎如同腰带缠裹在身上,足足缠了三圈。他一手挥舞着惊雷,一手挥舞着闪电,与魔鬼搏斗。当惊雷碎裂闪电破灭的时候,伟大的英雄解下他腰间缠了三圈的阴茎……
大约三年级,一个慵懒的夏日上午。我们用废弃电池里的锌棒在操场上写字。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们索性躺在墙根下面,听靳六娃讲故事:离我们村庄不远,靠近河流的那座山上,有一种怪兽。我看见它们长着翅膀,但却有着公羊那么大的猫身子。有人把他们叫作飞虎……
同样是在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太阳开始西沉。我们五六个孩子耷拉着腿,如同树上的猴子一样坐在村庄中央篮球场那个支撑篮板的铁架上。柴旦娃给我们讲述一个生殖器大如马勺的女人的故事。我已忘记了故事的细节,但是,一个生殖器大如马勺的女人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
善讲故事的那些天才,全都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自我教育迅速中断。随着电视的灾难性漫延,
3
每一次回故乡,我都发现,最善于讲故事的,还是那些未经电视污染的老人。他们的想象力和叙述能力,能够极为妥帖地搭配。但是,他们正一个个逝去。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故事,还有一套精彩的方言。如今,我故乡的同龄人已经变得失语,因为他们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无所适从。他们的心灵迟钝,他们的言谈寡淡。
由此,我才迫切地感觉到,只有原创性的作者电影,才能拯救人们的想象力,也只有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拯救我们日渐沦落的母语。而这却是多么不易。一方面,电影审查制度扼杀着作者电影,另一方面,被商业电影染污的观众,已经乐于浸淫在华丽的影像中享受感官的刺激而迷途不返。华丽影像的背后,满是心灵的干枯。
我是如此多愁善感,本应成为一个诗人,但却命运舛错,使我成了一个作家和导演。我不得不创造故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依旧需要借助故事来慰藉心灵。史诗和悲剧的时代业已遥远。如今是小说和电影的时代,我躬逢其盛。我不知是命运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命运。总之,我创造了少年丹巴,一个目击了1989年的十四岁男孩。某个朝霞映红大地的早晨,他被一辆警车送回。他被释放了,因为他柔弱的双手无力将一把刀子捅得更深。那个曾经殴打了八月和养蜂人的男子,只是受伤而已。
“快过来看看,丹巴。”养蜂人对着门口踟蹰的丹巴说。丹巴走进院子,径直走到养蜂人身旁。养蜂人正在观察一个蜂巢。蜂箱的盖子打开着。
“看到了吗,一个新的蜂王刚刚诞生了。”养蜂人说。“她的翅膀还很柔嫩,”丹巴说。“很快会变得茁壮。”
“蜂王!新的蜂王!快来看蜂王!”
丹巴欢呼着,跑向草料房。草料房的门虚掩着,他一把推开。草料房里除了墙上悬挂的农具和一垛麦草,再就是麦草上放着的一本《圣经》。“人呢?”丹巴一边询问养蜂人,一边跑向厢房。厢房里的炕上,摆着整齐的被褥。
“人呢?”养蜂人埋头观察着蜂王,没有回答丹巴的询问。丹巴急切地跑出院子。他在田野里奔跑。距离神像不远,那群寻找电视卫星转播信号的人突然欢呼起来。他们围绕着电视机跳起了古怪的舞蹈,同时还唱着古怪的歌谣。电视机里,一名拎着黑色公文包的男子,站在一列坦克前面,阻挡着坦克的前进。画面一闪。柏林墙缓缓倒塌,激动万分的人们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丹巴怔忡地站在风吹如浪的苜蓿地里,举目四顾。他不知道八月和大学生K去了哪里。一只鹰在虚空里盘旋。在鹰的眼里,伫立大地的男孩无比孤单,并且越来越远。而在我这个导演的眼里,苜蓿地里的少年丹巴如同电影《雾中风景》里走向地平线的乌娜和亚历山大,正在大地上迷失。
我应该在这部等待完成的电影的结尾,缀上一首未完成的诗——
1989年,秋天尚未到来,有人却听见轰隆而来的收割机。
在世界某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但在这亚细亚悲伤的大地上,一个时代就是所有的时代。
我们从未错失风暴,我们从未收获闪电。
——节选自待出版之电影小说《蜂王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