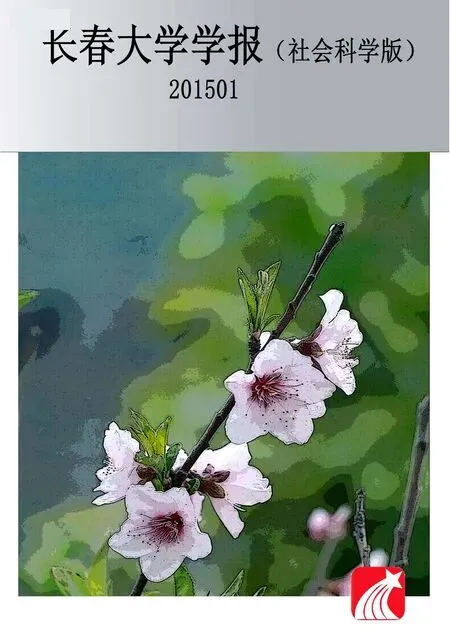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
2015-02-22蔡燕雁
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
蔡燕雁
(莆田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福建莆田351100)
摘要: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所带来的文学史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是,评论界在强调这场转向的同时,又无意间制造了新写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这无疑就割裂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事实上,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对话空间,要大于他们之间的对立空间。但也正是这种对话空间的存在,预示了新写实小说的短暂青春。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现实主义;零度叙事;深度;历史
收稿日期:2014-07-22
作者简介:蔡燕雁(1970-),女,福建莆田人,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
至今,新写实小说热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文学界关于新写实小说一些细节上的功过得失似乎远未达成定论。当然,我们这里不否认批评界对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一致认可。新写实小说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被批评界赋予了深刻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深刻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它引领了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尽管文学界对小说创作的这种转向表达了各种或悲或喜的看法,但是,文学界不得不承认,新写实热预示着一场文学格局和历史的巨大变动。文学在80年代末期逐渐失去了以往的轰动效应后,究竟应该如何调整自身的位置,这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界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写实小说的兴盛,无疑给之前沉寂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曙光,文学似乎又有了重新获得介入现实的机会。所以,当时擅长于指点江山的批评界甚至比创作界还要热衷于兜售这批作家作品。也可能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喜欢介入社会的这种冲动,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写作与批评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
1“零度叙事”里的生活
事实上,新写实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自觉的文学运动,新写实作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当下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是时代大背景下的被迫选择,不如说是作家写作姿态的主动调整。因为当时的新写实作家已经深感到中国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巨大脱节。正如刘震云所说:“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1]13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新写实小说中所不具备的一切,诸如激情、英雄、理想、爱情、忠诚、整体、阶级、革命、历史等崇高的美学成分,我们在新写实小说内部看到的只有诸如“恋爱、结婚、怀孕、打胎、生孩子、带孩子,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堵、气候的冷暖、菜价的上涨,小夫妻间的打情骂俏、争争吵吵,婆媳之间的鸡毛蒜皮、勾心斗角”[2]等等发生在每个人几丈范围内的日常生活琐事。新写实小说所描写到的我们当下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切,似乎与以往现实主义所展现的那些崇高的浪漫美学成分没有任何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可是,新写实所勾勒的这一切,似乎又是我们当下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试想一下,在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一斤豆腐酸了这样的生活琐事怎么可能会引起夫妻之间的激烈争吵?将这样的生活琐事纳入文学书写是否太有失文学本身的身份?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的日常生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或者批判距离,如果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这层距离取消了,那么这是否也就意味着文学自身意义的消失呢?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不无失望地将新写实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新写实根本就不是现实主义精神传统的延续,因为它“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坚守着的精神立场……日常生活开始作为一种经验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并消解了任何一种附着于其上的诗意象征”[3]。
然而,作为新写实作家代表的刘震云、池莉和方方等人,则对评论界的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通过对当下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感受到,以往依附于哲学、道德或政治的写作传统已经不合时宜,很多讲究“真善美”的明晰而抽象的概念或者知识,根本难以拿来解释当下浑浊而感性的日常生活。他们都一致认为,日常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启发要远远大于那些形而上的知识与诗意。正如刘震云所说:“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该体现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写作前总是有了独特的体验,然后再写作。”[1]17我们通过阅读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新写实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基本上都采用了“零度视角”。他们不愿意对小说里面人物的日常生活作过多的干涉,所以小说里面的叙述者基本上处于一种隐退的状态,叙述者只是如实地呈现小说里面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叙述者的这种零度姿态并不意味着作家本人就失去了判断的立场,完全认同了平庸琐碎的世俗生活。南帆曾在《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一文中指出:“不应当将人物的状态等同于作家的观点——人物对于平庸的认同,并不是由于作家的大力鼓励。平庸的现实上升至文学视野与文学下降至平庸的境地,这是迥然相异的两件事。”[4]43的确,作家并不等同于叙述者,但是作家又不能完全与叙述者脱离关系。“作家可以删去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社会理想表述或者人物鉴定,但叙述仍会在背景描写、人物识别或者时间性概括方面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4]41新写实作家所采用的零度叙述视角,与其说是为了彻底划清作家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变换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零度的叙事视角只是作家为了达成与读者对话的一个桥梁。新写实作家针对日常生活所采用的零度视角,与其说是对真实日常生活的一种如实呈现,不如说是作家经过对当下的生活一番自我反思之后所采用的另一种介入现实的方式。换句话说,新写实主义依然还是处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之内,它还是希望借助文学这一门艺术来达到改造现实的目的。正如池莉在访谈中所说:“我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通过小说唤醒周围的人,让他们觉得生活是不是应该更好一些,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文明一些。而要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深入地表现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使整个人类的素质得到提高。”[1]14
可见,新写实作家并没有像那些否定新写实创作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了平庸琐碎但也略带温馨与幸福的日常生活,从而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调起情来。新写实作家只是想通过描写平庸的方式来反抗平庸,他们所采用的零度视角目的只是为了与读者达成对话,能够让他们在强烈的审美体验中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平庸与难以忍受,从而引起读者对生活的自我反思。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新写实小说采用了零度叙事视角,就认为它背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批判精神。这与其说是新写实作家在八九十年代时代巨变面前的被迫选择,不如说是他们在写作姿态上主动作出的一种调整。
2日常生活:消解的深度
事实上,任何一个评论家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阅读经验感受到,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常生活之外意义的追求。但是,有些评论家为什么总是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不满呢?笔者纵观了一下早先文学界对新写实作家作品的评论,得出了这样的认识:虽然新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但是许多对现实主义传统抱有好感的评论家在总结新写实小说不足的时候都认为,这些小说缺少了以往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具备的历史深度感与崇高感。的确,这些评论家可以援引大量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曹雪芹、鲁迅等等,也都是这些评论家津津乐道的名字,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也都进入了公认现实主义经典的行列。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在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面前似乎显得相当地逊色,因为它们不具备这些经典作品所具有的宏大历史气魄。换句话说,新写实作品只是执著于对日常生活琐碎的描写,即使发现日常生活内部的一些闪光点,那也仅仅是一种局部性的东西,它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意识。而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时候,总要对日常生活进行筛选、提炼和升华,进而获得对日常生活一种超越性的历史认识。正如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价巴尔扎克时所说:“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们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5]683-684因此,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即“除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5]683显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新写实小说只突出表现了细节的真实,而并没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新写实小说中所描写的环境与人物都缺少了一种辩证法的超越精神,它们都普遍地缺乏历史深度感,人物基本上都是在环境内部迂回。这也难怪有人指出,新写实小说“在处理人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上,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6]。
如果说新写实小说之所以招致诸多批评人士的不满,是因为新写实小说里面的人物缺少了一种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人物超越现实环境或者日常生活的“主观战斗精神”。那么,“十七年”时期或者说“文革”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不是更符合这些评论家的口味吗?可以说,恩格斯的观点在这一段文学史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可是,这一段文学史自“文革”结束以来就受到了国内文学界上下一致的批判,评论界和创作界一致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只是充当了政治的传声筒。也许,否定新写实的评论家可以继续补充说,他们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并非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阶级英雄人物精神,而是像前面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战斗精神”,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人物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只不过是被政治所规训之后虚假的激情。可是,当我们纵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时,有哪一个人物不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者选择呢?相对于其他现实主义经典作家来说,巴尔扎克可能是最强调“环境决定论”的一名作家了。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得知,巴尔扎克在其小说中每次引出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人物周围的环境不厌其烦地介绍一番,而且这些周围的环境与即将出场的人物形象是如此地符合。也就是说,巴尔扎克所描写到的人物周围的生活场景,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生活场景,而且还是一种“符号场景”。这些“符号场景”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表征了即将出场的人物的形象。如奥尔巴赫所言,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任何生活空间都有一种道德的感官氛围,它弥散在自然界、房间里,笼罩在家具、器皿、衣着上,也表现在人们的身体、品格、交往、思想、工作和命运之中,而一般的历史环境又以涵盖了各个生活空间的总体氛围的形式出现”[7]528。巴尔扎克是如此地强调环境与人物的一致,以至于他将这种一致性抬升到了神秘化的高度。之所以被巴尔扎克赋予了神秘化的色彩,是因为巴尔扎克认为,可以站在日常生活的制高点上来清晰地把握当时整个时代的历史现状。然而,巴尔扎克是否把当时的历史想象得过于简单了,环境与人物之间难道就始终保持一致的关系吗?
相比于巴尔扎克那些强调历史宏大语境与个人关系的作品,福楼拜的作品诸如《包法利夫人》则主要描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夫人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平庸而又充满幻想的一生。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时代大背景对这个小镇的日常生活造成的波动或者影响。虽然包法利夫人每天总想着有点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可以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琐碎的日常生活告诉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在福楼拜看来,日常现实的本质并不是有着强烈动作的行为和激情,并不是狂人和恶势力,而是持续的状态”[7]550。包法利夫人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耗尽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在她的个人生活中完全看不到时代大背景对她的影响,也不能通过她的日常生活概括出某种宏观的历史现实。她的喜怒哀乐往往是由于几丈范围内的日常生活所引起的,而且有时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就是在包法利夫人这种封闭而又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读者的我们反而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忍受的“震惊”效应。这种“震惊”并不是因为我们怜惜包法利夫人的死,因为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悲剧式的人物,她也带有愚蠢、幼稚和乏味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本人的多面性才使读者与人物拉开了距离。读者对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既有“哀其不幸”的一面,又有“怒其不争”的一面。这便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带给读者的反思。但是这种反思的方向不是指向日常生活之外的,而恰恰是指向日常生活的内部。福楼拜清醒地意识到,日常生活内部的压抑与乏味,并不是源自某种日常生活之外的事实,诸如民族、国家、阶级等因素,而就是出自我们每个人看似平庸实则复杂的日常生活本身。对福楼拜来说,像巴尔扎克式的历史宏大叙事模式,已经在流动的现代性生活面前走向消解。试图通过小说来建构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实际上只是小说家的一种幻想。
在如波德莱尔所说的“一半是破碎,一半是永恒”的现代性生活中,我们再也不能通过类似巴尔扎克式历史宏大叙事模式来反映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当然,我们也不能像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那样,放弃对现实意义的追逐。我们在新写实小说中,同样能够看到个体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同样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点滴温馨与幸福。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意义,似乎与恩格斯从巴尔扎克作品中所得出的历史意识没法媲美,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一个事实:如果历史上提倡的那些整体性的概念或者观点难以转化成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些概念或者观点就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一样,就只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口号。正如管宁所说:“理想、激情和英雄主义这些因素,虽然构成了人的重要一面——精神世界,但并未形成对整个人的世界的囊括。人的世俗的、形而下的一面作为精神层面的承载体,非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具有基础的意义,这两个方面的集合共同构成了人的现实存在”[8]。新写实小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抛弃了理想与追求,而是因为他们深感于中国以往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下个人现实的巨大脱节。前文刘震云把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主要指向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作品,而笔者认为,这个现实主义传统还应追溯更远,应该追溯至梁启超。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危亡之际,小说负载上“兴民”之重任,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倡:“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小说在中国古代本来是一种最低下的文体,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谈,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小说这门文体却被一批知识分子硬性地与民族国家使命捆绑在一起。于是,近代中国小说就从被迫到自然慢慢地接受了一份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嘱托。直到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大规模出现,小说才渐渐从以往的宏大叙事传统中抽身出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然而,相对先锋小说来说,新写实小说无疑是一场比较接中国地气的创作“流派”。它并没因为反叛传统而遁入类似先锋小说形式主义的误区,它无疑有着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一些评论家总是认为新写实小说有些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从而置国家民族和他人的悲苦于不顾。他们认为,新写实作家的这种倾向与市场经济的引进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赵联成所说:“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10]65因为“市场经济拒绝形而上的理念形态,而是以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与世俗性引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它所建构的价值平台是以功利性来衡量价值取舍的标准,等价交换原则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准则”[10]61。事实上,像赵联成这样将新写实小说创作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评论家,还不乏其人。90年代,王晓明等人之所以发起“人道主义精神大讨论”,就是源于对市场经济价值形态的不满。可是,这些评论家在毅然决然地批判新写实小说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时候,有没有后退一步对新写实小说作出重新的评价?近代以来,中国的小说有没有像新写实小说一样不约而同地形成一种创作潮流,开始大面积地关注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施予“严肃客观的态度”,开始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予以认真的反思与尊重?再者,新写实小说在读者大众阶层的普受欢迎,难道不是在另一个层面说明个人意识的觉醒吗?相对于之前那段没有个人的历史,个人意识的觉醒不恰恰意味着历史的进步吗?有时候,笔者在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之所以进步缓慢,到底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份始终割舍不掉的现实主义传统?
3现实主义的窠臼
从回到当时历史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并不是表现在它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上,而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正面注视上。正面注视,意味着作家个人意识和读者个人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不能将这种个人意识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人意识里面首先就包含了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事实上,以往像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同样把视角对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这里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理想或者历史的一个中转站,它们并不具有自足性的位置。换句话说,这里所描写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日常生活,如黑格尔或者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经过正反合的过程之后会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不管我们用民族国家命名,还是用阶级命名,其实都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如果我们融入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清醒地发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地复杂粘稠,我们又怎么可能从中概括出某种抽象的理念呢?当然,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了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放弃了对日常生活之外抽象价值的想象,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价值的追求。事实上,举凡那些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价值的凸显又未尝不是源自日常生活。张承志的《黑骏马》真正感动读者的地方,兴许并不是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那份纯真的爱情与理想追求,而是他与奶奶、索米亚一起生活的日子。虽然那段生活充满了辛酸和劳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不幸福。这便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笔者在本文中之所以强调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转向的文学史意义,并不是想刻意营造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的对立;也无意于由新写实小说得出某种抽象的历史结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产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更无意于毫无保留地赞赏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的重大解放意义。事实上,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对话空间要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对立空间。不过,笔者认为,要对新写实小说作出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单单从它与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对比是难以得出全面的答案的。因为新写实小说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历史原因导致的。新写实小说对文学史的贡献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恰恰是因为造就新写实小说环境的多样性所导致的。所以,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转向代表了文学史一场意味深长的转向,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敞开来评价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新写实小说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相对于寻根文学,相对于先锋文学,相对于新生代小说,相对于90年代的通俗文学,分别贡献了什么,这才是我们客观评价一种文学现象的标准。
不言而喻,新写实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相隔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打开这些文本,依然能从中获得不少的共鸣。这无疑证明它们的价值所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新写实小说似乎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脱节。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日常生活背后还保有作家对某种真假事实的判断,那么,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似乎再也难以区分出真假。在这种前提下,新写实小说的迅速式微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事实。新写实小说虽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呈现采用了零度视角,放弃了对故事情节的整体架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把握住其背后的因果逻辑。也就是说,新写实小说中所描写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与纠葛,其实都是有章可循的。可是,我们现实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很多的情绪或心理的波动,很多时候是无因可循的。我们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某一瞬间会毫无缘由地悲伤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新写实小说是无意于探索人的这种心理空间的,而这也恰恰是它的败笔所在。新写实小说并没有认真探索日常生活的内在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来说,新写实小说为了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对日常生活作了简化处理。作家除了考虑读者的感受之外,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姿态呢?这可能就是有责任的作家在面对当下日常生活所要作出的反思。
参考文献:
[1]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3).
[2]杨剑龙.论新写实小说的审美风格[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59.
[3]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2.
[4]南帆.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J].文艺争鸣,1992(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张学军.新写实小说再评价[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58.
[7]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M].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8]管宁.人性视角:新写实小说的价值重估[J].浙江学刊,2001(5):107.
[9]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
[10]赵联成.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J].文史哲,2005(4).
责任编辑:柳克
DiversionofDailyLifeNarrationofNewRealisticNovels
CAIYanyan
(BasicEducationSchool,PutianUniversity,Putian351100,China)
Abstract:Thesenseofliteraryhistorythatthediversionofdailylifenarrationofnewrealisticnovelshasbroughtissignificant.However,whenthecriticsemphasizeonthischange,theyalsoinadvertentlymaketheoppositionbetweenthenewrealismandthetraditionalrealism,whichundoubtedlysplitthedevelopmentcontextofliteraryhistory.Infact,thespacefordialoguebetweenthenewrealismandthetraditionalrealismisgreaterthantheoppositionspace.Itispreciselybecauseoftheexistenceofthespacefordialoguethatindicatesthetransientyouthofthenewrealism.
Keywords:newrealisticnovel;dailylife;realism;zeronarration;depth;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