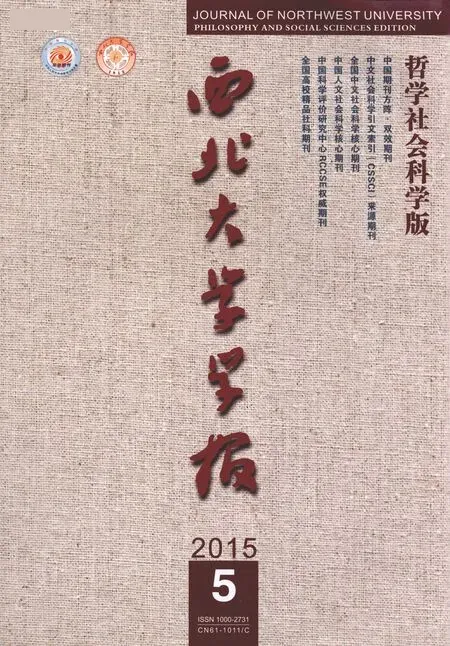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2015-02-21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秦汉帝陵是当时社会在地下的再现,其发展变迁与当时秦汉社会密切相关。从秦始皇陵到西汉十一帝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规模巨大,厚葬严重。它们既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又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价值观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灭亡。
关键词:秦汉;帝陵制度;社会
古代人信仰灵魂不灭,统治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行“事死如事生”,于是将地上社会搬到了地下。因此帝陵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集中反映。秦汉时期的帝陵制度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在中国陵墓制度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使人们得以通过陵墓窥探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中国陵墓史上的里程碑
秦汉时期是中国制度史上的创立时期,在陵墓制度史上也是如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秦始皇陵和汉代帝陵犹如“金字塔”一样至今仍然屹立于三秦大地之上,是研究秦汉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秦汉帝陵的情况,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吕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1](P535-536)曾经主持过秦始皇帝陵园规划建设的丞相吕不韦,自然而然地在陵园建设中体现了“若都邑”的理念。正如蔡邕在《独断》中指出:“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P14)
秦始皇陵的规划与建造,是对秦国几百年王公陵的继承与发展。随着秦国力的不断增强,从秦惠文王开始,陵墓已经从“中”字形的两个墓道变成“亞”字形的四个墓道了。到秦始皇时开辟了帝陵制度之先河,成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大、埋藏丰富的帝王陵园。其庞大的规模、雄伟的建筑、丰富的埋藏品著称于世,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已经在陵园中发现了六百多个陪葬坑和陪葬墓,内涵极为丰富。正因为如此,1987年秦始皇陵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单位之一。从陪葬坑的性质来看,既有象征生前南征北战军事性质的兵马俑军阵,也有反映生前浩浩荡荡出巡的铜车马;既有各类实战用的兵器,也有石质铠甲和头盔,其生前享有或者希望得到的在陵园中都能找到。段清波认为:“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发现的众多陪葬坑为文献中所记‘百官’在地下的再现,通过这种陪葬坑的形式将秦帝国的中央政权组织机构、皇宫管理机构以陪葬坑的形式埋藏于地下,真实再现‘事死如事生’的理念,从而确保秦始皇帝在死后亦能有一套完备的官僚机构侍奉其在灵魂世界里得到安稳。”[3](P173)
秦始皇陵众多的陪葬坑与陪葬墓的分布不如汉代帝陵排列整齐有序。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与秦都城咸阳的发散式布局有关系,而汉长安城的布局相对要整齐有序。段清波则认为:秦代的外藏系统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前制度时代”的特征,那就是其外藏系统空间设置和埋藏内容的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形制多样等,也正是在这种“前制度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下,规范化制度并未成为秦代外藏系统设置的阻碍和束缚[4]。
秦始皇帝陵对汉代帝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汉承秦制”在帝王陵制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汉时期的十一个帝陵的规划与建设大多是继承发展了秦的制度,以都城长安作为规划的范本。刘庆柱、李毓芳认为:“西汉帝陵陵园系模仿都城长安而筑。”[5]赵化成认为:“西汉帝陵陵园是大体模仿宫城即未央宫而设计的。”[6](P507)焦南峰认为:“对考古资料和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论出以下几点认识: (1)阳陵的帝陵、后陵、‘罗经石’遗址、外城分别是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城垣在陵区的地下再现。(2)阳陵不同的陪葬坑代表和象征‘宫观及百官位次’,代表不同的政府机构及设施。(3)阳陵诸侯王的墓园代表其管辖的王国,西汉王朝是汉阳陵的建设模本,汉阳陵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建设而成的。”[7]
西汉帝陵陪葬墓区的设置在继承秦始皇陵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其陪葬墓区的设置在规划整个陵园时已经进行前期规划,比较有规律。陪葬墓大多都分布在帝陵之东,长陵的陪葬墓区规模最大。曹龙认为:西汉帝陵除康陵外,其余诸陵均有陪葬墓。分布在帝陵以东的陪葬墓,位于东司马道南北两侧,其中尤以南侧的陪葬墓数量较多[8]。陪葬墓距离帝陵的远近显示出陪葬者当时地位的高低及与皇帝的关系,比如,萧何与曹参是汉初丞相,墓就位于长陵陪葬区内最显要的位置,即长陵东司马门道北边,距离长陵最近。刘庆柱认为,长陵陪葬墓区西起长陵,东至泾河南岸的原上,东西绵延约15里,20世纪80年代统计有63座带封土[9](P175-176)。杨家湾汉墓是长陵的陪葬墓,出土了3000余件兵马俑,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大型军阵,气势恢宏壮观。学界一般认为该墓墓主是西汉名臣周勃或周亚夫[10]。汉景帝阳陵陪葬墓的发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信息,已发掘的陪葬墓园大多位于东司马道的两侧,规模比较大,应为皇帝重臣、近臣。汉武帝茂陵113座(组)陪葬墓中现有14座保留封土,可确认身份者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金石单墓、霍光墓、上官桀墓等[11]。茂陵陪葬墓同阳陵一样,也是分布于东司马道两侧,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极为宠爱的大将,为汉王朝开拓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两人的墓葬距离汉武帝陵最近。
从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可以看出,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曹龙认为,高祖长陵创立陪葬制度,经惠帝安陵到景帝阳陵时基本确立,此为陪葬制度的形成期;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为陪葬制度的发展期;自元帝渭陵罢设陵庙及陵邑以来,至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为陪葬制度的萎缩或衰退期[12]。汉代帝陵陪葬制度对后世帝陵陪葬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帝陵普遍设立了陵邑,这在中国帝陵制度史上开了先例,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陵所设之丽邑。汉承秦制,自汉初至汉元帝下诏罢置陵邑止,其间各陵也都设有陵邑。但是设置陵邑的作用与目的是发生了变化的。一是供奉陵园,二是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以便起到强本抑末、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三是繁荣关中经济。陵邑的人口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达官显宦、学者文人、俳优世家、市井子弟、“五方杂厝”。西汉的陵邑与汉长安城的关系极为密切,相当于汉长安城的卫星城,分布在汉长安城的周围,减轻了汉长安城的人口压力,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会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史上也属奇葩。
二、事死如事生———秦汉帝陵是秦汉社会的缩影
秦汉帝陵既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也是地上世界在地下的形象反映,还是“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的具体表现。
(一)秦汉帝陵是专制制度的高度反映
春秋以前,墓葬的外在形式是“不树不封”的。春秋战国以后,富豪大族为祭祀先祖和便于墓葬的识别,于是将“墓”变成了“坟”,平地上堆起了坟丘,后来又由“陵”发展成了“山”。于是坟丘的大小就成为显示权威富贵的重要标志,设计高度达“五十余丈”的秦始皇陵更是将陵墓封土的高度达到了极致。
从前文所述,秦汉时期的帝陵营建都与当时的都城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其位置都在都城的附近,这是当时出于管理与祭祀便利的需要。同时其陵园内的各种建制也是仿照都城建设的。秦的帝王陵随着都城的迁徙而迁徙,由雍城、栎阳到咸阳周边。西汉帝陵位于长安城的北部和东南部,而且其陵园的建筑布局也受到都城建制的影响。大多数陵墓在陵区的南部,帝陵在西,后陵在东,这种布局和长安城内皇帝所居的未央宫在西南部、皇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在东南部非常近似。陵墓居陵园中央,陵园四面均有一门,正门在东,其形式和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在宫城中央、四面各辟一宫门、东门为正门的布局也是非常相似的。
秦始皇陵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家陵园,其高大的封土堆犹如一座小山,地下宫殿豪华无比。这些正是秦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的产物。统治者不惜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陵墓建筑,以表现其威权。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13](P265)笔者认为,这里的“百官”不当作“百馆”理解,而是特指维持秦中央政权运作的官僚体系,是秦王朝官僚制度在地下的真实反映,是秦人墓葬“事死如事生”实践的必然结果,尤其是秦始皇本人来世思想观念的反映。段清波认为:“为亡灵模拟一套现实存在的王朝体制是秦始皇帝前无古人的创举,因为他相信灵魂需要一套与现实相一致的机构和人员的服务才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顾。秦始皇帝对他创设的集权官僚体制情有独钟,忠实于帝国皇帝的各级宫僚和他们所统属的机构,是维系皇帝死后能继续享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保证,离开上传下达的权利运作机构,而希望维护其既得利益则是不可想象的。”[3](P176)
汉景帝阳陵是汉代帝陵的代表,也是目前汉代帝陵中考古勘探最多的一个帝陵,和秦始皇陵一样,坐西面东,帝、后设有两重陵园,同茔而异穴。帝陵居于整个陵区的中部偏西,皇后陵与南区外藏坑、北区外藏坑、陵庙、陵寝等布局在帝陵的四周,嫔妃的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以北,阳陵邑设置在陵区的最东端。从而形成了以帝陵为中心、布局规整的陵园布局,标志着唯我独尊的皇权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在帝陵制度中的形成。
阳陵陵园之内部分陪葬坑发掘成果显示,帝陵陵园之内陪葬坑的性质为皇宫管理结构,这些机构的作用是为皇帝提供服务,包括管理皇族事务的宗正以及少府中为皇帝提供直接服务职能的衙署。这些服务机构在帝陵陵园之内封土周围呈放射状分布,有81座大型陪葬坑,东侧21座,南侧19座,西侧20座,北侧21座,从坑内出土物可以看出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四侧陪葬坑均为东西或南北的条状坑形,绝大多数距现封土约10米左右,从地层上看当年这些陪葬坑都被压在封土之下。各侧陪葬坑靠近封土的顶端与地宫的边圹形成平行线,各坑的间距最窄的2米左右,最宽的为7米;绝大多数坑体的宽度在3. 5米左右,最长的超过100米,最短的只有4米。帝陵东侧的陪葬坑分布在东墓道的南北两侧,第13号坑长92米,期间以夯土隔梁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而且以木板为架上下两层搁置,东部主要放置羊、狗、猪等动物陶俑群,各类家畜整齐地分区分类摆放在坑内;西部放置两辆原大的木车马及大量的彩绘漆箱大陶仓。第11号陪葬坑内出土了骑兵俑及战车等物; 12号坑出土龟钮银印“宗正之印”和鼻钮铜印“大泽律印”各一枚; 13号坑出土“太官丞印”封泥; 14号坑出土“太官令印”; 15号坑出土“仓印”“甘泉仓印”“别藏官印”以及“导官令印”封泥6枚; 16号坑出土“大官之印”“府印”“内官丞印”“左府之印”“右府”5枚铜印; 17号坑不仅出土了宦官俑,还出土了鼻钮铜印“长乐宫车”“宦者丞印”; 18号坑出土鼻钮“永巷丞印”“永巷厨印”“府印”“西府”铜印4枚; 19号坑出土鼻钮铜印“徒府”; 21号坑出土鼻钮铜印“山府”“东织寝官”“东织令印”封泥[14]。
从阳陵帝陵周围陪葬坑出土的印章、封泥可以看出,这些陪葬坑是管理汉王朝的政府机构的再现,是皇帝生前管理的机构在地下世界的重现。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管理机构是三公九卿,与皇室事务有关的管理机构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宗正、太仆、少府等,这些在阳陵的部分陪葬坑已得到确认。
(二)秦汉帝陵是经济发展的物化
要建造诸如秦始皇陵、汉代帝陵等大规模的国家重点工程,没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大型工程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秦始皇陵的大规模的营建是在统一后进行的,直至秦亡尚未完成。汉代的帝陵也是如此,在汉初经济实力不济的情况下,陵墓的规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文景时期的节俭政策在其陵墓制度上也体现出来了。“文景之治”以后,汉代的经济实力增强,帝王陵的营建规模得以扩大,特别是汉武帝的茂陵,其封土是西汉帝陵中最高大的,陵园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地宫中的陪葬品也是最好的。《汉旧仪》记载:“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15](P106)到西汉后期的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由于经济萧条,其帝陵的规模和设施便每况愈下。
(三)秦汉帝陵是当时科技实力的再现
由于帝陵工程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所以在修建过程中,当时的高科技都得到了应用。秦始皇陵修建过程中就有不少的科技成果被采用,其兵马俑坑中的青铜兵器的制作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各种金属的配比达到了《周礼·考工记》的要求。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兵器尽管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仍然寒光闪闪。出土的剑、矛、戈等青铜兵器上为了防锈,采用了氧化铬技术。经激光显微光谱、质子X光萤光、电子探针和光谱分析检测,原来它们表面是一层呈青灰色的氧化膜。据研究,这些兵器表面确是经过人工处理的,其可能是在铬酸钾溶盐或溶液中浸煮的结果。在古代铬酸盐或重铬酸盐是用铬矿石和火硝焙烧后浸出制备[16]。标准化制作在秦始皇陵文物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类似的例子在秦汉帝陵中非常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13](P265)其地宫中的设置无不反映出当时的高科技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汉代帝陵中的高科技更是如此,尽管汉代帝陵的地宫还没有打开,其中的高科技应用目前还无法看到,但是从目前在帝陵陪葬坑中的出土文物也可以略见一斑,鎏金铜马、鎏金鎏银竹节熏炉、精美的陶俑、高档玉器等正是高科技在汉代帝陵中的展示。
(四)秦汉帝陵祭祀制度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乃秦汉帝王陵的大事。帝王死了以后还要像生前一样,每天、每月、每年都要按活人一样伺奉祭祀,因而在陵墓旁就必须有相应的建筑。蔡邕的《独断》中明确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17](P14)后来的应劭也有相同的说法,但是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考古工作者发现秦始皇的祖坟东陵就在陵侧设置寝殿。只是秦始皇陵的寝殿规模更大,其寝殿在坟丘西北50余米处。基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500平方米,中间为高台基,周围有回廊。在寝殿西北,南北长670米、东西宽250米的范围内发现由南向北成组排列的建筑基址,之间有石子路相通。已发掘的一组包括东西横列的四座建筑基址,踏步与室内地面均用青石砌筑,在其遗址内发现了直径达61厘米的大瓦当。以其规模和形制推测当属“便殿”。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勘探发现了由九条通道分割的东西对称的十进式建筑群,南北长610米、东西宽25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这一建筑遗址的突出特点是保存状况较好、布局结构严谨、建筑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在中国古代帝陵建筑遗存中不多见,是研究秦始皇帝陵园及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陵寝制度极为重要的新材料”[18]。
西汉帝陵的陵园旁边多建立寝园。园内以寝殿为中心,配以便殿等构成一组建筑群。寝殿陈设皇帝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由宫人像生前一样侍候。《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19](P3199)当时还有“日祭于寝”的礼仪制度,说明秦汉时代的“寝”应是先秦墓上建“堂”的发展,已具备了用于祭祀的功能。便殿是存放帝王生前衣物、葬仪用具以及参与陵事活动和管理的官员办公、休息、宴饮的场所。
西汉初年帝陵寝殿大多建在陵园里,高祖和吕后陵的寝殿就在陵墓旁。从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陵园以外,一般在帝陵东南,独立成园。目前尚存建筑遗迹的有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均在陵园外东南方。宣帝杜陵和王皇后的寝园经过钻探和发掘在陵园的南侧。杜陵寝园四周筑墙垣,北墙利用陵园南墙的一段,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有门,内有寝殿和便殿两组建筑。寝殿在西部,为大型宫殿建筑,通宽十三间,进深五间。壁柱下部置基石并箍以八角形鎏金铜锧,墙壁内抹糠泥,外涂白垩,复施粉红色,富丽堂皇。殿堂四周建回廊,回廊外为卵石铺砌的散水,整座建筑显得庄重典雅。便殿在寝殿以东,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间组成,每套房屋间数不一、面积不等、布局结构各异,从而表明其作用是不同的。后陵寝园布局与帝陵相似,但规模较小。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昭、宣三帝陵园中奉陵宫人竟达数百人之多。这样的规模,绝不仅是一座殿堂所能容纳的。寝园南部有大面积建筑基址,大概是守陵宫女或从事陵事活动人员的住地。
汉代帝陵旁还建有陵庙,用以供奉皇帝“神主”。“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20](P3115)庙的规模很大,周围筑有墙垣。内有正殿、殿门和阙等建筑。陵庙的位置并不一致,一般都不在陵园内,也不一定与陵园建在一起。如武帝的龙渊庙、昭帝的徘徊庙均在陵东,元帝庙在陵西北,宣帝庙在陵东北。陵庙与陵墓的距离远近不一,远者几里,近者几百米。庙寝之间修建“衣冠道”。宣帝庙中央现存一座夯土台基,东西长73米,南北宽70米,厚5米。东西两边各有一条道路通往陵墓。当时祭庙活动非常频繁,除月祭外,各主要节气庆典都要举行仪式,将衣冠由寝殿迎入庙内,接受祭祀。文武大臣遇到重要事情,也要参谒陵庙。
三、秦汉帝陵修建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秦王朝是建立在对外战争基础之上的,不断的南征北战使国家经济实力耗费殆尽。统一后的秦王朝,为了保证政权长久,必须采取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策,以增加积累,安定民心。早在《商君书·徕民》中,商鞅就确立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21](P87)。即保证一定量的自然资源田地与一定量的农夫之适度的比例关系。然而秦始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兴土木,修建了众多的、规模庞大的、与经济无关的奢侈性大型工程,特别是修建其陵墓,最多时使用劳动力达70余万人。袁仲一认为:“秦王朝大约有二千万人口,如以五口之家计,全国不过有青壮劳力四百万,仅就土方工程一项计算,则每个劳力平均将负担修陵的徭役四十余天,如果把整个工程计算在内,则每个劳力服役的天数将会增至二三倍或数倍。”[22](P1191)王子今也认为:“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超过七十万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23](P1206)
秦始皇陵建筑工程,使数十万计的劳动力投入进去,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从而出现了“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20](P2800)的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秦时徭役繁重,乃至“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0](P2812)。目前在秦汉时期的帝王陵旁大都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秦始皇陵修陵人墓地中发现的瓦文证明,当时修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汉武帝茂陵修陵人墓地据估计有两万人埋葬在此,规模很大,而且在修陵人墓地中还发现了刑具。广大劳苦大众为了修建秦始皇陵,不得不忍受着长期饥饿和繁重的徭役,挣扎在死亡线上,从而引起了社会动荡,终于引爆了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摧毁了秦王朝的统治,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厚葬盛行的时期,其帝王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其地宫内的陪葬品我们只能从简单的记载中看到一斑,但我们从外藏坑的陪葬品就可以推测出最核心的地宫埋藏情况,因为地宫之内才是其陵墓最重要的部分。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已经够豪华了,但不是秦始皇乘坐的车子,最多也只是属车而已,秦始皇乘坐的六马驾金根车应该在地宫之内。《汉书》记载:“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20](P1954)
汉代帝陵的豪华情况,据《晋书·索靖列传》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24](P1094)《汉书·贡禹传》载:“及(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20](P3070-3071)即使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生前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但实际上因山为陵的工程也是十分浩大的,于是“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蜀国悍为将屯将军、朗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13](P434)。即使实行节俭、与民休息的的汉文帝霸陵尚动用三万余人,其他汉代皇帝的滥用民力便可想而知了。
汉昭帝死后,由田延年负责修陵,当时光运河沙一项工程就征用了长安附近牛车三万辆。汉成帝为了修建陵邑,借口咸阳原地势不利,遂将已营建16年之久的延陵作废,然后在长安东新丰县境内重建新陵———昌陵。但由于昌陵所在地地势较低,因而积土为陵的工程十分浩大。正如《汉书》记载:“昌陵因埤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钜万数,至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20](P3024)刘向也指出:“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太奢。”[20](P1950)其后果是数万名修陵人日夜劳作五年尚未完工,又回到原地继续修建,真是劳民伤财。
秦汉时期的帝王厚葬制度是建立在对老百姓的搜刮之上的,因而导致老百姓怨气十足。于是“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20](P1954)。“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20](P1956)
可以看出,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密切相关,其发展演变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不仅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而且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忍无可忍的劳苦大众只有揭竿而起,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衰亡。
参考文献:
[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2]蔡邕.独断(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段清波.秦始皇陵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2003,(11).
[5]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1985,(5).
[6]赵化成.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M]∥远望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7]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J].考古,2007,(11).
[8]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2,(11).
[9]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0]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10).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12]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2,(5).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焦南峰.阳陵从葬坑初探[J].文物,2006,(7).
[15]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王学理.秦俑坑青铜兵器的科技成就管窥[J].考古与文物,1980,(3).
[17]蔡邕.独断(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园2010年度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1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M]∥秦俑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3]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M]∥秦俑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责任编辑刘炜评]
【历史研究】
Qin and Han Dynasties Mausoleum System and Society
XU Wei-mi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Qin and Han mausoleum system i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under the ground.There is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Mausoleum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to the Eleventh Western Han Dynasty Mausoleum,we can see that imperial tomb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The feature is huge and luxurious.It is the result of the supreme imperial power and also the need of the value of dynast who like to do grandiose things to impress people.Because Qin and Han rulers use the limited growth of economic forces to the unlimited building of mausoleum,it took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which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and class.At last,it accelerates the declin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y; Mausoleum System; Society
作者简介:徐卫民,男,陕西华县人,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从事秦汉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ZS006)
收稿日期:2015-03-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2
中图分类号:K232